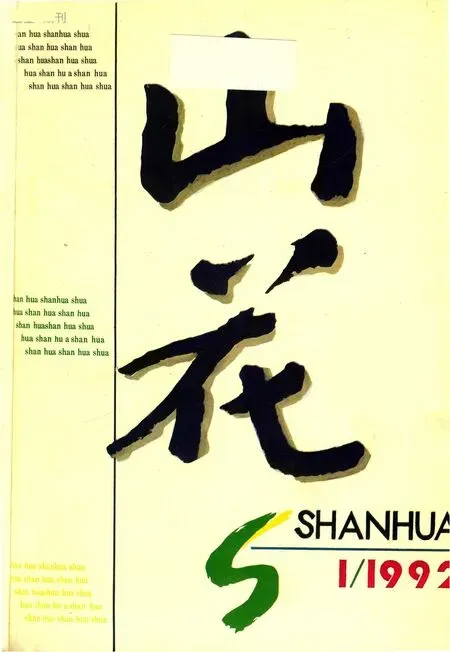红
阿航
凌这十年里、尤其是近五六年里顺风顺水。他由一位非法入境者成了拥有意大利绿卡的人。然后是家庭团聚。六年前凌做了老板。公司规模不大——不过船小好调头,没触礁没搁浅,赚一个是一个。日子猶如一支歌,既流畅又明亮。这天凌要去那不勒斯办事儿。头天他即交待小刘明天要出门,检查一下车况。第二天他们如时上路。凌让小刘将车开往火车站,停下后他说,你去看下票,时间合适我们就乘火车好了。小刘大声问道,不开车去啦?
凌老婆打电话来时,凌和小刘已坐在从罗马前往那不勒斯的列车上。凌老婆说,怎么……你们改乘火车了?凌说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坐火车了。凌老婆注重细节,连珠炮发问,那车子呢?你既然是乘火车……干吗带小刘呢?凌回答说车子停在火车站停车场里;带上小刘是因为他就跟在我屁股后头嘛。凌老婆说了句神经病,挂掉电话。
凌为自个儿的“破例”行为激动了好一阵子。日子太过按部就班了,总嫌沉闷,所以得破破例,或者说人会情不自禁地破开罩于身上的网。凌今天的所作所为,只能这样子解释了。凌对小刘说道,自己开车,能够这样看海景么?这晃悠悠的……那心情不一样的,那叫赶路,这是欣赏!从罗马开往那不勒斯的列车,大部沿海岸线走,论景色没话好说的。途中上来一位中国男子,戴眼镜,经多识广的样式。凌和他攀谈开来,知晓他原先在日本留学,现在意大利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做事。
晚上凌和报关的人谈价钱。那不勒斯是座藏龙卧虎的城市,什么人都有,黑道方面尤甚。过去,凌的货柜是经由第三方从海关提的,剥了一层皮。这回他找着门路与对方直接挂上了钩。那位黑手党小头目说道,凌老板,你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凌笑道,这与生意有关啊?小头目说,我喜欢与精神面貌良好的人合作!去旅馆出租车上,凌回想起火车上碰见的那位眼镜男。眼镜男说我在日本曾经做过消防队员呢。凌迷惑不解,他说你没人日本国藉,怎么可以加入他们的消防部队呢?眼镜男说我在日本边读书边在一家医院打杂工,勤工俭学嘛,不过尸体是没背过的……我认识了一位眼科大夫,那人气质优雅,是个高高在上很难接近的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帮他一个忙。凌问道,你说这些与消防队的事儿有什么关联?眼镜男说你薄荷糖还有没有?我嗓子好像是冒烟了。眼镜男鼓起一边腮帮继续说道,大夫的夫人性欲旺盛,而大夫本人文质彬彬不是她对手,大夫叫我替他帮忙。凌听出了门道,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眼镜男,不再多话。凌心想,这大概就是人打破常规后所得到的收获吧。眼镜男接下来所讲的事儿,在凌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眼镜男说,……大夫让我随叫随到,有时上半夜还好点,凌晨时分马马虎虎,有时却是大清早,操!我睡得正香甜哩,电话来了,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到他们家……大夫穿睡袍坐在客厅里,他朝我点下头,说进去吧。大夫夫人躺床上,灯光很暧昧,气味很暧昧,她像一条热锅上的白鱼……大夫给我限定两条规矩,第一条必须戴套,那部位不可以有肌肤接触,这一条我想起来都觉着滑稽透顶;第二条不允许动情。实际上这是废话,他夫人是政府部门职员,养尊处优,会和我穷学生谈情说爱么?从卧室出来,大夫一般仍坐在客厅里,喝酒或看电视,他将小费给我,请我喝杯威士忌,嘴上说辛苦您了……日本人他妈的就讲究礼貌!
十年间,凌循规蹈矩,卖力打拼,心思没用在其他地方。这回听了眼镜男的一番话,他心旌摇摆开了。凌拿自个儿与眼镜男相比,觉得自己真是活糟蹋了,竟是一杯白开水。第二天吃过早餐,凌磨磨蹭蹭,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小刘说老板,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凌大为不悦说道,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急!小刘抓了两下头皮,开始东张西望。他们坐在宾馆小餐厅里,隔玻璃墙外头是个街心花园,走动的人以遛狗的为主。凌问小刘道,昨天那个中国人,你说他会不会来?昨天抵达那不勒斯后,眼镜男帮他们找到这家宾馆住下。眼镜男说他是穷打工的,要找青年旅舍入住。小刘又抓了两下头皮,摇起脑袋说不知道。凌说昨天太手忙脚乱了,没留他手机号,连他的名字都没问一下……按理说我是说过也去庞贝看看的,他说不定会过来叫上我们的吧。他们转移到街心花园条椅上,从这儿能看见宾馆出入的人。两个小时过去后,小刘问道,我们怎么办?去火车站买票?凌说不急的,干吗不自己给自己放放假呢!
他们驱车前往郊外海滨浴场。车是一个叫阿毛的人开来的,里面坐着两位同为大陆出来的妇女,一位年轻点的名叫伟红。凌装聋作哑,没点破那层薄纸,由着小刘漏洞百出地自圆其说。他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午饭,点了海鲜大餐,喝的是产自葡萄牙的一种粉红酒瓶子的葡萄酒。阿毛乐得眼角堆皱纹,说咱们今天算是见识到大老板了!伟红眼睛会说话,举杯敬酒,嘴上说凌老板,让我借花献佛一回吧。凌给自己和伟红的高脚杯倒上酒,说让我回敬你一杯。伟红脸染桃花色,摇头说我不会喝酒的,凌老板你就放我一马好了嘛。阿毛说这不行的,老板对我们这么客气请我们吃饭,他敬的酒非喝不可!伟红拿眼角余光瞟了一下小刘。这一幕被凌给捕捉到了。凌面对小刘说道,你给句话,让伟红给我一个面子。
昨天晚上,凌去谈事的时候,小刘通过一张华文报纸的广告栏找到了那家隐藏于公寓楼里的“按摩店”,与这位名叫伟红的按摩女交易了一回。凌决定在那不勒斯再待一个晚上。阿毛哈巴狗样子说道,老板你先回房间休息,我过会儿送她来就是。小刘愁眉苦脸,被凌训斥了几句,大意是说他脑子不灵清,对千人骑万人嫖的婊子乱动情!阿毛打电话来说伟红大姨妈来了,换一个行不行?凌很不高兴,大声嚷道胡扯淡!你蒙谁啊!过后,阿毛敲凌房门。凌打开门,见阿毛身后站着位年轻貌美女子。
第二天凌与女子勾肩搭背下楼吃早餐。春宵苦短,凌尝到了甜头,他的心情像花儿一样绽放。可他在餐厅见到用餐的小刘和伟红时,好兴头顷刻间一扫而光了。凌恼羞成怒,虎着脸没与他们打招呼。伟红跑过来说,凌老板……我以为您还要睡会儿的,就没敢叫你们啦……凌小口喝牛奶,不做声。伟红脸偏向女子说道,春燕,凌老板他人很好的,你昨晚服务尽心了没有啊?凌冲小刘嚷道,愣着干吗,上楼收拾走人啊!回罗马不久,凌将小刘给辞退了。
进入九月,秋季服装开始粉墨登场。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公司两个集装箱被海关扣留了。凌火速赶往那不勒斯港口,黑手党小头目已在就近一酒吧等候。小头目说道,这不关我事,你们在货柜里塞香烟,被抽查到了!凌说,香烟数量又不多的,是我们员工自己抽的,他们抽惯了中国烟,你可以对他们说明的嘛。小头目说,那药品呢?在意大利走私药品那可是犯重罪的!凌说总共就那么点药,也是自己用的,备用药、常用药。我的员工中有没医保的,去不了医院。小头目说,还有一种东西,乌黑的植物干,是不是毒品?凌叹气,他没法解释霉干菜,意大利是没有霉干菜的。
事情终归解决了,烧钱而已。凌心情坏透了,本想当天坐车回去的,临行时他想起了那个伟红,便给
阿毛打了个电话。阿毛说他开车过来接他。凌上车后,阿毛没直接拉他去按摩店。阿毛说他今天分发卡片的任务没完成,他让凌稍候片刻。阿毛将车停在火车站广场旁树阴下。这儿过往的人多如过江鲫鱼,基本上不是本地人或者说意大利人,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财利无头苍蝇般飞来飞去。阿毛说卡片不能给当地人,当地人会报警,那样子老窝就要被端了。凌坐在车上,看阿毛鬼一样机灵,见单身黑人、阿拉伯人、东欧人及黄种人,就往上凑,皮笑肉不笑,塞张卡片给他们。阿毛发完一百张后回到车上。阿毛说,这叫广种薄收,一百张卡片有一两位上钩就不错啦。凌心头闷闷的,呕吐的感觉都有了。他说我还是回去算了。阿毛说,你这是干吗呀,伟红现在还在睡觉呢,房间钥匙我有的,我直接领你进去就是了。
按摩店女人晚上干活,白天睡觉,这是定律。凌进入那套房子时,小客厅里仅老板娘一人在看香港电视剧碟片。阿毛说,这位凌老板,钱的大大的有,想伟红都要发疯了。凌皱起眉结说道,你太夸张了吧,乱弹琴!老板娘化的是浓妆,眼圈如两个黑洞。她起身瞄了一眼凌说道,看得出来,老板是个有福之人啊。阿毛说,伟红还在房间吧?我领老板去。老板娘说,那怎么行呢,总要先叫她起来洗洗吧。阿毛说没事的,凌老板就好原汁原味这口。他们登上窄楼梯去顶楼。
顶楼原先肯定并非住人的,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空间不大,除了面朝楼梯口的窄门外,尚有一个小窗户。窗户外头是斜面屋背,几只鸽子在屋背红瓦上悠闲徜徉。此时房间里就凌和伟红两人。凌局促不安,他说我可以坐下来吗?伟红说随你啊。凌拖过房间里惟一的椅子坐下。凌说你们都睡这么迟的么,今天外面天气不错的。伟红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凌说,我今天过来有事,想起你了,就过来了。伟红说那谢谢你喽。凌笑着说道,不必客气的。伟红说,你能请我吃饭吗?我好久没去餐馆了。凌说,只要你肯赏脸,我没理由不愿意的。伟红背对凌脱下睡衣。凌从身后将她抱住。伟红说,先别捣蛋了,我得冲一下。没想到这阁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个小洗手间的。这洗手间想必是后期改造而成的吧。
秋日里,海天一色,都是蓝的,很透气。凌说,那不勒斯不错,离海近,比罗马强。伟红说,对我们穷人而言,在哪都一样,都是地狱。凌说,你这人特会哭穷。伟红不语。他们在海边别具风格的餐馆就餐。凌不安分,或是抚摸伟红的手,或是摸她的腿。伟红那天穿短裙,黑丝袜。凌说,你的腿是颗炸弹,要人的命呢。伟红让他占便宜,吃自己的。凌说,等下吃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开宾馆吧。伟红摇头。凌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伟红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凌老大不高兴,说有话你就直说吧。伟红问了个俗不可耐的问题:这世上真有爱情吗?凌不禁大光其火说道,你是说……你跟那个姓刘的是爱情关系?别让人笑掉大牙了!伟红擦拭嘴唇,喝干杯中物。伟红说,他前些天来过这里。凌说,请别在我面前提那小子了,他对我来说狗屁不是!伟红说我知道你把他退了。凌冷笑道,这又怎么啦?伟红说,所以,我要报仇。凌嘿嘿冷笑两声说道,今古奇观啊,我算服了!
来年春上,阿毛出现在罗马凌的批发店里。凌正和员工在店铺后头仓房盘货,不说蓬头垢面的话,至少是衣冠不整的。那天阿毛倒是衣着光鲜,煞有介事地扎了条猩红色领带。员工领阿毛进来,说老板有人找你。凌从纸板箱后面出来一看,原来是阿毛。阿毛伸出手要和他握手,凌说手脏。阿毛说,我厉害吧,我根本就没怎么打听就找到你这儿了。凌对阿毛自然没好感,他警惕地问道,你找我有事?阿毛嘻嘻哈哈,说没事儿,来罗马玩就找老朋友来了。凌为了避开他老婆耳目,带阿毛去了一家酒吧。落座后阿毛开门见山,说他不愿再干拉皮条的活儿了,想来凌公司做。凌说,我目前不缺人手。没事的——阿毛舞着手说道,我每次来罗马都急匆匆的,这次就走走看看……我没地方住,能在你工人的宿舍打个地铺吗?凌本想一口回绝的——他转而一想事情不能做绝了,便说时间不可太长了哦,那样会影响工人休息的。阿毛这颗牛皮糖就这样粘上了。阿毛什么地方都没去,员工们起床他也起床,员工们干活儿他也干活儿,只是员工们是拿工资的,他是白干的。阿毛身板结实,不胖不瘦,脑子好使,几日下来,凌老婆对他十分中意。她对凌说道,我们把阿毛留下吧,像这样的工人打灯笼都难找的。凌说不行,他这人品质不好。凌老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喃喃说道,什么品质不好?我们又不让他管银行,干活嘛只要肯出力就行呗。凌说这人嘴碎,万一搬弄是非还不把员工队伍水搅浑了啊。
凌约阿毛去酒吧谈谈。凌说,你可以走了。阿毛头一沉,说老板你就留下我吧,我可以拿比他人低的工资。凌说问题不在这里。阿毛哦了一声后说道,我明白了,你是信不过我……怕我多嘴。老板我实话实说吧,我可能其他毛病不少,但就是不多嘴,我是在社会上摸打滚爬过来的人,知道多嘴的人没好报,我会守口如瓶的。凌很不高兴地嚷道,你多不多嘴和我什么干系?我有什么底牌拿捏在你手上?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阿毛抽了一下自个儿嘴巴子,嘴上说我还是多嘴了,该死!凌说我不与你泡时间了,你说吧,今天还是明天走人?阿毛嘴一扁,似乎要哭的样子。凌起身要走,阿毛赶紧站起横在他前面。阿毛说老板,我现在是走投无路才投到你门下的啊,我不是不愿拉皮条……是他们把我赶出来了,你就做做好事收留我吧。凌想了想后说道,我一个朋友店里需人手,我介绍你去他那儿好了。
次日公司仓房起火,阿毛一马当先端了灭火器冲进去。火不大,起火原因不明,损失可忽略不计。可偏偏阿毛的手被烫伤了,他小题大做地直哼哼。凌一眼识破其中有诈,但无奈抓不住把柄,只得由阿毛表演下去。凌老婆是个信佛的人,平日没事都要显示下慈善的,这下子有的放矢,对阿毛好得不得了。阿毛在医院待了两日,包上纱布,打过消炎针。出院后凌老婆安排他住到自个儿家里,热菜热饭招待,好言好语劝说他安心养伤。阿毛感激涕零,他说我就是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你们对我的恩情啊。
凌有什么法子呢?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阿毛伤痊愈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公司里。一段日子下来,风平浪静。渐渐地,凌发觉阿毛这人并没想象中那么令人讨厌。阿毛的勤快,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这人挺知趣挺识相的,至少在面上看来他并非一个多嘴多舌之徒。由于阿毛车技好,凌有时候出门就让他来开车。凌自己是会开车的,但他一支胳膊有毛病,发麻,他担心关键时刻这支胳膊会误事,所以通常跑远途就让别人开。有次在车上,凌见阿毛有只装了黄豆的玻璃瓶子,便好奇问道,你吃零食的?阿毛说生的。凌不解,问什么生的?阿毛说黄豆是生的,不能吃。凌更加不解,问那干吗带着?好玩?阿毛说是的,好玩。凌懒得再问。
这期间伟红来过一趟罗马。伟红来罗马凌本应不知道的。罗马那么大,进来一个人就如在大海里掉下了一枚针,起不了波澜的。但阿毛把伟红来罗马的事儿对凌讲了。凌一时没反应过来,反问道你说什
么?阿毛结结巴巴说那不勒斯那个伟红她人在罗马呢。记忆的阀门打开了,那个即将要被忘却的伟红浮上了凌的脑屏。想起伟红这个人,凌恍若隔世,很不真切,像是游移在旧照片里的一些人与物。凌本能地问道,她来罗马干吗?阿毛说,那个小刘……他要结婚了,伟红来吃喜酒的。凌松了口气,他叼起嘴角说道,这对活宝还真像模像样了哪。
伟红给凌打电话,说凌老板咱们可不可以碰下面呀?凌心头仍有怨气,说你还要报仇?伟红说凌老板你就别取笑我的无知了……我晚上回去没车了,你能开个房间给我住吗?凌心头七上八下,有个小鬼在捣蛋似的。凌驱车去接伟红,一路上胸口都在敲锣打鼓。随后他们共进晚餐。那天的伟红穿着得体,在暗色调的灯光下妩媚生动,没有风尘女子的沧桑和低俗。也就是说,这次见面,伟红给凌的印象还不赖。凌打破略微尴尬局面,他说咱们又吃饭了啊。伟红说,还是你好。凌看了眼伟红说道,你受刺激了?伟红说没有啊。凌说你这人……有时让人吃不准。伟红说以后不会了,我不再相信爱情了。凌说人落到实地就好。开好房间,他们顺理成章进入程序。伟红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或许她天生这方面强项,总之凌很享受,觉得今天这步跨进来是值的。伟红说我问你个问题行吗?凌笑道你问题就多……你该不会说出和我产生爱情的话来吧。伟红说,你这样冷淡,我真受不了!凌说怎么啦?你在乎我的态度干吗?伟红说,其实……我是一直喜欢你的,当时我不好那样表示……凌说你千万别那样,我求你了,咱们露水鸳鸯做一回是一回,千万别搞沉重了。伟红说,我挺恨自己的,太多情!凌捧起伟红脑袋,说真的假的呀,瞧你像真的似的。伟红说你上次许诺过,要帮我开间小店的,我自己已有点积蓄……你还会帮我吗?凌当然想起是有这么回事儿,那不过是哄人的把戏罢了。凌说我有说过这话吗?不可能吧。伟红说你有没有说过没关系的……我做梦都想离开那种地方,你就做做好事成全我吧,我保证……只跟你一人好……凌想了想后说,那你要做到,不要神经质,我们要做到理智对待这件事情。
凌和阿毛上路。这回前往那不勒斯是去看伟红的店铺。伟红在电话里对凌说道,她在那不勒斯城边盘下一家小店铺,想做大众化的服装生意。伟红的意思很明白,她的积蓄仅够盘下店铺,付一个季度的店租,至于货物,那得靠凌帮忙了。伟红说,这儿紧挨菜市场,老太婆家庭妇女很多,中国货应该是有市场的。凌说,那也未必,你又没做过服装……要不我哪天过去看看吧。
伟红盘下的店铺很一般,她本就是图个店租便宜嘛。周遭环境乱糟糟的,有股刺鼻的腐烂气味。伟红一副陪小心的样子,尾随凌屁股后头,想听听他的评估。凌慢条斯理说道,有一点你得搞清楚,老太婆和家庭妇女是你的潜在消费对象,这点没错,但你有没有想过,她们如果是去菜市场买菜的,会不会又买服装呢?换作你你会不会那样做?拿着方不方便?或者说带去的钱够不够?这些都得考虑到的,并不是说这些人多的地方就一定有生意做的,那也要看她们出门是干什么的,她们的目的是什么。一席话说得伟红哑口无言,半天回不过神来。凌顺手搭上丢魂失魄的伟红肩膀,语气明显放缓说道,不过嘛,话说回来,你已经盘下了店铺,付了店租,钱已经砸进去收不回来……这是前提,所以就得围绕这个前提看问题了。伟红眼睛一亮,她说你的意思……这店还能开?凌说当然能开啦,你这店铺房租省,这成本就低了,这符合做生意的基本原理。再说啦,那些妇女……她们虽然来买菜的时候不大可能会买衣服的,但她们看到了你这家服装店,可能也会顺便过来看一看、摸一摸,过后她们就会专程过来买衣服了,这就是店铺开在菜市场旁的好处。
伟红请凌和阿毛吃饭。结账时他们两人猶如推太极拳般地争着付款。伟红郑重其事说道,凌老板,论钱我自然不好和你争的,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饭后凌自个儿驾车和伟红跑出城区。他们沿海堤大道慢悠悠走,比骑自行车快不了多少。凌说,我还是喜欢那不勒斯,这海风吹过来,这做人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伟红半撒娇性质说道,你现在这儿不是有家了嘛。离海岸不远处的礁石上立有一座古堡,夕阳下熠熠生辉,煞是好看。凌问伟红道,我们是不是下来走走?这海岸与礁石古堡间,是有石板桥相连接的。海鸟翩翩起舞,时隐时现,景象浑然一体。伟红缩着肩膀说道,我冷。凌说,那行,咱们往回走吧。
传来门铃声。凌老大不高兴地走向门边用意大利语问道,谁啊?门外阿毛应说是我。凌简直火星子都要飞溅出来了,他厉声嚷道,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阿毛说老板,你门口有把刀!凌心口紧了一下,他声音发颤问道,你是说……门口有把刀?这是什么意思呢?阿毛说,我看这事儿凶多吉少,你还是留个神吧。凌说你先别走开!他回头替伟红盖上被子,自己手忙脚乱穿上衣服,将门打开。那把在夜色里仍寒光闪闪的刀在阿毛手中。阿毛进来后随手带上门,然后对凌说道,把大灯打开。凌没反应过来,木雕一般站着。阿毛提高声调说道,你耳朵呢,把灯打开!凌机械地拧亮大灯开关,木然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阿毛掏出那只装黄豆的玻璃瓶子说,我瓶子里现在有一百颗豆子,最后这粒豆子是压垮骆驼的那根草你懂吗?我阿毛今天要开杀戒了!凌脸色苍白,他是完全被搞懵了。这时,头蒙在被窝里的伟红嘤嘤哭泣。阿毛冲她嚷道,你哭个鸟!老子受够了、忍够了,现在老子的命已不是自个儿的,死了拉倒活着就要出气,所有的鸟气我都要出!
在凌意识中,认定这是一出阴谋。可这个阴谋,却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头绪繁多,模棱两可。如说敲竹杠,凌明天即掏腰包要替伟红进货了,干吗不等货进了再下手呢?阿毛扬言,伟红是他老婆;伟红没做声,默认了。故此,凌睡人家老婆,阿毛是有一万个理由砍他的。那天接下来的场面,动静颇大。阿毛举着刀要砍凌,凌抱头乱蹿,好几次都差点要吃刀子了。危难关头,伟红勇敢地从床上跳下来,死死拖住阿毛,让凌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阿毛咬住凌不放松,他没离开他的公司。而且表面上,纹丝未变,仍然干活那么勤劳,那么麻利。凌老婆甚至为留住这样优秀的员工而给他加了薪。凌苦不堪言,十分地焦虑。病愈后的凌找阿毛谈话。凌说,我愿意一次性割断,两万欧元总可以了吧。阿毛说,要是我不答应呢?凌哭丧着脸说道,那你提嘛,只要你不提过分要求,我就答应你。阿毛将烟头弹得远远的,他说钱财现在对我没卵用了。凌紧张兮兮问道,那你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不管是华人圈里还是意大利当地人……都有人头的,咱们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哦。阿毛轻描淡写说道,这点我有数,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肯出本宰个人还不像宰条狗一样简便啊。问题是,我阿毛现在根本就不怕死……除非让我立马毙命,要不打蛇不死成蛇精,那就够你受了!
不久,凌家的那条爱犬失踪了。这条苏格兰牧羊犬是凌花大价钱购得的,是他们家的守护员。现今守护员没了,那么他们家就可长驱直入,安全性根本无从谈起了。果不然,凌老婆有一天整理被褥时,闻到
了一股异味,还发现了几根并非她和老公的发丝。凌老婆把这事儿对凌讲了,凌的脑门于顷刻间淌下了虚汗。凌老婆说,我们的床上怎么会有别人的气味和头发呢?凌打马虎眼说那可能是我身上带回的吧,我整天和这些工人搅一块儿,说不定就把他们的气味和头发给带回了。凌采取行动,换了门锁。因阿毛曾在他们家住过,凌怀疑阿毛早就怀有歹心,当初翻了他们家钥匙的。这样子安宁了一段日子。有一天,凌老婆发现自己卧室洗手间洗得干干净净的抽水马桶粘上了粪便的痕迹。凌老婆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没等老婆发问,凌赶紧把责任往自个儿头上揽了,他说他今天回来过一趟,解手后因有个电话催来他就走了,忘了用刷子刷了。第二日,凌找来工人,将所有的窗户安装上了铁栅栏。
凌这次对阿毛放了狠话,他说你别以为就你不怕死,你把我逼急了,我照样会豁出去的!阿毛一言不发,尽由凌大发雷霆。几天后,当地华文报纸和意大利一家较大报纸均报道了一名叫刘扬的中国人被莫名打断双腿的事件;紧接着两家报纸又报道了那不勒斯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妓院被警察查封的消息。根据报纸上所刊登的地址,凌确认那家按摩院正是伟红待过的那家。凌松了口气——这个变态的家伙终于把气出在他人身上了。一天,伟红给凌打来电话,哭哭啼啼,上气不接下气诉说阿毛回那不勒斯每次都打她,她现在是人像熊猫都没法子见人了。伟红抽泣一阵后继续说道,他每次非但打我还骂我烂婊子……当初干上那行、一方面是无可奈何……我们的厂被火烧了,皮革机器、原料烧了,自己的住房和厂房连着的,都烧了,我们就是水里爬上岸的人了……债欠得比山还高……我们凭旅游签证到这意大利,两手空空居留证没有……当时不是他要我干那行,我怎么放得下脸、我丢不起那个脸的啊,可他说在这国外没人晓得,等有了钱后就洗手不干、就可太平过日子了,这些话都是他说的,我到现在耳朵边还响着这些话……凌没好气说道,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谁知道你们演的是什么把戏!伟红声细如丝说道,我是没路走了……才给你打电话的,在意大利……我再没人可找了,不管你认不认……我心里、是拿你做最亲的人的……凌说,戏不要再演下去了,你们要怎样痛快点,真把老子惹火了老子也并非吃素之辈噢!说完即关了手机。
凌痛定思痛,后悔莫及。凌非常后悔那一次的“破例”乘火车,真是饭吃饱了撑着啊,上了那一趟列车猶如上了贼船一般,碰上了那个巫师一般的眼镜男!凌至今都没搞明白,那个眼镜男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所说的话语像是裹了魔力似的,引领他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烦恼,直至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不能自拔的凌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这天,凌驱车去了那不勒斯。他要对伟红打破砂锅问到底,非刨个一清二楚不可!
伟红并未如想象中的那艘憔悴,也没如她自个儿所说的像只熊猫。伟红的日子不赖,至少呈现出来的是和风细雨的面貌。菜市场旁的小小服装店,生意不温不火,隔三差五来个老太婆,或一位经济状况拮据的家庭妇女,挑挑拣拣,总能落下一两单小额买卖的。凌将车停下,没马上下来。透过车窗玻璃,凌看着伟红,神思恍惚,一如梦里头一般不真实。这个伟红,害得他好苦啊!可是,凌很奇怪,他怎么都恨她不起来。凌对伟红的感觉、感受,或者说严重一点—情感吧,是错综复杂的,五味杂陈。伟红先看见了凌的车子,继而瞧见了车窗玻璃后头的凌。伟红情不自禁地从店铺里跑出来,欢欣的表情展露无遗。凌慢吞吞地从车上下来,尾随伟红步入店铺。伟红说,是什么台风把你吹来的呀!凌面无表情,叼上颗烟。伟红说,我这就把店门关了,吃饭去。凌说不必了,我可没那份心情。伟红垂下头来,喃喃说道,他……还烦你是吗……凌说,我今天来,要把事情弄明白,是横是竖,只要弄明白了我都愿奉陪到底……你、和那鸟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不觉得这样设圈套太伤天害理、太无耻么?我凌某人对你问心无愧。伟红半天没说话。她摸索一通后递了张相片给凌。那张照片上有伟红和阿毛,还有一个小男孩。那孩儿无疑是他们儿子了。凌重重地放下相片,他说我想不明白,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伟红低声说道,事情已经这步田地了,我有什么法子呢。凌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伟红说事到这步……我都不想活了……凌又点上根烟,终于吐出了那句话:如果说,当然我也是走投无路出此下策的……说白了,他现今已经是个无赖、是个不可理喻的变态人……如果说让他消失,你会怎么看?伟红闭上眼睛摇摇头,说,听天由命吧。
凌迟迟横不下心,猶豫不决。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体,做人做事一贯谨小慎微的凌,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天后阿毛的魔爪再度伸向了凌家,凌被逼到了绝境,他是忍无可忍了。凌老婆驾车去学校接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争先恐后地向他们母亲汇报说今天阿毛叔叔来看过他们,还带来鱼籽酱披萨饼给他们吃。晚饭桌上,凌老婆对老公说道,没想到阿毛他这人对咱们家孩子这么有爱心,他今天跑学校看望咱们家儿子了,还破费买了鱼籽酱披萨饼。凌一听脸色陡青,差点没将盘子掉落地上。
前往那不勒斯的列车按时从罗马站出发。凌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平息下来。凌闭目养神,心里头说,该来的风暴就让它来吧!凌去了一趟厕所,其实他一点尿意都没有,但他就是莫名其妙去了,站在那儿空抖了两下。回座位后,他脑子里又开始了刀光剑影,心乱如麻啊……凌心里的纠结愈演愈烈,血淋淋的场景都出现了——他浑身颤抖开来,像个打摆子的病人。
黑手党小头目打电话问凌怎么还没到?凌说,我来庞贝了。对方必定怀疑耳朵听错了,大声问道,你说什么?凌重复说了一遍。凌在那不勒斯下车后,他没来由地尾随在一对小年轻身后上了前往庞贝废墟的旅游列车。当时的凌脑子一片空白,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旅游胜地庞贝废墟,游人如织,莺飞草长,是处能让人神经松弛的地方。凌太需要暂且喘口气了。小头目说,人已抓来,要命还是废手脚?凌迟缓片刻后说道,……放他走吧。小头目说那费用你得照付哦。凌说,好的。你们吓唬他一下放人好了。没过多久,小头目再打电话来,他说那家伙走后,突然死大街上了。
阿毛的死因,在医学上都很难解释,说是肺部破了,吐了几口血就一命呜呼了。同时,阿毛的死也成了一宗无头案,归档自然病故死亡。伟红作为他的妻子,替他收尸,入葬公墓。而后伟红精神出现失常,时好时坏,她那家服装店也就一关了之了。躲隐于幕后的凌,每日里心惊胆战;而他还得关照和防备伟红这个女人。
这种折磨,更是变本加厉。伟红披头散发、天女散花的样子跑到罗马凌的公司。凌老婆念叨一句阿弥陀佛,上前扶她落座。伟红嘴上说,我老公死了,阿毛他死了……阿毛可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啊,他就走了,不知是去地狱还是去天堂了……凌老婆知晓这女人是阿毛老婆,愈发对她充满了怜悯心。凌老婆对凌说道,我们养她吧,阿毛对我们公司没有功劳有苦劳的。凌没好气回应道,公司又不是精神病医
院,怎么养?!伟红病情没发作时,与正常人无异。她穿着正统,头发梳得整齐,只是不苟言笑。有一回伟红和凌在酒吧时,她对他说道,阿毛他是被生活逼的,他的心理不正常是太压抑了……换作别人,恐怕比他更不正常。凌说,他的人生、或说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总不是我给造成的吧,可为什么……这苦果要让我来吃!伟红手按在凌手背上,她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的……我有时候真的没法控制情绪,让你受累了。
伟红自有让人销魂的地方,这一点凌很难抵挡得住。本来,凌见过她那失常时的样子——那样子已是几近于疯子,谁多看一眼都咽不下饭的。而且,凌面对伟红那等情形时,厌恶、甚至绝望的情绪就堵在胸口。可是他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时过境迁,无须粉饰的伟红以常态性的面貌走进他的视野,走入他的生活,凌即没招了。每次,凌都会灵魂出窍,飘飘欲仙……可提裤子时,他便后悔不迭,心里暗骂自己狗改不了吃屎习性!
捉摸不透的是伟红这个人。伟红有一次对凌说她是装疯卖傻,她心里明镜一样什么都清楚。凌大吃一惊。凌问道,你为什么要装疯卖傻?伟红说我心里苦。凌说讲大白话,别转弯抹角了。伟红将头枕在凌肩膀上,说你对我好一点,我心情就好一点,我心情好一点情绪就好一点。凌推开伟红说道,你说来说去又要将责任落我身上了,我可承受不起哦。伟红盘在床上哭泣,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
凌不是没有想过要斩断两人的关系。凌回了一趟国内,去义乌进货。往常去义乌进货,来回一个月时间足够了,这次他耗了两个月,去桂林旅游,去黄山旅游。凌把自个儿晒得黑漆漆的,拍摄了不少祖国山河的TV和照片。凌风尘仆仆回返意大利,在罗马达芬奇机场,他见到了老婆和伟红两个人。凌先是见到他老婆——正热切地向他招手——凌拉着行李箱快步靠近她。这时凌看见了老婆身旁的伟红。伟红羞答答的样子,说路上很辛苦吧。回家后,凌责怪老婆不该带伟红去机场的。凌老婆说,她现在情绪稳定下来了,基本上不会犯病了。凌说那也没必要带上一个外人去接机啊!凌老婆说,她在罗马无亲无戚挺可怜的,我想有机会出去就带她出来散散心喽。
伟红现在一家日本料理店打工,租了个小套房子。有天凌和朋友上那家日本料理店吃饭,伟红做的服务员。伟红跪着身子退出榻榻米后,朋友说这娘们儿有日本味,眼睛如两片豆荚。凌打趣道,老兄有兴趣,可进攻的,她没老公的。朋友哈哈大笑,他说你少来这套,谁看不出你俩有一腿的,眉来眼去就没歇过。凌也觉着那天身穿日本和服的伟红富有异国情调,十分生动,搅得他心猿意马。趁着清酒的劲道,当晚凌去了伟红的出租屋。伟红嗔怪道,你不是不理我了么,看见我像是见了鬼似地眼睛没处放。凌嘻皮笑脸道,这不喝酒了么。伟红拧了他一下,说酒不喝进去就不近我身了是啵?凌骑上伟红,让她不停地说日本话。伟红就会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不厌其烦地在那儿叽里咕噜。凌性幻想的翅膀充分打开,逗留在云雾深处。
凌让伟红多学日本话。他说你学一句,我就过来一次。伟红说我干吗?我前辈子欠你的呀,陪你睡还要学日本话!凌说话不能这样说的嘛,照你这么说我也欠你的了,一有空就往你这儿跑,生意上的事儿都耽误了。伟红说你生意上的事儿跟我什么关系?钱赚来又不给我的。凌说你这房租不是我付的吗,还有其他,钱不进来我怎么吃得消呢。伟红白他一眼,嘴上说,小气鬼!
学校放暑假,凌老婆要带俩儿子回国内度假。凌老婆对凌说道,再不带他们回国看看,他们对中国就没感情了。凌对她介绍桂林和黄山两处景点,他说一个是水好一个是山好,是比较典型的。老婆孩子走后,凌心里空落落的。他的重心转移到了伟红身上。伟红十一时下班,凌十点半即将车子开到店左首路边,听音乐抽烟。换过衣服的伟红小跑着过来,那只背包在她身后甩来甩去。凌丢了半截烟问道,肚子饿吗?伟红说回家做吧,我想在家里喝点小酒。凌平时不在伟红出租房过夜,现今是隔三差五在这儿过夜了。有天半夜里,伟红说梦话,连着叫嚷了好几句我要报仇!凌吓出一身冷汗。伟红讲“报仇”这话是有前科的,当年她要替小刘报仇,吊足他胃口后苦苦煎熬他,没让他上身。凌好几天没再露面,伟红打他手机他不接。这天晚上,伟红径直跑到了凌家楼下。伟红揿门铃,门铃声尖锐刺耳,凌脑袋都要爆炸了。凌没法回避,只得让伟红进来。伟红劈头问道,你为什么躲我?凌不说话。伟红揪住凌睡袍前襟,歇斯底里嚷道,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你还要我怎么样!凌垂头丧气说道,我害怕……凌对伟红说了所听到的梦话和自己的顾虑。伟红柳叶眉一挑,笑吟吟说道,梦里的话还当真呀,瞧你这熊样。
就在当天晚上,熟睡中的伟红口里再度出现了“报仇”两字。这回凌推醒了伟红,询问她还记不记得刚才做的梦?伟红眼睛瞪得大大的,她承认记得。凌说那么我问你,你是要报谁的仇?请你诚实回答。伟红突然就哭了,越哭越响亮。凌心中已明白大半。凌起身点上烟,他说我既然是你的仇人,那你……为什么要和我交往?是要活活把我折磨死吗?伟红摇头说,不是的……我真的没那么想过、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凌晃晃脑袋说道,又是今古奇观了,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话对得上号吗?
终于有一天—那天伟红休息——他们两人在露天酒吧喝咖啡时,伟红将自己心里的“隐秘”全说了出来。伟红说,她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她不该和杀死自己老公的男人睡觉。可是,她又掌控不了自己,越陷越深,所以才会在梦里说出那种梦话的。凌即刻分辩,他说阿毛又不是我害的,你自己一清二楚的,他是自己得病死的……你怎么可以把这祸水泼我身上来呢!伟红说,他是自己身上有病死的,这点没错,你也的确没叫人对他动刀子,可是……他是被你心里的那把刀杀的。
凌说,我敢断定,你的神经病又发作了……我们好自为之吧,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当这辈子从未认识过的。伟红叼起嘴角说道,你说得太轻松了吧。我老公死了,他就这么不明不白死了,你逃脱得了?我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自从老公死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在磨刀了……怎么说呢,我这人还是太多愁善感了,被感情牵着鼻子走……我这怎么可以啊。
凌老婆孩子从国内回来后不久——凌为防备伟红狗急跳墙——先一步对老婆说了自己和伟红的事儿。凌避重就轻,说伟红怎样勾引他,他顶不住引诱才做了糊涂事。凌老婆可说是个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社会经验全无,心理的承受力特别脆弱,她当场即昏厥了过去,一病不起。凌老婆嘴上念叨说,我一生信佛行善事,可到头来怎么会是这样的报应啊!凌的家庭乱成一锅粥,小儿子因缺乏照料,发起高烧也生病住进了医院。凌的大儿子,已十多岁,已多少明白些事理,他对凌的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人瘦了一圈,脸色蜡黄蜡黄的。他如若就此打住还行,可偏偏由于神思恍惚,眼光散淡,有一天被车撞了,断了一条胳膊,住进医院打上石膏。
凌在日本料理店门口堵住伟红。伟红对同事说道,我男朋友接我来了。说过笑脸相迎走向凌。他们转身走向泊车处,凌咬牙切齿说道,我要杀了你!伟红说为什么呀?凌怒吼道,你还有脸问为什么!你他妈的心里那把刀……杀得我们家片甲不留,你这个神经病的人,早就该关进疯人院去!伟红一脸无辜和愕然,呐呐说道,我不是对你讲过么,我没病……干吗要关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