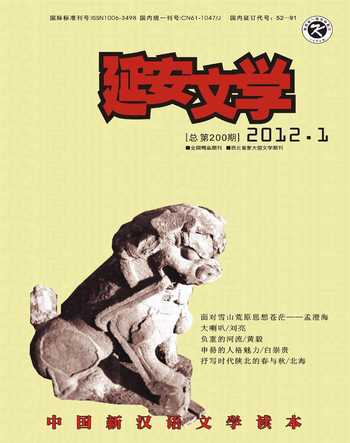西域手记
郝随穗
在一定的高度鸟瞰西域,无垠的戈壁荒漠呈现出的色彩是莫大的焦黑,偶有数道线条般的白在其间流过,原来是展堂堂的戈壁滩褶皱间停留的杂物。杂物本不是白色,有了戈壁滩的焦黑,不太亮色的杂物都会泛白。几个小时的空中掠过,云海下大地上裸露的莫大焦黑像宿命中设定的场局,不曾扭转,难以改变,令人心生纠结。被誉为“瓜果之乡”、“歌舞之乡”和“亚洲脉搏”的新疆,将要在这片看似不毛之地上为我们献上世界上最甜的葡萄和哈密瓜!将要为我们表演最美的歌舞!将要给我们的旅行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遗憾?
喀纳斯,途经风光的迤逦
真正到了喀纳斯,那一滩说是水怪出没的水很平静。喀纳斯湖的风光出乎我们的意料,说实在的,没有老家的那几个水库漂亮。而在通往喀纳斯的沿途风光却很迷人。从乌鲁木齐出发,八百多公里的沙漠、戈壁滩、草原,以及盘山路、白桦林、松树林、皮毛市场等等,都是在喀纳斯这个名下存留的美好回忆。
乌鲁木齐的天要比内地迟晚两个小时,也比内地的天迟亮两个小时。而我们明显感觉到的是迟晚两个小时,却感觉不到迟亮两个小时。早上七点多天已经亮了,我们吃罢早餐,就开始发往喀纳斯。汽车路过刀郎歌曲中的二路汽车停靠的八楼站牌点,然后走出城市。通往喀纳斯的是一条笔直的公路,公路在天地间像一条黑线,直直地连着天尽头。有风吹来,这条线好像动了起来。
一路上的车辆很少,看到的几辆车无非是载着客人的大巴车。偶尔有群马和群羊横穿公路,车便停下来,等着它们慢悠悠地离开路面。足足有五百公里的戈壁滩上,我们的车子像漂荡在汪洋中的一叶小舟,看似飞奔的车速,却怎么也走不到前方的路口。车子里的人大多睡着了,而我却一直睁着眼注视着车窗外单一的风景思绪万千。
到了一处叫火烧山的地方车停下来了,说是让大家下车参观火烧山。下车后大家东张西望寻找火烧山,却看不到想象当中的火烧山,随车的人说眼前那几个小山包就是火烧山。我们问凭什么这几个小山叫火烧山,有人回答说这山的颜色通红,像被大火烧着一样,就叫火烧山。大家尽量发挥想象改变眼前的景象,可是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场大火来。而这几个小山包的颜色相比较焦黑色的戈壁滩,色彩稍微亮了些淡了些,但根本不是红色的。或许这其中有我们不了解的故事,或是历史已经改变了它名字的由来的面貌。
不管怎么说,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能够停下车来看看这几座小山包也是不错的,总比闷在车里好多了。人如果长时间处于不能变化的景色中,由眼睛疲劳带来的浑身困乏,那是很压抑且烦闷的。于是大家又恢复了刚上车时候的说说笑笑,车内的气氛活跃了不少。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到了布尔津,而布尔津要到达目的地喀纳斯仍需要三个小时行程。住在酒店后,我们几个走上大街转了一圈。完全是俄罗斯格调的建筑楼房和路灯,使得这个小城安谧美丽了许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条不知名的街道一侧群楼的每幢楼上有着一幅巨大的浮雕,浮雕的内容全是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造型,一长排楼房布置出的这种情调,让人感觉到走进了俄罗斯童话。而在布尔津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座布尔津河大桥,据说那座大桥也是欧洲风格,别有一番情调。
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出发。三十盘的公路上,一些弯道上有当地人搭个帐篷挂着一些动物的皮出售,似乎极少有人去买。快要下山的时候仰头看看铁丝上挂满的皮毛在风中飘荡,让人联想到西藏的彩幡,顷刻间让人安静、淡然下来,似乎那些披着阳光飘荡在风中的皮毛是来自天堂的召唤,令人心生虔诚。
终于熬过了这段路,汽车停在一个皮草市场。大家下去转悠,一大堆皮子花花绿绿地堆满整个市场。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心里希望那些皮毛全是假的,想想看如果这么多皮毛都是从一个个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剥下来,将要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挣扎、呻吟、痛苦?
进入喀纳斯景区的时候,山路绕了几道弯,几道弯的两侧茂密的树林里偶尔有一丝黄十分打眼。那是被秋风染黄的白桦树,笔直得像一条线,更像一枚金针扎在绿油油的树林之中。渐渐地沟底的河水有了变化,随即山坡上的树也在不断地改变色彩。一条河里的水像变魔术一样,时而蓝色,时而白色,时而黄色,而河流两侧的树林却像打开了金色的宫殿,呈现出一派金灿灿的景象。此刻外面的世界在白桦林的金色中显得如此高贵,如此浪漫。
汽车像一位画家的笔,走过的地方就画下了美丽的图画。汽车更像一列时空列车,载着我们进入到史前人烟荒芜,却是满目阳光、满目原始、满目质朴、满目风光的地方。
到了喀纳斯,没有看到水怪,也没有看到一条小鱼,这多少让人有些失望。而更失望的是没有感受到它的神秘,就是一滩绿水,水的周围是山,山上的树没有沿途树林的金黄。倒是倒在河边的几株胡杨给了我惊喜。那树可能死了几百年吧,硕大的躯干千疮百孔,但是树心里存留的那脉坚硬像一条生命线连接着躯干的头尾。而像刀枪一样长满躯干的枝条儿虽没有了当初的锋利,却依然挺而不倒,削弱着岁月的峥嵘。即使岁月的侵蚀让那些枝条开始腐朽,而多少年来这些倒下的胡杨从来没有消失,以自己饱经沧桑的时光流转,诉说着它不死的灵魂和光荣。
白哈巴,牧场与村寨的世界隔离
依旧是一段盘山公路,一阵颠簸后,豁然间,视野宽阔了许多,山下是一大片草原,许多羊和马、骆驼和牛在草原上吃草。
那片草原不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四周有渐渐隆起的山峰,山上长满了绿黄相间的松树和黄了叶子的白桦树。这片草原像一滩安详的绿水静卧在一个近乎圆形的山峰之中,渐渐泛黄的青草像披了晚霞余晖,微风吹过粼粼泛光。草原上奔驰的群马和吃着草的羊群以及牛群驼群恰似这滩绿水中溅起的一簇簇彩色的浪花,而那群飞奔的马则像跳跃的鱼儿,腾起一道美丽的弧影。
相对于坐在车上沉闷的心情,此刻下车后融入草原之中,心情也亮堂了许多。阳光有意倾洒下的一片金黄,给这个深秋的凉爽带来些许暖融融的阳光味道。很惬意的时刻,大家的兴致被推至终极,把头依在骆驼的双峰间展开笑容,骑在马背上像个英雄一样扬鞭驰骋,眯着眼睛躺在地上假装什么也看不见。短暂的愉悦很快被漫长的旅途拉入只听到车轮声的前往中。
车子来到了一个由武警把守的边防关卡处,我们即将通过边防关口,到达白哈巴境内的边境线上。大家怀着好奇的心理来到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线。两国之间是一条河流,以河为界的格局让人想到象棋的棋盘。河的两边是起伏的崇山峻岭,长着一样的草木,归属于不同的主人。我们站立的这个山顶上立着一块刻有“中国”两字的石碑。放眼望去,便是哈萨克斯坦的疆域,那边隐约有碉堡之类的建筑物掩藏在山坡上的草木里。
在边境线上吹一阵风后大家匆匆赶往白哈巴的那个村落。是下山的路,蜿蜒的山道两旁大多是在这里常见的松树和白桦树。不一会就来到山下,来到了白哈巴村。
村子座落在一条沟谷之中,村里的房子都是尖顶木头房子,这些看似没有整体布局的房子却像天上星斗一样星罗棋布地散落在金黄色的桦树和杨树中间,两条清澈的小河蜿蜒环村流过,一条公路穿村而过,路的尽头淡淡地消失在苍翠的树林之中。白哈巴村内居住的图瓦人属蒙古族支系,图瓦人多少世纪以来繁衍生息在阿勒泰的白哈巴、禾木河、喀纳斯湖的肥沃草原上,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这个美丽的村落被誉为喀纳斯的后花园,也是世界上少见的人间净土。
似乎要来到白哈巴有些天意的要求。你必须抖落一切村子以外的尘埃,用意念荡涤浑身杂陈,把思维和眼光退回到孩提时代的单纯。而这种要求又是你进入白哈巴第一时刻自觉想要达到的。这里的阳光温暖而有了抚慰心灵的功能。你只要立身于这片阳光下,什么事都可以在此化为乌有,一身轻松,万念复一。这里原来是修身养性的好所在,也是宗教流派生息繁衍的一片圣土。而我们在白哈巴没有看到一所寺庙,这既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们内地的好多村落里从古至今兴建寺庙,为的是教化凡人,安放美好愿望和寻找一种精神依托。而这里偌大的天地本身就是一所梵音萦绕的寺庙,虽然没有佛像和神像来供奉,但是这里的人们,以及来到这里的人们所供奉的是自己清澈的善良心灵。有了这样的虔诚自拜,是对自我心灵的尊重,也是一次对自我心灵的净化和洗礼,以及升华。如果我们能够在此刻安静下来,能够让自己的气脉与这铺满心灵的阳光一并祥和,我们的行为就完全达到了宗教思想所要求的标准。
世界的喧嚣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我们曾经介入过,在这里又退出来。木质的屋子里居住的不仅仅是图瓦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一个个灵魂的道场。无论是来者还是去者,都是这个世界隔离带以外的一种精神会所。那些屋子也许很多年来在一代代生命的轮回中摇摇欲坠,但是始终不曾坍塌。我知道,支撑屋子永久留有余热的力量是来自图瓦人舍利子般永不腐朽的质朴生存密码。
这是一个游走在世界规矩以外的村落,一切都来自自己的心灵。
有一间房子,房子上写着硕大的“图瓦”二字。我在此停留一会,并以此为背景拍照片留念。这是我在村子里看到的唯一一个证明这是图瓦人居所的标记。
我来自黄土高原深山沟的瓦窑堡,惊喜看到这个带有“瓦”字的标记,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不想牵强附会地在自己和图瓦人之间找到某种关联,我只是通过这样的直白,想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在此时此刻融入这个村子,从情感上割舍一份依偎和温存留在这里,让自己的心灵一隅永远保留一份图瓦人的天然空灵和宗教意味的依托。
吐鲁番,炙热的拥挤
吐鲁番是融“火洲”、“风洲”、“沙洲”、“绿洲”为一体的自然地理历史博物馆。“火洲”是指火焰山的地表温度高达82.3℃。一个巨型温度计竖立在山脚下,准确地测量出当时的气温,告知来到这里的人,这里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火洲”;途经吐鲁番到达坂城区间的头道河、三个泉到后沟一带,便是三十里风区。这里也是新疆风力发电的重要基地,丰富的风力资源给这里的戈壁滩带来了一大壮美的景观,无数个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像一个个巨大的电风扇排着队转着风叶,颇为壮观。据说这里的大风来了,可以翻天覆地地大闹一场,房屋农具、汽车火车统统被掀翻。这就是被称为“风洲”的原因;而“沙洲”则是一片驼队都走不出去的沙漠,夕阳洒下金晖的时候,整个沙漠高贵了许多,像一个宫殿的墙壁,金灿灿地如此诱人。这里除过沙漠没有其它实实在在的事物存在,铺开的只是一片想象而已。
路过达坂城的时候,透过车窗一直看着公路下面的那个小城,企图看到那个长着美丽的大眼睛姑娘。飞快的车速在几秒钟内驶过达坂城的路段。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辫子又长又粗的美丽的达坂城姑娘。那双美丽的眼睛曾瞭望过天南地北年轻小伙的心事,和那条曾在梦中轻轻地在无数年轻小伙眼前甩过的辫子如今不知安在?
带着对达坂城存有的想象,或者幻想,汽车已经停在了火焰山下。几座普通的山下有一个小型广场,广场的一侧有一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雕塑。孙悟空的手中当然要拿一把芭蕉扇举在空中。温度很高,据说这里的地表温度创下了吉尼斯纪录。今天的温度是四十摄氏度以上。炙热的大地上,让所有的人汗流浃背。我是一个怕热的人,又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尽管很多人找个纳凉的地方呆着,而我还是冒着太阳的暴晒希望毫无保留地欣赏完火焰山的全部景致。无奈这个景点太简单了吧,就是几座山,山下的场地上东西两侧各有一组西游记小说里的故事雕塑。
离开火焰山来到葡萄园,温度明显降低,热是热,人们可以承受了。
葡萄园的葡萄架上挂着一些碎小的绿葡萄,没有一点诱惑力。大家走走停停被带到了一个葡萄干经销商的维吾尔族家中。用维吾尔族语调不会拐弯般地讲着汉语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先是给我们教几句维吾尔族语和扭脖子舞蹈,然后开始推销葡萄干。和内地好多景点的购物点一样,用其它产品跟他的产品作演示作比较,然后说除过他的葡萄干,吃了其它染了色的葡萄干都会患癌症。这也许是一个咒语吧,大家不在乎,很多人开始疯狂抢购。
到了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坎儿井,这里是躲避太阳辐射最好的地儿。古人的智慧和意志在地下水渠中至今绵绵不息地流淌着。
人很多,都是冲着吐鲁番来的,而这些景点也都聚集在吐鲁番周围。天气的炎热没有让拥挤的人群退下去,相反几乎所有的人在户外大汗淋漓地挥洒大半天,迫不及待地钻入坎儿井的水利系统之中,一边看着一边纳凉。
时间排得很紧,没有完全凉快下来就出了坎儿井的地下水渠。又是火热的太阳、拥挤的人群。来到维吾尔古村,这里展示的是维吾尔族民俗、生活的主题公园。我喜欢这个建筑,土木结构的阁楼古朴而简洁。想象一个驿站的风口,这里聚集天下英雄,飞檐走壁之人月色冷清,吹箫披发之人长风呼啸。风起云涌时候,英雄们只是把酒论剑,挥刀杀风。没有血腥,没有嚎叫,这里本就是英雄归隐后,栖息灵魂的地方。
吐鲁番的炙热和拥挤中塞满破坏和搅扰的味道,那是践踏古代文化和遗产的不道德行为。包括我在内的外来者都是喜欢热闹的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不是看景,也不是拾遗,更不是修炼。我们都是这片净土的入侵者,把一个本来有着自然温度和世袭安详的地方搅得凌乱而拥挤。
交河故城,沉没的往事凸显的遗骸
由于历史和地理知识的浅薄,没来到吐鲁番之前我竟不知道交河故城。古城和故城的本质区别是,都是古代留下来的城市,前者指的是到现在还活着的城市,后者指的是到现在已经死了的城市。交河故城显然是死了的城市,留下来的是这个城市的遗骸。
交河故城是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城的两面临河,四周为崖,易守难攻。城墙内纵横交错,临街的住宅都不设门窗。城门有瞭望台,城内有完整的主街相接、巷巷相连的交通网络。这样的设计和建造完全是出于军事需求。交河曾在南北朝和唐朝时候达到鼎盛。4世纪蒙古贵族海都等叛军经过多年的残酷战争,先后攻破高昌和交河。同时蒙古统治者还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传统的佛教信仰改信伊斯兰教。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打击下,交河最终悲惨地谢幕,走完了它生命的历程,退居在历史的风云之外。
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2000多年前交河商贾云集,繁华似锦。这里的屋顶炊烟相绕,城池披金,牛羊成群,人们老少相携,男女勤于持家。一派繁华中的城市远离战火,远离瘟疫,在西域这片辽阔的疆域一角,创造着一个个最终被战火和杀戮以及瘟疫摧毁的往事。
我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想象一个曾有着强烈意识拒绝残酷战争的城池,在和平年代的光景。当一场噩梦般的血腥漫过城池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能够听到的是生命的哀求和此刻的悲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眼神的恐惧和沉重的闭合。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或者是体会到那个末日的生命集体告辞。家园在那一刻难舍中开始荒废,亲人在那一刻与自己同时痛别,那些熟透了的葡萄等不到采下将会被战火烧尽,那些被自己养肥的牛羊被强盗赶走……
犹如幻灯片一帧帧在想象中闪过,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婴儿的脸上沾满血迹,眼睛里流出最后的命运之泪。他没有哭叫没有恐惧没有逃离,他就静静地站在城池的那个土包上,张开双臂欲要接住什么,但是好久好久了手中空空。我看到那滴眼泪始终没有流下来,像一颗夜明珠,挂在她清澈而明亮的黑色眼睛里。
在交河故城官署区旁边是一个大型的墓葬群,这里埋葬着200多个不满两岁的婴儿。对于那些墓葬群的出现至今没有解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婴儿集体安葬于此。有猜测是一场瘟疫导致婴儿集体夭折,也有说是古车师人祭祀供养的需要,更有种说法认为,是战乱中的交河人不堪忍受战败的羞辱,而将自己的孩子全部杀害。种种猜测都是有道理的,而我最希望是交河人不堪羞辱,自己杀害。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城池,以及一个时代的群体,都有他特定的品质和气节。交河人自然无法守住自己的生命之地,就有气节地集体消失在这片故土上,生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园,那就把魂留下来。
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土地,至今滚烫,遍地都是美丽而悲痛的往事,至今鲜活。一个城池的主人走了,而它的遗骸像胡杨一样不会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