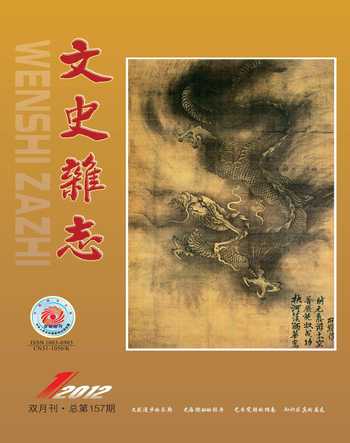鲁迅与李慈铭
那秋生
1912年5月5日,《鲁迅日记》的第一篇这样写着:“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且》一册。”
会稽名士李慈铭即是《越中先贤祠目》的编者,该祠就设在京城绍兴会馆里。此前鲁迅已对李慈铭的书发生了兴趣,并着手越文化的研究,包括乡邦文献与乡贤旧籍。他辑录校勘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历时十余年。确实,鲁迅同李慈铭的渊源较深。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介孚)就是李慈铭的好友,在北京常会于绍兴会馆。同治十年(1871年)他们一起参加会试,结果李下第,周中举。后来周犯了“图谋贿买考官案”而坐死牢。李在上奏中为此案作了侧面的辩解,并为他疏通关系。
李慈铭的博学多才,是以40年积累的《越缦堂日记》作为基础的。鲁迅阅读、收藏了他的《越缦堂日记》,由于颇受影响,也持续写了25年的日记。鲁迅在《马上日记》里写道:“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这是对《越缦堂日记》的内容作了基本概括。说到“相骂”,兴许是绍兴文人的一种传统,是谓:心直笔尖,一吐为快;臧否人物,不留情面。鲁迅的杂文总被说成是“骂人”的,其针砭病弊之犀利,绝不亚于越缦老人。
当然,鲁迅对前辈李慈铭也有过直率的批评:“《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吧?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三闲集·怎么写》)李慈铭的为人曾备受争议,他的内心充满着复杂的矛盾。鲁迅懂得以人为镜,不断纠正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的心总是坦露着的。
李慈铭的骈文功底深厚,具有代表性的如《城西老屋赋》。其中写到:“维西之偏,实为书屋。榜日水香,逸民所目。窗纸迫檐,地窄疑舻。庭广倍之,半割池绿。隔以小桥,杂薛花竹。高柳一株,倚池而覆。予之童骇,踞觚而读。先生言归,兄弟相速。探巢上树,捕鱼入洑。拾砖拟山,激流为瀑。编木叶以作舟,揉条枝而当轴。寻蟋蟀而剀墙,捉流萤以照牍。候邻灶之饭香,共抱书而出塾。”赋中记述了自己童年时的“水香书屋”,对环境的印象,尤其是学童玩耍的趣事,充满了活泼的情趣。联想到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何首乌藤和水莲藤缠络着,水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在时空的跨越中,两颗童心发生了碰撞。
山阴道是绍兴人引以为荣的风光标志,涵有一种深厚难忘的故乡情结。鲁迅在《好的故事》中回忆:“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目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散文的笔调如此优美、舒缓,令人有如入其境之感。李慈铭则以诗词表达自己的深情,如《虞美人》:“扁舟行尽山阴道,曲曲青山抱。几重云树几村庄,但见汀洲无数、入斜阳。松杉遮断来时路,舟载浓阴渡。湖山晴绿满年年,知否落花芳草、怨江南?”曲调缠绵而欢悦,谁能读了而无动于衷呢?
鲁迅念念不忘的是王思任(季重)的那句名言:“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思任又上士英书》)它概括了古越民族那种刚硬正直的精神,被世代传颂。李慈铭曾为王季重的山水画题诗:“画江一檄足锄奸,孤竹庵空鹤不还。”其中的“一檄”正是著名的《思任又上士英书》。
在鲁迅的心目中,李慈铭、周福清这一辈都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书生。他们的灵魂被扭曲,言行烙上了腐朽的印记,经历十分坎坷辛酸。这些后来都成为鲁迅的创作素材,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出现了“孔乙己”(《孔乙己》)与“陈士成”(《白光》)之类的人物。比如,李慈铭参加过十一次科举考试,而陈士成“屈指计数着想,十一,十三,连今年是十六回”。
1936年10月3日,鲁迅临终之前的一篇日记里又提到了李慈铭:“夜三弟来并为买得《越缦堂日记补》一部十三本,八元一角。”《鲁迅日记》的一头一尾遥相默契。这样的巧合难道不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