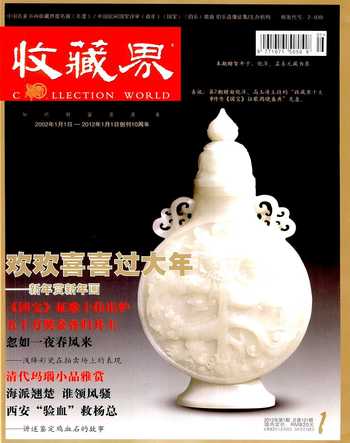石鲁传奇
阎正


(接上期)
“春卷风云月色哀”
石鲁不堪忍受那非人的待遇,他从“牛棚”里曾两次出逃在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深更半夜,石鲁悄悄起身了。他顺着马路边沿溜出了南门,走到了那个当年千里辗转来西安与乔某吃羊肉泡馍的地方。
时过境迁,弹指二十年了,但西安南门一带的变化仍不算太大,他走进那个改革扩张了一些的羊肉泡馍店。好长日子没吃过一顿饱饭了,但根据他自身的情况,也只能瞅着那热气升腾的羊肉汤锅,狠狠地咽一口涎水。
棚内守夜的小店员,迷迷糊糊地听到响动,发现有人站在了汤锅面前,赶忙迎过来说:“同志,来碗泡馍吗?”
“同志”这个词汇对于石鲁早已陌生,尽管它是那样随随便便地被一个小店员喊了出来,然石鲁却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这就是说人家没有把他当做“牛鬼蛇神”,没有把他当做“专政对象”,而是作为“同志”、作为“人”看待了!他激动地脱口答道:“来一碗羊肉汤。”
店员又问:“要几个馍?”
“不,不要馍,只要一碗汤,多放点辣子!”
店员熟练地操勺端碗,盛了满满一大碗羊肉汤,又特意多撇了一勺羊油,浇上辣子端了出来。
石鲁对着这美味扑鼻的汤碗,搅了两下,汤成了通红通红的颜色。他不再犹豫,风扫残云,一口气便喝下了肚,碗里的热气移到了他的头上,他浑身暖和多了。
他喝完了汤,坐在那里不走。
小店员试探着问:“再来一碗吗,同志?”
“够了,不要了。”
石鲁既不离开板凳,又没有付钱的意思,小店员不便催问,两人隔着灶台不言语地相持着。
好半天石鲁才吞吞吐吐地说:“小同志,我……忘了带钱,你看……”
店员更迷糊了,他还没经过这种事,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样吧!”石鲁摘下身上的一只钢笔说:“我把这笔押到这好了!”
店员缓过了劲,他看出这不是个骗饭吃的人,马上说道:“不用不用,押东西丢了不好,你明天有空把钱送来就行了!”
这小店员显然是个忠厚的年轻人,他心里想:羊肉汤多一碗少一碗没什么打紧,怎么能押人家一支钢笔呢。
石鲁心里也在想:明天还不知到什么地方,怎么能白吃人家一碗羊肉汤。虽只有三毛钱,也不能这样,良心上过不去啊。他不再说什么,轻轻地把钢笔放在汤碗边上,扭头走了。
离开了市区,路上的灯光稀薄起来,渐渐地全然没有了。一片黑黝黝的天地,把石鲁裹在了当中,他停住脚步,四下漫无目标地看了看,两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凄凄惨惨地蹲靠在路边不知修什么工程遗弃下的石灰管筒上,僵直的眼睛望着天空疏落的几颗星星。他觉得自己真成了那个走投无路的杨白劳:“我往哪里走?我往哪里逃?哪里有我路一条!”他能往哪里走啊?
回四川,回老家去!永远隐匿起来,忘掉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忘掉他!主意既定,石鲁站起身来,径直向南迈动起脚步……
人世的浮沉变幻是多么不可预料,三十年前,他背叛家庭孤身从四川走着这条路奔上了延安,如今,地球在绕着太阳转过了三十个整圈之后,他带着“反革命罪人”的烙印又从原路返了回去!是谁做了这可恶又巧妙的安排?是命运吗?是上帝吗?老一辈曾说:人到世间来之前,上帝把一幕一幕的场次早都安排好了,每个人只不过按各自扮演的角色,在人间走一遭罢了,这是真的吗?他朦胧出山,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整整三十个春秋,喜剧出场,悲剧结尾!原路逃出,原路逃回。难道这是早安排好了叫他演吗?他凝望着似曾熟识又异常模糊的老路,泪水伴着凛凛寒风,洒在了他的面颊和苍鬓胡须上……倥偬中,他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一首老诗:
未生我时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乐去时悲。
他摇了摇头,不!这怎么就真到了收场的时候?即便是“命运”如此,那也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拼一拼,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完结。人既然来世上一回不容易,那就要顽强地活下去!挣扎!扭转这命运的摆布,变换一个别样的结尾!
他踉踉跄跄又移出了向南的步子,人的精神可谓神奇,只要有了这个支柱,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力量。他走啊!走啊!一位步履艰难的老人,一夜间竟量出了五十里地。
晓星残月,东方泛白了。那碗羊肉汤的热量早已消耗殆尽。他渐渐受不住寒冷的袭击,越走越觉得饥肠辘辘,旷天野地,一棒棒玉米绣出了穗穗。摘一棒吧!人总不能守着可以吃的东西饿死、冻死啊!他钻进了玉米地,挑了一穗“窝米”,就是那种害了病不再结籽的玉米棒棒,饥不择食,三嘴两口就吃完了。他再找就找不到这黑窝米,只好又掰下了一个嫩棒,啃了个精光,嫩棒子的芯也是嫩的,他连棒芯也干脆吃完。顶住了饥,他便不忍心再去掰,老百姓种庄稼够难的了,糟蹋不得啊!他用手抹了抹沾在胡子上的棒穗和窝米黑灰,钻出了地头。但刚走了几步,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回去,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又摸出半截铅笔,趁着蒙蒙亮的晨光,在膝盖上面写了个条子,某月某日,路过吃了两棒玉米。署他的姓名,以后再来还钱。他谨慎地用草棍把纸条挂在被掰掉棒子的玉米叶上,才一走一望地寂然离去。
三天之后,他风餐露宿走进了秦岭山区。
旭日冉冉,透出山巅,一抹红金色彩罩住了秦岭的苍莽山峰,深谷险壑,云蒸霞蔚,万物浴金,紫气升腾。石鲁的眼前明亮起来,呵……无言的大自然仍是这样美!他收住脚步,顺手折断一根灌木枯枝拄在手中,抬眼向高远处环视。就在他目光所及的右前方,他发现山峰半腰间怒放着一丛丛五颜六色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野花经受过太阳光的沐浴,闪耀出一种神奇玄奥不可言云的臻妙光芒。这一丛丛在萧瑟秋风中袅娜摇动的野花,把山谷反衬得更加深沉,把一线天空映得更蓝。它千姿百态,开得那样自由自在,那样神采奕奕:石鲁愈是定眼仰视,它愈是如通人性似地摇舞得洋洋得意,愈显其娇容可掬,高隔数十丈,犹觉闻流香……
这超凡脱俗的大野之美,使石鲁忘乎所以,一霎时,他只觉得香来、情来、兴来、神来。他捉石代笔,凿岩当纸。他要抓住这即兴灵感,抓住这第一印象,就在山岩绝壁上,留下一幅与山河共存的永恒之作。
朝阳山花寻常物,借来都作绝妙词。
他全然忘了他是一名被人追捕的“逃犯”,他全然忘了他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住处……没有一切。他只有孑身一人,孤立无援的一个人哪!但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画家。此刻他只想到要画,要画一幅他渴望马上动手的真正“壁画”,其他仿佛都是与他无关的身外之事了!
他找来了几块尖硬的石头,选好一面比较平坦又能够得着的石壁,开始如痴如醉、浮想联翩地构思了,这哪里是寻常的闲花野草?这是“缪斯”在“独托幽岩展素心”,神使在借花喻意,启示他呀!他很快构思好一幅“秦岭山花图”。想好就干,他双手握石,在岩壁上推刻起来。……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不乏有石岩壁画的出现,然那都是众多画工石匠们用凿、用锤、用钎、用钻,用钢铁之器切割下石屑石块!哪里有用石头对石头凿刻壁画的呢?如果说有,也就是上古时代原始人的作为了。想来可笑,当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在中国秦岭山中竟有一位伟大画家在重复着原始人的劳动,退到了新石器时代,而这位画家又是一个多病的老者,缉拿逃犯!噫嘻,可悲可叹!可歌可泣!
整整一个上午,他面壁挥石无休止地凿刻着。饭虽没有,山谷里各种各样的野果却不少,趁歇息的时候,他摘了满满两大兜,也不管能吃不能吃,只要少添加一点可以新陈代谢的东西,他就又能借此维持生存!难怪人被称为万物之灵长呢!
坐地日行八万里。石鲁苦斗于岩壁下过完了一天,夜幕低垂,苍天也可怜他的辛劳,逼迫他必须休息。他摸着已经看不清的壁画,才感到困倦极了!一天没喝一口水,嘴被野果的苦涩弄得发麻发木,也该找口水喝了。
他拾级而上,总算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山洞边找到了一洼泉水。他捧起冰冷的水灌了一肚子,又捎带洗了洗多日未曾洗过的手脸。他庆幸找水意外发现了山洞,这几日既要在此处作画,总算有了一个栖息之处。说这是山洞,未免夸大其词了,实际这是一个较宽的山缝,缝底找不出一席平坦地面,虽有些潮湿,却足以坐卧。他头稍歪斜,横身一躺,很快入睡了。
说不清睡过多长时间,他又被冻醒了。一阵阵寒风扑向他单薄的衣服和身体,他萎缩一团,牙关紧咬,却禁不住浑身颤栗。他困得要命,却无法再能安睡,他只好坐等天明。
风声里卷进了凄厉的狼嚎,死一般的山谷之夜,这嚎叫传得很远,使人听来毛骨悚然。石鲁并非害怕,只是天冷心寒。倘若这野狼真钻到洞里,他很难再有抵御的能力,好在这声音随风而去,渐渐微弱而后消失了。
又是一个黎明,当勤劳的庄稼人还在梦乡的时候,石鲁已在昨日的岩壁下干了好大一晌了。他要用这劳动驱散风寒,他要尽快完成他的作品……奇迹往往在不可想象的情况下产生了,几天后,于晨曦中,他刻完了画上最后的题字: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之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石鲁刻范仲淹《岳阳楼记》摘句”
他扔掉了手中的尖石,拍了拍身上的石粉,后退十几步,认真审视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朗朗大笑,凌晨的山谷被他豪放的笑声震得八处回音,鸟儿也被惊醒,飞凌山顶上下盘旋……
“真是一个幽静的创作环境,整整三天竟无人打搅!”石鲁自言自语地说着,又扫了他的杰作一眼,随即转身走去,再不回头。
越过了秦岭,庄户人家又多了起来。
石鲁已经多日不沾米面,再加上在岩壁下的日夜辛苦,使得他衣衫褴褛,瘦骨嶙峋。他怕招惹麻烦,只好避开村庄绕道而行。
他走至一个山坡岔口,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石龛。这石龛洞原来大概是放土地爷之类神位的,如今却在里面敬上了一尊金身的毛主席塑像。石鲁定住不动,他的思想抛了锚。早先他听人说,华山的几十座庙宇,玉泉院、青坷坪、南岳山四万多尊佛像,只几天功夫就被荡平,有些几丈高的铁佛铜像,一般方法砸不碎,就专门带着大锤、錾子、焊枪、炸药等现代化工具向佛像开战。和尚造反队“反戈一击”,深知底细,砸得更是彻底。恐怕就是那短短的时日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数百万佛神之像都同遭劫难,寿终正寝了。
不料,法轮常转,人们打掉了旧神又造出了新神。可怜的盲目,浮浅的信仰,善良到了愚昧的地步。八亿人民高唱着:“不靠神仙、皇帝”的《国际歌》,难道是为了进行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吗?
石鲁百思不得其解,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上坡来,旁若无人地虔诚地在石龛前跪下,点燃了一炷香,口中念念有词,但绝不是“老三篇”,谁知是念得哪一本经?她心里虽然有一尊佛,精神的堕落更甚于良知的泯灭。
“把塑像放在这种地方,真是糟蹋领袖!”石鲁忿忿地喊出了声。
老太太闻声扭过头,看到路旁站着的石鲁,吓了一跳!惶惶起身要走。
石鲁从失态中恢复过来,紧两步赶上了老太太说:“大娘,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老太太惶惑地答道:“红卫公社。”
“我问这个村子!”石鲁指了指前面。
“噢,噢!那是我们胜利大队。”
老天爷!谁知这红卫公社胜利大队究竟是哪里?几年功夫,新旧更换,村庄、学校、工厂,饭店以至刚生下的孩子……邮递员怎么投递,邮电部长怎么当啊?
石鲁现出一丝苦笑:我才是多余操这份闲心。他不再乱想,随走随与老太太拉起家常,不几个回合,他就摸清了事情的缘委—老太太的儿子有病。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难得去趟医院,赤脚医生也归属“革委会”的头头们私人所有,哪轮得着给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看病啊!
石鲁悄悄说:“我学了几手医道,叫我给您儿子看看行不行?”
“那感情好!”老太太露出了笑容,他求“神”保佑也是万般无奈,听到石鲁的话,她自然非常高兴。
石鲁随着老太太走进她的家。这是两间离村子还有半里路的一个斜坡上搭起的草房。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窗户,简直等于没有,屋里床铺、灶火、柴堆、狗窝都挤在一起,泥抹的墙长年被烟熏,分不出个子丑寅卯,猛一进到屋里,就像进入了黑夜。
“解放二十年了,我们的农民还过着这样苦的生活!”石鲁皱起了眉头。
老太太赶忙抓过一个高树墩,用袖子擦了擦递过来说:“同志,你请坐。”
这就是她家唯一的高凳子了。
石鲁坐下,凑到小床跟前,看了看躺在床上的老太太的儿子。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像石鲁一样瘦,面带菜色。石鲁号了号脉,回头对老太太说:“不打紧,是着凉感冒。”
老太太焦心地说:“躺在床上十几天了呢。”
“不妨事不妨事,主要是身子虚,扎两针就会好的。”
石鲁拿出了针头,跟吴大觉学的本事想不到在这外逃途中用上了。他三两针下去,病人全身抖动,顷刻间出了汗。
半个时辰,针灸完毕。老太太做的两碗饸饹也端了过来,先给石鲁一碗,又给儿子一碗。
“哇!饸饹,太好了!”石鲁喜形于色,他终于见到粮食了。
“真对不起你,我们庄户人家,长年也见不到一星白面。”老太太抱歉地絮叨着。
“我的肠胃受不得好东西,只爱吃饸饹!”
“你这个人可真会说话,哪有不待见精米白面、爱吃高粱面的。”“不不!我说的是实心话。”石鲁一边应酬,一边急促地吸溜起来,他真要饿晕了。
吃到一半,他从碗底搅出了两个荷包蛋,他斜眼看看另一碗,一个也没有。他移碗过去,把两个全拨到病人的碗里。老太太慌慌拦阻,石鲁已经笑着走过来:“大娘,再给添点汤吧!”
老太太接过碗说:“汤有,饹饹也有,只是……”
石鲁说:“鸡蛋应该病人吃,我不喜欢那东西。”
他猜想得到,这样的家庭,荷包两个鸡蛋,给予他已经是上宾招待了,而这两个金贵的鸡蛋对于老太太来说,能换火柴,能换盐或者一点酱油醋什么的,可以办好多事情,他饿死也不忍心去吃它!何况已经有了胜似山珍海味的饹饹。
老太太重新盛了满满一碗递给石鲁,难得有泪的老眼红了。
石鲁没有勇气再去看那老人凄楚感激的眼神,他低着头只管吃,第一碗吃得太快,丝毫没有品出味来,第二碗他细嚼烂咽,越发感到饹饹的香甜。
吃罢饭,石鲁谢过老人起身要走。老太太才想起来问他:“同志,你这是要上哪?”
“我也说不清,走哪算哪吧!”石鲁说。
真要感激这位不关心“政治”的老人,她既不问石鲁的来历,也不管他究竟是什么人。当然她有她的标准,她认定石鲁不是个坏人。
“反正就我们娘俩,你要不嫌弃,就在这歇两日吧!”老太太劝道。
石鲁扭头看看床上的病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也好,等你儿子下床了我再走。”
老太太一听就忙着要收拾床铺,石鲁一把拦住:“大娘,我就在这柴堆上睡,给条被子连铺代盖就行了。”
老人还要坚持,石鲁执拗地说:“你要不同意,我就不在这里住了。”
碰到了固执人,老人也不再退让,便从那陈年老箱子里抱出了一床粗布被子,里外都是拆洗过的,石鲁感激不尽地接到手,整平了柴堆,老人拉过一张破席,石鲁将被子铺了上去……
一晃,石鲁在老人家住满五天,小伙子果然下床了。
每日里,他按时给小伙子针灸,陪着老人聊天,和这普普通通的一户农民处成了一家人。老太太把他当成神仙,不再喊他“同志”,喊开他“先生”了,并且还给他介绍了几个病人,请他看病。石鲁乐而为之,竟也真充起了行医的“先生”。
平静的日子里,时间已过得飞快,不知不觉石鲁行医已拖了将近一个月。他几回要走都走不脱,老百姓们把他当作救命菩萨,与他已经是难舍难分,死活不让走,他也只好一留再留。
劫数未尽,灾难又一次临到他头上。
那时正好台湾向大陆派出了几批武装特务,公安部门向各地发出通知,提高警惕,严防破坏!于是乎马上就有“请功者”将石鲁告了密。
这也怨不得那告密者,石鲁的模样、装束、举动,实在令人可疑。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一身少见的服装打扮,跑到这大深山来行医,又不要报酬,真怪!不是美蒋特务是什么?
公安部门的行动一向是兵贵神速,等着石鲁意识到危险准备逃跑的时候,摩托车载来的公安战士已经把斜坡草房围了起来。
老太太看着一支支对准石鲁的枪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惊恐地望望石鲁,想说又说不出一句话,石鲁走到她跟前,静静地说:“老人家,我不是美蒋特务,你别害怕。”
石鲁被戴上手铐,押送进县公安局,到了这个地方,他不得不申明自己的身份了。
长途电话当即挂通,西安正在到处通缉他,专政队马上跟踪而来,见面就是一顿毒打!他们打得连公安人员都看不过去了,一位审讯的同志正色道:“他有多大罪判他多大刑,这样打法太过份了!”
一个家伙气咻咻地说:“这老东西跑了不打紧,可苦了我们到处找,不打他太便宜他!”
那公安拂袖站起:“要打带回去打,谁打死谁负责!”
几个家伙把石鲁背铐铐上,怒气冲冲地押回了西安。
这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了!石鲁遭到更加残忍的报复!他们把石鲁吊起来死命地抽打!一声赛似一声地逼问石鲁还跑不跑?石鲁看着这些畜生们,不再讲一句应该对人说的话……
过了好些日子,石鲁的伤渐渐又有了好转,他被罚去做苦役。石鲁强支撑着身体忍受煎熬,还是一个夜晚,石鲁趁他们防范疏忽,又一次跑了出来。
此时天气已进入深秋,寒气更浓了,凌晨,石鲁急不择路逃到了草滩农场。他又累又饿,地里的玉米早已收割干净,连玉米杆也吃不到了。他只好在野草地里挑灰灰菜拔下充饥,他需要吃东西,无论什么都行,连草带土他都塞到了嘴里。他身体里缺少的食物太多太多,他急到顾不得再一点点挑拣。然而野菜野草总不能当饭哪!他要找点能填住肠胃的东西,天无绝人之路,他终于找到一块红薯地,慌忙用手抓刨,手指磨出了血,他不管,他一定要找到吃的,不然饥寒交迫,他多病之身非死不可!最后,他总算刨出了半半截截的七八疙瘩红薯。他掏出手绢,正要找个背风的地方去吃,突然,他的背后被人踩上了一只脚。他猛地一惊,心想完了,这次抓回去就别想再活了。没等他多想,这背后一脚抬起,把他踢翻了。他不再动,也不睁眼,等着皮鞭棍棒一起下来,今天就死在这算了,他的苦难也该到头了……
不料,他迟迟等着反倒没有了动静。他慢慢睁开眼睛,却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面对面地琢磨他,石鲁见不是专政队,顿时又有了生的欲望。
“你是干什么的?跑到地里干嘛?”那青年人问。
“过路的,肚子饿了找点吃的。”石鲁答道。
“过路的?我咋看你不像好人,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地吗?”
石鲁笑着说:“不知道,但我不是坏人,我吃你们这几块红薯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取钱好不好?”
“到哪取钱?”
“我现在就写。”石鲁说着掏出了自来水毛笔写道:
“见来人请付给人民币拾元。
西安北大街32号找闵力生。
石鲁。”
那年轻人接过条子哼了一声:“扯他妈蛋,拿这烂条子,想把老子诓到市里白跑一趟?”
石鲁仍然带着笑说:“小同志,我不会诓人的,你就按这个地址去找这个人,她会给你钱的!“
“好罢,老子放了你,你要敢骗我,下次碰着别怪不客气!滚!”他朝着石鲁又是一脚。
石鲁的微笑成了苦笑,这单纯天真的年轻人,竟像是从一个学校毕业的,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都变了形。然石鲁对他们总像是看待孩子一样,他坐地上还补了一句:“你去试试吧!”
说不清这年轻人是怎么想的,也许他想知道这个被他踢了两脚的人家里是个什么样?也许他想碰碰运气,一张条子,白赚十块钱,也许他就是想去城里玩玩。总之,他真地跑到北大街去试试了。
闵力生一见条子,急切地问:“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在草滩农场。”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他一看这破房子,心里凉了半截,暗想白给这老家伙送了个信,十块钱没影了,反正踢他两脚,又逛逛钟楼也划得来。
“他还在那儿吗?”闵力生火烧火燎。
“我他妈哪知道?喂,给钱哪!”他提醒对方一下,能敲,就敲一下,不给就拔腿,他不准备在这多罗嗦。
“对对,你看我忘了,给,给你!”闵力生马上从屋里取出来十元钱。
这一下小伙子傻了眼,他没想到那老头真没骗他,见钱眼开,他马上热情起来,又是介绍情况,又要充作向导,闵力生抓起衣服跟着他走出家门,直奔草滩农场。
石鲁早已无影无踪,闵力生哭天无泪,这时上边已经有消息要解放石鲁了,“你为什么还要跑啊!”闵力生忍不住哭了起来……
几天以后,石鲁被三百里外的一个公社派人送回西安,原来他连续奔跑,终因又冻又饿,昏倒在半山坡上,幸亏被放羊的老汉发现背回,才捡了一条性命。
时来运转,石鲁的前面似乎又露出了生机。
……
据说那年轻人后来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他的朋友,偏偏这其中有一个知道石鲁,人家看着他得便宜卖乖的样子,忍不住说:“你觉得一个条子换了十块钱,怪高兴,其实你是傻蛋!那人是石鲁,知道吗?石鲁啊!他一幅字到口岸可卖几千块钱,你可倒好,十块钱就扔出去了!”
“真的?”年轻人的眼睛瞪成了电灯泡。
“我骗你干嘛?不信你去问问文化馆,要是我就留着,再过几十年就变成了文物,更值钱了。”那朋友故意这样讲,好让他更加后悔。
年轻人果真跑到文化馆去问,看来那朋友说得不假,他当天下午就又带着十元钱去找石鲁夫人闵力生,想用这十元钱把那张字条换回来。
“我留那没用,撕掉了!”闵力生说。
年轻人拿着这张又烫又羞愧的人民币,这回真该他后悔了!(未完待续)
(责编:魏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