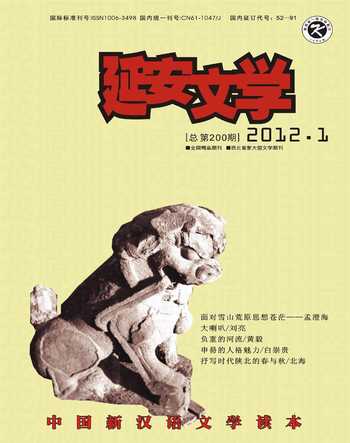小小说茶馆
竹剑飞 王丽 高涛 东壁逸人
最后一天
竹剑飞
这些天,王川被那些存款指标搞晕了,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怕自己存款数下滑,被单位淘汰。今天是星期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存款指标的最后一天期限。眼看只剩最后一天了,王川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妻子张英在房间跑前跑后忙碌着。王川忽然想起妻子有个同学的老公似乎是大老板,就说,你那个同学的老公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帮忙?老婆介绍过,她同学的老公是老板,原先曾说要给王川帮忙的。张英说,我前两天打电话问过了,他说再说。
就在这时,王川的手机响了,电话却是钱行长打来的。他问王川:你在那儿?王川听到这种威严的口气不由自主地说:在家里。钱行长大声说,我都在上班,而你却在家里休息,像话吗?你这个月的任务呢?今天是几号?他一口气说出很多问题,像机关枪扫射似的,王川一下子就被击倒了。钱行长又说,你快跑出去揽存款,现在行里很多员工都放弃休息,在想尽一切办法哩。
王川揽存款,不是不努力,他曾经想了许多法儿。就在前天,他为一个客户办好业务,提出能不能存一些钱。那个客户戴着一副眼镜,样子倒挺斯文,一边笑着说,有什么好处?一边就当场拿出二十万存进银行,而且还是一个定期。数目虽不大,但王川还是十分感激。这个斯文青年将钱存好后,却并没有离开,而是看着王川。王川马上拿出为客户准备好的纪念品,但“眼镜”摇头拒绝了。王川想来想去,唉,算我少拿奖金吧。就从衣袋里拿出一张消费卡,说,一点点,小意思。但“眼镜”还是没有接,似乎还在等待。王川急了,这怎么办呢?最后他只得从钱包里拿出人民币给了他。这下“眼镜”才高兴了,拿了钱就走,连招呼都不打。这算什么事嘛。
张英看着自个男人接电话时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就拿出手机主动给老公的同学打起电话来。
张英打电话过去,马上接通,好像胡老板正在等她。张英说,胡老板吗?对方说,妹子啊,我想你,上次见面后你就一直不理我,很伤心啊。张英拿手机的手微微颤抖,是不是喝醉酒了?张英看了一眼王川,还好,王川还在专心打他的电话。张英悄悄走进卧室,将门虚掩,对胡老板说,上次说起过的存款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胡老板很爽快,说,行,你来吧。听口气胡老板已经准备好了似的。张英又问,是现在吗?胡老板说,当然,你不是很急吗?过了今天还有用吗?张英说,是啊,是很急,最后一天了。不过今天能来得及?胡老板说,我给妹子时刻准备着,办完后我请你吃饭。张英忙说,不好意思,应该我请你吃饭。胡老板说,哪能叫女同志请客,你寒碜我?张英忙纠正,说,不是的,我和老公一起请你们俩吃饭。胡老板说,我老婆旅游去了,就我一个人。一霎那,胡老板声音变得淡了,也冷了。张英听得出,胡老板不欢迎王川,上次见面时他就说过,王川是窝囊废一个。
这时,王川走了进来,一脸茫然,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看得出,日子不好过。张英慌乱地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到,便挂了电话。
张英对王川说,胡老板答应了,为你存进二百万元钱,够不够?王川说,够了,能完成任务。好吧,张英说,我现在就去。王川问,我去吗?张英说,不用,我会办好的。张英没有说胡老板不想让他去。
张英扫视四周,嗨,这个星期日,全搅了。又对王川说,剩下的活你接着干。
王川没有动,看着张英化妆打扮准备出门。张英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换了一个人似的,容光焕发,像一只熟透了的柿子。
张英说,你看着我干吗?你干你的。王川此刻心里像打翻的五味瓶,却没办法阻止。张英换了一双高跟鞋,人顿时长了一大截。临出门时他又看了王川一眼,似乎有心事,说,你不用等我,晚饭我不回家吃。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头说,你也不用打电话催我。说完,她扭动臀部,款款走出去了。坐着的王川看着老婆走了,眼珠子都要射出来,却没一点办法,十分无奈。
老婆走了,家里一下子静了,静得让人心慌。王川安慰自己,胡老板的老婆也在,她还是张英的同学。王川拖地板,擦玻璃窗,自己弄晚饭吃。王川忙完了家务活,终于又可以躺在沙发里。打开电视,心却空落落,好像掉了什么似的。茶几上放着一杯绿茶,是新沏的,王川放了很多茶叶,他要提神。
频道换了又换,就是找不到想看的内容,连平时喜欢看的和老婆抢着看的都不喜欢,乏味,像放了人工色素。王川拿起手机看了看,想给张英打电话,可张英关照过不要打电话催,不要发短信。王川放下手机,只好继续看电视。
王川有点迷糊,但还能挺住,一定要等到老婆回家才能睡,这样放心,否则宁愿躺在沙发里等天亮。王川想,存款肯定办好了,揽进银行。钱行长一定会很高兴,咱银行比其他银行存款余额要多。钱行长也看到王川揽进的存款,说他有能耐,在这么短时间内揽进二百万元钱……
王川笑了,却笑得十分模糊,像他看的电视节目一样,越来越模糊。屏幕上显示时间是23时59分59秒。
李四儿其人
王 丽
李四儿者,李老汉的第四个儿子。李老汉一辈子粗枝大叶,就连给孩子起名字也是大而化之。当李四儿作为第四个儿子出生后,老汉眼瞅着又是一个带把的,皱着眉头吧嗒了两下烟嘴不耐烦地丢给老伴一句话,就叫四儿吧。于是乎,李四儿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四儿虽为李老汉嫡亲儿子,性格却与父亲截然相反,凡事认真较劲,加上读过一些书,虽然因为经济的原因,学业中途而废,但书呆子劲儿却保留下来。
那些年的村民,农闲时间常常会趁着午饭后或晚饭前后的时间,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凑在一个方便的场所打打麻将玩玩扑克。因为当时大家的手头都不宽绰,一根烟或者一颗糖都可以成为赌注。一个人赢了,全场人都有烟抽有糖吃,既消遣了时间,又丰富了生活。但后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有人开始觉得赌注太小,渐渐地用零钱来代替其它物品,再后来,零钱被更大的赌注代替。一圈麻将下来,输赢竟然在一百元左右。玩麻将从开始的消遣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赌博。村里那些个爱玩的人,逐渐沉迷于麻将桌,就连一些从来不玩的人,也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参与了进来,村里的赌博者从开始的几个上升到几十个。眼看着到了阳春三月的天气,这些人既不上山务农,又不出去打工。整日整日地聚集在村口老光棍家里吆五喝六地玩通天。
在一个毫无异常的下午,三个便衣警察从天而降,将几个正在麻将桌上的赌徒抓了个正着。那些从来不知道派出所门在哪个方向的赌徒们面对明晃晃的手铐,吓得面如土色六神无主。那次行动,除没收现场的五百多元赌资外,还每人罚款二百元。
村民的思想真是奇怪,平日里对赌博人厌恶得要死,等看到同住一个村,不是沾亲就是带故,不是同族就是邻居的村民受罚,心里却又感觉到不受用起来。大家私下里琢磨警察是怎么知道的消息?最后一致认为是四儿所为,因为四儿有“前科”。
那是发生在九十年代末的事情。村里有两个从内蒙打工回来的人,带回了一样奇缺的东西——花籽,但他们都不说那究竟是什么花籽。更奇怪的是,他们竟然将这些花籽和西红柿玉米之类的植物混杂种植在一起。从春到夏,花儿渐渐长大开花,那花鲜艳非凡,但是有上了年纪的人看着那些花就开始交头接耳,慢慢地,村里的人都知道了那花原来就是罂粟花,虽然花色艳丽,却是毒品的一种,是国家禁种作物之一。
知道了这些外来之物的神秘,村民除了偷偷议论议论没有人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一个偏僻乡村,山高皇帝远的,即便国家禁种又如何?听老人们讲,那东西对头痛脑热之类的小病有相当好的疗效,说不定哪天自己也有用着的时候。还有些脑筋活泛的人,甚至开始打这东西的主意。
但让大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就在罂粟花刚刚结壳尚未成熟的时候,几个警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直接走进了罂粟花的种植地。当然,除了正值长势喜人的罂粟花保不住外,处罚更是难免的。这事在村里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村民们就开始犯嘀咕,这罂粟花虽然是毒品,但种在很隐蔽的地方,既不污染空气又不骚扰四邻,怎么就引来了警察?如果不是有人告发,哪有这样蹊跷的事儿?于是,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时间,村民就一直议论这个话题。最后终于有人指认是四儿告发的。因为有人曾看见四儿从镇派出所大门里出入过。
这个四儿,接二连三地干这些在村民们看来很龌龊很卑鄙的勾当,他在村里的威信就坏了下来。村民们在他跟前走过的时候从不给他一个正脸,就连大人教育爱告状的小孩子也是这样说,“你可别学得像四儿一样讨人厌啊。”因为陕北方言中四儿跟事儿读音相似,而且在大家的感觉中,这四儿也实在太好事了,于是村里几个捣蛋鬼私下里给他更改了名字,从此四儿就成了事儿。
四儿成了事儿,四儿很无所谓。但他那个一贯直爽的老爹受不了了。几次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这个不成气的东西,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难道不告发人你就活不成了?对着老爹的痛骂,四儿只是一声不吭地蹲在墙角,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些谁也看不懂的东西。
话说政府开始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也就是把土质肥沃地势较好的土地留下来种植农作物,把一些土质不好地形偏远的土地用来植树种草。这对于村民是再好不过的耕种安排,而更让村民兴奋的是,上面还将按照植树的面积在年底给每家每户一定的现金补贴。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啧啧称奇,说真是千年不遇的好政策让我们赶上了。
然而让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从年头盼到年尾的枣树补贴竟然连一分也没看到。有几个胆子大些的村民鼓动村长到乡里跟乡长洽谈了几回,最后才象征性地给每户分发了一点钱。乡长在这几个人面前一再强调,是因为县上没有给乡上拨下来款,才导致村民领不到补贴,就连现在这点钱也是乡上从其它资金里挤出来的。乡长说到情绪激动时竟然拍了桌子,村长和几个村民被乡长感动了,他们回到村里后马上组织村民大会。村长在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感谢乡政府,现在这些钱都是人家乡长从其它地方挤出来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村民们个个点头称是,唯有四儿站在村民们中间没吭声。
村民大会后的第二天,四儿就搭了一辆拉木料的四轮上了县城。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就连他媳妇也不知道。
四儿离开的日子,除了老爹和媳妇一天天翘首等待外,没人关心他的去向。这个四儿,除了时不时给村民捅个不大不小的篓子外,太不起眼了,村民们完全可以忽略他的存在。
但四儿终究是四儿,他在沉寂了半个月之后,突然回村了,而且带来了县上的工作组,他们是专门针对村里的枣树补贴款而来的。经过调查核实,原来是乡上扣了县上补给村民的款项。工作组的介入,不仅将属于村民们的补贴一分不少地发到手上,而且将乡长等相关责任者都做了处理。
从此,事儿又变成了四儿。更有年纪小辈分小的人,开始喊四儿为“四哥”“四叔”之类的。听着这些称呼,四儿生平第一次涨红了脸。
举 报
高 涛
收到办公室梁主任的退休报告后,局长心里有些犯难。梁主任还有三个月就到退休的坎了,按说办公室王副主任递补上去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可是王副主任的年龄明显偏大,他只比梁主任小不到两岁,一个属马,一个属猴。“猴子”就是上去,屁股还没来得及暖热又得腾板凳。同一办公室的杨干事年轻,也就三十出头,笔头子的功夫也要在两个老主任之上,可处理一些复杂事情,特别是一些棘手的事情不如两个老家伙老成圆滑。杨干事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王副主任只在地区师范学校读过两年中专。王副主任惟领导命令是从,从不越雷池半寸,领导说西他绝不说东,可杨干事就不一样了,他有自己的个性,举个例子,他下巴上老蓄着一撮胡须,领导看不顺眼,说,好端端的,非弄得跟日本鬼子似的?甚至要他把那撮刺眼的毛剃掉,他呵呵一笑,可依然故我。
用谁不用谁局长一下子难定夺。和班子成员私下沟通,一半说这个好,另一半说那一个也不错。最后就把球踢给职工,让职工推荐,结果两个人得票一样。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局长收到两封信。一封是王副主任写的公开信,一封是匿名信。王副主任在信中极力推荐杨干事,说杨干事年轻能干,学历又高,脑子又活,还说自己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还表态说请局领导放心,他一定会摆正姿态好好配合杨干事的工作,在位一天干好一天,发挥一个老同志的余热。另一封没有署名,说王副主任工作虽说认真负责,处事得体,工作经验丰富,可毕竟“廉颇老矣”,就算是夕阳,也没几天红头了。而且身体长年有病,一直依靠心脏起搏器支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都没有了,还拿啥革命?还说如果王副主任扶正,随时都有可能倒在工作岗位,导致单位正常工作中断。
在班子行政会上,局长把两封信读给大家。他握着信纸的手颤抖着说:“同志们看看,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把单位的事当做自家的事,一个却阴暗下流,暗箭伤人,背地里搞些见不得人的把戏。同志们设身处地地想想,一个为了工作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人,在如今的社会里打着灯笼能找见吗?!”
三个月后,王副主任顺利接替了梁主任的班。
大家在私下有两种议论,“别看姓杨的那小子人模人样的,背地里尽玩阴的。”可也有人说:“王副主任就是王副主任,生姜还是老的辣啊!”
半年后,局长猝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局长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安装了心脏起搏器。
和乡下老娘说低碳
东壁逸人
星期天,我一家三口,骑上多年闲置的自行车,向五十多里外的老家驰去。
和往常一样,娘早早站在村口等我们了。今天的轻车从简并没提前到家,而是比从前推迟了好长时间。等了一脸疲惫的娘,看到我们因劳累而成的狼狈相,嘴在那里张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说出话。
我急忙上前握住娘的手:娘,您怎么啦,咋说……说不出话呢。
你,你犯啥事儿啦?娘惊恐地问。
没有呀,俺都好好的呀。娘,有啥事儿您慢慢说。妻劝慰道。
没犯事儿,这长天老日头的,咋骑着洋车子(自行车)回来啦。
我一听,知道了原因。就笑着对娘说:这骑车子呀,一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二是响应政府节能减排号召,过低碳生活,一举两得呀。
哦,我想着你犯事儿啦,政府把车给收走了。娘解释说。
俺爸是清官,他这样的人,政府戴着眼镜也不好找,你就放心吧奶奶。儿子也宽我娘的心。
嗨,咱人老几辈子都清明,为人清,为官也得清呀,要听政府的话呀。娘给我交代着。
妻子去忙着做饭,我和娘拉起了话:是听政府的话呀,节能减排,过低碳生活,从点滴做起。
你是政府人,知道这些道理,你爹就不知道,他不会节能,也不会减排。我跟他几十年,他就知道吸烟,吸烟就得往外排,白天排不完,夜里接着排,长夜呼噜、呼噜跟拉风箱一样。他要是知道减排,少出点气,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哩,唉——这老头子呀。娘唠叨开了。
孩子在那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给他妈说,哎呀,俺奶的减排呀,真笑死我啦。
妻催促孩子:你去给您奶解释解释,让她知道低碳的道理。
孩子走来扳着奶奶的肩:奶奶呀,低碳是咋回事儿,我给你说吧。
你小孩知道啥。我知道低碳,去年你爸给我买的碳,都在低处放着哩,在我床底下,够低的吧。娘按她的亲身做法,反过来教育孩子。
不是的,奶,你又错了。这低碳呀,是指生活作息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碳,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三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
娘听了孩子的解释,不懂。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岔开话题:这孩子,跟你小时候一样,就好嘴脚不停,胡说乱抡,他拉呱的啥?最后强调性问我。
他说的呀,是政策导向。现在人这么多,工厂这么多,车这么多,都在消耗有用的东西。排出对人类对环境有害的东西,政府让这些所有消耗,在合理程度内降下来,从而求得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我像在大会上作报告一样给娘解释。
这就对了,咱这虽说没工厂,排的脏东西也真不少。你狗剩哥家喂的驴,成天吃饱撑得慌,对天咴儿咴儿叫;你三叔家的老母猪,吃饱了往那一卧,那屁呀,扑突扑突放不停;还有你枣花嫂家的狗……我这赶紧给他们说去,不能再喂恁饱啦,这些畜生吃的都是好东西呀,它们也得听政府话,不能再任意排出去了。
娘说着,拉起孩子去左邻右舍布置节能减排任务去了。
娘的意识虽说和政府政策有所偏颇,但有我这个当官的儿子在,积极性倒是蛮高涨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回市的路上,接连遇到乡亲们提的几个问题:骚壶(我的小名)呀,听说不让喂猪呀?我的驴可没惹谁呀?这乡下要是连个狗都不让喂,那还能……
听着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我想,下次回来,就节能减排过低碳生活的具体事宜,一定要继续和娘“商榷”,并进一步给乡亲们贯彻如何执行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雷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