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巫史传统下屯堡地戏文化之探析
陈发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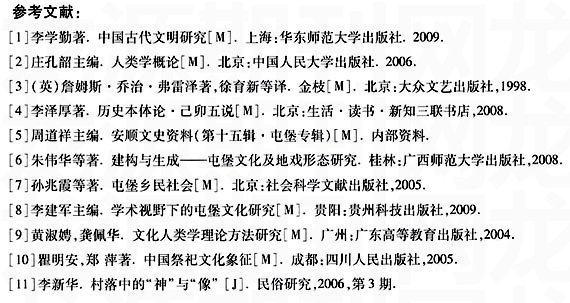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世界越来越走向趋同,因此,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呼吁多元文化的并存已成为时代的旋律。近年来,屯堡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一个子文化备受中内外学者关注,而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名片,它的探索与研究便成为屯堡文化开放化的标志。对屯堡地戏进行巫史传统的分析,一来符合多元文化的历史大潮,二来也是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积极开发,倍感重要。
关键词:屯堡地戏巫史传统傩戏巫术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113-119
自蔡官屯地戏队应邀到法国演出后,贵州安顺屯堡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一张精彩名片传递到世界,使世人开始关注屯堡这一社区群落。“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东西需要世界的认同和理解,世界也需要民族的东西作为诠释和支撑,形成人类生存的多元格局。世人发现屯堡人比发现屯堡地戏早,那是在上世纪初日本著名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在贵州高原进行人类学民族考察时无意发现的,在这之前屯堡人都被人们误认为是苗族的一个支系。鸟居龙藏的发现,揭开了屯堡人几百年被历史掩盖下的历史,这群被边缘化和不被世人理解的明代军事遗民,自称是“骑着高头大马”受明朝皇帝敕以“调北征南”名号而来的正宗大汉族,他们的“身世”随着对屯堡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被人们渐渐所熟知。屯堡人作为明代的军事遗民,几百年的历史洗礼,至今尚保存着明代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区别于当地其他民族和迁移汉族而形成了“文化孤岛”,不断地吸引中内外许许多多专家学者的膜拜和研究。在屯堡社区,保存了诸多汉族传统的文化习俗,这些文化模型中尤以地戏最令世人神往,地戏屯堡人俗称“跳神”,它以唱腔、武斗、妙绝的服饰(面具最甚)和一套古典的程式化模式被看成戏剧的“活化石”。地戏的成因在学界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地戏源于巫术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戏渐成为取悦于人的表演形式则是后来的事,并把它作为戏曲的一种原始形态来加以认识。早先的地戏是基于巫术活动而展开的,用来驱邪避凶、消灾除祸的一种仪式。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对屯堡地戏的巫史传统作一浅表性分析,以示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屯堡地戏这一文化现象。
一、“傩”与“巫”
“傩”与“巫”是人类学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是分析和解释原始人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精神信仰等的“开门钥匙”。“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旧时迎神赛会,驱逐疫鬼。”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旧指驱逐瘟疫的迎神赛会。”两本工具书的解释相差不大,可以看出,“傩”是指一种活动形式,它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信仰方式,傩的开展进而形成后来所称的“傩仪”、“傩舞”、“傩戏”等,“傩”的表演形式在今天世界各地较古朴的民族中仍很盛行,我国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大多数农村地区也普遍存在。如在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举行的“莲花生大师金刚法舞大法会”,俗称“古鲁狮子吼”,云南昭通地区开展的“踩九州”坛会,均为“傩”表演。
“傩”是原始人在科学极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自然缺乏认识和了解,“萌生图腾崇拜和宗教活动时所产生的。”在“傩”活动中,傩舞表演最吸引人眼球,也是整个“傩”活动的重要环节。“傩”是原始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认识低下并处以无奈状态的思维认证,它的起源已经久远,在我国能够为人们了解到的是1973年从青海省大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原始陶画,就有头上戴着兽角,身后配有兽尾的五人携手舞蹈的场面。至于傩是什么,傩舞又是怎样一种表演样式,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持疫”,这段文字记录了作为主持傩仪的主要人员方相氏身穿花衣,手套熊皮,脸蒙面具,持矛握盾,率百来个奴隶装扮神兽,从室内到室外逐出疫鬼的仪式。(屯堡地戏学者沈福馨先生把傩舞分为“百姓傩”和“宫廷傩”,以上对傩舞的描述沈先生认为是“宫廷傩”的最早描述,相比之下他认为《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描述的“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麇耠质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之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应为原始的傩舞。笔者认为以上的这种伴以鼓、磬,仿百兽而舞的活动只是傩舞成型前的过渡状态,理应以“方相氏”为最早。)以“方相氏”主持而举行的傩舞表演活动的概况已初步定型了傩舞的大体样式。到汉代时,“傩”的这种表演仪式达到鼎盛,傩的表演也在民间流行起来,因之《后汉书·礼仪志》中说:“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当时已有了确定的表演日期,其表演形式、行头与《周礼》中相同。汉代以降,傩的表演不但长盛不衰,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一些地方特定日期的祭仪演出。从现存的各民族“傩仪”表演形式看,功能大体相当,在岁首、岁末进行的居多,都以驱逐鬼祟、敬奉神祀、禳灾祛祸等为目的;在装束行头上都以扮成各种夸饰的神兽、神祀或各种英雄人物,一般都佩戴面具(面具是“傩”表演最具标志性的符号);除了装扮各种神物的人员外,还伴以各种乐器敲击的人员,以增添舞姿节奏和热闹气氛,一般是发声响亮的乐器,这样的乐器还有威吓鬼魅的作用。
“巫”是研究原始宗教产生的切入点,何为“巫”?《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指巫师,女巫;姓”。《新华字典》则解释为:“专以祈祷求神骗取财物的人。”两部工具书的解释不甚相同,可以看出“巫”是作为一种专职而称呼的人员,在破除迷信的现代语境下多以一种排斥、贬低的态度。由“巫”所开展的巫术活动能看到原始先民最为常见的思维模式和精神信仰,体现出原初先民在对待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而受制于大自然强力下幼稚、无奈的生存状态及其原始意志,他们需要一种超现实的力量来进行解释或解救,从而抚平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峙。因此,“巫”及“巫术”在当时被看成是那样地合理,巫术活动如今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这已为人类学者研究人类历史演进的标识,因此,人类学上是这样解释巫术的,“所谓巫术,是指人们企图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过一定的仪式对预期目标施加影响或者控制的活动。”巫术的源起已久,世界各地均能发现上古社会进行巫术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雕刻、壁画、纹饰等,在没有文字出现之前,多以图案的方式记录这一神圣的时刻。巫术作为上古社会国家开展的大事宜,为记录下来,我国古代也是采用雕刻图案、做记号等方式,随着文字的出现,学界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形式——陶符也部分记载了巫术祭仪,后来的成形文字甲骨文更是以记录国家重大的巫术活动为其主要内容,而且还直接提到了“巫”,如《殷墟文字外编》410记录“大雨,巫不出”,《殷墟文字乙编》5112记录“其舞其雨”(甲骨文字“巫”和“舞”是通用的)等。由此看出,最迟在殷商时期巫的这一概念已经成熟,说明巫术活动在当时是极其地盛行。可以说,巫术活动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巫术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母源地”,巫术也是产生宗教的基础,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阐述了这个观点,还有部分学者把巫术作为原始宗教来加以认
识,我国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持弗雷泽的观点,在他的著作《已卯五说》中对巫术与宗教的区别有很好的解释,而且李先生在他“巫史传统”观点中把巫术作为中华文化的起源,由“巫”产生“易”、“数”、“医”等,进而产生政治,产生礼仪,产生道德,从而形成从巫到史的一条文化线索。到现如今,世界各地各民族中仍很流行巫术活动,我国各少数民族及广大汉族农村也还保存着巫术文化传统,在宣扬科学的唯理性时代,巫术可能被列为“清除四害”的对象来处理,但从人类发展的文化层面来看,巫术是我们认识人类自身从蒙昧到文明历程的最好见证,是我们研究人类源远流长的重要物质资源和文化遗产。
通过以上对“傩”和“巫”的简要叙述,“傩”和“巫”有很大的渊源关系。按照一般的认识,傩应该属于巫术的一种形式,是巫术体系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仪式之一。巫术和傩都是在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对自然缺少普遍认识,受自然力的强行支配的情况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产生的信仰力量、思维模式与精神寄托,希望把这种“脆弱”寄托在一种神力的解救,通过神力达到生命的超脱,从而寻找到对灾难、困苦、疾痛等的心灵上的抚慰。傩和巫术都很注重表现形式,也就是仪式的展示上。在傩或其他巫术活动中,仪式要求虔诚,要对某种神力进行信仰,介于仪式的种种程式展演,达到人神的沟通。李泽厚先生认为巫术要求的是人神一体,通过人神的对接来获得某种神力,从而去预见、禳除灾祸,迎取吉福;宗教讲求人神隔离,人神划等,人只能把希望寄于神的意志之上,不能主动迎取。傩活动比较注重仪式程序,尤其傩舞是傩表演活动的重要环节,是人神一体的外化显示,整个傩仪讲求庄严,这样才能表达对神物的崇敬,神力也才会降临;从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看到“巫”和“舞”是通用的,以此可知巫术的仪式主要是以舞蹈的方式来展现的,巫术仪式上的动作是形成今天戏剧舞曲等表演的原型,但绝不能用现代舞曲的表演去理解庄严的巫术。从巫术与傩都比较重视庄严的祭仪表演上,也印证了“傩”与“巫术”之间有难以割裂的“血缘关系”。
二、屯堡地戏的巫史传统
把地戏看成是傩戏虽然在学界也还稍有纷争,但地戏即傩戏也大致算为定论,因为地戏的表演形式完全依样于傩戏,这兹且不论。傩戏是由古代的傩表演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如果说今天的戏曲是傩戏发展而成,那这一发展的线条则为傩——傩仪——傩舞——傩戏——戏曲,这是从古朴到开放、粗糙到细腻、蒙昧到文明、威严到轻松的发展轨迹。傩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以得出作为傩戏中一种的屯堡地戏也应该起源于巫术,这算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都多少能联系上巫术的传统,而且尤其是作为“跳神”旧称的地戏,更能看到它与巫术的脉承关系。
地戏在屯堡社区又称“跳神”,地戏的称呼是晚起的。屯堡作为明代受奉“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的军事遗民的标称,虽然广布于贵州很多地区,但地戏则集中在屯堡人比较密集的黔中安顺,是屯堡群落区中独有的文化遗产。屯堡居民经上百年的历史演变,已由原来的军人生活到半军半民生活,再到现在的纯农耕生活。屯堡人跳地戏,据屯堡人自己的口吻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述,主要是为了驱邪逐疫,年头跳神,能使一年户户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有的村寨在谷子扬花的季节(一般是农历七月半前后)也要跳地戏,称为“跳米花神”,以祝愿谷米的丰收。地戏不同于今天尚存的很多戏曲那样,演出并不随意而安而保留巫术活动中严整的程式,从地戏表演的仪式我们尚能感受到巫术的威严。地戏的演出程序,宋运超先生在《传神戏剧志述》里,概括为八项:
(一)“开脸”:择黄道吉日,由“神头”率演员去神庙,在寨主主持下,从箱子中请出珍藏的“脸子”(面具)后,进行用鸡血(象征生命的复活)给“脸子…‘开光”的仪式;演员戴上“开光”后的“脸子”,即为“神”而非人了,故不称演戏而称“跳神”。
(二)“参神、辞庙”:“神”之中的“一号人物”居中,其余一字而排开唱:“庆祝七月中元节,将爷引兵来参神——参玉皇、阎罗、罗汉、土地、孔子等,求其保佑无病、无灾、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此语应为“跳米花神”的开场白,年头跳神另有他语,引者注)
(三)“扫开场”:由两个小童分戴红、蓝“脸子”,手持扇、帕(花灯也用此道具)雀跃科场,在喧闹的锣鼓声中,边唱边舞,跳完祝吉舞蹈后,念:“和合三仙,两手把住肩,有人侍奉我,财宝万万千……”
(四)“朝廷”:小童扫场毕,剧中正反四员将官同时出场同时起舞驱邪并吟诗。
(五)“设朝”:小童“扫场”毕,剧中正反四员将官和将演出的史实以及看戏的人三者连接起来,超导人演出的作用。
(六)“跳神”:即地戏演出。
(七)“扫收场”:由戴“脸子”的峨眉山和尚与南天门土地对唱:“口是心非扫出去,一团和气扫进来;多灾多难扫出去,清吉平安扫进来;坏人坏事扫出去,正大光明扫进来……和尚拜土地,年年有吉利;土地拜和尚,年年大兴旺。”(此语为结束的祝福语,引者注)
(八)“封箱”:“扫场”结束,“神头”念念有词,放好“脸子”后“封箱”,送回神庙珍藏,以待来年再次请“神”。
在信奉“地戏”仪式的屯堡人心里,这种仪式是链接“神”的有力媒介,“神”参进到屯堡人的生活,在他们看来,这无疑会提高生活中的幸福指数,或者这样说,在广大中国民众心里,受原始巫术中“神”的意象的精神旨趣和历史心里的影响,信“神”、祈求神灵的拯救成了生活中规避灾祸或心灵受阻的惯用性心向,因为“理想生活内容的现实,作为老百姓,是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把握完成的。于是‘神灵成为民众理想生活愿望的诉说对象;成为理想生活愿望达成的精神寄托。”作为傩仪之一的地戏可人之处在于它融进了现代戏曲的唱腔,但仍不失巫术的神圣性,在其他早期戏曲原始形态都趋于消失的情况下,地戏的尚存被看成是现代戏曲的先驱,戏曲中的“活化石”。如此弥足珍贵,何以保存下地戏这种古朴的文化遗风呢?
首先,正如我们前文所讲的地戏是傩戏,是被看成为祈神,人神沟通的巫术祭仪,它具有对神灵“不可冒犯”的庄严与神圣,因此,信奉地戏的屯堡居民一直坚守了这份庄严与神圣。如当问及“为什么只挑一个剧目,不增加其他剧目;为什么总是挑一个剧目,不可以更换其他剧目”时,屯堡人顾之渊说:“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哪个(人)敢!我们只是负责在技术上改进一下,只负责把它传下去。《四马投唐》这堂戏祖祖辈辈都是在跳,换了,怕自己家不顺,怕寨邻老幼不顺。到(不顺的)时候,哪个(人)负的了这个责。”(屯堡地戏全上演的是历史上的征战故事,不演儿女情长的言情戏,也不演反叛、不忠不孝的剧目,这与屯堡居民为明代军事征战遗民有关,引者注)
其次,地戏这种纯朴特色能保存下来还与历史、地理有关系。正如很多学者研究屯堡文化认为其形成的根源是历史环境与地理位置所造成的一样,屯堡先民是受奉征讨云贵的军人,作为国家的意志力量,他们代表着天朝皇权,尔后定居镇守一方,历史风云变幻,明亡清继,这群明王朝的遗军渐渐被历史淹没,成为了一支独特“怪异”居民。再则,现代的屯堡居民是由先民屯居云贵高原而来,云贵高原地貌是典型的山区,崇
山峻岭阻隔了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桃源生活,而且贵州自古以来皆为荒凉的蛮夷之地,经济文化很是落后,从而使屯堡居民独守文化形成“孤岛”自不待言。
再次,地戏的延存还与屯堡居民及其与周围各民族间的文化心理有关。屯堡居民自定居云贵以来,他们是受天朝皇帝的委派,带着发达的中原文化进入蛮荒的边疆夷区,他们有崇高的民族心理,正如屯堡人引以自豪的“我们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我们老祖宗是什么什么官”、“我们家以前住在什么府,离皇城不远”等,对周围的少数民族则以不屑一顾的交往方式,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最正宗,也最优越。随着迁移到贵州来的汉族人的不断加入,他们带来了时代发展的信息,当连同部分少数民族在接受外来变化的“改装”后,回首看到这群还高高在上的屯堡居民,发现他们是那样的“怪异”与“另类”,也就渐渐地孤立起这群仍保存明代遗风的人群了。
屯堡地戏因屯堡人的坚守而部分保存了具备巫术传统的原初风貌,唯物理论认为只有发展的事物而没有静止的事物,地戏毕竟也在发展变化着。对于屯堡地戏如何带到贵州这片高原上来,又如何发展变化,也即是地戏的源起何处,学界可谓论述者无数,主要有沈福馨的“安顺地戏属于原始傩戏”,范增如的“安顺地戏不是傩戏”,高伦的“地戏是在历史推演中,得以幸存的一种古朴戏剧,是有别于北杂剧、南传奇之外的一种戏剧”和朱伟华的“安顺地戏是屯堡先民进入贵州后不断创造发展演变而来,地戏的发展见证了屯堡人的发展”等。虽然各有所论,但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地戏起源于傩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按照文化源流上推的话,现代的各种戏剧均来自上古巫术表演,这暂不深究;在此我也同意我的老师朱伟华先生的看法,朱先生以她严谨的资料列举论证了地戏并非与江南戏剧同源,我们这里的同源是避开巫术这个大环境而论,至少不是来源于“弋阳腔”,令人折服。地戏既然来自傩仪,又怎样在贵州土生乃至发展呢?
要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把问题的矛头指向远古的巫史传统。在巫术活动极端发达的上古社会,巫术具有多方面功能,引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除了上述历史经验和天象历数两大因素外,‘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还有另一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军事活动。‘国之大事,日祀与戎。祭祀(祖先)仪典与军事行为是上古君王所领导从事而关系乎整个氏族、部落、酋邦生死存亡两件最为重大的活动。”巫术在上古社会军事战争中的地位可以想见,我们至今尚能从古书记载中看到军事中举行的巫术活动。在相信神奇力量的上古社会,巫术被认为可以预测吉凶,消灾避祸,获得神助等特性,而以为了国家命途,减少伤亡的军事战争更是需要巫术的“解救”,希望能从巫术的举行来获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有在发动军事行动时要举行巫术活动的传统。屯堡居民的祖先是明代皇帝派往征讨西南的军人,他们在行军和准备战事时自然会举行一些巫术祭祀活动,而军中举行的巫术则不同于一般民间的巫术,它以祈求战事顺利和将士平安为的,因此,巫术活动的内容自然要以战事为主。地戏是傩戏,起源于军中巫术,是屯堡先民以祛除巫祟、祁保战事顺畅为目的而举行的巫术傩仪表演。在地戏表演节目中,以历史上出现的忠君爱国、勇猛善战的英雄健将为“神”来加以崇拜,通过巫术仪式中的人神沟通,希望把这些“神”的神力降临于军中,或者借用“神力”来祛除影响军中作战的污秽。随着屯堡人由军变民的转化,地戏的巫术性质也相应地变为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等,但表演内容仍沿袭旧制。由巫文化中的傩仪变为傩舞,再到傩戏以至现在的地戏,可以看到地戏发展的趋势,从功利性向娱乐性发展,因此,朱伟华先生认为“地戏伴随屯堡人的发展而发展”是不无道理的。
三、屯堡地戏的巫史意味
巫术的产生存在着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巫术本身可以看到人类在脱离兽格走向真正人格,获得智力不屈从于生命自然化的束缚,进而积极超脱自身有限性的幻想与渴望的努力。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解释巫术仪式发生作用的原理时说:“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古已有之的存在;一切人生重要趣意而不为正常的理性努力所控制者,则在一切事物一切过程上,都自开天辟地以来便以巫术为主要的伴随物了。咒、仪式,与被咒及仪式所支配的事物,乃是并存的。”马氏清楚地认识到巫术的产生是人类诞生以至成长所必需的精神养料,正如同人被上帝创造并送予人类巫术思维一样不需探源与解释,进而让我们了解到巫术对人类发展的意味。巫术之于整个人类发展的意味可以窄化为地戏之于屯堡居民发展的意味,为了对地戏形式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把巫术理论挪用在地戏上。
对巫术进行形而上分析较为成功的著作要算弗雷泽的人类学名著《金枝》,全书主要围绕巫术的两个原理而展开,即“相似律”与“接触律”,前者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后者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在巫术中两种原理是混合着使用的,而不是把巫术进行分类,当然地戏表演仪式也是暗含着这两种巫术原理。首先,“相似律”强调同类相生、果必同因,认为通过一定仪式,模仿想要达到的效果就能真实地实现,地戏仪式中武斗表演占据整个活动的重点,武斗就是模仿历史上的英雄名将在历史事件中战斗的取胜环节,如《三英战吕布》、《五虎平南》等,仪式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征战中像这些英雄一样取胜。地戏表演并不局限在历史人物的模仿上,也引进了一些现实的因素,如武斗角色中就有一个极其丑陋的角色叫“歪嘴老苗”,可以看出屯堡先民在征讨当地少数民族时的心理印记。除了希望、祈求战事胜利外,作为军人必须效忠王权,因此又有了诸如《岳飞传》、《杨家将》、《四马投唐》等地戏剧目,通过对这些忠臣良将的模仿来使屯堡人能对明朝皇权誓死效忠。其次,“接触律”认为“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事物是否为那人身体的一部分”,地戏主要体现在演员的装束上,地戏典型的特色即在俗称“脸子”的面具上,面具刻画的是各色英雄模样,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借用英雄们的神力,然后利用表演性的武斗场面的直接性接触,用兵器砍杀诸如“歪嘴老苗”等反面人物,达到真实与虚拟的统一,虽然这些都不是本人所接触过的东西,但由面具所刻画的模样也便暗指某人。弗雷泽的巫术原理也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或者说巫术的意味也在于“象征”。巫术是真实与虚拟之间转换的标尺与媒介,通过巫术仪式把虚拟、幻想层面以达到真实层面的转换,这就是巫术中的“象征”。三国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里说“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意指在人际交流中人们总把真实的意思藏掖起来,只显示能代表或暗指某种意义的表象,也就是南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给象征定义“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的意思。如果把地戏放入“象征”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联系的两端——“虚拟”与“真实”也符合西方现代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关键词——“能指”与“所指”,虚拟的“地戏实在”=能指,而地戏所要表达的
“真实实在”=所指,“能指”与“所指”是一对紧密联系的矛盾体,这种联系方式就是“象征”,因此索绪尔说:“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象征法律的天平就是不能随便用什么东西,例如一辆车,来代替。”
“巫史”是借用李泽厚先生的概念,李先生的“巫史”是以华夏文化这个大环境来加以把握的,根据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他把“巫史”与政治、礼仪、道德和术数等联系起来分析,从“巫”到“史”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发展、文化分支、社会规范与社会控制的过程。屯堡地戏的巫史特点也暗合于这样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作为巫文化之一的地戏,巫史传统中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分支可暂为不论,但从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来看,地戏为屯堡人能安息生养及传承民族心理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社会规范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屯堡社区作为明初西征的“中央军”大规模地定居在当时的蛮夷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他们失去与中央的联系,逐渐变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屯堡社区的社会发展就不会那样井井有条乃至形成仍保持明代遗风的历史遗民,地戏理所当然应成为这种社会规范的“发条”。屯堡人自称是正宗的大汉族,自然传承着讲究伦理纲常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它以家族为一个文化单位,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把民众相安无事地紧锁在土地上。屯堡人生活在贵州这片远离中央王朝的蛮夷之地,完全可以受当地少数民族非儒家文化的同化,结果恰恰相反,他们仍坚守着以儒文化为代表的汉族习俗,地戏便成了强化儒思想的主要因素之一,地戏演出的剧目多是具有典型儒家思想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可见一斑。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范如同硬币的两面,规范了也就是控制了,地戏对屯堡居民的规范作用是地戏在控制屯堡人思想的过程,地戏的表演在潜移默化地控制着屯堡人作为军人传统必须效忠皇朝的思想,屯堡人认为“地戏目前在安顺各民族间流传,是他们传出来的,他们的地戏才最正宗”,由此可看出他们对这种文化的拥护,也就恪守了地戏内含的儒家思维方式的传统,虔诚地遵从着地戏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与社会规范作为地戏的巫史传统,是如何形成屯堡人强力的心理范式的?地戏的仪式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一个思想再增强的过程,用英国象征主义人类学大师特纳的话说,这样的仪式存在“阈限前(日常状态)——阈限期(仪式状态)——阈限后(日常状态)”的过程,也即是“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动态的结构,不是周期循环,而是螺旋上升的动态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控制要求屯堡居民保持一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价值,当日常生活中隐隐具备这种心理与价值时,如果进入到地戏仪式的表演中,这种心理与价值就会在仪式中得到辩驳与认同,进而加深演出前的心理范式,仪式结束后回到日常生活中,这种心理与价值与演出前是截然不同的,它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升华,从而及时地使这种心理与价值得到补位,达到长盛不衰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屯堡人能延续明代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之一。
总之,屯堡地戏的“巫史”传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地戏的历史线索和文化根源,从而使屯堡地戏这一传统文化现象在研究和传承方面都会大为有利。目前,在文化世界大同趋势到来的情况下,多元文化的开发与保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地戏不断地深入研究和多视野观照是这种多元化情势的必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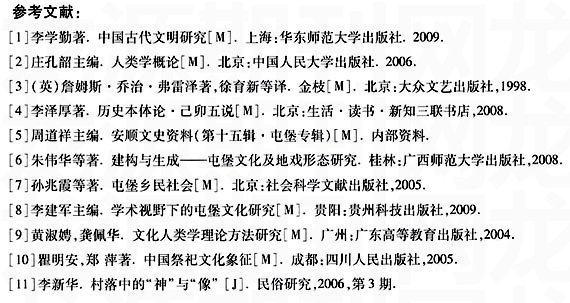
责任编辑王羊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