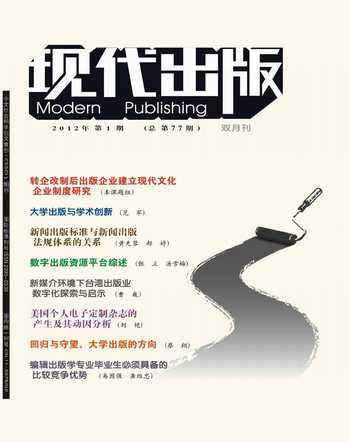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摘要: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其贡献在产业之外。倘若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社背靠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大学,何愁没有出版创新?我们讲大学出版社为大学服务,恐怕主要也在于坚定地支持这种探索、思考和创新。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事,才会对大学的变革发展持以正确合理的期待。
关键词:大学出版;现代大学;学术创新;出版创新
对大学出版战略以及“十二五”发展思路这类“宏大叙事”,我个人无甚新论和高见。这里,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这个老话题。我始终认同的观点是:出版,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其贡献在产业之外。我们是赚钱为主,顺便做点文化;还是主要经营文化,顺便赚点钱。顺序颠倒,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我谈的问题,在经济与文化中,侧重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侧重传统;在务虚与务实中,侧重务虚;在大学与出版中,又侧重大学。
一、从“诺贝尔奖情结”说起
“诺贝尔奖情结”不仅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教育界、科技界,也存在于新闻出版界,国人谈及此每每痛心疾首!中国奥运会办了,世博会办了,扬眉吐气。看来办世界杯足球赛实在太难,就特别渴望举全国之力、不惜代价早点拿个诺贝尔奖。每年10月初是诺贝尔奖颁发之期,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照例要发作一次。至于举办者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先后授给达赖、刘晓波、高行健等人,实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国人共愤。但对于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包括经济学方面的奖项,似乎海内海外并无多大争议。人们普遍相信,中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尚无一位大陆籍学者获得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不错,是已经有多位“华人”获得诺贝尔奖,2009年又有一位,这证明诺贝尔奖委员会并不歧视华人科学家。这一事实恰恰让人疑惑:何以无一人(不包括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西南联大培养的杨振宁、李政道)是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又在大陆从事研究呢?
柳斌杰署长在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蔡翔社长的《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几十年来,我国的大学出版社为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们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成就显赫。学术品位成为‘校园内出版社区别于‘校园外出版社的最大亮点。然而,在确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学出版社应当以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去追求更加高远的宏伟目标。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大陆)的大学出版社,还没有任何一家出版过我国(大陆)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我认为,由于我国(大陆)的诺贝尔获奖者暂时还没有诞生出来,不仅成为我国大学出版社‘心中永远的痛,而且也可能成为我国大学出版社层次还不够高、影响还不太大的潜在原因。”①我个人以为:我们的大学出版社将来若能推出自己国家科学家的优秀论著并获得诺贝尔奖,无疑是非常光荣的。但中国科学家是否能获得诺贝尔奖,与大学出版社层次如何、影响大小,与出版社有没有推出能获该奖的论著关系并不直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层次之高、海内外影响之大(当时属于亚洲第一、世界前三),出版史家都是熟悉的。至于牛津、剑桥大学获得诺贝尔奖之多,众所周知,但与他们各自的出版社似乎关系也不是太大,尽管这两家大学出版社都很“牛”。出版,特别是图书出版,从本质上看它可能更适合人文社科的东西,或者说,在人文社科方面更能体现出版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从“诺贝尔奖情结”,我们很自然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同样的问题钱老后来又反复问过几次,真是智慧老人!其实,“钱学森之问”提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存在,或许更为严重。这个“之问”的答案别说是科学巨匠、两院院士、学部委员,就是稍具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也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大家或启而不发,或故意让答案“跑偏题”,或有意“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回到出版上,人们总是怀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这些出版大家渐渐远去且日益模糊的背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王建辉董事长在参观张元济纪念馆时题词:“张元济不可追!”后来又有知名出版人写过同题文章公开发表。如今的经济水平、物质财富、科技能力都已大大增强了,各种“硬件”比起张元济的那个时代,真有天壤之别。但一代出版大家今天有几人能望其项背。现在,我们出版界可以涌现房地产大亨、资本运作高手、多种经营能人,甚至是制造股市神话的“故事家”,但就是难以产生真正杰出的出版家。盛世可以修典,但盛世未必能出大家,包括大出版家。
二、现代出版与现代大学共生共荣
提到现代大学,不得不说北京大学;讨论现代出版,也绕不开商务印书馆。二者可以比肩,也有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回顾它们的历史渊源,也对我们面向“十二五”的大学及大学出版有某些启示。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经这样说:“在我的内心深处,优秀的出版社永远是无形的大学和无声的老师(不包括现今音像出版物)。而像商务印书馆这样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对文化的贡献决不下于任何一所著名大学。”②因此之故,有历史学者将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比作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从人际关系的“细部”来考察,二者的共生共荣,相互扶持,可说是现代出版史、教育史上的不朽佳话。
出版家张元济和教育家蔡元培的私交公谊以及共同成就的事业,一直让人感叹和追怀。他们是浙江同乡,又是光绪己丑(1889)乡试同年,壬辰会试同年,又同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若算旧历,二人还是同庚,加上志向相同,可以算“六同”。因为张元济,蔡元培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关心商务的事业,对其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着重要贡献。他虽然不是商务的股东,却于1934年被选为董事,后来一直连任,参与制定“一·二八”的复兴规划。他虽不是商务花名册上的人,却自愿以商务人“自诩”:他给商务印书馆的人写信,历来用“本馆”而非“贵馆”称商务印书馆。有研究者说,蔡元培是张元济的精神支柱,胡适是王云五的精神支柱,而胡愈之是邹韬奋的精神支柱。我则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说两两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息可能更恰当。
过去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没有商务印书馆,中国的现代大学也可能还要多摸索若干年。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要从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算起的,而蔡元培出掌北大,主要是按照德国大学模式改造旧北大成新北大,这与他两度留学欧洲(主要是德、法)大有关系。商务则是帮助蔡元培完成留学梦想的最有力支持者。1907年,获得半工半读机会的蔡元培留学德国,经费还差不少,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约定,通过为商务编书,给予一定报酬,实际是每月100个大洋,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决定再次出国,商务给他预支稿费每月约200大洋,同时还帮助他留在国内的妻小,使其得以安心求学,数年后顺利归国。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被迫请蔡元培重主北大,不知他的行踪,催请电报无处可发,只能发到商务印书馆,请商务转交,由此可见交谊之一斑。蔡元培一生廉洁,无恒产、无积蓄。他去世时还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治丧事宜却是由商务印书馆料理的,可见其与商务关系之深。我想,商务成就了蔡元培,而蔡元培的思想,特别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商务印书馆,也无疑是有某种影响的。
三、大学的学术创新是大学出版创新的基础
在出版社编辑活动中,是选题策划更重要,还是审稿加工更值得重视,历来是有争议的。我以为,对于大众出版来说,特别是一些普及之作、文化快餐乃至跟风产品,策划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在专业的学术出版领域,编辑的工作主要是“价值判断”和“规范化”,对策划的作用不可随意拔高和过分倚重。周振甫对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的编辑贡献固然值得称颂,但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还是来自作者的创造。学者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乃至能拿出什么样的成果,与策划者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优秀的学术成果来自优秀的学人,特别是学术大师,而学者最重要的东西是学术的精神,是敢于质疑、勇于批判与创新的精神。
因此之故,出版学专家们格外青睐学术精神、大学精神。不可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学术精神、大学精神。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现代学术大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其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是日、月、星。这样的评价当然完全适合于陈寅恪先生自己,而这段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何以今天的大陆学者不能拿到诺贝尔奖之类的大奖。
香港著名教育专家金耀基曾说:“学术的独立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辨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少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③前面提及的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深受尊崇,让人景仰,就在于他奠定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数十年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并且付诸实践。抗日战争中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环境之恶劣与成绩之显著,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它的“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也与我们今天日渐富裕、奢华,也日渐世俗化的大学形成巨大反差,以至让今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名家大师几乎是在饥寒交迫中创造出传世之作、培养出栋梁之才,原因何在?当年执教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或许能给我们答案。他说: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正因此故,一个已经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还能如此吸引那么多知识者的目光。它的魅力远不止于“艰苦创业”和“人才辈出”。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我看来,谈论联大的意义,对今日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更为永恒的命题在于探索、思考,以及挑战各种成见。”④试想,倘若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社背靠西南联大这样一所大师云集、英才辈出、思想活跃、成果迭出的大学,何愁没有出版创新?我们讲大学出版社为大学服务,恐怕主要也在于坚定地支持这种探索、思考和创新。
四、大学出版与学术的创新需要自由的空气和宽松的环境
大学出版的创新、大学学术的创新看似大学及其出版社的事,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个国家要想其科学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取得创造性成就,就得创造一种制度环境,让科学家们能独立地、自由地思考、研究。在学术文化创新上,可以说是“制度决定成败”。众多的基金,大量的投入,无穷无尽的各种“工程”,最终都解决不了学术创新、科技创新的难题。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关于如何理解“钱学森之问”时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激,也是很大的鞭策。温家宝强调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个人认为,“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有三个层面:专家学者个体,大学与专业研究院所,国家——党和政府。套用老话讲,党和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才是“纲”,其他两个层级都只是“目”。能否有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环境,能否真正按教育规律办学,按科学规律研究,主要取决于“纲”,而不是“目”——“纲举则目张”。
有学者针对前苏联说过一段话,似乎就是针对当下中国说的:苏联向科研机构拨了大量资金,但唯有当这些资金“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即由自治的科学共同体掌握、使用,才能对科学研究产生积极作用。否则,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影响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当代中国投入到大学、研究机构包括出版社的经费越来越多,堪称庞大,但它们大多数是由行政权力主导分配的,因而其作用也是相当不确定,至少是十分有限的。倘若思想的自由、学术的包容还是宏观一点的困惑,而现行的学术GDP崇拜、有百害无一利的量化考核、按数字搞学术及教育上的“梁山水泊排座次”,更是从学术评价机制上彻底断了学术与文化创新的“后路”。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最近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强调重质,重创新,重同行评价。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这一“意见”,学者反响积极,而一些科研管理者反应则比较冷淡。实际上,不合理、不科学的量化考核体系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了一个利益链。一种新的机制的建立,是对既有利益集团、利益链的一种冲击。
如何办大学、如何办大学出版,现在是不是可以允许有略带自由的思考、略显个性化的选择、稍微多样化的模式?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秉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版人?我觉得出版社与大学在文化品格上有相近、相通之处。章开沅先生2007年从牛津大学访问归来后,发表了《泰晤士河源头的思考——从“牛津现象”谈起》一文。他说:“牛津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旧。”“牛津就是这样悠然自得地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巨变,旧貌并未完全换新颜,却又不紧不慢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无论是人文还是科技,许多学科仍然处在世界前沿,人才与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论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绵延。”⑤在章先生看来,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必然会流于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话语创新。出版的创新与守旧也当作如是观。
无独有偶,美国的耶鲁大学也是以保守的文化品格著称。王英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介绍了耶鲁保守文化品格的形成,剖析了该校保守的管理、保守的教育理念,以及由此而引申的“大学保守文化品格的合理性”。作者在文末坦陈心曲,发人深思:“当我们沉下白日躁动之心,秉烛夜读耶鲁大学的发展史时,我们就会被耶鲁清新的文化品格,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打动:它几百年来不为躁动的社会变迁所动,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社会职责,如同人类社会漫漫路上的一盏明灯,星光闪烁,为世人所瞩目。它在静谧中发展,在稳定中前进,以其保守的文化品格营造出一所循序渐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人才和重大科研新发现如清泉从中汩汩流出,永不干涸,永不浑浊。”⑥
事实上,大学与社会经济组织的区别,就突出体现在“保守”这一独立的品质上,大学的魅力来自于保守基础上的丰厚积淀和创新。“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跟着社会同凉热;大学必须经常给社会提供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一定都是社会所想要的,而往往是社会所需要的,这才叫“引领”。大学要服务社会,但需要保持某种距离,要有“张力”。大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保守性,也可以说保守性是大学的遗传特征。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曾经深刻地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大学的这一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学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就要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大学的保守性,才会使得大学在稳定中发展。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事,才会对大学的变革发展持以正确合理的期待。
大家熟知的周国平先生曾这样写道:“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的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⑦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大声呼吁:“别让实用主义遮蔽大学精神。”⑧其实,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出版界,这种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现在是绝对占上风的。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保护,对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如果说在极左时代对出版的冲击主要来自政治,现在则还来自市场化、商业化、功利化。在出版界,老商务也成为出版人崇奉的一个似乎不可企及的梦想。其实,假如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在淡定中坚守、在稳健中创新,出版业或许有更美好的未来。
记得柳斌杰署长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要大力培育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研工作是探索规律、发现真理的工作,第一需要的是科学精神。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首先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历史反复证明,没有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没有真正的科研,也就没有推陈出新的创造能力,没有继往开来的时代进步。我曾给研究所的同志多次讲过,科研要坚持科学性、独立性原则,不要看着眼色、顺着上级说话,要说真实的话,有根据的话,别人不爱听而有真知灼见的话。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弘扬追求真理的精神,倡导批判的精神,尊重科学结论,崇尚理性质疑,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敢于负责。”⑨
窃以为,以上所言算是不看眼色的一点实话、真话,或者像“白头宫女说玄宗”的一点闲话。无论如何,大学不能没有理想、失却精神,大学出版也不能没有精神的追求和文化的梦想。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军2011年11月17日在宁波“大学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注释:
① 柳斌杰.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章开沅.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4.
④ 陈平原.大学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7.
⑤ 章开沅.章开沅演讲访谈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8、109.
⑥ 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J].比较 教育研究.2003(3).
⑦ 周国平.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N].文汇报. 2002-12-01.
⑧ 纪宝成.别让实用主义遮蔽大学精神[N].人民日报.2010-10- 27.
⑨ 柳斌杰署长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