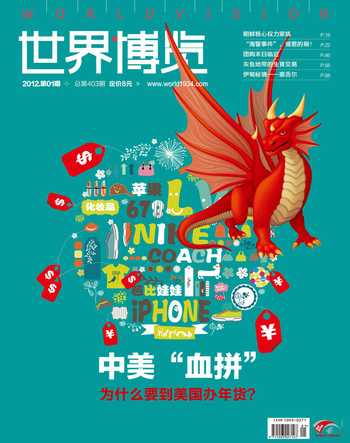初识纽交所
俞靓
在纽交所,我渐渐理解到“交易”所涵盖的不仅是数字和金钱,更包括了一切关于人性的东西。
多年前我采访金融期货的创始人利奥·梅拉梅德(LeoMehmed)的时候,这位80岁的犹太老人告诉我,他在十几岁时某一天误打误撞地进入交易所后,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那个地方。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把此生奉献给这个像电影般惊险的行业。
梅拉梅德并不孤独。对巴菲特、索罗斯这些教父级的人物来说,或多或少,交易所在他们少年时代的梦想里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交易员们如触电般地来回飞奔,扯着嗓门叫骂,对着电话大吼,挑战与紧张,冒险与诱惑,这种震撼是无法抗拒的。
我原以为这辈子大概是无缘体会这种感觉了,没想到几年后却被命运安排在纽约继续财经记者的生涯。除了采访华尔街大大小小的人物之外,我每天例行的工作就是穿梭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录制市场点评节目,撰写消息和分析。
说起纽交所,不得不提到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任之前五年,他已经在华尔街48号创设了纽约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银行承担了美国中央银行的职责,发行了大量国债,由此拉开债券交易的序幕,并使国债成为美国金融货币体系的根基。
汉密尔顿的墓地就在距离纽交所仅几步之遥的三一教堂里,他的青铜雕像目光正朝向纽交所。这位华尔街崛起的代表人物,死后依旧日夜注视着华尔街的一举一动,不知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守望。
纽交所大楼建于1903年,外观古朴,安静典雅。如果不是已经知晓,人们很难想象这里面发生的一切对世界资本市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1792年5月17日,当时24个证券经纪人在华尔街68号外的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梧桐树协议》,宣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诞生。如今,在纽交所交易的品种有证券、债券、期货、期权,平均每天的交易额约为1600亿美元(1美元约合6.3元人民币)。在这里上市的公司总市值达到13.39万亿美元,为全球最高。
纽交所的第一层便是闻名遐迩的交易大厅。老实说,当我第一次走进纽交所交易大厅时还是有点小小失望的。由于科技更新,世界各国的交易均完全电子化,传统交易中用手语和暗号彼此联系的场景只能在电影里看到了。所幸的是,纽交所的交易大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交易席位,众多交易员围着终端忙碌地下着订单,看起来一片热闹,其实每个人却像一座孤岛,只专注于自己面前的风景,无暇顾及周围的熙攘。
我怀着略微忐忑与好奇的心情,穿过满是纸屑的地面,看到行色匆匆的人们,听着此起彼伏的电话以及交易员沙哑而疯狂的声音时,逐渐兴奋起来。直到置身于其中好几个小时,我才慢慢体会到这里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决定着世界证券市场的走势。
纽约股市这两年从体无完肤到恢复元气,投资者欢欣鼓舞,一度忘却金融危机的阴霾。可是,一场欧债风波来袭,又让市场瞬间回归昨日的萧条凋敝。历史不断出乎意料地重复,人们总是不可思议地健忘。
随着在华尔街采访次数的增加和观点探讨的深入,我逐渐体会到了如何通过观察证券市场去透析一个经济体的脉搏。我越来越相信,“交易”所涵盖的不仅是数字和金钱,更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他们的家庭和未来,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贪婪,以及你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关于人性的东西。
交易即人性,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