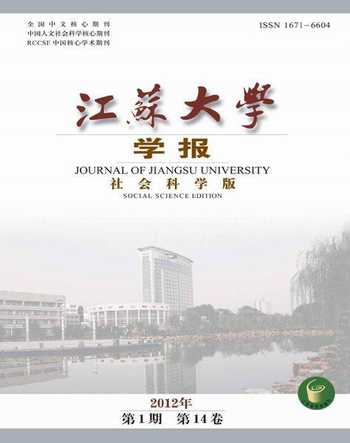民国时期“劣绅”话语源流考略
摘 要: 民国以前,“绅”多与“士”结合,指称拥有权势的士大夫阶层,代表一种政治特权和社会荣耀。民国以来,“绅”多与“劣”、“豪”结合,指称与人民对立的“反动”阶层,“劣绅”、“豪绅”由此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在短短几十年间,“绅”从社会荣耀变成“反革命”,以至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
关键词: 绅; 绅士; 劣绅; 反革命
中图分类号: K256;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41-04
收稿日期: 2011-09-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重点项目(2010ZDB43)
作者简介:余进东,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民国以前,“绅士”指称有权势的士大夫阶层,代表一种政治特权和社会荣耀。民国以来,“绅”多与“劣”、“豪”结合,指称与人民对立的“反动”阶层,“劣绅”、“豪绅”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短短几十年间,“绅”的社会内涵发生巨大变迁。
一、 从“绅”到“搢(缙)绅”
“绅”的商周古文字来源已难考稽,只能借助造字法来理解。“绅”是形声字,“绞丝边”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像“束丝”之形[1]109或“束丝挽绕”[2]325;“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像“电闪耀”[1]125或“阴雨天闪烁的电光,其形呈曲折伸延之状”[2]356。电的“闪耀”和“曲折伸延”是对电光的描摹,电光的“曲折”与束丝挽绕之状极相似,“伸延”则与织物多余伸延而出的情形极相似。因此,“绅”虽是形声字,但无论形旁声旁,都已将它们的原始义羼入新造字中。“绅”在造字时的原始义与织物多余伸延而出的情形高度相关。
春秋战国时,“绅”字在文献中已较常见。《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荀子•礼论》有“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一语,《庄子》有“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一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绅,大带也。从系,申声。失人切”;“带,绅也”。郑玄解释:“绅,带之垂者。绅,重也,谓重屈而舒申。”胡承珙指出,桓二年左传疏云:“大带垂者名之为绅,而复古不厉者,绅是垂之名,厉是垂之貌”(《小尔雅汇校集释》)。刘宝楠解释:“子张书诸绅。孔曰:绅,大带。……正义曰: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十三经注疏•论语正义》)王力认为“绅”是古代贵族束在腰间的大带子,也偏指其伸展出的部分[3]。
由此可见,古今学者多认为“绅”是束腰之带,或腰带垂饰部分。整条腰带称为绅带。绅带多为丝帛所制,所以又称素丝大带。《诗经•曹风•鸤鸠》“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讲淑人君子的腰带用白丝镶边。如此可知绅带并非常人所能享用,只有上层贵族才有条件佩戴,因此它不仅是装饰,更是社会身份的体现。
当时,人们记事用竹简、木牍,叫做“笏”,“笏”插腰中,就是“搢笏”。《说文解字》说,“搢,插也。”“搢笏”是礼制上的重要事情。《礼记•内则》提到,儿子晨起,衣着完毕系好腰带后,就须“搢笏”,如此父母一有嘱咐,就可随时抽笏记下,到时办理;“搢笏”还是君臣朝见时的重要礼节。《礼记•玉藻》记载,“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由于贵族和官员腰束绅带,因此他们的“搢笏”又称“搢绅”[4],时间一长,“搢绅”就成了官员的别称。
“搢笏”本义为记事,“搢绅”代表官员外,还有记录之意。《庄子》所谓的“搢绅先生”,恐怕就是专门为贵族记录礼、乐、诗、书的人。西周文物多在邹鲁,所以背诵古训的儒者多为邹鲁之士[5],这恐怕是“绅”与“士”在历史上的最早渊源。
孔子生于邹鲁,青少年时期即以恢复周礼为志向,因此其学应是从搢绅先生那里得来。孔子以传承古礼为志业,但不赞同死守古训,而主张将诗、书、礼、乐改造为救世良策。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儒门恐怕是与搢绅先生关系最密切的。
西汉时,随着儒家礼治体系的建立,先秦某些礼节又得以恢复,比如“搢笏”或“执笏”;而且不同级别的官员执以不同的笏板,以区别高下尊卑。由此,“搢绅”多指官员和贵族阶层,这意味着“绅”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密切,其政治含义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秦时“以吏为师”,搢绅先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搢绅”的文化意味随之减弱。不过,由于很多官员信奉儒家,所以“搢绅”与“诸儒”关系依然密切。《后汉书》就将两者并称,史载蔡邕晚年死于狱中,“缙绅诸儒莫不流涕”。
两汉时,“搢”、“缙”通假。《史记三家注》说,“集解李奇曰:‘缙,插也,插笏於绅。绅,大带。索隐姚氏云‘缙,当作“搢”。郑众注周礼云“‘缙读为‘荐,谓荐之于绅带之间。今按:郑意以缙为荐,则荐亦是进,进而置于绅带之间,故史记亦多作‘荐字也”。两汉以后,“搢绅”亦称“缙绅”、“荐绅”。“荐绅”不常见,“缙绅”渐成主流,成了官僚的代称。
二、 从“绅士”到“绅商”
唐宋以前,“缙绅”常与“诸儒”并称,但界限明显。《后汉书》“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在此诸儒单列,与“冠带缙绅之人”明显不同。不过,唐宋开科取士,儒家士人逐渐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来源,儒士就与缙绅(搢绅)重合了。
余英时认为,“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在不同阶段,“士”的面貌不同。先秦时是“游士”,秦汉后是“士大夫”,秦汉时“士”的活动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方面。魏晋南北朝时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教化天下”的大任从儒家转到了佛教身上[6]。儒家之“士”在唐朝之前并没形成固定的政治力量,这与“缙绅”明显不同。隋唐之际,这种状况发生历史性转变。
隋唐开科取士使得掌握智识并以匡济天下为旨归的儒士成了考试的最大赢家,他们不仅获得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而且逐渐垄断了行政职位,最终形成为天下认同的士大夫阶层:“缙绅”与“士”逐渐合一,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代称。在宋代文献中已经出现了“绅士”一词,宣德七年,苏州知府况钟曾颁过《绅士约束子弟示》,这里的“绅士”显然指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
唐宋以前的“士”就以参与政治为目标,但他们并未形成独立的道德意识。唐宋之际,儒家在佛、道两教刺激下,士大夫阶层对“道”的关注愈来愈强烈,他们开始将自己定位为“天下大道”的践行者。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他们的阶层宣言。
“绅士”与“缙绅”的内涵就此分野: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代称,“绅士”除了象征某些权力外,还拥有文化意味,以及道德标杆的象征意义。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更是天下大道的践行者。由此,“绅”以儒家道德的践履为中介,进入百姓日常生活。在儒家标榜的道德层面上,“绅士”阶层最终获得普通百姓的认同,成为整个社会人人仰慕的荣誉性称号。这种荣誉和仰慕不是源于权力,而是道德的力量。
从孔子时代起,“士”人鄙薄利益的传统直到明代中叶才发生变化。由于朱元璋废弃丞相,压制士人,使士大夫失去了“得君行道”的平台,开始将目光转向个人与社会,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由此,儒家思想出现新动向。据余英时研究,从16世纪开始,很多儒家士子不但不歧视商人,相反开始强调要保护商人。黄宗羲就认为“大贾富民”或“素封巨族”是一方元气、社会根本,政府如果过度打击他们,必使国贫民弱[7]。士大夫对商人的改容相向和“亲近”,使他们有了与商人合作或直接参与商业的可能。最迟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已出现“绅士”与“商民”并称的称谓。谢放考察清代巴县档案后发现《乾隆二十八年重庆府捐修城垣引文及捐册》引文部分7次提到“绅士商贾”一词,捐册部分也有“绅士商民”的记载。而且,他还同意余英时关于“绅商”就是“绅士商民”简化的见解[8]。据此可知,“绅”在清代已向经济方面扩展。
不过,“绅”仍是政治和文化的代表,“商”仍主要以盈利为目标,“绅商”并非“绅”、“商”的合称。马敏认为,“绅商”虽在多数场合指绅与商的合称,但有时也是对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9]。邱捷对清末广东文献研究后得出了同样结论。他认为,在清末广东,即使字面看来是分指的“绅商”,结合其语境,实际上主要也是指亦绅亦商的人物[10]。如果我们认同上述观点,那就更可推出:“绅士”之“绅”的内涵尚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绅商”之“绅”已明显与经济连在一起。
明清之际“绅”“商”对流已成一时潮流。皓首穷经使得不少士子日益穷困,绅士需要经商才能摆脱贫困;同时商人也需儒家的道德意识来自律和取信他人,此外,商人还需要一些基本知识技能来应付日益扩展的商务。由此,绅士染指或直接经营商业及富家子弟经营举业已成普遍现象。
三、 从“绅商”到“劣绅”
民国以前甚至民国初年的多数绅商仍有士大夫的传统职责担当。他们一方面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另一方面又推动立宪、教化族人,基本担负了绅士的应负之责。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终结和军阀混战的来临,广大绅商和绅士们的责任担当意识消失,出现了绅士阶层普遍劣化的现象。
宋明之时,士大夫以内圣为根本,拥有无穷无尽的外在动力。然而,随着清代朴学兴起,理学(心学)对士大夫的内在促动愈来愈脆弱,及至清末民初,已呈强弩之末。等到新(西)学彻底代替中(旧)学,理学(心学)对他们的促动作用几乎烟消云散。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绅士们如何坚持责任?科举废除、武人崛起之后,士大夫实已经失去传统特权。等到留学生回国以及大批新式学生占据文化教育领域,传统绅士连教化大众的最基本的权利都失去了。“绅”之名号已华而不实。
对绅士和绅商而言,丧失特权让他们放弃社会责任,拥有财富又迫使他们拼命维护既有秩序。大革命到来前夕,绅士与国家政治间的联系实已切断;大革命时,当国共两党要将绅士与地方政治的联系都斩除时,绅士对地方特权的顽固维护就使其成了理所当然的“反革命”。
更巧的是,早在中国革命者指斥绅士为“反革命”前,日本知识界就已做好相关理论铺垫。1904年,日本社会主义者Sakai Toshihiko和Kōtoku Shūsui发表《共产党宣言》日译本时,就分别以“shinshi绅士”和“shinshi(瞭eki)绅士(的)”对应英语的“Bourgeois”和“buergerlich”[11]351-352。在此种译法下,“绅士”不就是革命的敌人吗?1908年《天义》刊载民鸣《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根据陈力卫研究,该译本75%以上沿袭日译本。它同样以“绅士”、“绅士阀”翻译“Bourgeois”、“Bourgeoisie”。译文之后,编辑刘师培加注:“案:绅士阀,英语为Bourgeoisie,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绅士英语为Bourgeois,亦与相同。然此等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位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11]355。这说明刘师培了解“Bourgeois”不等于中国的“绅士”。但在其意识中,中国“绅士”属于“Bourgeois”之一种应无异议。
“绅士”与“Bourgeois”的较大差异使不少革命者放弃这种译法。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民报》1906年第5期)指出,“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陈望道再译《共产党宣言》时,以“有产者”翻译“Bourgeois”。这样,“绅士”似已退出马克思经典中译本。不过,语言上的退出却阻挡不了事实上的进入。“绅”字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权力、文化、道德和财富诸含义,使它注定成为旨在推翻“旧社会”的革命者的敌人。叶德辉们对革命运动的破坏仅起催化作用。1926年10月,湖南省建设厅发出布告,要求各地严禁土豪劣绅把持农会[12]426。同年12月,湖南省政府表示,“省政府对于土豪劣绅,业具有铲除肃清之决心,如匿枪抗命之杨致泽,通敌坐探之周嘉淦,先后处决在案”[12]487。1927年4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铲除反革命派宣言中,将“土豪劣绅”置于“反革命派”之首[12]259。
“劣绅”一词的出现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语使绅士阶层遭遇覆顶之灾。“劣绅”即品行恶劣的绅士,此词最早出于何处已难考稽,但绅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基础,封建王朝肯定会对这一阶层制定行为准则和奖惩标准。据柳诒徵研究,顺治帝仿照明制钦定“卧碑禁例八条”作为生员行为准则,这无疑也是对绅士群体的基本要求,成为判断绅士“正”“劣”的基本标准[13],按照品行绅士可分为“劣绅”与“正绅”。由此说来,有关“劣绅”的类似称呼应在明朝就有,至少在清朝顺治帝时就已出现。但文献里的大量记载则是晚清,当时称呼各不相同。汪士铎将正绅称为正士、廉明公正书绅、正派绅士;而把劣绅称为劣生、刁劣之士绅、华士、刁衿、刁绅劣监等等[14]。大革命时则统称为“劣绅”并将其固定化。
土豪劣绅成为群众运动目标后,两湖地区相继出台“土豪劣绅罪”。 1927年1月,湖南省颁布的《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凭借政治经济力,或其他特殊势力(如团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为之土豪劣绅,依本条例惩治之:(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二)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三)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12]259同年3月,湖北省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该条例具体内容与湖南条例大同小异。上述规定意味着凡是反抗或阻挡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运动的,都可以视为“土豪劣绅”治罪。由此,对“劣绅”的界定已由传统儒家道德标准转为革命标准。
到了这个地步,“土豪劣绅”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成了抽象符号——一个绝对负面,或说“本质反动”的符号。时任湖南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的话是“土豪劣绅”抽象化的绝好说明:“一般土豪劣绅,他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既然“土豪劣绅”是革命的天敌,那么谁被扣上这顶帽子,谁就铁定被打入地狱。当叶德辉被冠以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时,他的死期自然不远了。
民国以前的“绅”或“绅士”概念积累了政治、文化、道德和财富等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传统社会权力、地位、财富及道德荣誉的化身。这种权力是皇权的自然延伸。现代革命到来前,它意味着一种威势和荣耀。然而,对革命运动来说,“绅士”所拥有的威势和荣耀却是不折不扣的“负资产”,注定要成为革命的目标之一。革命者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传统社会的权力象征。这些权力象征,除了皇权之外就是绅权。那些因废除科举而失去特权的绅士对自己仅有财产和身份的维护,更激化了革命者对他们的仇恨。至此,大革命中打倒“土豪劣绅”运动的迅猛开展已经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 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王梦华.说文解字释要[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3] 王 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918.
[4] 朱启新.搢笏与搢绅[J].文史知识,1999(9):68-69.
[5] 侯外庐,赵纪彬,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39-140.
[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7]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传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8-260.
[8] 谢 放.“绅商”词义考析[J].历史研究,2001(2):124-125.
[9] 马 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J].历史研究,2001(2):132-138.
[10] 邱 捷.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J].历史研究,2001(2):139-147.
[11] 李 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 倩,王 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673.
[14] 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174.
(责任编辑 潘亚莉)
Etymology of the Expression “Nie Sh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 Jindong1,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aracter “shen (gentry)” wa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shi (scholar)”, and referred to a powerful social stratum that stood for a kind of political privilege and social glory. But in the Republic and after, “shen” was often associated with “nie (bad)” and “hao (despotic)”, and referred to the reactionary social stratum in opposition to the people, therefore, “nie shen” and “hao shen”became the synonyms of reactionaries. In a few decades time, “shen” changed from those of social glory to reactionaries, even the targets of revolutionaries
Key words:shen (gentry); shen shi (gentry and scholars); nie shen (bad gentry); reactionary
——从“反革命罪”的存废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