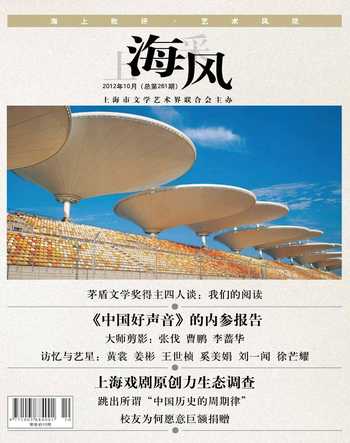1956年秋在上海
彭荆风
去过上海许多次,印象最深的还是1956年秋天那近40天的小住。
在20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1956年是个难得的安定岁月;没有战争,邻近的朝鲜半岛的硝烟烈火,前两年就停歇了,也没有政治运动,1955年那场让文学界心惊胆战的“反胡风运动”并由此引发的“肃反”,也悄然结束了,人们又恢复了平静生活!上海这座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就能从容显出它那特有的魅力!
新时代的上海,不同于旧中国那在表面繁华下掩盖的贫困、混乱。
我1947年春夏曾经来过上海,一方面惊讶这城市高楼大厦之多,灯红酒绿中富人的奢侈,又深感这城市的下层贫苦人境遇之惨,报纸上每天报道的是物价飞涨、路有饿殍。以致过了许多年,我对上海这大都市,都有着一种既感神奇又充满恐惧的矛盾心情!
1956年上海的城市格局还是从前的样子,老楼房、老街巷,并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建筑,热闹的还是那些老地方,但城市的精神气质却不一样了,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又平稳,更没有挨饿的人,给我的感觉是每个上海人都在安心地工作、学习,把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及这个城市多年形成的精巧细腻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时候来上海旅行,既可欣赏这城市传统的大都市气派,又可感受上海人在新的社会焕发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真挚热情,也就是今天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你问个路,那些大娘、大嫂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该去哪条巷口坐车,如果要省几分车票钱,可多走几步去另一条街坐车……
话语亲切、周详,听得我们心里都是暖暖的。
那次,我是因为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被中央电影局局长、老作家陈荒煤电召来上海参加为期40天的、有苏联专家讲课的电影剧作讲习班。
荒煤把这个讲习班选在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是中国电影发源地,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多。
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的人数较多,时间也较长的一次电影研讨会,半天看中外电影,半天讨论,我还记得那次的同学就有海默、孙谦、徐怀中、鲁彦周、黄宗江、公刘、白桦、季康、公浦、张天民、郑秉谦……
在这以前,我刚刚在云南边地一个景颇族村寨的竹楼里生活了六七个月,突然换了个环境,从整天云雾缭绕的山野飞临这高楼林立、珠光宝气的大城市,真是有些眼花缭乱。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常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和周末的休息天,在街巷里尽情游逛,细细欣赏那些产生于各个时代,有的是洋场味,有的是古典情调,风格各异的建筑,大陆新村的鲁迅先生故居,幽静的长长短短石库门,热闹的城隍庙、大世界,包括那名人聚集的万国公墓……当时人还年轻,虽不是老饕,却也爱吃,也就很关注那些经过一代又一代美食家筛选肯定过的精美吃食。
时过50多年,那次在“讲习班”看过了哪些电影,我却一部也记不得了,但老正兴的鳝鱼糊,陆稿荐的百年老卤鸭脚、鸡翅膀、大虾的鲜美,却是现在想起来还是垂涎欲滴,特别是那价廉物美的油炸肉馅饼……
当时,我们住在苏州河边的老新雅酒家。楼下就是热闹的大街,每天晚上华灯初上时,就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挑着一副担子过来,在酒店楼下摆开摊子。这是一副精巧、整洁的木制担子,一头架着一口平底锅,另一头摆着各种作料的案板;他就在街头切葱、和面、调鸡蛋、剁肉末,然后一边做饼一边煎饼。看来他是很有号召力,在他刚放下担子时,就有人开始排队了,虽然这要等很久,大家都很安静、耐心,没有人拥挤地乱插队,更没有人嫌他和面、煎饼的动作缓慢,他也决不会因为排队的人多而匆忙潦草地减少工序,一定要把面和匀,煎得油香四溢两面焦黄才卖给顾客;也不管你来得多早,排了多久,或者是天天来买饼的熟人,都是一人两个,决不多卖给。
我那天从楼下过,也被这又香又脆的油炸肉馅饼引诱得加入了买饼的行列。从此每天都是常客。
有天晚上,我出去办事走远了,赶回来已是晚9时左右,最后的两个馅饼已卖掉。没有买到的人,也已叹息地散去。他每晚上只做200个呢!
我当然也颇惆怅。问他为什么不多做一些?他笑道:这副担子只能装这200只饼的原料,做起来也很费力,马虎不得呢!
当他知道,我是从遥远的云南来。十几天来,每晚都来排队买饼,颇高兴,就说:“你是出差的人,事多。以后,就不要排队了,来晚了,我会给你留两个。不过也不要太晚!”
第二天晚上,我刚加入排队,他就认出了我,马上把刚煎好的两只饼递给我。
队伍里有了骚动,对他来说,这可是异样之举。他解释道:“人家是从云南来出差的,几万里远呢!来一趟不容易,优待,优待!”
队伍里又安静了,我连声向人们道谢。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又回来晚了,这时候已近晚10时,上海的夜市结束得早,街头巷尾已是灯火阑珊。我想,他那馅饼摊子也该早收摊了。行前却错过了这最后一次美食,真可惜!哪知道,他却在已没有人排长队的摊子前,迎着秋夜的凉风悠然地吸着烟。见我来了,只说了句:“你再不来,我就该走了。”
灶里只剩下一些余烬的平底锅上放着两只微温的馅饼。
我连连道歉,也告诉他,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并为以后不能再吃到他的鲜美香脆的馅饼而遗憾!他却爽朗地笑了,“以后再来嘛!你们公家人,出差的机会多!”
我想也是这样。我亲热地握了他那满是油的厚实大手。
但世事是那样难以逆料。第二年就“反右”了,我在苦难中一泡22年;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去上海,虽然街巷大致依旧,但经历了“文革”10年,上海还没有恢复它的活力,颇有“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之感。有天晚上我专程去了老新雅酒家的楼下,哪里还有那个油炸馅饼摊,再找老正兴的鳝鱼糊、陆稿荐的百年老卤,也失去了从前的口味。
我才恍然,这二三十年可不是平常的二三十年,许多人事都被冲击得变了样呢!
不过我对上海的美好记忆却没有变!我相信,优良传统和美好现实总有一天又会融洽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