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就让它发生,你要做的是盯着它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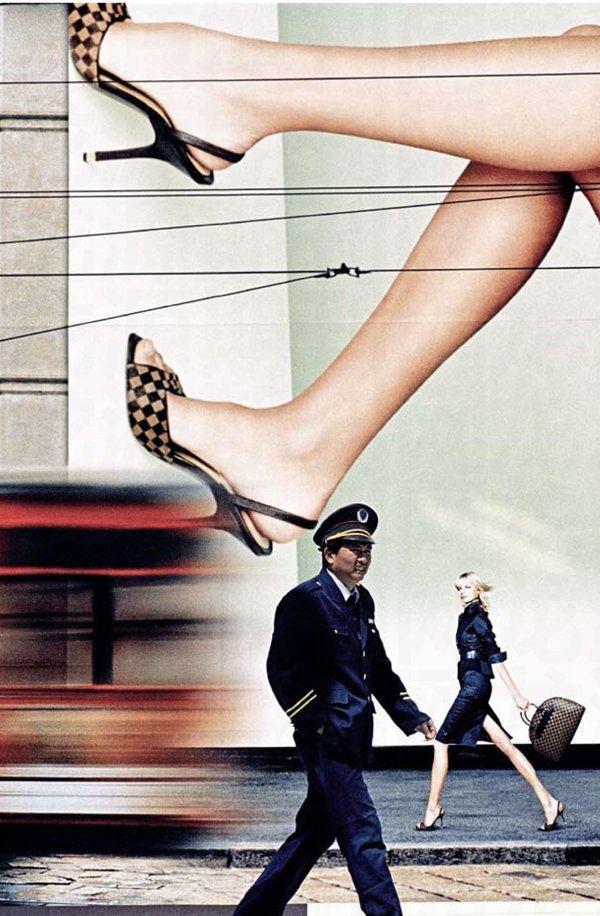

顾铮: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
雍和:我小时候就已经接触摄影了。我父亲经常在家拍照,有时候也会拿着照相机带我去公园给我拍,甚至带我到照相馆拍合影,所以我从小对拍照就不陌生。我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拍摄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去拍别人,只是拍自己,纯粹是留影纪念。1982年我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拍,看到好的景、有趣的人和事,就用照相机把它拍下来,这个时候就不只是拍自己,也开始拍别人了。
顾铮:1982年你开始有意识地拍摄时,是去外地拍,还是就在上海拍?
雍和:外地和上海我都拍。但那个时候一是因为眼界没有那么远,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就没有跑去很远的地方拍。1982年我去过苏州和杭州拍。真正跑到很远的地方拍,是以后的事情了。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周边地区拍,大概一公里或半公里以内的范围。我经常去的地方是我家附近的虹口公园,门票只有5毛钱,可以天天去。那个时候没有卡拉OK,没有茶座,公园就是市民的文化娱乐中心,单位、工会和团组织都会在公园里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就经常去公园拍。
顾铮:相对于拍景,你初期拍摄的兴趣和重点主要是人物?
雍和:刚开始拍的时候,我没有刻意要朝哪个方向去拍,只要看到有兴趣的东西我都会拍。公园里的活动、景,包括垂柳、荷花、秋天的落叶,我都会拍。如果晚霞很好,我就摆渡到浦东去拍,当时浦东还很荒凉,或者以外滩为背景拍。那个时候照相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也不是记者,所以看到什么都会很激动,都想拍下来,不管是景还是人,我都会拍。
顾铮:你最初的摄影作品是通过什么形式发表的?
雍和:最早是1982年5月向《大众摄影》和《摄影画报》投稿,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是在上海虹口公园拍的《击鼓传花》。当时拍完之后我把这张照片放大,压在家里玻璃板底下,有两个邻居看到了,说我拍得不错,可以投稿。那时我没有投稿的概念,觉得投稿是离我很远的事情。当时我看了《摄影画报》,觉得上面的照片不过如此,我的这张照片不能说比他们的好多少,但也不比他们的差。邻居再三劝说我投稿,加上我自己也觉得这张照片拍得好看,想炫耀一下,就同时向《大众摄影》和《摄影画报》投稿了。投了以后,都入选了,1982年7月,《击鼓传花》同时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这是第一次正式把自己的作品变成印刷品。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关心往哪里投稿,有哪些摄影比赛,什么比赛希望收到什么作品,投稿作品尺寸应该多大,对这些开始有一点研究了。
顾铮:你最早参加了哪些摄影活动?
雍和:80年代上海虹口区有一个文化馆办过一个摄影班,老师是孙燕君。我有一个邻居,比我小几岁,也喜欢拍照,我们俩就一起去报班上课,想提高一下。课上学的都是最基础的知识,什么是光圈,什么是速度。在摄影班上,我看到很多人拿着长枪短炮,背着摄影包,都是一些比较资深的摄影发烧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摄影这个圈子。
顾铮:那时你从事什么工作?
雍和:1973年我去崇明岛的上海市前进农场,1982年年底离开。在农场的最后两年,就是1981年和1982年,我人其实是在上海,但实际关系在农场,工资也是农场发的。那两年我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就拿着照相机拍照,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后,对摄影的兴趣就更大了。1982年10月,我调入上海公交公司,呆了几个月。1983年上海举办第五届全运会,需要人拍照。我的一个邻居在上海市闸北区体委工作,他向体委一个摄影干事推荐我,说我照片拍得不错,还得过奖,就把我临时调到体委去拍全运会了。全运会结束后,我留在体委帮忙拍照,一直到1985年《中国城市导报》创刊,我就被调过去做摄影记者了。
顾铮:在闸北区体委拍全运会的摄影经历对你此后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雍和:那时候没有大镜头,没有高感光度胶片,体育馆的灯光照度也不够,而且我只负责拍乒乓球比赛,别的比赛没有机会去拍,所以当时我对拍全运会兴趣不大。但这段经历还是让我在摄影技术层面得到了一些训练和提高,因为体育摄影对技术要求特别高,影像必须定下来,不能虚,这方面比一般的摄影要讲究一点。那个时候体委的老干事孙以嵘带着我拍,我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顾铮:这段经历其实对你接下来的新闻抓拍很有帮助,你既能抓住特定的瞬间,又能拍得很清晰。
雍和:1985年我进了《中国城市导报》,这份报纸非常专业,报道内容涉及城市自来水和煤气供应,桥梁和道路建设等等。80年代的上海是保守的,城市建设非常落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高楼、隧道、大桥几乎都是90年代浦东改革开放以后才建成的。所以对专业摄影记者而言,《中国城市导报》太小了,不能和《文汇报》《新民晚报》相比。报社提供的照相机、镜头都只有一个,胶卷也算得清清楚楚。上海大部分市民是不知道这份报纸的。
顾铮:我觉得《中国城市导报》会帮助你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雍和:这份报纸是周报,一个星期出一期。报社只会让你去拍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路面柏油重新涂过了,换新路灯了等等,这都是小打小闹。而且报社只有我一个人拍照,没有同行可以交流,报纸也被上海的同城媒体看不起,没有人愿意和你交流,所以这个时期拍照都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和报社没有太大关系。但在报社工作,我有大量时间可以拍照,也有了拍照的正当名义,还能够借工作机会到外地去拍,我去过广州、九江和山东,这在80年代是很难得的机会。
顾铮:当时整个中国对新闻图片的需求也不大。
雍和: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死气沉沉,我们看到的新闻照片,就等同于宣传片。现在的新闻照片还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那个时候的照片没有技术可言。
顾铮:社会对新闻照片需求不大的时候,你的拍摄兴趣和动力从哪里来?
雍和:1985年《中国仪器仪表报》在老上海美术馆办过一个“上海新闻记者七人展”,包括俞新宝、夏永烈、刘开明、还有我等七个人的作品参展。他们都是大大小小专业媒体的摄影师,有些人已经做了几十年的记者,甚至在国外呆过。那么我要展什么作品呢?我拍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新闻照片,我拿不出手。后来我选了20幅以暗调为主的黑白作品参展,看上去很深沉。这些不是新闻照片,但也不是纯粹的风景照片,我把它们的标题取得很有诗意,是有隐喻在里面的。比如我拍一个老太太后脑勺的一张照片,我取的标题是《默默地燃烧》。从最后的反馈来看,我的这些照片反响很好,和其他人的一下子就区别开来,影响也比他们大一些。其实我没什么新闻照片,就只有这些。那时候新闻照片在我的概念里也不能说“假”,就是宣传的感觉,我没看到过真正好的新闻照片。虽然我的身份是新闻记者,但我的照片和新闻没有关系,只是有一点社会隐喻在里面,不是完全的风花雪月,所以效果还是不错的。
顾铮:从《默默地燃烧》这个标题看,你的文学才华也不错。
雍和:那个时候我喜欢诗,在农场的时候也写诗。愤怒出诗人,那时候很苦闷,发泄的方式一个是借酒浇愁,一个是以诗言志。写诗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的。70年代中国时兴诗歌,有很多配乐诗。我们农场有两万多人,广播站除了播新闻,就是诗歌朗诵,背景音乐是《红旗颂》,我写的诗也有好几次在广播里播出。这是可以公开的诗,可以广播出来的。还有一种是“歪诗”,是发泄的、灰色的、愤怒的、埋怨的,这些诗很多只是构思,不一定要写出来,不过这种构思的训练是有好处的。
1991年安徽发水灾的时候,我拍的一组照片影响蛮大的。那时的国情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帐篷、棉被、食品等各种各样的救灾物资,那时一发水灾就束手无策,灾民看上去无可奈何,吃的麦子都是发霉的,人都是浮肿的。当时我拍了两次,冬天夏天各去了一次。那时候的影像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台湾《中国时报》的萧嘉庆,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他让我把拍水灾的照片给他寄过去,他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和照片一起发表。我寄照片的时候,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关于这次采访拍摄的感受,信写得比较放得开,不是很书面的语言,是我自己的语言。结果发表的时候,他把我的那封信放得很大,他说我这封信写得非常好,他要的就是这种东西,真实的、有感情的,不要那种冠冕堂皇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可以把摄影和文字结合起来,不要故意拿腔拿调地写,就写最真实的东西,大白话就可以。
顾铮:1991年拍摄安徽水灾的时候你还在《中国城市导报》吗?
雍和:那时候还在,我是1992年11月离开的,大概在那儿呆了6年。之后,我进了《青年报》,一直呆到1998年11月。然后进了《新民周刊》,呆到2003年11月,紧接着又进了《新民晚报》。在工作方面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轨迹。
顾铮:80年代,我记得《海南纪实》也跟你约过稿。
雍和:1982年我开始拍风景,这个也拍那个也拍。1985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跑到外地,去西藏、青海、云南等地拍。拍到后来觉得没什么劲,不知道出路在哪里。1988年有两件事情使我的摄影生涯发生了改变。
一件事是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新闻摄影周。摄影周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办讲习班,请法新社的记者和《国家地理》杂志的图片编辑等来到摄影周和我们一起拍照,一起分析。同时还有荷赛作品展,这是荷赛第一次到中国展出。这个摄影周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知道原来新闻照片可以这样拍,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照片。作为记者,拍了照片要发出去,否则只有几个朋友看,起不到传播效果,一定要把照片传播出去。那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网上一发就有人反馈,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发表。首先这个传媒用不用你的照片,就是一个反馈,你自以为拍得很好,但人家不用你的照片,觉得你拍得不好。而且就算要用,他怎么用,怎么压题,怎么帮你配说明,最后上了报刊,读者的反馈是什么。这些方面的知识对我都是有正面作用的,这是新闻摄影周给我的启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南纪实》开始向我约稿,这两件事情就搭在一起了。《海南纪实》是韩少功、蒋子丹这批作家创办的,是大众传媒性质的杂志,发行量很大。蒋子丹的老公是我的好朋友,在杂志社做副总编兼图片编辑,他需要一些照片,就跟我约稿。80年代末新闻业、出版业都比较活跃,我就开始帮他组稿、拍摄,一直到1989年7月杂志停刊。这段实践经历让我开始意识到关注照片的人不仅仅是所谓的摄影圈、艺术圈里的人,一般的读者和市民都会关注你的照片。他们关注照片并不是看照片拍得好不好,是怎么构图的,他们关心你拍的照片背后的意义。90年代上海发生经济转型,大量工人失业,社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城市天际线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和拍摄方法也有转变,就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拍摄的东西。
“这个时代和社会给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顾铮:进入90年代,中国传媒业迅速发展,大量照片开始出口。我记得你的照片不只在《青年报》上发表,一些境外的媒体也用你的照片。
雍和:给境外媒体比如路透、Getty供稿,就会让我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身边的事情。我们这里觉得是天大的新闻,拿到世界上人家根本不关心。我们这里可能很平常的事情,拿到国外,放到一个特定的新闻背景下,就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这样一来一去,就训练了我做新闻的方式方法,什么新闻是重要的,放在什么背景下去看这个新闻。国外的人特别想了解中国,了解上海,他们想看特定背景下的新闻照片,我觉得这样的照片才是有价值的。
顾铮: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你自己拍的时候不觉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在国外,通过发表时的处理让读者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和民生有很大关系的事情。
雍和:这样的例子蛮多的,我举一个拍股票市场的例子。2011年B股市场诞生,然后被关闭,后来又重新向全民开放。一般来说,股民会认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会想很多。我们本地拍B股市场的照片,最多也就放在财经版。但我拍的那张B股再次向全民开放的照片,在西方一些大报上做得非常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拍“中国制造”的照片。很多外国名牌产品其实都在上海生产,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代加工的事情,但国外就会把这张照片放在“中国制造”的概念下去表现。
西方大报会给我一些反馈,他会证明你的照片很好,发一些东西过来,比如哪些报纸用了你的照片,希望我多给他们拍。几次下来,就能训练你不仅仅是以本地视角来拍摄,更要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拍。本地新闻有本地新闻的做法,发生一起车祸撞了两个人,本地就是大新闻,但在西方就不是新闻。但如果是关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新闻,人家就可能有些兴趣了。拍摄方法最重要,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之后,可供拍摄的题材很多很多。特别是目前我们城市的环境问题,还有圈地、抢钱、假货、假药、有毒食品、空气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快速转轨期而产生的。这些问题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现在我们碰到了,就要传播出去,至少让它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被记录下来。
顾铮:像拍B股市场这种照片,是你自己有一种警觉性去拍,还是说有媒体约稿,让你意识到他们比较重视这件事而启发你去拍摄的?
雍和:这个是多方面的。媒体会先告诉你它需要什么东西,但如果你具有反思能力,就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弄清楚之后,你会用鼻子到处去嗅,用眼睛到处去看。你和其他拍摄的人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你不是和他们在共有的平台上竞争。我拍的照片不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发表,所以我对你没什么冲击和威胁。
顾铮:你刚才说,除了新闻摄影之外,你也看荷赛的作品。那么你觉得,真正的新闻摄影应该包含哪几个方面的要件?
雍和: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感兴趣去拍的东西,不管是不是真正的新闻,起码是和新闻有一点关联的,是有新闻由头在里面的,所以会引起我的兴趣去拍。或者说,我往往是以新闻作为一个由头就地取材。
我真正关心的是这座城市—上海,在近二三十年来是怎么变化的,这种变化使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在这个社会转轨、经济转型的形态下,他们的矛盾点是什么?他们有冲突吗?他们谁得意,谁失意,谁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大的环境里面,社会各个阶层所处的位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时代的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他们之间的联系、冲突、对立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和社会给上海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往往是拍这些我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多新闻要素夹杂在里面,但也不完全是新闻。我现在拍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所谓发表不发表。我们所说的新闻大多还是一种宣传。我做我的,他做他的,有的时候可以吻合并行,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坚持做我自己的。
顾铮:就是说,你是根据某个新闻由头来判断你需要拍什么东西。如果工作要求你拍的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会去拍吗?
雍和:有些东西是很好的新闻,但是我可能没感觉。举个例子,假如台风来了,建筑物、树木都被毁坏,造成很多伤亡,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第二天的报纸肯定都登这个。但是如果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刚才我讲的那些要素它就没有,我就觉得无所谓拍不拍。但是为了工作,我可以去拍。
我现在会放弃很多东西,我去拍的时候,着重点不一样。我介入工厂是来观察这个厂子里面的人,那些管理者是怎么对待工人的,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是幸灾乐祸还是诚惶诚恐?我挖空心思其实是想朝那个方向做,是在想问题。
顾铮:这些新闻事件在你看来是一种背景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各种表现才是你的重点。
雍和: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大喜欢讨论太理论性的问题,因为在理论方面,我可能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新闻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我拍的很多东西是从我想的那一点切入的,有很多东西是为我所观察的对象服务的。当然,我的这些想法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的,不是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根据生活当中我接触的人和事而得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些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改变。但是我的世界观是既定的,不会有大的改变。所以我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不会随便又跑出来一个世界观,还是在我这个既定世界观的框框里面。很多时候我是在寻找我需要的材料。有些东西其实是很好的新闻,但对我来说,尽管它是真实的,但和我没有关系,我就会忽略不计。
这也是真实—这个真实是符合我的世界观的真实。它和我对这个城市、这个时代的观察是吻合的,是我的所思所想。我不奢求拿着照片到各个报刊去发表,去赚稿费,我是想表现我的观察所得,我的想法和观点。在新闻理论上,我的这些观点可能是歪理、谬论,这一点我也存在疑惑,所以关于新闻,有时候我故意回避,我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顾铮:我觉得,你今天表述的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的。新闻,包括在其他人看来是大的、突发性的新闻,对你来说,它只是你怎样去考察人性、呈现人性的一个背景、舞台和契机。你很深入细致地去观察一些新闻事件里人性展现了什么,这些方面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机会看到的,是在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强烈作用以后才表现出来的。总的来说,是人在面对利益时的人性展现,这是基本的考量。但是新闻也不能缺少,无论这个新闻是突发的,还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出现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些新闻事件,人性的呈现就不一样。你的摄影,是从特殊的事件来观察人性中更根本、更内在的东西。
雍和:有很多事情,它不凑在这个场里面,它是不会呈现的。原来是分散的、没有关联的,然后发生了一个新闻事件,让这些不应该在一个时空当中出现的东西,在一个时空中出现了,发生了撞击。所以说,我往往把新闻作为一个由头,如果没有这个新闻,我也就没有办法切入了,也就没有我想要拍的照片了。
顾铮:包括你一直在关注的上海的拆迁、动迁问题。
雍和: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当天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日本领事馆开放绿色通道,所有的记者采访当场就签。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人问我去不去拍。当时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件事,我只要向单位提出来,还是有可能去拍的。但是我当时说,我不去。有很多年轻的记者就问,这么大的新闻事件,你怎么不去?
我就以这个事情为例来说,日本地震是很大的事情,但它毕竟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它发生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利益纠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懂日语,我不能深入采访,假如我碰到一个人在哭,我就不能问他为什么哭,是为损失的财产哭,还是为失去的亲人朋友哭?这些我都只能臆想。对我来说,真实是很重要的,假如那是我乱猜的,就不是新闻,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而且日本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民族,他们不会把喜怒哀乐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我没有去。
但是同样性质的一个事件,上海胶州路发生火灾,我就觉得要尽我所能去拍。胶州路火灾的灾民是我们全体市民中的一部分,他们遭受的灾难,其实是我们以前碰到过,或者以后会碰到的问题,所以我就会去关注这个事件。
再比如说,昨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金正日逝世了,上海有一些朝侨表演,你要去拍吗?甚至今天早晨还问我,上海几所大学里有一些朝鲜学生悼念,你去不去拍?我对前面说的歌舞表演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是哭是笑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但假如在复旦、同济和上海交大里面有这样一个学生灵堂,我倒很想去看看。我想看的不是朝鲜人的反应,他们哭是天经地义,我是想看看我们这些经历了文革的这一代人的后代是怎么来看朝鲜人的这个行为的,我想看他们的反应。朝鲜人的哭是正常的,我们国家也经历过那些苦难,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到我们前辈的影子。如果是这样的事我就有兴趣,就想去看看。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和我们有关联的,我才会关心,没有关联的,就算是很大的新闻,我会关心一下,但不一定会去拍。我有一个大的标准在,会有所取舍地去拍。
“无论是荷赛还是其他摄影比赛,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专业性。”
顾铮:现在有很多年轻记者,经常给荷赛投稿,他们把得奖作为专业业绩,认为得奖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认,你怎么看待这种投稿行为?你参加过吗?
雍和: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很赞赏他们参加。无论是荷赛还是其他摄影比赛,你都不能说它是最权威的,但是它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专业人士的认可,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且它能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只是各个摄影比赛评委会的价值取向可能不同。荷赛和在密苏里新闻学院举行的“年度新闻图片大赛”就有点不同,但是它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
我认为中国的记者去投稿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种对话,就像我以前给路透社投稿,其实都是一回事,只是反馈形式不同。能获得奖金和稿费对作者来说是一种补贴,是好事,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大的价值在于你的照片能够为别人所关注。当然,比赛和平常投稿还不一样,比赛的偶然性更大,所以也不能很绝对地说我投稿没中,就肯定是我不行,投中了就一定是好的。因为你投稿参加比赛,比如荷赛,它有一个主流价值取向,特别是获得大奖的作品,一般都是和它的主流价值观相吻合的,只会在一些个别的小奖上,有一些实验,有一些变化。
2008年第52届荷赛奖年度图片是美国摄影师安东尼的《陷入危机的美国经济》,当时国内就有人写评论说,荷赛今年发生变化了,以前都是战争、饥饿的照片获得大奖,这次大奖是金融危机的照片,荷赛性质变了。我觉得根本没有发生变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最重要的事件,这恰恰可以证明,荷赛在这一年没有发生变化,获奖作品和它一贯的主流价值观是完全吻合的。只是以前是战争,现在是经济领域的全球风暴。所以说,一些理论家的文章,我觉得可以不看,会误导人。你说它有道理吧,有点道理,他说变化了,是从战争灾难变成金融危机了,但是它的本质变化了吗?没有。就像我现在喝杯茶,刚才喝杯咖啡,不都是我在这个咖啡馆喝饮料吗?我的生活方式有变化吗?没有。
顾铮:也就是说,新闻事件对人的生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荷赛评奖的标准。
雍和: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关注到人。荷赛评选出的环境、风景照片,或者其他照片,都是和人的生存环境,或者说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存环境紧密联系的。比如常河拍了动物园里的一组照片,发表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和常河有过交流,我说,这些照片看上去都是动物,没有一个人,都是用LOMO相机拍的。但是照片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用意在哪里?我觉得用意并不在于是不是LOMO拍的,用平常的相机也可以这样拍,是方镜头还是别的镜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拍这些照片想干什么,你想告诉别人什么。有很多人没有看出来,只是被你黑白的、LOMO的效果吸引了,其实你关注的是动物的生存状态,而不是那些所谓的LOMO的东西。
“我始终是带着一种质疑的、批判的观点去拍,这才是我拍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顾铮:另外,从工作方式上来说,有的美国摄影家,他会有平时自己一直在拍的东西,而报社要求的东西,他也在拍。我觉得你的工作方式也有点类似这种。比如说拆迁,你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市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然后一碰到这方面的题材,你就会去拍,而且这个问题是你持续关注的。可不可以举几个你一直持续关注的题材。
雍和:有的东西从大的方面是有既定的想法的。比如说时间方面,你不可能拍到50年前的画面,也不可能拍到50年以后的事情,肯定是现在这个时间段,20年或者几十年。地点也是定好的,就是上海。也就是说,时空都定下来了,肯定是以这个时间和空间为主,每个人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就行了。没有谁对谁不对,没有谁一定要否定谁,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像我以前写诗,我不觉得是浪费了青春,愤怒一段时间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针对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不标榜自己什么都想清楚了,有很多东西是做一步看一步的,不要说我,连伟人邓小平都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设计师,他都看不清楚。有很多事情是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你设想就一定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也关注很多事情,但有些事情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去关注。或者说,不一定非要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果之后才去拍照。你觉得有疑问了,就先去切入,把它拍下来再说。20年前谁会想到强拆迁和房地产会演变到现在这个程度?
有些事情就让它发生,你要做的是一个很勤奋的观察员,要盯着它看。就像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观察员。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都会对时局发表一些看法,甚至用一些段子来表达观点。但是像我们这些人是用照相机把它记录下来。我现在就是用拍照把我平时想的、和朋友聊的、我关心的问题和事情,用照片来表现。照片只是一个工具,我用照片把我思我想呈现出来。但有的人只是聊天的时候讲,拍照的时候就换一个方法拍,他们拍的是另外一种风花雪月的东西,和我关心的现实没有关系,我不是说不好,只是他们是另外一种人,我是相对来说内外比较一致的。
顾铮:你刚才说你拍东西是从自己的观念出发,去捕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那么你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中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雍和:有一种说法,纪实摄影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的,不是歌功颂德,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记录一些事物。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对我的心思。因为我17岁就下乡种田,回城后在公交公司干了几个月,然后调到体委,后来又到报社,从小报纸到比较大的报纸,这一路走来我都是靠自己。但是我的家庭出身还是不错的,小时候生活也比较优越。17岁那年突然就下乡到农村,分到一个几百人的连队,在连队谁都可以指挥你,叫你干什么就必须干什么。
在这个社会生活几十年,我会不断地增加这种认识,而且这种认识没有大的改变。所以我的世界观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然现在还在不断地丰富,人的知识结构都处在不断地变化当中,只是大的方向和大的价值判断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具体到摄影方面,我的观念不是很具体,但我始终是带着一种质疑的、批判的观点去拍,我觉得这才是我拍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如果是很好的东西,也可以拍,但不需要我这么努力去拍,有很多人在拍,报纸、杂志等媒体记者都在拍,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我是用带有疑问的眼睛和脑袋来看这个事情,如果我能看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的价值就和别人有一些区别。我指的从观念出发去拍主要就是这种批判的精神,质疑的精神。这是一个大的观念,是对世界的一个整体看法,不是具体的观念。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我怎么去相信它,没有办法去相信它。
姚坤泽:我看你的作品,发现80年代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在风格上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你觉得这种变化反映了什么?
雍和:这种变化可能旁人会判断得更准确一些,我个人感觉我一直是这样拍的。现在我更多的是以一种批判的、质疑的眼光去拍,把拍摄对象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拍。
80年代的时候,在我还没有拍《海南纪实》上的那些照片之前,我更多的是追求新鲜、刺激和视觉效果,这方面考虑的比较多。现在拍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同。这些变化并不是刻意的,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过。我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记录变化上面,视觉这方面就凭本能了,没有太在意。就是说,视觉效果这方面会自然地融合进现在的照片。其实在视觉方面我可以再用点心,可能效果会更好,可以尝试一下。
姚坤泽:你现在对拍摄对象都了解吗?
雍和:基本上都了解,尤其是有特别需要的,我就会去问一下,多了解一些。去问一下可能就能问出很多情况来。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问问,采访不一定要拿个本子,一本正经的。和人家聊几句,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大致的脉络。有的时候是先拍好了,我再和他聊,有时候是边拍边聊,有时候是聊好再拍,都有可能,没有一个特定的公式。
姚坤泽: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拍出来的照片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雍和:有。有时候一下子就达到预期效果了,有时候拍了半天也找不到想要的感觉。
比如昨天和今天一大早,我都到外滩去拍那座大金牛。2011年股市又回到原点了,到年底,股市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包括机关、个人、散户、大户,都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关于股市,你怎么去表现呢?有些人可能会到某个证券营业厅去拍。其实这座金牛放在外滩,老百姓是会有一些想法的。我也有自己的一个设想,但是没有具体画面。昨天和今天上午我都在那里等,但是都没有等到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只是今天我拍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画面,一个男人摆了一个pose要拍照,他好像要把牛角扳过来一样。这个画面有一点象征意义,似乎在说这座金牛不听话。拍好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这个扳牛头的动作非常棒。这个就是了解拍摄对象的一个小技巧,跟他套近乎,套他的话。他说他是河北来的。我说,你做股票吗?他说,你看呢?他不回答我。他说他不懂这座金牛放在这里干什么。我说这座金牛主要是金融股市的意思。他说,是不是证券市场在这里?我说这后面都是银行,证券交易所在浦东。如果他说,唉,我今年亏大了,亏了300多万,或者亏了多少多少,如果他发一通言论,那么我做这个报道,就比较完整了。现在呢,就欠缺一口气。
“有时候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是可以吻合的,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姚坤泽:你怎么界定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不同?
雍和: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觉得新闻摄影有时不是纪实,有一些新闻,比如说我刚才举例提到的,好像是蛮大的新闻,但是放在纪实这个层面上,让它作为一段历史,或者作为一段记录生活的影像,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比如说,几棵百年老树被风刮倒了,因为这样的老树在上海并不多见,所以它可以作为新闻,但作为历史影像记录下来,意义不是很大。
再比如说火灾,上海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火灾,对一个里弄来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但是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新闻。有的火灾大,有的火灾小,但是,我判断这个火灾有没有意义,是需要更多地从社会层面去考虑的。火灾不一定大,不一定像胶州路那样的大火灾才有意义。上海乌鲁木齐路曾经因为动迁发生过一起火灾。一个房地产老板为了把一个钉子户吓走,烧了一把火,结果火没控制好,老人被烧死了。这个火灾的意义就不同于平常那种火灾。所以说,有的新闻照片可能成为纪实照片,有的却不是。
另一方面,纪实照片也不见得都是新闻照片。比如说记录一个弄堂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贫民窟里面一些外来人口的文化,它不见得有新闻性,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纪实的。记录一种生活状态或者它的变化,这是纪实而不是新闻。有时候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是可以吻合的,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顾铮:你喜欢哪些摄影家?
雍和:其实我喜欢很多摄影家,但我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觉得我只要喜欢他们的照片就可以了。可能布勒松这几张我喜欢,《新闻晨报》某个人的这张照片我也蛮喜欢。就是说,对我胃口的我就喜欢,我没有特别刻意地喜欢某个人。有好照片的人其实很多,拍照片拍了一两年,每个人都有一两张好照片,但是要拿出很多好的照片,就比较难。
姚坤泽:你认为什么样的照片才是好照片?
雍和:好的照片,一种是比较漂亮的,看了让人赏心悦目的。比如说咖啡馆墙上挂的,不一定要深刻,不一定要写实,不一定要批判,但是从美学方面讲,有意义就可以了,或者能够触动我心里的一点涟漪,也可以。这样的照片可能会引起我购买的冲动,或者我根本没有购买的冲动,但是我可以欣赏一个好的创意,这也是好照片。风光照片就一定不如新闻纪实吗?风光照片是必不可少的。咖啡馆里挂一张“糖水片”总比放一张我拍的很尖锐的照片看起来舒服,就是放在我家里也一样,我回到家轻轻松松的,当然想看一张有点愉悦的照片,血淋淋的照片放在家里干什么。但是在媒体版面上,就不能放那些风花雪月的照片。其实照片要放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看,不能混在一起。广告照片也有好照片,创意啊,景观啊,新闻啊,都有好的照片。
姚坤泽:你了解纪录片吗?
雍和:纪录片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纪录片的记录方式和我们拍照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原来想,哪天我不行了也去拍纪录片。我们想象中觉得纪录片和电视台新闻片子的工作方法有点像,不需要脚本、机位这些考虑,把现场完全记录下来就行了。其实纪录片很专业,真正拍纪录片,它的记录方式,机位等等要件,都是比较专业的,和我们平常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有些不同。
顾铮:现在纪录片的工作方式有些变化,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拿着一部性能上佳的相机,就可以去拍。我觉得,纪录片还是需要一个团队,但是现在很多纪录片都是一个人拍,一个人剪片。
雍和:也不是说一个人不好,一个人也可以拍,可能一个人也能形成一种风格,就算粗糙也是一种风格。但是从根本上讲,纪录片是一个多媒体,至少拍摄要一个人,录音要一个人。它应该有专业的分工。
责任编辑/ 段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