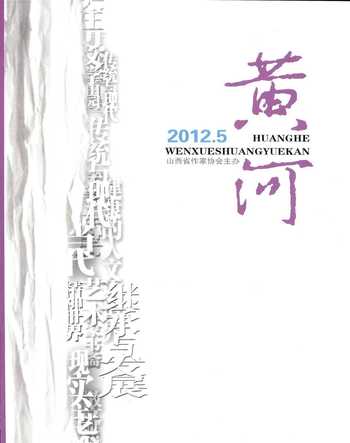城市二题
王瑢
细节
从太原回到上海,眨眼已七年。
上海给我第一个感觉,“节奏”快。生活节奏、学习节奏、行走节奏、做事节奏、说话节奏、思维节奏,甚至吃饭的节奏。
城市高楼密布,像驻扎在明街暗角处沉默守护,灰黑色的机器人。楼越来越高,人们像寄养在空中的鸽子。小区里每家每户,被厚厚的防盗门隔开,别说串门,打个招呼都是匆匆忙忙。走在路上,原本住对门或住隔壁的邻居,擦肩而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现代大都市的一种“病”。怀念儿时在太原上学,十几户人家住大杂院,主妇们下班回来,忙着烧饭,时不时探出头去聊几句,看各家孩子聚在一道玩耍,一天的疲惫在这种快乐中消失。那时候,一家烧肉,肉香四散,闻着也是一种享受。现代都市人,正被孤单侵扰吞噬着,压力是随时随地无形的一张网,越挣扎,困得越牢。不得不习惯“奔生活”。楼下保安手中的喇叭不停在喊:锁好门窗,防火防盗!
上海人烧菜讲究精致,一只鸡能变出十几种做法,青山绿水搭配几样小菜,一桌宴席就齐了;太原人烧菜讲究排场,盘盘碟碟,盆盆碗碗极为丰盛,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你若参与其中,人很容易就被气氛感染,到后来,杯子莫名端起。
每次回太原,最怕喝酒,亲朋好友三五成群,酒桌上吆三喝四,很是爽气,最后往往就喝高了,豪言壮语指点江山;上海人则不然,他们吃酒很少酩酊大醉,不是没有,是分寸把握得好,头开始微微犯晕,心里始终是笃定的。太原人就笑,说你们上海人喝酒小气得很,其实,那是拎得清。
女人的旗袍风情万种,身体线条曼妙婉转,走着,一步三摇,是上海特有的风景。听老人讲,二三十年代,开放与闭塞交界,穿旗袍的女人们,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第一记忆,旗袍成了年代的象征。张爱玲笔下的女子都穿旗袍,带着那个“小开衩”奔跑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奔跑出喜怒哀乐,奔跑出城市故事。在上海,穿衣打扮向来讲究个性,无论你穿什么,走在街头,绝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围观更不可能,上海人讲究自顾自。刚回来时,街边小巷随处可见有人穿了睡衣睡裤,这情景若是在太原,一路会有人观望,会有人脱口而出,呀呀,看nia(意:人家)穿的vai(意:那)是甚衣服就跑出来咧,啧啧!
走在上海街头,你会自觉跟随人流按部就班,红灯停绿灯行,即使是蹬三轮摇着铃铛收垃圾的,或短打赤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兄弟,也自觉自律,车行马路人走道,比较规矩。世博会期间,城市交通更加井然有序到质的高度;太原人生活讲究随意,走路步伐也优哉游哉,常常有行人走进机动车道去,逛街一样,司机也不生气,习惯了,摇下玻璃探出头,说一句,nia(意:人家)你也不怕(被车)挂上。那人回身一笑,像一幕情景喜剧。
细节,一闪而过,或流利清晰,像扑腾翅膀的飞鸟,是陌生人眼梢眉角的表情……记得有本书叫《读城记》,读一座城市,要读细节,细节里自然离不了人。
经常出差,一走十几天,隔壁阿姨每天会把那些塞在我家防盗门中的广告单一一取出来。又一次我堆在门外大大小小的硬纸箱子,来不及处理,忽然消失了,疑惑不解时,阿姨笑微微站在我面前,说我帮你叫了收垃圾的来,手心里摊着几枚硬币……我只是一个刚搬来的邻居,甚至还没有太多言语交流。想起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细节让城市更美好。
面食
被友人笑称“南北产物”——爸爸地道太原人,妈妈出自江南水乡。衣食住行,四大生活要素,饮食习惯上,我更偏向于上海人,骨子里虽有一半北方血统,对于太原面食,了解多多,却食之甚少。
山西面食著名,品种多,吃法别致,风格各异,成品劲道,滑利爽口,余味浓长,单是面食,便可成宴,从头到尾不重样。太原是省会,山西文化的中心,面食萃集,誉飘四海。常听上海朋友念叨,真喜欢吃你们太原的面食呀,都怎么变出那么些花样来的呀。
太原面食文化,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包括山西太行一带,黄河西岸中原段,更是北方农村文化的摇篮。古书有云:“立冬猛寒,清晨之会,充虚作战,汤饼为最。”冬,指北方冬天;汤饼是早期面食的总称。三十年代在上海,曾有《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甚是轰动,可见“面食”的名声效应。这里描写的,正是北方特有的冬天景象。汤汤水水一通吃喝下去,四肢舒坦,筋脉疏通,周身细胞都暖和起来。汤里多加些姜末胡椒,不但驱寒,还预防感冒。以前,太原人谁家女人生了儿子(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也讲究吃面,是一种民俗事项,好比过生日,无论老人还是小孩,一定少不了要吃“长寿面”。面条之长,象征寿命之长,反映出人类对生命绵长的心理追求。
爸爸一年四季要吃面,每次回上海,吃不几天本帮菜饭,就嚷嚷着要妈妈做太原面食吃。做法种类繁多,吃一个月可不雷同。用手指把和好的面撕成小片状,称“揪片”;一团揉到劲的面团端在手中,拿一把专用的薄片刀削出状似柳叶的面片,称“刀削面”;拿一根专用的铁筷子,把面分成细细长长的条,拨进锅,叫“剔尖”;稀糊状的面置于一只海碗里,让面溜溜像一根线那样滑进锅去,称“流尖”;还有一种现多在乡村农户家才可见到的,俗称“河捞”(也称“河漏”)的面食,很具“视觉”震撼力:把和好的面(要够硬)投入特制的河漏床(中间有圆洞,下方有孔,上面有与圆洞直径相差略小的木柱圆形头伸入洞中挤压)迫使面从下方均匀的孔内挤压落入锅里,河漏床引用杠杆原理,横跨锅上,待面压到一定长度,用刀从下方把面条截断,煮熟后配上各种浇头或打卤食用。我最喜欢一种面食,称“猫耳朵”的,现在上海市面也有的卖,但都是机器预先压好的,太原人家里多自己动手,面按要求和好,擀成厚匀合适的面皮(太薄会粘锅,不成形),先竖切成指来宽的条,再横切至指甲大小四方丁,用手指将小面丁一压一挤一搓,成猫耳朵形状,卤汁调配着吃,真正秀色可餐,一大享受。还有切面、拉面、刀拨面、擦尖儿等,不计其数。现在,人们饮食讲究“绿色”,面食也悄悄变化,白面里掺些荞麦面、玉米面、高粱面,或是豆面,做成包皮面吃,味道鲜美,利于身体健康。
妈妈喜欢上海人常吃的“酱油拌面”,煮好的面捞出沥干,加一勺葱油,面拌匀,淋上酱油肉丝,撒上葱花即可。爸爸不爱吃,嫌干,没汁水。太原人吃面,四季都要有“调和”,炸酱、小炒肉,素卤荤卤,把香菇、黄花菜、豆芽、黑木耳等作料跟炒好的肉丁加水慢火炖,是太原人常吃的面卤,连汤带面哧溜哧溜吃,想想就过瘾。小时候记得妈妈每年都腌番茄酱,夏天番茄质优价廉,买很多来,家里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装满,红彤彤一片,厨房间、卧室的窗沿上,屋里四处角落,摆一溜,到了冬天,炒酱或浇面条,经济实惠,太原百姓最喜欢的味道。
频繁穿梭于太原与上海两座城市间,传递南北面食的味道,不枉被称作“南北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