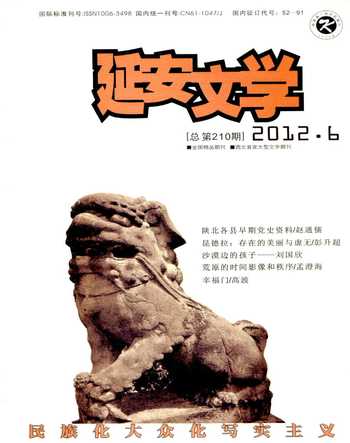远逝的歌谣
苏世华
此生爱歌,已是无可改悔的宿命了。但对于歌坛,我却无些许贡献。尽管,天赋的乐感和中学时校乐队的自学使我可以把第一次观看的电影电视上的插曲或音乐基本无误地记录下来,九十年代中期在延安师范读书时我所参加的男声四重唱曾获得一等奖,但却未尝试着去做一首歌,因为我总觉得那是专家们才能做成的事;尽管上学时作的歌词就曾在《上海青年报》发表,被许多艺术家看好并获当时延安地区民歌创作大奖赛上惟一的一个歌词一等奖,但经我们当地的作曲家谱曲歌唱家演唱后竟然连十里路外也没传出去,从此,便断了我想在歌坛有所作为的想法。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当我陪《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朋友在延采访,一次偶然的联欢中他们听了我被逼无奈唱的《三套车》、《小路》及一首歌唱故乡春天和父兄、初恋的歌后,几个人拥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如此好的条件,特别是对歌词的理解和感情的处理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为什么从小不学音乐呢?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好好用功呢?
对他们夸张般的话语,我苦笑一下,未作回答。他们哪里知道,当他们穿着干净的少先队服在北京少年文化宫伴着风琴和黑管演唱时,我黑瘦弱小的身躯正背着一捆比我大得多的柴在陕北的悬崖畔上一步一挪地往山下走。
还有,饥饿的肚子;
还有,布满一道道血痕的手臂……
但歌曲,对我,她的确是魅力无穷。印象最早最深的一首歌,是在故乡的田野上听的一首歌。那天,一位高年级同学在家乡的小路上边走边唱: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着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听歌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呆立在了小路边,眼前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神奇的地方:蓝天、白云、骏马、挥动鞭儿的牧人、欢叫着飞翔的鸟儿……啊,世界上竟然有那样美丽的地方!多少天,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那美妙的旋律和动听的歌词,向往着那个神奇的地方,幻想着我已飞到了那个美丽的地方,骑着一匹小马儿,拿着羊鞭赶着一群洁白的羊在辽远的草地上走,身边,是一群群欢叫着飞翔着的鸟儿……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正是红色歌曲到处传唱的时候,天天听的都是“革命歌曲”。对现在为数不少的年轻人否定排斥的革命歌曲,我觉得有许多非常动听,甚至可以成为经典。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唱毛泽东医疗卫生路线治好聋哑人的歌叫作《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老师在学校教会后倒没觉得有多好听,但公社大喇叭上每天清晨播放的根据这首歌改编的大提琴独奏曲,把一个渴求解放的生命在灾难面前的痛苦和对有声世界的渴望、期盼以及恢复听觉后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拨动了那么多的善良的心灵,叫人感动不已。
那时候,七八岁的我,还常常把一些歌听得风马牛不相及。记得二年级时,延安城调来的一位女教师用非常好听的声音给我们教唱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歌,我当时学会的是“小王公社缝手巾,洗开家家好生活……”,等十八岁那年在伊犁河谷巡逻,在漫长的夜色中怀想家乡的一切,哼唱这首歌时,突然觉得自己丢了人!枉为一个“读书人”,准确的词应该是“向往公社丰收景,喜看家家好生活……”或许是童年时学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歌词虽然是理解错了,但那优美的旋律和悦耳的歌声却三十多年来一直回响在耳边。
在物质、文化生活都陷入饥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姚店中学上高中。我与胡向东等几个爱好文学、音乐的校乐队的同学,拿着好容易才借到的一本《外国民歌三百首》,每天下晚自习后,关紧教室门窗,点着蜡烛,神秘、紧张,又十分感动、幸福地低声哼唱俄罗斯民歌。记得当时唱的最多的是《三套车》《灯光》《小路》《喀秋莎》《红梅花儿开》和《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等,优美的歌曲给我们这些整天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农家孩子开启了一扇偷窥世界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望到生活竟是那样的多姿多彩,那样的美好迷人!通过这扇窗口,我们望到,在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上,一个赶车的青年正在忧伤地唱着他那将要被财主买去的老马,为今后苦难在等着它的凄凉命运而伤心悲叹;望见在梨花开遍天涯的时候,一位美丽的姑娘望着远方,深情地歌唱她的爱情;望见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第一次发现,歌曲,竟然把残酷的战争和温柔的爱情表现得如此和谐,如此美好!……
中学毕业借到渴盼多年的《静静的顿河》后,厚厚四卷本的书我几个晚上就读完还给了主人,但第一卷扉页上的“哥萨克古歌”却盘据在我心中几十年挥不去。我怎么也想不通,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歌词!它把酷爱自由,靠骏马和刀剑、靠生命和鲜血生存的哥萨克人对土地和顿河的浓烈感情表现得那样的震撼人心!不知有多少日子,在干完繁重的农活后,十七岁的我一人坐在无人的河边默默地吟诵、品味着这首歌(无曲谱):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
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妇人,
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
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
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
就这样,俄罗斯民歌,如一位慈祥的母亲,用她不竭的乳汁,给严重缺乏营养的一代人以滋养哺育,使他们的感情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使他们的精神走向充实,品格走向高尚,灵魂得以健全。在那个年月,在这个国度,有多少青年是靠唱着这些歌而走过来的呵……
电影《农奴》,是二十年前在风雪边防线上看的。时过境迁,详细剧情已记不清了。印象中这部电影与它的主人公一样,寡言而少语,但表现的内容很沉重,很厚重,艺术感染力也很强,特别是它的主题歌《无字的歌》(作者名之)。曲子深情辽远,优美动听,歌词简单明了,平白如话,但它对心灵的撞击却是非常的强烈:
阿哥,你听我说,
我为你唱一首歌,
我只能唱一支无字的歌。
为了我的歌,
你也要活……
一个没有自由的农奴,在皮鞭和刀剑的压迫下,在到不了爱人身边的情况下,用歌来传递她对心中深爱着的人的关心:为了我的歌,再苦再难,你也要活下来!这简直是撕心裂肺的恳求了。蓝天之上,它已经比白云都纯粹了;蓝天之下,已没有比这再真挚的感情了。这种歌,岂能不动人心魄,感天动地!
还有一首歌,在我心灵中占据的位置也很重要,它就是歌唱造反起义的英雄的颂歌《嘎达梅林》。八十年代中,刚从延师毕业分到枣园职中任团委书记的我同时兼办公室主任,其实是学校行政杂务。当前任抱来一摞旧唱片交接时,我一眼就盯在了这张唱片上。尽管这是一盘交响乐,不是歌曲,但我神往它已多年了,因为童年时读一部反映草原人民斗争的小说时那歌词已刻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啊,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那时的我,根本就不可能买得起录音机之类的奢侈品。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便在大喇叭上反复播放这首曲子。常常是把唱针搭在唱片上后,我走到校门外的原野上一个人站着听。好在对别人,那只是一个单位活力的象征,是当时一种普遍要求的必做的事,除我之外,没有谁会去认真听那些乐曲,故也没人提出意见。乐曲的那种苍凉雄浑,那种悲壮慷慨,那种惋惜慨叹,叫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而这种难受又是一种难得的高尚的享受。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文艺的复苏,密林群鸟欢鸣般的歌儿仿佛一夜间便飞满了世界。应该说,在那个文艺的春天,我们压抑了多年、积蓄了太多的情感的艺术家们或出于对经历过的苦难的倾诉,或出于对走出阴暗的庆幸,或出于对充满阳光的新时代的热爱,或出于对久蓄的能量的渲泻,一下子创作出了那么多的优秀歌曲。那时候,好像走到哪里人们都在唱歌,都在倾诉,而且都是那样真挚、真诚。那个时期,好歌的确是太多了,作为在山沟里劳作的农人,我所能接触到的,肯定比城里人少多了,但由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国家文艺繁荣的关心,真正的好歌我觉得我没有错过几首。印象较深的有《在我童年的时候》、《乡恋》、《月亮之歌》等。写到这里,我又要提一句影视。我以为,歌曲和影视,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姐妹。歌曲为影视增加了感染力,使它更具有打动人的力量;影视为歌曲提供了翅膀,使它可以在一夜之间飞遍大江南北。《在我童年的时候》把电影《小街》中一对年轻人在那个年代的辛酸遭遇以及他们进入新生活后的迷惘失落渲染得令每个观众怅惘不已。通过纯洁透明美好爱情的破灭来表现现实,编剧是够残忍的了。它的旋律伤感哀怨,它的歌词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在红色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一对恋人,丢失了用生命相爱的女友的主人公心内充满忧伤和哀痛,但那唱过来唱过去的歌词却是相反: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唱起它,
心中充满欢乐……
它的旋律,它的歌词,在那个年代,是一度流行的青春通行证。我觉得它是对一代在荒谬的年代丢失了青春和爱情的年轻生命的哀婉的咏叹,是一个时代的挽歌。唱歌的人都是用眼泪和心灵在唱。进入九十年代的《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这两首歌,现如今人们可能已听烦了,早不新潮了,但它们在当时的那种轰动效应却是破纪录的。那些优美如诉的旋律,那些优美如诉的词语,加上歌者那纯朴、宽厚、温柔的女中音,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为饱经创伤的一代人安抚灵魂的作用。
产生于八十年代初中越反击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有一首歌曲非常感人,歌词纯朴如小儿在梦中对母亲发出的呓语,曲谱优美如远方孩儿对母亲的诉说,但由于它的背景是激战后静下来的战场,是一弯黄色的月亮映衬着的经过战火洗礼的山峰,是抱着吉他给母亲唱歌的年轻的战士和聆听的战友,以及卧在战士身边,同样静静地聆听的战场上的一只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力,打动了无数颗关心着南疆风云的心灵。我记得歌词是:
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
常对着月亮甜甜地笑,
它是我的好朋友。
不管心里有多烦恼,
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
心儿像白云飘啊飘。
当我守在祖国边防的时候,
常对着月亮静静地照,
它像妈妈的笑脸。
不管心里有多烦恼,
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
心儿像白云飘啊飘。
只要月亮照在我身上,
心儿像白云轻轻地飘啊飘。
月亮,我的月亮,
请你夜夜陪伴我;
月亮,我的月亮,
请你夜夜陪伴我,
一直到明朝……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能打动灵魂,能使心灵为之颤动的好歌我听到的很少。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引起轰动的歌”,君不见在那些转播或直播节目中场面居然是那样的狂热,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为之疯狂的原因所在。那几个被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老学生们捧为“星”的老眉茬眼的“天王”和“星”们过来过去地贩卖着那几首被他们唱了几十年,赚取了青年们无数眼泪和钞票的陈旧的歌子,在台上扭怩做作,丑态百出。尽管在利益面前丧失了良知的媒体不惜版面不顾脸面地与经纪人一同阴谋着阳谋着煽情的手段,但我从他们的歌中还真是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感觉。我闲下来时也想,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说真正的好歌,真正的好歌手确实已很难找了,山中无老虎时,猴子也总得找几只来凑数;另一种是说也可能是我自己真的落伍了,听不懂歌了。但在这个荒凉寂寞的年月,一首关于国人在海外谋生丢失了爱情的歌蓦地扑入了我们的心怀!出于为剧中制造特定的情境,这首歌的曲子尽可能地想表现些“异域风格”,但它的词却一下子打动了那么多人的心灵: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
热情已被你耗尽,
我已经变的不再是我,
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问我到底恨不恨你?
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当人们揪心于主题歌悲愤的质问,关切的心灵为之焦灼不安时,更多的心更被本剧的另一首插曲创伤。与主题歌相比,它的词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失恋失爱,但那低缓忧伤的曲子和体贴入微的歌词却更具有深入心灵的力量:
相约如梦,誓言如风,
你的笑容使我心痛。
歌词如诗。但它道出的何尝不是无数个失去爱情的心灵伤痛的写实。我以为在表达爱情的伤痛上,它已成为经典之句。
青春是血,爱情是冰,
一切终将消融。
忘了昨天的约定,
别再有海誓山盟。
我已经是看客,
请让我走得从容……
歌曲把一个失去了相爱多年的爱人,痛彻心骨,但面对强大的世界又无力抗衡的人在命运打击下那种绝望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激起每一个有此遭遇的心灵的强烈共鸣,使这些破碎心灵的抑郁情绪得以释放,孤独的心灵得以慰藉。人类如同兽类,越是受伤的部位,越是要时时去舔;越是伤害了自己的刀剑,越是要刻刻去想。因之,真正的心灵深处的创伤,在这世界上是无药可医的。写到这里,我想谈一句对歌曲的看法。我以为,对一首歌而言,最重要的,永远是它的词,这应是一首歌的灵魂。是打动心灵的力量之所在。真正好的歌词,是给这个世界上承受苦难的人写的,是给纯净高尚的心灵写的。是直接触向人类心灵深处最纯洁、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的最神奇的力量。它言人之心灵同感,发人之笔下皆未。它表现的应该是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东西。也有人不这样认为,说词根本无所谓,只要是一个名家的谱曲,就能受到欢迎,就能流传出去。他们还给我举了诸如“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那道河……”和“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之类歌曲的流行情况来说服我。在这点上,没有人能说服了我。红极一时的东西这世界上太多,但它们更多的是重复昙花的命运。做为歌词而言,若没有使心灵震撼的力量,就不可能走向永恒。
九十年代末,一首以世俗话语为名的歌突然唱出了人的眼泪,令我等无能之家族长子弟妹长兄为之心颤,它的名字叫《心太软》。当时,我正在远离延安府城的北方大山深处扶贫,初时无电、无水、无路,除日夜揣在怀里的一个微型收音机外,这个世界的信息几乎与我绝缘。数天数十天后捎进深山的旧报纸便成了我难得的精神食粮。一天晚上,开完生产会议,村干部们吆喝着下山走了,我一人躺在荒凉的山梁上土窑洞的土炕上就着煤油灯读去50里外的乡镇上赶集的农民捎回的报纸时,一篇批判“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章吸引了我。文章很有些文革遗风,批判的锋芒很锐利,大意是这首名为《心太软》的歌太腐朽太萎靡,听了会消蚀人的意志,使人无革命斗志云云。因不知道此歌究竟有多“萎靡”,也不喜欢动辄戴帽子打棍子的文风,随手便将报纸扔掉了,《心太软》这个歌名却留在了心里,但感觉却是怪怪的,估计不怎么样,是否有些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直到有一天,我跑拉电修路项目回到延安城里,时逢星期日,职能部门不上班,便应三弟之邀去他开办的“苏三面庄”吃饭。等待吃饭时,餐厅服务员在用录音机放歌曲,突然一首歌的几句词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脏:“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一身扛!……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坚强,你这样到底累不累?……”此后的歌词有的未听清,有的记不住,但这几句词我从此再不能忘记。当时感觉,这首歌就是写给我的,是写给我这样的家族的长子,姊妹的长兄的。一个寄予了贫寒农家希望的长子,一个被弟弟妹妹们眼睁睁望着的兄长,一个独身闯世界的瘦弱青年,他根本不具备与这个强大的世界抗衡的力量。这个家族有那么多事要他去做,那么沉重的大厦要他支撑,他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但他必须要坚强,必须要强迫自己硬撑起来!我想起了为父母治病四处奔走,想起了为了给多病的父母满足心愿少年学生的我去深山林场求购寿木,想起了在冬日的寒夜去几十里外去找外出数日未打招呼的弟弟,想起了为弟妹的上学工作我八方求告……那一天,我一遍遍放着那首歌,疼痛中的心感受到理解和安抚。我感谢词曲作者对中国文化中“长子”、“长兄”的关心,感谢他们用这么一首被政治文人批判的“心太软”安慰了似我一样无能为力却责任重大又无法推卸的长子、长兄。我们这些人,也是需要理解需要关心的呀。
九十年代歌界最令人痛心的是李娜的离去。读者朋友大概也已注意到在我的文章里,是第一次提到一个歌手的名字 。我不是一个慕“星”者,更不是一个“追星族”。我所从事的工作,曾无数次地接待和安排那些“大腕”和“星”们,他们与我们也很好相处。我没感到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当人们趋之若骛地与他们合影时,我都躲开了。我尊重这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但我要去崇拜一个人,恐怕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至今,我说不出任何一个歌手的有关情况。留在心底的记忆全都是歌曲本身。至于哪首歌是谁做的词,谁谱的曲,是哪一位歌者唱的,则根本没有用过心思。之所以记住了李娜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境界,一种属于西藏和佛教的境界,一种属于祟高和庄严的境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凡脱俗的境界。它具有一种净化心灵和再造灵魂的力量。透过声音,你眼前出现的是空旷、辽远、巍峨、大气,你心内感受到的是纯净、虔诚、庄严、崇高,你听到的不是歌声,是天籁之音,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很大一部分来自歌手的再创作,来自歌手本身。其它的歌,风格相近的歌手们都能去唱,但这首歌不能。除李娜之外,谁也唱不出它的灵魂。我始终认为,是那个远离红尘、给无数双眼睛留下一个飘逸背影的圣洁的歌者,成就了这首歌。在用心灵和生命唱出这首歌后,歌者永远走入了她自已也被征服了的那个境界,那个庄严、圣洁的《青藏高原》。她不会再走出来了,红尘的功名利禄对她已没有了任何的诱惑力,她本身已化成了那片巍峨庄严的青藏高原。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再听这首歌了(到藏区也是这样)。尽管出于各种目的,各方的组织者们常常安排人唱这首歌,尽管我们那些可怜的“新秀”们一直在不停地声嘶力竭地模仿她。每听一次,我的心灵上都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我无权阻止他们,我心痛的是,那歌声,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那不是歌,是天籁之音,而天籁之音是不会常有的。这首歌是幸运的,它因李娜而成为圣歌。李娜是幸运的,她因这首歌而成为“圣女”。仅就这首歌,李娜在人们心中获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称号,我以为她是受之无愧的。
这就是歌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