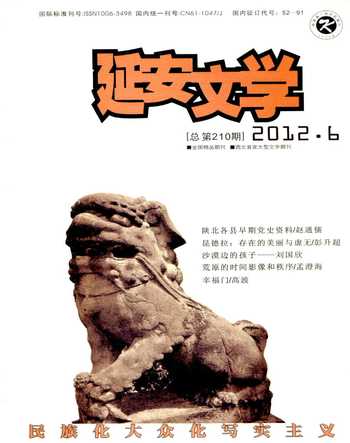荒原的时间影像和秩序(外一篇)
孟澄海
我走进荒原的时候,第一次感到岁月的诡秘和模糊。那种被人比喻成河水的东西呈双向流动,一方面指向过去,一方面指向当下。在时间的不断冲洗下,有一些事物变得朦胧、隐秘、空洞、迷茫,而更多的则显现出或壮丽悲凉,或哀婉绮丽的风貌轮廓。荒原之上是辽远无际的天穹,之下是沉默无语的岩层黄土,时间穿行于其中,漫漶苍茫,给人留下无尽的怅惘和惶惑。
大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吹来。大风过后,荒原一片岑寂。野花与芨芨草停止了晃动,几只狐狸摇摇摆摆地走来,而后又向干枯的河岸走去。狐狸的眼睛闪过草丛的时候,一两只野兔便飞快地跃起,朝荒原深处逃遁。我看见只有花朵上的瓢虫安然酣睡,它们的翅膀上点缀着黑色的斑点,宛若微缩的星星。对一颗豌豆般大小的瓢虫来说,辽阔的荒原不啻是一个宇宙,神秘而险象环生,但它们却没有任何恐惧和担心。瓢虫闭上眼,透明的翅膀星点闪烁,与天空的银河相辉映。
河床龟裂,粗砺的裂纹一直延伸到河岸,像褐色的皮条,拧紧了大地的忧伤。古老的河岸裸露着身躯,没有植物生长,甚至连地衣青苔也无影无踪。从剖面上观察,河岸的立面构成十分复杂,沉积岩,石灰岩,花岗岩,页岩,泥沙,煤层,一叠一叠向上累积,仿佛是向天空打开的书页。时间的纵深处依次排列着寒武纪、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二叠纪、炭灰纪……远古的动植物遗骸残留在岩石的罅隙中间,生命早已消亡,骨骼变作了化石,跟石头一起沉没。一只蝴蝶和一颗贝壳,一片树叶和一瓣花蕊,都呈现出坚硬、冰冷的质地,无语述说沧桑。
时光随着苍天般的唐古特海一同消隐和退却,亿万斯年之后,只剩下苍凉的轮廓——忧伤得让人落泪的祁连荒原。我站在河岸上,发现在狰狞丑陋的巨石背面,仍然有水的痕迹。那些痕迹一圈一圈的荡漾开来,织成一张变幻莫测的图案。石头的花纹银白闪亮,从水迹的四端扩散,犹如几缕白云,恣意地书写着浪漫。在死去的岁月中,石头的灵魂与水的灵魂互相纠缠,宿命般地倾诉着开天辟地的秘密。海水跟石头走过的心路历程,最终都结束在死寂荒凉的地方,把黑色的咒语呈示给人间。我靠近一处背着阳光的沙丘旁坐下来,举目彼岸,波动的地气若隐若现,恍惚间正有浩渺的海水逼近。我窥见了海底的珊瑚树,还有游动的海洋生物,它们伸开触须,托着宝石蓝的波纹朝我走来。而那一棵嫣红灿烂的珊瑚树,慢慢抖动着苍老的枝干,把金币般的叶子洒落我的心灵……
在荒原上,有一些苍狼的洞巢,幽深,黑暗,蛛网密布,经年的雨雪从外面灌进去,更显得潮湿、阴冷,像极了老泪纵横的瞎眼。祁连山下,那种充满灵性和智慧的动物——苍狼,如今已不见了踪影。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匈奴跟苍狼的故事。据说,一只红海的公狼与一只黑海的母狼交配,生下了一只毛色青苍的黑狼,黑狼一直跟随着西伯利亚的寒风,走进了河西走廊的大荒原,在头曼单于征战四方的时候,它偶然一次闯入了牙帐,形影不离地守护着单于的爱妃阏氏,从此,苍狼就成了那个游牧民族的舅舅。公元三世纪前后,西方的一个地理学家曾读到过一本羊皮书,里面就记载了这个神秘的传说。可惜那本书后来失传了,据称被一个信仰萨满教的人带进了自己的棺椁。
萨满是匈奴单于身边的神职人员,巫风鬼雨的年代,他们夜观天象,作法荒原,一把锈迹斑驳的铜剑直通神灵。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他们可以带着苍狼,漫步于亡灵的世界,还能通过神秘的巫术,让死去的尸骸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萨满使永不可逆转的时间发生神奇的倒流,让苍狼的影子与亡灵重叠,幻化成美丽妩媚的少男少女。
然而,我目睹到的依旧是死气沉沉的狼洞,或者说,能感觉到的是时光浓重的背影,它与萨满苍狼毫不相干,倒像一黑色的青铜饕餮,隐藏于荒原腹地,伺机吞噬一切。苍狼消失以后,洞穴归于寂静,日寒草短,月枯霜白,春风的吹拂中,一墩一墩的狼毒花枝叶扶疏,猩红的蓓蕾在阳光下绽放,妖媚,灿烂,有着一种先验般的隔世孤独。
我去了一个叫东西灰山的地方。据考古工作者说,那里应该是祁连山荒原最早的人类遗址。从出土的文物看,有石刀,石斧,石臼,属于新石器文化遗存。几十万年过去了,灰山依然平静如初。青草寂静,野花寂静,石头寂静,流水寂静,所有的寂静凝结成一种大孤独,大悲凉,在八荒四合间氤氲、弥散。一条狭窄的沟渠横卧于山脚下,接受秋阳的抚摸。渠沿两侧的土层下,隐约可见被碳化了的小麦颗粒,那些遥远古老的植物亡魂,深埋在坚硬的土壤之中,永恒地守护着枝青叶绿的春梦。一个远去的村落就这样安睡于西风白云之下,一任岁月在它身旁静静流淌。石头沉默无语,而打制成的男性生殖器官却坚挺张扬,在时间的抚摸下,传递着父系社会的信息。生命崇高如山,也许,当我们置身那个原始神秘的氏族时代,面对稀少单薄的种类,崇拜的不是神,也不是英雄,而是男性的一颗睾丸。茫茫的荒原中,就是那一颗种子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春天,带来了瓜瓞绵绵的希望与憧憬。
废弃的梦想和繁华,时间的残骸以及不朽的睡眠,还有盛开的马兰野菊,飞来飞去的蝴蝶蜜蜂,这一切构成了荒原魔幻奇诡的生死影像。走进荒原的时候,给我心灵巨大震撼的,是那些古城废墟。一个叫永固的地方,曾经建有匈奴王城,越千年之后,隋炀帝西巡,还在此接见西域七十二国使者。史书上说,城阙巍峨,宫殿林立,尽显皇家气派。可以想象,如此规模的都城,里面会有怎样的世俗场景。是胡马啾啾,腥膻弥漫的游牧风情?抑或是朝歌夜弦,风帘翠幕的汉族生活?不管做如此推断假设,都离不开繁华与风骚,只要闭上眼,就能看见商贾走卒的背影,歌姬舞女的长袖,当然偶尔也会看见阴谋与陷阱,刀光,杀戮,血腥,嚎哭……
不过永固城最终还是坍塌了,变成了残垣断壁,时光的洪流把绝代风华疑义湮没,飞镝沉落沙土,琵琶喑哑黄昏,舞殿长满荒草,宫廷成为猪圈。在古城周遭,我们只能与累累的汉墓对话、低语。而幽暗阒寂的墓道里,瓮棺破碎,窟窿连着窟窿,像深藏幽冥的瞳孔,无望地打量着云卷云舒的天空。
走离那个古城废墟,我在荒原的一处芨芨草滩前停住脚步,弯下腰时,发现那里有许多蚂蚁正忙碌着建设自己的家园,它们托起比自己重量大几倍的土粒,费劲地垒筑窝巢。在蚂蚁王国里,那个皇帝和皇后安然地睡在宫殿,享受荣华富贵。
时间的沙漏点点滴滴,在苍茫的荒原,蚂蚁仰望世界的高度,能超过人类吗?
被月光和青草湮埋的声音
我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一个有月亮的黄昏,月光在薄薄的雾气中氤氲,像一朵朵澄碧洁净的蓝色雪花,飞翔或飘动,之后就消失在青草和花朵之间。寂静与月光同时弥散开来,慢慢地爬上了我的指尖、头发、皮肤,再一点一滴渗入骨髓。似乎就在那些青草茎叶颤动的瞬间,我听到了那种声音,从草丛深处传出来,是轻微的喘息和呻吟,夹杂着植物倒伏的响动,仿佛黄昏的露珠坠落,沿着花蕾的边缘,在美丽的蕊柱上盘旋,带着潮湿芳香的气息,向四周扩散。那时候,我感到声音是有形有色的,它在我的面前停下来,逐渐扩展、膨胀,像一个巨大的气泡,笼罩了我所有的感官。片刻的窒息过后,我恍惚幻化成一条青绿的蛇,在迷离朦胧的月色中追逐那一种声音,直至深入到青草根部,随着叶脉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飘荡……
这个场景出现在遥远的年代,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我是在走进一个废弃的园子的时候,听到了那种声音。那个园子先前住过人,主人是地方上的绅士,有两房太太。他的房子带有穿廊,朱门雕窗,庭院深深,后门与河相望,前门连着巨大的花园,花园里种植着月季和玫瑰。后来,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主人被划为地主,判刑入狱,家道衰落,两个太太先后离世,房屋被风雨侵蚀,坍塌腐朽,最终成为废墟。花园里的鲜花也渐渐枯萎死亡,代之而起的是狗牙花和荒草,偶尔还会闪现出狐狸与野兔的身影。记得是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穿过废园的豁口,慢慢靠近那些房屋的老墙,在一处拐弯的地方,那种声音就钻进了我的耳朵。事实上,那声音只传播了几分钟,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来不及捕捉更多的细节,声音就倏然而去,宛如一片雪花溶进了土地,被草叶和花朵所吸收,反正什么也听不到了,剩下的是寂静—空空荡荡的寂静。而站在我面前的是蓝水晶般凹凸的天穹,以及挑在荒草穗子上的月亮。村上的人传说废园里有鬼魅出没,是女鬼,专门吸食男人的精血。我想到那情景,头发簌簌地竖了起来,但过了不久,声音再次传了过来。这一回,我听到的是荒草嚓嚓啦啦的响动,之后,分明有一男一女两个身影从草丛中闪了出来,好像低语了几句什么,就匆匆分手,男人向村南走去,女人则沿着河岸,不急不慢地朝北方的山坳里移动。他们很快被夜色淹没。留给我的只有远处的树影,以及树影背后的草垛和山峦。
而那种声音却一直纠缠着我的肉体与灵魂。我不止一次地踏入废园,于朦胧的月光中寻找神秘的青草地。我甚至固执地认为,在声音出发的地方,肯定会留下男欢女爱的物证,给我提供更多想象的空间。然而,我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青草茂密,草叶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微风吹过,露珠纷纷落下去,无声无息。在草地深处,马兰花绽开的蓓蕾上,栖息着一只硕大美丽的黑色蝴蝶,翅膀并拢,触须一动不动,仿佛沉浸在一个幽深诡秘的梦境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那种声音的边缘,好像被一种潮湿而混浊的气流包围覆盖,即使在白天,只要闭上眼,那声音就从地下飘出来,紧紧握住我的感官,把我拉向黑夜深处。橙黄的月亮。碧绿的青草。蝴蝶。瓢虫。纷扬的草穗。影影绰绰的老墙。神秘的男女背影。所有的事物在那种声音中呈现、浮动,然后又悄然消失。在迷朦隐秘的幻境中,声音总是拖着一条紫蓝色的光带,来回在青草地上空盘旋,缠绕着那些苍老的浮云。有时候,声音越走越远,我看到的只是废园里的亡灵,像一盏暗红的灯影,游弋,闪烁。
我高中毕业后,跟几个亲戚到铁路上打工。我的工作是帮助他们清理路边的石子,把乱七八糟的枕木码放整齐,活计应该说比较轻松。我们的工地紧挨着一个繁华的集镇,那里有一个湖泊和坟场,到了夜晚,镇上的青年人都三三两两穿过坟丘,来湖里游泳。有一回,我去湖边打水,刚绕过芦苇丛,就看见一对恋人,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亲吻,抚摸,旁若无人地做着该做的事情。我又听到了那一种声音,是呻吟和喘息,紧张,急促,热烈。但那个傍晚没有月光,事件的背景是一片墓地,在远处是集镇高耸入云的水泥厂烟囱。声音传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火葬仪式,或者说,在我面前倒下去的是两具尸体,惨白的肉体和骨骼,轰然溅落的骷髅……
那个夏天,我们就住在铁路旁边的窝棚里,陇海线上的火车每隔一小时,便疾驰而过。火车留下的声音很特别,尖锐,坚硬,震耳欲聋。也就是那个夏天,我在低矮潮湿的窝棚里,读完了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丁洁琼和苏冠兰的爱情纯洁而美好,凄婉神圣的故事把我带出了故乡的废园。此后,我感到那种声音一天天远去,停留在记忆中的也仅仅是美丽的月光和青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