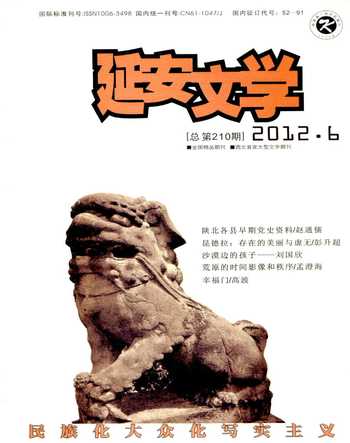走上杨家岭
杨葆铭
一条黄土小路,两排白杨树,老远便望得见杨家岭礼堂的楼顶。这座用陕北的石头砌成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礼堂而今已失去了它的使用功能,变成教科书中一帧能唤起人们历史记忆的老照片,变成了让亿万人进行精神宴会的所在。
后人已经无法知晓毛泽东当年幽居这里时的心境。那条黄土小路上是否还存留着他悠然散步的足迹,那白杨树的窣窣絮语是否在阐释着他那奇谲难测、天马行空、缜密而又多变的神秘思路。岁月没有使这条窄狭的山沟退出人们的记忆,杨家岭礼堂依然在温煦的冬阳下闪耀着光芒。
逼人的寂静和朴素,使得每个游人来到这里,都要下意识地整衣正冠,犹如朝圣。曾汇集过时代英才的神圣礼堂而今空空如也,只剩下一排排杨木花椅像一条条经历了海浪颠簸的帆船,在将革命送往胜利的彼岸后,停泊在这里,来接受游人们的抚摸。毛泽东的大名气派而大方地被写在了礼堂中央的横幅上。这个早年不过是一介寒儒的卑微书生,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乡村教师。但当他看到神州板荡离乱,万民翘首,以大旱望云霓之心盼英雄出世来拯救风雨飘摇的破碎山河时,他毅然脱去了长衫,带着一支起义失败后的残军到井冈山寨落草起家。这个集湘人的强悍、顽缠、坚韧、不畏强暴、敢为天下先等诸多鲜明性格于一身的草根英雄,用自身所具有的丰沛的生命力光源在罗霄山脉点燃了星星之火,并迅速使其得到蔓延。他将身处底层、心怀绝望的万千民众所共有的诉求准确地化成通俗易懂,能得到及时传播的口号,并将这口号付诸行动。他坚信小石子终将能砸烂大水缸,他洞察到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伟力蕴藏在民间。他将他组织和指挥的战争称之为人民战争,他将他发动的运动称之为群众运动。他雄视千古,蔑视王权、强权和霸权,对秦皇汉武的文治不足、风雅稍逊敢放言评说。可对于“小石子”他却恭敬有加。他知道,一颗单个儿的“小石子”看来并不起眼,可一旦将它们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庞大的积方,就足以填埋掉盘踞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大水缸”。
杨家岭三面环山,十分向阳。尤其是南北两翼的山脉,蜿蜒多姿,蔚然深秀,属陕北地面上风景绝佳的形胜之地。刚从征鞍上下来时,毛泽东面容枯槁,神色疲惫,可入住杨家岭没多久,他的体态就变得健壮起来。就在离杨家岭不远处的一个名叫凤凰山的山脚下,他刚刚锻造出一柄倚天方可抽取的利剑。其时,倭寇日逼,半个中国已经沦陷,可这位战略大师竟在一孔窑洞中看到了这场大战的最后结局。他是一个先知,他的许多精准的预言让人感到吃惊。二十一岁那年,他看了一本小册子,开头的一句“呜呼,中国灭亡有日矣”的话刺痛了他。他随即发下预言式的狠话:吾辈竭诚奋斗,不出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将得到彻底改造。结果,三十五年后,他的话得到验证。这一次,中日之间的一场空前恶战已经展开,算无遗策的毛泽东看到这是一场以中国广阔的空间来换取时间的持久战,并预言,这场战争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国人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至少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结果,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日寇投降,刚好八年一个月零八天。人们喜欢将天才的预言家视为先知,视为是受到“神”的某种启示的超人。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演绎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无数传奇,使得人们在他面前除了爱戴和颂扬之外,甚至会失去正常的心智,感到手足无措,语言贫乏。当他被尊为“神”之后,又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这时,我们突然发现,他身上所笼罩的巨大光环并非是由人为的热情所造成,而是在于他自身具有一种如阳光普照万方的天然魅力。我们越是理性地审视他,就越发感到他超群绝伦,是一位凡躯之“神”。他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立了垂之久远的不朽功绩,更在于这些业绩具有着明显的毛氏徽记始创性。查遍史籍,遍观前朝,历史上有哪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将政治、军事、哲学乃至艺术中许多难以言传的玄机操持和运用得如此潇洒和娴熟。他打仗神机妙算,不拘常法,出神入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组织者。他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很高的审美意趣和广博的人文知识。他的诗词融曹孟德的沉郁顿挫、李太白的飘逸高蹈、苏子瞻的旷达豪放于一炉,风调独绝,文情并茂,且气魄之大,无人可及。他的书法笔意纵横,天上一笔,地上一划,起承转换看似随意,实则有大章法蕴含其中。他又是语言大师,讲演平易生动,文风朴素自然,历史典故、村言俚语被他顺手拈来,化成口语,让村妇老叟都能听懂。他善于打破神话,又在不断地创造神话般的传奇。他敢将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作为党代会的闭幕词。那一年春天,就在这座礼堂的中央,他绘声绘色地讲完《愚公移山》的故事后,不到五年,便径直登上紫禁城外那座朱色的城楼,振臂一呼,一个民族的新纪元开始了。
顺着石砌的山路缓步而上,礼堂背后的几孔土窑洞就是他当年栖身的地方。这位出生在湖南水乡的农民的儿子,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大半生将会在中国的北方度过,他生命中最鼎盛的岁月将会留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当他第一次穿着草鞋走完了湘乡五县,他的家乡就再也挽留不住他了。他一旦跨上马背,整个中华大地不够他驰骋。而一俟安定下来,便按照经济的原则,只给自己选一块能够散步的地方。就在这所小院里,他日夜劬劳,忧念天下,漏夜披览,寄意寒星。这时,我们发现,此时的他已不是建党初期的那个雄姿英发、面貌丰润俊朗的毛润之,亦不是在马背仰天吟诗,在矢石交攻的征战之地谈笑风生的毛泽东,他已经由一个具体的人外化成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用手摸不着,只能用智慧去了解的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被我们称颂为光耀千秋的毛泽东思想。诚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卡莱尔所言:“任何时代,只要能找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且这个人又具有时代所需要的思想与智慧,这个时代就会得到拯救。”中国人经过苦苦寻求,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为了将这个人确定下来,杨家岭礼堂主席台中央为他空开了位子,使他成为我们的“船长”。那一年春天,当他用绵长的湖南口音,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致完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后,礼堂内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这掌声,作为对他思想的回音,不仅热烈,而且长久。
先哲有言: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令人称奇的是:能结出硕大的物质结果的思想却往往产生于穷乡僻壤,正像圣洁的雪莲生长于苦寒之地,高雅的莲花生长于泥淖之中一样。每天,络绎不绝的人流涌入杨家岭这条狭窄的山沟,他们到这里来拜谒,凭吊,沉思。那些受好奇心驱使,将研究毛泽东传奇一生视为乐事的西方学者,每当看到这朴素的窑洞,简陋的陈设,无不惊讶地耸起了双肩;那些经过战火洗礼的老兵,满头的华发辉映着胸前的勋章,他们在儿孙的搀扶下,在这里的每一件遗物前都伫立沉思。而更多的人是来自遥远的都市和偏僻的乡村,他们在对世风日下、物价飞涨的抱怨中,却慷慨地将印着他的头像,具有国家体制象征的百元大钞悄悄地塞进他盖过的被子里。而那些身穿T恤的莘莘学子,刚看完教科书,又来到这里借助眼前的实物将书中的那些抽象概念给予重新理解。看一看他盖过的粗布被褥,用过的劣等笔砚和悬挂在窑壁上的发黄了的地图,估摸一下这一切在游人的心灵上所产生的崇高的教化意义。伟人故居里所陈列的每一件实物,都携带着一种特殊的气息。它在无声地告诉人们:有那么一些人曾在这里居住过,生活过,现在故去了。假如这些故居和遗物对活着的人在道德方面有某种教益的话,那么,它首先蕴含的是对那些出入于豪宅之间,安坐在“宝马”之内,虚皮胀鼓、徒事奢华、喜欢“扎势”的庸碌之辈所具有的深刻的讽刺意味。
感谢历史,感谢造化,它在不断演进和变换过程中总能将一碗水端平。它在给了江南水乡以丰饶的沃土和秀美的景致的同时,也给了黄土高原这一历史的殊荣。杨家岭因了毛泽东的大名而声名远播,由一个荒僻狭窄的山沟变成了令人心仪的朝圣之地。我们知道,谈论伟人和英雄的最佳处所应该是在纪念碑下或博物馆内,但毛泽东是人民的毛泽东,他具有更广泛的民间性和世界性。餐桌前,茶馆里,出租车内,篱笆墙下,他的名字在口口相传中又被附丽上各种华彩,以至使得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又被外化成千百万个不同人心目中的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镌刻在水晶棺上的他的生卒年月只是一种时间的表示,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似乎未曾离开过我们一天。从卡拉OK里传出的“红歌”里,从手机的彩屏上,从拳王泰森和NBA球员强健的臂膀纹绣着他的头像上,从钢琴王子理查德弹奏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乐曲而引发万人掌声雷动的场景中,让人看到了一种非时间所能够湮没了的东西。任何一个伟人,都得有一个远比大理石和花岗岩更为坚固的基座,这基座就是人民的感情,而毛泽东恰恰赢得了这种感情。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毛泽东以万分悲痛的心情为罗荣桓元帅写下的这首悼亡诗,其中会不会含有一种对身后的自况,我们不得而知。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么高。”燕雀只能在蓬间飞来转去,而鲲鹏的疆域是在扶摇九万里的云霄之外。
“奴仆眼中无英雄”,是因为奴仆根本不懂得伟人和英雄都是在与对手的较量中成为伟人和英雄的。正像奴仆只配去欣赏奴仆一样,只有与毛泽东较量过的对手才真正能知道他的厉害,能知晓和掂量出他存在的意义和分量。
红日当空,杨家岭一片明媚灿烂。守护在礼堂两侧的白杨树伟岸挺拔,与礼堂顶端比肩而立。山坡上,颂扬他的民歌小调从牧羊人的口中唱出,随风飘来。这歌声在告诉人们:丰碑,一旦植入到人的心田,就不会有倾塌或被风化之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垂之久远的伟大功绩和为我们提供的永恒的实际学说与他的英名一样,不会有最终的长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