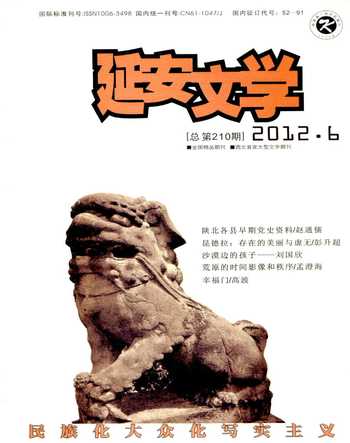别动我的地盘
杨逍,原名杨来江,1982年生于甘肃张家川。作品散见于《飞天》《青海湖》等。出版诗集《二十八季》。
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吴克意外地停下了手中的活,招呼手下的五个小工休息,大家大喜过望,一个个说着讨好的话,卸下手套,围着吴克坐下来。他们用兔子似的眼神期待着,吴克笑了笑,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按照大家的要求逐一分给他们。这是中午老板过来检查时,大家托他借的生活费。吴克把剩下的数了两遍,确定是五张才装起来。这是他今年借生活费最多的一次,按理说,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的衣食住行包括电话费都是老板报销的,几乎没有自己掏腰包的机会,可吴克偏偏就毫无理由地借了五百块。
老板还会隔三差五地开着他那辆皮卡车拉上他去猛灌一回,两人提着乌海二锅头的瓶子狂饮,直至瓶子倒地。那时候,吴克总是在车上大喊大叫,扯开嗓子唱一会儿歌,又唱一会儿秦腔,老板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痛快,得劲,也跟着他唱。
在吴克看来,他和老板之间是透明的,谁心里有一丝的猫腻都逃不过对方的眼睛。中午老板给钱时,他眯着眼说晚上有行动吗?吴克当时没接话,老板就冲着他嘿嘿笑了两声,拍着他的肩膀说要小心身体。吴克知道他说的是找小姐的事,老板曽多次为他物色美女,但吴克都以找小姐不能让别人埋单为由谢绝了,至于为什么不能让别人掏钱,吴克有自己的理由,他觉得这种事倘若是别人掏钱,那就等于是拿着自己的身体为别人干了一回事,心理上有些被动。也许是他对多年来听命于人,给人做事太多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吧,总之,他没有和老板一起找过小姐,但在老板眼中,吴克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且坚信他经常背着别人干这种事。
既然有钱了,就得花出去,而且要在一个短期内花出去,要不然等大家都没钱了,他就得在大家的同情中领着他们去蹦迪吃烧烤。十月份的时候,他余下了一百块钱,而这一百块钱最后还是被小六子拿去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小姐挥霍了一夜,最可气的是他还得以学习的名义陪着去。其实,对于找小姐,吴克是成天挂在嘴上的,也极力地怂恿别人去。民工对女人是敏感的,即使是和他们一起脏兮兮进进出出的女工,大家也会想入非非,他们在给女人打主意的同时,总会不断地忏悔,乞求心里安宁,乞求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儿老小原谅,但他们控制不了自己,毕竟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和自己的女人是疏远的,甚至有人在寒冷和困顿中会连自己女人的模样也模糊了。这肯定不怪他们,怪就只能怪生活和命运,所以吴克也和所有的弟兄一样,有着他们身体饥饿时的需要,有着他们同样的欲望,唯一不同的是,吴克没有自己的女人。
大家坐在一起愉快地交谈着,时间缓慢地流动。小六子兴致勃勃地为大家讲述了上次和吴克一起去找小姐的事,他一甩头,右手的两个手指不停地在空中指指戳戳。你们不知道,咱们吴头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那可是个有意思的去处。老幺那个老王八蛋把我们领到了地方,就跟一个年龄和他一样大的女人走了,那个女人丑哎,粉粘在脸上掉渣,额头就像乌海的山,还穿着裙子,屁股大得出奇,一走一扭的,那娘们儿一上来就抱住老幺亲了几个响,老幺捏了捏她的胸,屁颠屁颠地跟着走了,神气得像只公鸡。小六子摸出一颗烟,点着后猛吸一口,顺了顺气。其实,我们也怕啊,他接着说,你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没去过的人肯定以为是善良的老实人家,门口坐着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剃了光头的中年男人,院子里大约就三四个女人吧,他们简直就是一家人。当那个男人走出的时候,我们就溜了。
大家哄笑起来,开始攻击小六子。吴克坐在硅铁炉边的高台上,想着钱的事,他想应该找个小姐花一次吧,以免大家把他当成软蛋。与其让他们质疑自己的能力,还不如拿出实际行动让他们看看,他也不想在这群男人堆里把自己搞得很另类,与那只在所有的羊们都吃草的时候回头张望的羊一样孤独。同时他也想到了工程,还有三个烟罩子(硅铁炉两侧的抽烟机)做完就结束了,这将意味着老板在这个叫宏达的硅铁厂的生意也在这一年里宣告结束了,也意味着再有十天的样子他们就该打包过年了,还意味着他在这一年里能干的事也不多了,该犒劳一下自己了。
巨大的厂房里,二号炉子正在出白天的最后一次铁水,天车在轨道上滑行,缆绳时上时下,倒腾着铁水和慢慢硬化的硅铁,铁水溅起很高的浪花,在即将暗下来的空间里跃动着,那个质检化验室的小女人抖着一身肥肉,一边用还算漂亮的脸向吴克这边瞟着,一边用铁夹子往簸箕里捡拾几块溅落在厂房外面的小铁块,不时地用小锤敲碎拨拉着。大家立马躁动起来,向她吹口哨,那女人神气地甩甩头,用近似勾引的笑回了一下,扭着屁股走了。厂房里的热浪层层袭来,大家身上的汗又一次不断地往外冒。
小女人走后,大家平静下来,下班的时间近了,小六子又在众人的催促下开始讲述。你们可别笑啊,我们溜是溜了,但最后还是进去了。小六子一副得意的样子。我们蹲在巷子口,好像是叫李家巷吧,就那个刚进市区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的小巷子。当时咱们吴头说要剃头,可他的头刚剃过,还是汗毛,他那是故意。大家冲着吴克笑起来,吴克也跟着笑。后来我们还真去剃头了,可谁能想到,那个剃头的女人却是拉皮条的,她边剃头边问我们要不要女人,我们说要,她马上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三个女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退役下来又重操旧业的那种。有个戴眼镜的年龄好像小一些,大概也就二十七八的样子,可她不但丑,指甲里还满是污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扫大街的。倒是那个穿白裙子的还行,我问那剃头的女人有没有好一点的,她说其他姐妹正在上班。嘿,弟兄们,她说是上班,新鲜啊,她们把当妓女也光荣地称之为上班,那我们算什么。我问价钱,那女人说是四十,我犹豫了一下,倒不是因为钱,主要是质量不行,可谁想那个戴眼镜的马上说三十也行,瞧她那样,让人倒胃口,我说我要那个穿白裙子的,那娘们非要四十不可,我咬咬牙说四十就四十,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去了前面那家院子。
大家又议论起来,郭子问吴头去了没有?几个人又说起吴克来,对他那次行动捏造出许多版本。
吴克还是坐在硅铁炉旁边的高台上,抽着烟,想着花钱的事。要不就不去了吧,找小姐有什么用,那只不过是快活一时的事,弄不好还会染上什么病,得不偿失,况且,万一遇到讹诈怎么办。想着找小姐带来的诸多不好,吴克又想花钱买东西,他想到了父亲和儿子,家里就只有他们爷俩了,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他有两年没有见到他们了,想他们。吴克想到这儿,不觉脸红起来,他觉得他没有资格去想他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但他还是愧疚。父亲应该老了很多,这么多年来,他承受了太多的不如意,大风大浪过后,他肯定是脆弱的,衰老了,那高血压也不知道有没有好转。儿子现在应该是十一岁了,上五年级了,奖状都贴满了整个屋子吧,也不知道懂事了没有。可他目前连他们的一丝消息都没有。还是买点东西寄回家吧,给父亲买一包茶叶,最好能再买个血压仪,给儿子买一套新衣服。吴克想到这,似乎对钱的去向有了眉目,可恰恰在这儿他又犯起了更大的愁,他知道父亲不会接受他的东西,因为两年前他已经在他的世界里把吴克踢出来了。他是个倔强的老人,容易进死胡同,一旦进去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如果寄东西回去,他老人家绝对会在胸口的剧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重新昏倒一次,然后在病中把一切都塞进炕眼里喂火,吴克了解父亲,所以他很快就打消了这样的花钱方式,他知道这样花钱不可能,但他还是想到了,在他看来,想到了就是忏悔一次,忏悔一次他就会轻松一回。
大家对于吴克的议论最后仍然归结在以前的结论上,没什么新意。的确,吴克在和小六子一起嫖娼这件事上,没有做出让大家改变对他看法的事来,他的做法让大家在觉得可笑可怜的同时产生了怨恨,他们认为你凭什么就可以鼓励别人找小姐,而你却装作圣人一般东躲西藏,南遮北掩的?凭什么呀?要么就是那玩意儿真有问题,当然,这样的话他们当着吴克的面没人敢说,只好说吴头是胆小鬼,怕女人。
吴克冲大家笑笑,示意小六子继续,小六子像是受到了鼓舞,清了一下嗓子,接着说,我和那个女人进了院子左侧最里间的房子,房子的低矮和灯光的昏暗再次证明了廉价的含义,那娘们掩上门,要我先交钱,她怕我调戏后不投入战斗。我骂她说这又不是牛肉面馆,凭什么先交钱?但她死活不肯,说面馆里不吃饭只喝汤的人多的是。无奈之下我只好先交钱,她把钱点了一次迅速地装进胸罩里,就势躺在铺着一张芦席的床上,催促我快点。
四周静下来,大家都瞪圆眼睛看着小六子,小六子从他们咕咕发响的喉咙里看穿了他们火一样的欲望,但这又使他很为难,对于接下来的问题,他很难说出口,并不是赤裸裸的情色使他难于启齿,因为对民工而言,讲述一场性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博得大家的尊敬,而倾听则无疑是一次奢侈的享受。小六子的尴尬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和白裙子女人之间的那场看似轰轰烈烈的性事,是他历经多场战斗之后的一个污点,它并不像书上说的那样动人心魄,小六子为此懊恼不已——他在白裙子女人的极力撺掇之下毫无章法地迎接战斗,从而在战斗的开端先行败下阵来,让那女人白白赚了四十块钱。事后,小六子为了证明自己驰骋疆场的惬意,用因焦急而生的满头大汗向吴克进行了炫耀,他把吴克的手两次放在他的额头上,让他摸摸,并底气十足地强调这是一场不可多得的硬仗,而那时吴克已经在小旅馆里喝了一瓶二锅头,他没有怀疑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夸张地向小六子作了一番极为羡慕的恭维。小六子知道,事情的真相已经不可能重现,他只能继续作假,但又很难保证在这些饱经风霜的男人中,难免会有人听出破绽,万一被揭穿了,那岂不是大丢面子。
几个人已经急了,他们不断地催促小六子不要卖关子,快些接着往下讲。小六子故作得意地冲吴克笑笑,吴克站起来,说下班吧。
吴克还是提前半个小时宣布了下班,就在二号炉子的最后一次铁水冷却下来,并由铲车全部拉走之后,他宣布下班。其实吴克没有想到下班,他只想着钱的事,也许就是小六子得意地笑暗示了他,使他误以为下班的时间到了。命令宣布了,他才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做好下班的准备,他对钱的去向至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准确地说,下班对吴克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下班后永远都是盲目的。
可到底已经下班了,不能把命令收回,再说收回也没有多大意义,今天的工作在他看来应该是做完了。大家大叫着关了电焊机的电源,收拾了工具,一齐唱着“妹妹你坐船头”,走出了巨大的厂房。
大家去工厂的澡堂洗澡,此时正是空闲的时候,澡堂里显得异常清冷。女职工的澡堂在外面,他们进去的时候,刚好听见两个女人爽朗的笑声,小六子就向门缝里凑,郭子在小六子的头挨上门帘的时候,在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小六子就向前一挺,破门而入,女人大叫流氓,大家大笑起来,像是打了一次胜仗。
洗澡就像赛跑,每个人都想争取时间,他们觉得一天里最令人兴奋的时间就是洗澡。洗澡就意味着今天的工作结束了,也意味着今天已经挣到了八十或者一百块,同样意味着城市的夜晚已经伸开了手臂即将拥抱他们。
十分钟后,大家都走了,而吴克才刚进入状态。空荡荡的澡堂里,蒸气弥漫,不时有水滴从头顶落下,打在他的后背上。隔壁女人的声音依然隐约可见,或者是女人已经换了,但他没有注意这些。正如书上说的,吴克此时进入了无限的莫名的悲凉之中。他一点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才有这样糟糕的情绪?而这样的坏心情的源头又在哪里?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被人控制的麻雀,想飞却又飞不走。
水从吴克的头顶漫过全身,他无由地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女人。那个叫小芙的女人在吴克的记忆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他甚至无法准确描述那个女人的容貌了,那一举一笑就像一只小巧的风筝在空中展开,是那样遥远。可女人的影子却与日俱增地重复出现在他的眼前,只要一闭眼,就会出现,连同那把血淋淋的刀一起出现。他的印象里最为明亮的就是那把刀。刀在某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无声无息的刺进女人的胸膛,是她自己刺进去的。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了,那时吴克刚好二十岁,他身上孩子的习气还没有褪尽,和他同样大的孩子还在上学或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所以他压根就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一切。
记忆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不可靠。吴克只能想到那把刀和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天上没有一丝云,阳光把一切压得低沉,让人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吴克会想到霉变这个词语,他说那天的空气有发霉的味道。他从山上摘了一筐桃子回来,就看见父亲蹲在厢房的廊檐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阳光斜射过来的金属光泽直接打在他的那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上,下摆的那一大片血变成了灰黑色。他挡住了厢房门口的阳光,不停地大把大把抓着自己的头发,仿佛要连同头皮一起撕扯下来。
至于那把刀,是他发疯一般向厢房里冲的时候,他从阻拦他的三个叔叔的胳膊缝里瞅见的,起初他以为是刀扎在被子上,可后来他就看见了开药店的驼背八爷硬生生从女人的胸部抽出了那把刀,剩下的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很多天后,当他重新醒过来的时候,他曾试图分析当时的情景和后来的事,但都因为那种戳心的疼而不了了之。所以他有时候怀疑自己的记忆简直就是想象。
水依然流过吴克的身体,一如书上说的那样,冰凉的时间也流过了吴克的身体。这种冰凉就这样持续了十年。他有些怕那个家,家里的一切还是和十年前一模一样,包括他和女人以前住过的厢房,也是十年前的模样,那块被女人临死前打碎的大衣柜上的镜子依然棱角分明的露出一个大大的豁口,像一张嗜血的嘴。他没有换,他怕家里冷飕飕的风和那种持久的发霉的气味,甚至更怕阳光斜照在厢房的门口,那白花花的一片。
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吴克做一切坏事:打架,赌博,喝酒。他知道他伤透了父亲的心,可他觉得除此之外,他无事可做。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找女人,他想他完全能对得起小芙。吴克蹲下,像做了错事的孩子。那水,白花花的一片,像极了当年的阳光。
如果说失去了女人的吴克一直沉浸在对亡妻的悼念之中,那也能够称之为忠贞,如果他能再娶并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话,那他也能够回家和父亲团聚。可谁能想到,两年前的吴克还是背叛了自己。
吴克马上就想到了两年前那个淫雨霏霏的秋日。他也弄不明白十年前的那个夏日和两年前的那个秋天为什么总是会同时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像一对孪生姐妹,他知道,疼痛始终是能够重复的。
那个八月的晚上,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天气有些寒冷,吴克在李元平家里打了十五圈麻将,李元平睡着了,像个死猪一样,推都推不醒,李元平的女人坐在炕角为她织一条围巾,时间过了凌晨两点,大家都提议说让李元平的女人弄些吃的来,李元平的女人有些为难,吴克说要弄只鸡来吃,大家说让吴克去弄,吴克说要和李元平的女人两个人去弄。事情突然得没有任何预兆,等大家清醒过来的时候,吴克已经领着李元平的女人逃跑了。书上说的是私奔。
吴克想到这里的时候,脸红了,血液开始加剧循环,似乎是一颗仇恨的种子慢慢发芽。他们的私奔并不圆满,那个女人在他们逃到乌海之后,偷着给李元平打了电话。于是,吴克就在偷着乐了几天之后,被李元平领着人从乌海抓回了老家,他像罪犯一样被圈起来,接受了李元平和他的朋友的审讯,最后,他拿出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才得以了事。这件事导致了吴克和父亲之间的彻底决绝。从那时起,他就没有了家。
水依然从吴克的头顶倾泻下来,他仰起脸,紧闭双眼,又一次看见了阳光,刀,阴雨和李元平砸向他后脑的那块石头。
吴克在做了超大容量的回忆之后,于无尽的失落中走出澡堂,至此,他除了知道自己要吃晚饭之外,还是不知道这个夜晚他能做些什么,那沉甸甸的五百块钱就像磁石一样把他以往的伤痛一点一点地吸附出来,抽走他的温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今晚做一件事,花掉这些可恶的钱,赶走那些可恶的过去。
吴克吃完饭,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这个晚上是个有头有序的晚上,乌海繁华的夜市和以往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因为工头吴克要在今夜花掉五百块钱而有所错位。吴克花钱的行动还是来得有些突然,不是因为夜晚的城市没有准备好,而是吴克没有准备充分,急于求成。
其实,吴克还是比较倾向于找小姐一事,是因为好奇,或者是赌气,或者仅仅是证明一下而已,总之,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站在了快活林的门口。快活林里的小姐密密麻麻地坐了一圈,目光像无数道手电筒的光束,照在吴克身上,他的皮肤立马就像破碎的玻璃,在剧烈的心跳中有了崩裂的声音,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成了诸多手掌之下的面团。他闭上眼睛,任凭她们的手游走,任凭她们的气息吹拂他的耳根。
他梦游般地被其中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领到了后面的包厢。包厢里陈旧的床和发霉的气息让吴克知道了并不像书上说的那样浪漫和刺激,他想他要忍受温暖。吴克想,不就是花钱吗,哪儿不能花,我有的是钱。可谁能想到,当那个女孩笑吟吟地伸出手向吴克讨钱时,他因快乐而蔓延至全身的绯红就像猪肝一样僵硬在了面部。他突然有了做贼的幻觉,仿佛是被抓住了。一瞬间,罪与罚在他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闪过,像刀片一样割在他坚硬的肌肉上吱吱作响,吴克想都没有细想,发疯一般逃了出来,在众多女人的眼皮底下,惶恐地逃走了。
吴克走在大街上,哗哗闪过的车辆人流逼得他寸步难行。路边坏了的灯,像中了瘟疫的牛羊,乜斜着眼睛,懒懒地闪着。其实,并没有人关注吴克,而吴克却觉得大家都在看他,他已然像是赤裸着身子,供大家玩赏的木偶,他真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
吴克迅速地隐入南大街一个昏暗的巷口,蹲下猛击自己的头。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性乞丐正诡异地看着他,他坐在距离吴克不足一米远的马路牙子上,身下铺着一堆破旧的棉絮,右手拿着半个馒头,嘴角还留存着馒头的碎屑,左手拿着一根超过一米的竹竿,他似乎被吴克惊吓了,警觉地拿起竹竿挡在腿前,眼睛里充满着惊惧和不可忽略地敌视,甚至在吴克缓缓抬头的间隙里,他还呀呀地说着什么,似乎是在呵斥。他的衣衫破烂,瘦脸肮脏。突然,吴克就从他的样子里看到了蹒跚在城市一隅的自己,百感交集。
吴克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了,他快速地转身,向马路右侧的百货市场走去。他在那里购置了一套被褥和一些洗漱用品,尤其是多买了一条纯白的毛巾,然后又在身后的夜宵摊点上买了一大包小吃,包括水果和一只烧鸡,算了算,足足花去了他一百五十八元。
吴克觉得再也不能耽搁了,他以为自己手里的这些东西足以救活一个人的性命,而在这之前,他却可耻地准备把它花在一次嫖妓上,他有些痛恨自己。他想着,救一个人,哪怕是给他一点点温暖,那也是他在今夜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他甚至一下子就把自己看得高尚了。
当吴克再次来到昏暗的巷口时,那个乞丐却不见了,只有那破烂的棉絮在寒风中微微颤动,棉絮上还有一小块馒头。吴克越发伤感了,一如书上说的,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哀。他慢慢蹲下来,把那些破棉絮卷起,用棉絮卷儿刷了刷地面,冰冷的水泥地面嘶嘶作响,像众多的蛇吐着信子。他想他要把这些东西在不远处的那个垃圾坑里亲自烧掉。接着,他把新买来的褥子铺好,把食物塞进被子里,还压了压被角,把其他的生活用品挑出了几样,诸如洋瓷饭碗和一个手提的塑料大水杯,整齐地码放在褥子的左上端靠近墙角的地方,他想那个乞丐今晚定能在这个新窝里睡个好觉。吴克还想到了他来时,看到新被子一定会两眼冒着幸福的火花,他还会在一觉醒来后,伸手吃到新鲜的不被别人掂量过的食物,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吴克做完这些,有些自我得意了,他觉得自己真该躺下来感受一下这个夜晚他做的这件善事,也为意想不到的收获庆幸不已。他眯上眼睛,浑身都放松了,静静地躺着,这夜晚是如此的美好。
然而,一眨眼,一张青面獠牙的嘴脸一晃而过,紧接着一根超过一米的竹竿从天而降,劈头盖脸地黑压压砸下来。吴克就失去了知觉。那个中年男性乞丐,看着昏过去的吴克,一脸得意。他缓缓卷起刚刚铺好的被褥,把所有的零碎东西塞进被子深处,扎成捆,斜搭在肩上,胳肢窝里夹着那根超过一米的竹竿,看都不看吴克一眼,渐渐从黑暗里隐去。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