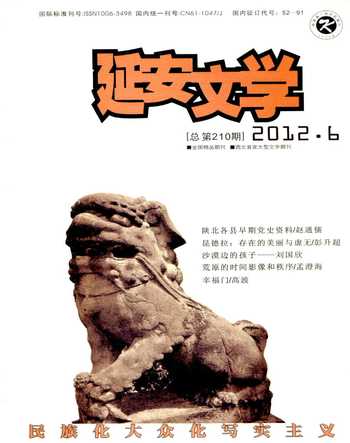野鸡翎
警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北方文学》《岁月》《小说林》《文学报》《辽河》等。
1
大雪封山了。
铺天盖地的大雪,把骆驼峰的沟沟壑壑都填塞得臃肿起来。
毎年到这个时候,林茂屯就开始热闹了。山外伐木头的、倒套子的、打猎的、耍钱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聚到这儿。一旦聚到这儿,大雪就玩笑似的把他们牢牢地围堵在这深山窝里。山路就此断了头,一时半会儿就走不出去了。
这些人的到来,大车店里根本容不下。家家户户都打发人到大车店外面候着,插空往家里拉客。老客们(外来商人的统称)也很乐意到各人家里去住,屋子自然要比大车店里敞亮些,暖和些。处好了也许还能捞着点荤腥(指女人),虽然比在店里花的钱多些,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冬天,有活干,有女人给做饭,兴许还有女人陪着睡觉,这总算是件很幸福的事儿。
二麻子家在梨花过门之前,毎年都招老客。不招老客已有几年了,今年也想挑拣个本分的主招来一个。
二麻子来到大车店门口晃晃,心想要是能招个老客来,就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一个冬天下来,进项要比自家平时一年,甚至几年的还要多。
二麻子也只是在那儿晃晃,跟谁都没搭讪。晃了一会儿,就折转身回家了。刚到院子,就有一个大肚子老客跟上门来。
大肚子老客站在大门外,看见了二麻子的老婆梨花在院子里,眼神就粘在了梨花身上不过去,脚步就急急地凑了过来。问招客不?
看着大肚子老客那种眼神,二麻子就没有这样的打算了。他觉得这个大肚子老客很不地道,就跨前一步,没等梨花说招还是不招,二麻子蹿上去说,不招。
大肚子老客瞅瞅二麻子,底气十足地说,我出双份的钱。
二麻子踱脚折身说,不招!
大肚子老客巴眨巴着一双小眼睛实在有些不舍地瞅瞅梨花,失望地摇着头走了。
梨花问二麻子,你不是想招个人吗,为啥又不招?
二麻子说,今年雪大,野物多,能整几只狍子或野猪,日子也能对付着过。再说那个大肚子,搭眼一瞅就邪心霸道的,我怕你有啥闪失。
梨花也觉得二麻子说得在理,就把这事撂在了一边儿。
2
整整嚎了一夜的北风,在天放亮时渐渐地停了下来。二麻子抬头瞅瞅东山骆驼峰上那两个突兀耸立的片砬子,像匹被冻僵了的骆驼横卧在风雪里。林茂屯通向山外的路,一准是封死了,整个屯子快要掩埋在这场大雪之中了。
过了一会儿,太阳从“骆驼”的身后缓缓地露出了灰土土的脸,雪地上便有了些光亮。
二麻子抄起木锨,把院子里的雪攒成堆。庭院里攒出一条狭小的通道。二麻子跺跺脚面子上的雪走进马棚,用簸箕撮点草料倒进马槽里。然后,捡了些木头柈子抱回了上屋。把木柈子添进铁炉子里,回手扯块桦树皮,用洋火点燃丟进去,便弯下腰使劲地吹着,木柈子腾腾地燃烧起来,顷刻间儿,屋子里被热气填满了,暖烘烘的,就连窗子上的霜花也渐渐地融化了。
二麻子姓王,不用说也知道他在兄弟中行二。四岁时出天花差点没命了,在炕上蒙着被子躺了三天三夜,憋出些红疙瘩,落下一脸坑坑洼洼,因此得名二麻子。二麻子父母下世早,跟着哥哥嫂嫂过日子。哥哥嫂嫂哪像父母那样经管他,二麻子便和村里的小嘎子们成天钻山玩。采山菜,摘山果,掏鸟蛋,下套子啥都干。
二麻子磨练出一个顽皮的性格,别看顽皮,二麻子为人却挺厚道。平常蔫啦巴叽的,就像缺了水的豆芽菜,支楞不起来。蔫巴厚道的二麻子有福,娶了一个水灵灵的媳妇梨花。
梨花娘生梨花的时候,村头的山梨花白白的开得正好。梨花娘一看生个丫头,就说叫梨花吧。梨花嫁给二麻子时,虽然不是黄花大闺女了,可她没嫁过人。把她从女孩变成女人的是个日本人。梨花的娘家住在天增泉子,离林茂屯也就十几里。那时天增泉子来了些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些人,之所以选在天增泉子落脚,是因为那里靠绰罗河,两岸水土丰盈,是适宜种水稻的好地方。
梨花的娘家是天增泉子的开荒户,土地虽然不多,可那都是上好的二洼地。土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日本人说收就收了,不容商量。梨花的爹不服,就和日本人闹别扭,县警署和维持会的人就把他抓走塞进了大牢。
梨花娘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准备躲进山里,离日本人远远的。临走时,梨花娘想再看一眼这片汗珠子掉下来摔成八瓣浸泡出来的土地,就领着梨花来到地里,大祸就出了。
梨花家的地紧挨着绰罗河,河边的柳条通一丛丛的,绿油油的,细长的嫩叶随着春风飘揺着。梨花跟着娘从柳条通钻出来的时候,两个正在地里放哨的日本人,见从柳条通里钻出来两个清清爽爽的女人,就像饿了半个月的狼突然见到了两只战战兢兢的小鹿,眼睛立马放出了绿光。
两个柔弱的女人就这样成了两只饿狼的猎物。
林茂屯的人对是不是黄花闺女没人太在意,只要身板和脸蛋儿长得好看,让人瞅着顺眼比啥都重要。二麻子娶梨花时,也不是很在意这个。把梨花娶到家里,二麻子的心就像被拴在了梨花的腰间。见天细致不厌地侍候着,四季如是。
二麻子温好洗脸水,招呼梨花起来梳头洗脸。二麻子把梨花娶过门来天天如此。也不是梨花非要他这么做,是因为二麻子喜欢看梨花梳头洗脸时的样子。
此时,二麻子坐在炕沿上,用那满是老茧皴黑的手捋着正在被窝里熟睡的梨花的头发。梨花秀气的脸就在他眼皮底下,梨花睁开眼睛问,亮了?
二麻子点点头憨笑着,再不起,太阳就照腚了。说着拿起梨花的棉袄棉裤在铁炉子上烤了烤,烤得裤和祆都暖烘烘的再递给梨花。
梨花从被窝里爬出来,接过二麻子递过来的棉袄棉裤麻利地穿上,挽上发髻,穿上蓝底白花的带大襟儿的夹袄,系上蒜皮疙瘩扣子,整个人立马就清清爽爽起来。
二麻子觉得若没人讨麻烦的话,这样舒心的日子,是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的。
3
正在看梨花梳头洗脸的二麻子,突然听到大门吱嘎一声。二麻子把脸扭向窗外,一个衣衫褴褛戴着狗皮帽子的人趔趔趄趄地跌倒在大门里。
二麻子急忙跑到院里,见“狗皮帽子”浑身哆嗦成一团。
二麻子问,咋啦?
“狗皮帽子”说,求……求你了,救救我。
二麻子二话没说就扯膀子把“狗皮帽子”丟进雪堆里,抓起雪面子在“狗皮帽子”的脸上、手上一顿揉搓,然后背进上屋。
正在梳头洗脸的梨花见二麻子背进个人来吓了一跳。
二麻子把“狗皮帽子”放在炕上,对梨花说,快把獾子油拿出来。
二麻子把那人的狗皮帽子摘下来,露出了冻得绛紫的刀条子脸。那人厚嘴唇儿,眼睛不大,眼泡子有点肿,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
二麻子把“狗皮帽子”那双冻得像冰疙瘩儿的鞋子脱下来,把脚插进凉水盆里。然后一点点把獾子油涂在冻伤的脸上、脚上。
奄奄一息的“狗皮帽子”睁开了红肿的眼睛,挣扎着想坐起来,二麻子将他摁下,说,动不得。
梨花端过来一碗小米粥,舀出一勺用嘴吹了吹,送到了厚厚的嘴唇里,“狗皮帽子”的泪水便从细细的眼缝里溢出。
梨花问,你为啥进我家来?
“狗皮帽子”说,整个林茂屯就你家院子有条道儿,想必是人已经起来了。
梨花没再问,拣起几块木柈子丟进铁炉子里,火光从炉膛里射出,照红了她那俏皮的脸蛋。
经过几天的调养,“狗皮帽子”恢复得差不多了。说,大哥,大恩不言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今后我就是你的兄弟。说完,就一个头砸在了地上。
二麻子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抬举,慌忙手脚说,兄弟,快起来。
自从两个人拜过之后,平时蔫蔫巴巴的二麻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话也多了。没事的时候,两个人就坐在炕头上闲聊。这时,二麻子才知道,“狗皮帽子”居然是个出家人,就在骆驼砬子山上的玉皇庙里修行,名叫赵春霖。
几日后,赵春霖要回玉皇庙,二麻子和梨花再三挽留。二麻子说,兄弟,出家人讲究的是个缘分,不管咋说,一个头磕在地上,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今后要有个难着歹的你就过来。赵老道执意要走,留也留不住。二麻子说,这样,大哥给庙上兄弟准备了点粮食,你带上。
赵春霖客套一番扛着半袋子小米走了。
在大门外,赵春霖停下脚对二麻子说,大哥,现在屯里人多眼杂,我盯把来恐怕不方便,就按咱俩说的办,只要看到野鸡翎,你就赶爬犁上山。
二麻子说,记下了,放心,这是咱俩的秘密,对谁都不会说。
那几天,天空中总是飘着雪花,西北风也是没头没脑地刮着。
自从赵春霖走后,二麻子就像丟了魂似的。白日里整天望着飞扬的雪花发呆,夜里也翻过来调过去地折腾。天一亮就爬起来,围着篱笆杖子转悠。
梨花问他,你咋了?
二麻子憨笑着说,没咋的。
梨花说,有话就说出来,别搁在心里憋屈着。
二麻子说,你别瞎想,真的没事儿。
梨花说,那就好。
二麻子每天早晨依旧装作若无其事地围着杖子转悠,突然有一天,他终于看见在杖子一块裂缝的杖条上插着一支野鸡翎。二麻子贼一般地扯下野鸡翎子塞进雪窠里。然后,回到马棚给马添了些草料,抱一抱木柈子回到上屋。
吃完早饭,二麻子对梨花说,雪停了,我上山蹓蹓套子(用钢丝作的套狍子的工具),看看有没有傻狍子钻套儿。
梨花说,加倍小心,雪大。
二麻子答应着忙三火四地穿上靰鞡鞋和羊皮袄,拽过爬犁套上大青马朝骆驼砬子山走去。
山路已经被大雪漂得分不清道眼儿,不过,二麻子不怕。这上山的道走了大半辈子了,就是闭上眼睛也能摸到。爬犁刚到骆驼砬子山玉皇庙下,远远地就看见赵春霖在那儿等他。等爬犁一到,赵春霖急忙从雪窠里扒出两麻袋粮食,装上爬犁,嘱咐一定要交给张大个的手上,这是救命粮,他们等米下锅呢。
二麻子说,兄弟,这事儿你交给哥手里你就放心。说着就赶起马爬犁钻进了山里,一直向北,驶向老黑山。
走过十几里山路,刚到老黑山山根下,二麻子的马爬犁就被人拦了下来。
二麻子怯生生地问,你要干啥?
来人一抱拳说,道,道,道,道上有座玉皇庙。
二麻子懵了,问,啥意思?
来人嗖地一下拨出盒子枪,指向二麻子。
二麻子见这阵势吓出一身冷汗,忽地想起赵春霖说的话,急忙说,有,有,有,庙里有个赵老道。
来人收回枪,哈哈大笑,问,你是王大哥吧?
二麻子问,你咋知道?
来人上前抓住二麻子的双手说,我是张大个子啊!
二麻子问,你是张大个子?
谢谢大哥,我们就指望这米下锅呢!张大个子打了一声呼哨,有十几个人拿着枪冲下山坡。
二麻子问,你们是?
张大个子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的。怎么,老赵没跟你说?
二麻子突然觉得大腿肚子有些转筋,瘫坐在爬犁上。早就听说过张大个子是条打小鬼子的硬汉子,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
回来的路上,二麻子有些忐忑不安,咋就一没留神和抗日游击队弄到一块了。这事一旦传出去,没了太平日子不说,还是掉脑袋的事儿。
马爬犁正在茫茫的雪野里慢慢穿行。突然,大青马惊恐地一声嘶鸣,翻蹄亮掌慌不择路地狂奔起来,二麻子勒紧缰绳吁吁地喊着。马爬犁箭一般地向山坳里滑去。滑在半山腰儿,终于被一棵树桩子卡住。二麻子从爬犁上爬了下来,意外地发现不远处有一只被套子撸死的狍子,二麻子一看这狍子是被死套套住的。二麻子断定这不是屯子人干的,屯子人下的都是活套子,不下死套子。二麻子知道这一定是外来打猎的老客干的。索性就卸下狍子,把这个意外的猎物连同惊喜和恐惧一同装在了爬犁上。
到家时,天快黑了。
梨花见爬犁上真拉回只狍子就兴奋地问,真套着了?
二麻子含混地说,啊,套着了。
梨花说,行啊,这大狍子够咱们吃一冬了。
二麻子笑笑说,这咋会够,过几天还得去弄两只。你放心,不招老客,咱们也照样有肉吃,你汉子长了本事啦。
4
大车店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喝酒的、耍钱的、说荤段子的,五花八门。山里发生的事儿,每天都在这儿抖落个遍。
家里有老客的男人,也多在晚上来这里,说是凑凑热闹,其实是给娘们和老客腾地方,大伙就心照不宣地凑在一块。
二麻子这两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总去大车店里转来转去,不过他家里没有老客,他去大车店是为了听听有没有关于给抗日游击队送粮的事儿。这个事儿没听着,到是说起套住的狍子被人拣走的事儿。
其实,二麻子只是想为兄弟赵春霖做点事儿,没想和什么抗联掺和在一起。现在是手插磨眼,想抽回来也难。好在没人知道这件事儿,二麻子的心总算踏实了些。没想到为抗联做事竟然如此简单,简单得就如同走了一趟亲戚。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没有他送去的粮食,抗联的战士说不定会怎么样。
二麻子也恨日本人,确切地说从梨花过门那天晚上,他就有了这个念头儿。梨花是他的人,梨花的恨就是他的恨。二麻子也曾发过誓,狗日的小日本,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得把时定要敲碎你几个脑袋。动我的女人不中,占我的地皮也他妈的不中。
二麻子给抗联干事不想让梨花知道,他怕梨花为他担心,就和赵春霖定了个插野鸡翎的暗号。二麻子觉得抗联有粮吃,吃饱了肚子才能打小日子,才能替梨花报仇。二麻子觉得值!
二麻子从大车店里出来,迎面碰上了那个大肚子老客。大肚子老客很惊异地问二麻子,咋的,家里有老客?
二麻子说,你放屁!在二麻子心中,说家里有老客,就和骂他祖宗,或者说他是王八没啥两样。
大肚子老客也不恼,依旧笑呵呵地说,我就住在你家隔壁张蔫巴家,你把娘们儿看紧喽。
二麻子愤然地一抬脚,雪面呼呼直飞,又重复地说,你放屁!
行,算我放屁!不过你这个人,脾气太操蛋。不管咋说,现在咱们界毗邻居住着,得往好了处,远亲不如近邻嘛!有啥事儿相互有个照应。现在是笑贫不笑娼,整个林茂屯有几家不招老客的?女人那玩意儿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了,你那娘们到你手里早就不是处女了,而且还是小日本子祸害的,你还当×宝呢。大肚子老客说完,嘻笑着进了大车店。
一提到这事儿,二麻子脸上不光彩,心里就没了底气。准是他妈老刘婆子瞎嘞嘞的。不然,他咋会知道?
二麻子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沮丧地朝家走去。
没人知道杨大肚子大号叫啥,他不伐木头,也不倒套子,只是游走江湖的耍钱鬼。杨大肚子耍钱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偷牌送牌易如反掌。杨大肚子赢了钱回到刘半拉子家,常常给刘半拉子些钱打酒喝,可他从不碰老刘婆子。
这让老刘婆子挺纳闷,也挺憋屈。
四十出头的老刘婆子,人长得不寒碜,该鼓溜的地方鼓溜,该瘪的地方瘪了,也算是有些姿色。男人刘半拉子性子温顺,但他喜酒,只要有酒喝就行。逢酒必喝,逢喝必多,逢多必睡,两眼一闭像头死猪。老娘们想咋折腾咋折腾,想跟谁折腾跟谁折腾。自己老爷们不稀罕也就算了,哪有老客不打野食儿的?老刘婆子很不服气,跑腿子三年,老母猪赛貂蝉,我不信你他妈的不食人间烟火。只要杨大肚子一回来,老刘婆子就像只发情的狸猫前钻后跳地折腾,时不时地哼哼唧唧地唱段单出头:
忽悠悠做了一个南柯的梦,
渺茫茫梦见丈夫走进房屋,
笑吟吟不言不语牙床上坐,
急忙忙解衣宽带脱去衣服,
刷拉拉揭开了奴家红绫被,
羞答答露出来那幅迷人图啊……
不管老刘婆子咋折腾,杨大肚子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迷迷瞪瞪地往北炕一倒呼呼地睡了过去。
5
二麻子毎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杖子上有没有野鸡翎。在他看来野鸡翎就像亲人的嘱托一样,不管咋难都是要办的。只要野鸡翎插在那杖子上,就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召唤他一样,一刻也耽搁不得。
二麻子正在围着板杖子转悠,杨大肚子从刘半拉子家出来,问,找啥呢?
二麻子心里一忽悠,扬着脸瞅着杨大肚子,说,啥也不找。
杨大肚子说,啥也不找,一大早出来晃悠啥?
二麻子说,碍你屌事?
杨大肚子说,你这人叽叽歪歪的不好。
二麻子说,你少整这没用的!
两个人正在嘀咕,梨花推开门来到院里,喊二麻子回来吃饭。
杨大肚子瞅着梨花,惋惜地说,多好的娘们儿,本应该让大伙都沾沾,你自个用可惜了啦。
二麻子脸上现出了不可琢磨的笑意。问,你想用用呗?
杨大肚子说,你别误会,我这个人也就是过过嘴瘾,其实耍钱人是不近女色的。不过,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把女人看得那么紧有啥用,换点钱花是真格的。
二麻子说,我不但要看好自己的院子,还要保管好自己的女人!
杨大肚子说,就凭你这两下子?
滚犊子!二麻子吐了口涶沬踱着脚回家了。
回到家里的二麻子,瞅着梨花,心里酸叽叽地难受。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念。他真怕梨花再有啥闪失。
二麻子第二次见到野鸡翎,是在三天后的早晨。二麻子从杖子上拔下野鸡翎,像做贼一样把野鸡翎塞进雪窠里。
这一细节,被站在邻院房山头撒尿的杨大肚子看得清清楚楚。
二麻子套上爬犁,打马直向山里奔去。杨大肚子便从雪窠里拿出那支野鸡翎,琢磨半天,也没弄出个子午卯酉来。但他断定二麻子赶着马爬犁上山肯定与这野鸡翎有关。
杨大肚子想弄个究竟,就把刘半拉子家的马爬犁赶出来,尾随着二麻子的马蹄印子上山了。
到了骆驼砬子山下,杨大肚子见山上有个人,和二麻子往马爬犁上装东西,整整四个麻袋。看得杨大肚子倒吸了口凉气,急忙打马下山。
不几天,有个消息在大车店里传开了。张大个子领着抗日游击队夜袭了康金井火车站,打死了十来个日本鬼子。二麻子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了一阵子。他觉得自己干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事儿。
杨大肚子这几天手气挺背,输得腚眼毛光。他倒在炕上,望着房顶,望着望着,突然眼前一亮。披上棉袄,去了二麻子家。
二麻子急忙从屋里出来,把他截在院内,问,你来干啥?
杨大肚子说,找你。
二麻子问,找我干啥?
杨大肚子说,这两天手头有点紧,借我俩钱。
二麻子说,借钱?没有。
杨大肚子向屋里张望了一下说,话别说死啰!扯破脸皮对谁都不好看。前几天,你去骆驼砬子干啥,别以为谁都不知道。
二麻子脑袋“嗡”了一声,便强打精神,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少他妈放屁!
杨大肚子嘻笑着说,你说我放屁,我就放屁。我先放个屁撂到这儿,要么你借我俩钱,要么把娘们儿舍出来,让我也用用。
二麻子吼着,滚!
杨大肚子说,好,我先滚。你琢磨琢磨,两头着一头。我等你信。
望着杨大肚子的背影,二麻子的心跳得咚咚的,他搞不清楚进山里的事儿杨大肚子是咋知道的,他觉得这事挺麻烦。杨大肚子是一个难缠的主,除了不拉人屎,啥屎都能拉得出来,整不好势必栽在他的手里,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
杨大肚子滚回东院,屋里已经黑了。便摸出洋火准备点灯,老刘婆子一把夺了下来说,灯没油了。
杨大肚子也不言语,回身倒在了北炕上,还没等把身子放平,腾地一下坐了起来,用手一摸,炕瓦凉瓦凉的。问,咋没烧炕?
老刘婆子没好气地说,没柴火。
杨大肚子来到南炕抻手一摸热烘烘的,就知道这娘们整事。心想这两天手背,拿她凑和点也将就。就问,刘半拉子呢?
老刘婆子盘腿坐在炕上,大花棉袄敞开半怀,瞄着他说,上山外了。
我那铺炕拔凉,没柴火,你这炕还烙屁股?杨大肚子把屁股搭在炕沿上,抹头穿过她的衣襟空隙,看见里面光溜溜的什么都没穿。
老刘婆子勾了他一眼说,一铺炕打扑棱睡,还烧两铺炕干啥?
杨大肚子心想这可是你送上来的,不用白不用。于是,二话没说,一下子就把老刘婆子撂倒在炕上……
二麻子这几天挺闹心,他想这事应当和赵春霖说说,可是赵春霖有交代,不见野鸡翎不能上玉皇庙找他,去了恐怕也见不着。
于是,二麻子期盼着野鸡翎的再次出现。
天刚放亮,二麻子就围着杖子转悠。
杨大肚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二麻子身后问,找这个吧?
二麻子一看杨大肚子满脸坏笑,手里拿根野鸡翎。那翎子生生像刚从野鸡身上拔下似的,鲜鲜艳艳的。
二麻子心想,坏了,他咋知道我找这个?马上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我找它啥用,你拿着玩去吧。
杨大肚子把野鸡翎上羽毛撕下来,放在嘴边用力一吹,羽毛轻悠悠地像雪花似的飘着。
二麻子吃完早饭对梨花说要上山。
梨花说,别去了,这两天我右眼皮总跳,别出啥事。
二麻子说,扯,能出啥事?
杨大肚子用烙铁把窗子上的霜花烙化,一块镶嵌在油纸里巴掌大的玻璃块便露了出来。他盯着二麻子家大门口,不一会儿见二麻子赶着爬犁走了,杨大肚子露出了满脸的坏笑。
二麻子来到骆驼峰上左等右等不见赵春霖,心想备不住有啥事耽搁了。既然到了玉皇庙外,何不上去问个明白。
二麻子把马缰绳栓在树上,朝玉皇庙走去。
玉皇庙山势险峻,怪石嶙峋,犹如刀削斧劈一般,二麻子轻如猿猴爬上山顶。赵春霖推开庙门,问,你咋来了?
二麻子一脸糊涂,我还问你呢?你插完野鸡翎,咋不下山呢?
赵春霖,野鸡翎?没有哇。
二麻子预感事情不妙!就把杨大肚子拿野鸡翎和他说的话与赵春霖学了一遍。
赵春霖觉得事情严重,沉吟半晌问,这个杨大肚子什么来头?
二麻子说,不知道,只知道他整天在赌场上混。
这个人很危险。赵春霖转了个圈又说,这样,你回去后,要象往常一样,别惊动他。这个事儿,我会尽快向张大个子汇报。
二麻子回到家,刚拴好马,正撞见杨大肚子慌慌张张地从屋里出来。二麻子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抄起鞭子狠狠地抽向杨大肚子。杨大肚子躲闪不及,这一鞭子下去正好扫在杨大肚子的脸上,杨大肚子慌不择路,纵身跳过篱笆杖子。回头看二麻子没追过来,跳得高高大声骂道,我日你老婆的,我早晚给你戴上绿帽子。
二麻子急忙冲进屋里,见梨花手握着菜刀蜷曲在炕里旮旯那儿,哆嗦得像个刺猬缩成一团。
梨花,他没把你咋地吧?二麻子急切切地问,眼里喷着火。
梨花缓过神来,甩手把菜刀撇到地当腰,呜呜啦啦地哭着说,这是啥世道啊?中国人咋也这么坏呀?
二麻子看着梨花的衣裳还算齐整,知道没出大事。他从牙缝子里挤出几个字:日本人和杨大肚子都该杀。
杨大肚子捂着脸回到东院,老刘婆子问,脸咋了?
杨大肚子也不避讳,说是二麻子拿鞭子抽的。
老刘婆子知道,肯定是他去调戏梨花了,让二麻子堵上了。问,捞着没?
杨大肚子说,要捞着,还值了呢。
老刘婆子说,现成的你不用,活鸡巴该!
三天后,林茂屯出了大事儿。那天晚上大车店里来了三个耍钱的,牌九推到半夜,因杨大肚子出老千,发生口角,杨大肚子死于非命。
二麻子心明镜似的,这一准是赵春霖让游击队干的。他觉得赵春霖厉害,游击队也厉害,想干谁,谁就没好。
惊魂未定的梨花,听说杨大肚子被人弄死,脑袋突然“嗡”了一下,她觉得这事有些蹊跷。这几天二麻子也怪怪的,整天去大车店里凑热闹,而且心情特好。每次回来都在自己身上折腾到半夜。梨花想杨大肚子的死肯定与他有关。就问正在身上干活的二麻子,杨大肚子到底是咋死的?
二麻子吭哧着说,出老千,谁让他出老千,该死!该死……他越说该死越兴奋,几下便翻身落马,一边喘去了。
梨花抚摸着二麻子胸脯子说,不对劲儿,你肯定有啥事瞒着我。
二麻子说,扯,我咋会瞒着你?
梨花便不再问。
6
老刘婆子觉得挺倒灶,费了一好大劲儿,好不容易扯上了,居然白白让这个杨大肚子折腾了几天。答应赢了给她钱,这下钱没到手,人没了。老刘婆子想想就骂杨大肚子,下三路,上三辈,骂得血淋淋的。
刘半拉子断了酒钱,憋得难受,有时也骂上一句,你个不值钱的货!老刘婆子就不再言语,抽抽嗒嗒地哭泣着。
其实,杨大肚子的死,说不清楚刘半拉子是悲是喜。虽然说杨大肚子花在他身上的钱不多,但毕竟还有酒喝。可一想到自己的娘们儿被别人糟蹋心里也多多少少不是滋味儿。又一想到被一个死鬼给白玩了,就更不是个滋味儿,真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
有了那样事儿的女人,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顺从的还是强迫的,也不管出于啥目的,女人与那个男人赤裸裸地亲密接触,或恨或爱总是忘不掉。也许老刘婆子忘不掉杨大肚子,是因为他那句口头的约定。杨大肚子许愿不还,闭上眼睛走了。他妈的,不讲究。
天增泉镇里的警备队骑着马挎着枪,来了一帮警察。查了一六十三遭,也没查出个子午卯酉来,就要把老客们遣散,也要把大车店封了。
大车店掌柜的毛了,急忙拿些钱,找警备队长商量,你把老客都撵走,账没人结,这一冬天吃吃喝喝的,我亏大了。
警备队长也没客气把钱揣起来,说,这事你摊大了。你知道这个杨大肚子是什么人?
店掌柜说,不就是个耍兰码(耍钱的)的吗?
屁!他是……警备队长看看左右,便把嘴贴在店掌柜的耳朵根子上悄声说,他是日本人的特务子,是来打探游击队,执行公务的。
店掌柜的吓得目瞪口呆,寻思了半晌说,你看这样行不,这个杨大肚子是被几个拿枪的人干死的。现在啥人带短枪?打猎的人不使那玩意儿,除了游击队还有别人吗?把这事儿往游击队身上一赖不就结了?
警备队长说,你的脑袋是尿罐子?这要让日本人知道,游击队在你的大车店里杀人,你的事能小得了吗?
店掌柜的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一忽闪。
警备队长摸着兜里的票子,琢磨了一会儿说,这个杨大肚子不是住在刘半拉子家吗?不如这样,就说杨大肚子和刘半拉子老婆瞎搞,让刘半拉子发现,刘半拉子便雇凶杀人,把刘半拉子一抓,完事儿。
店掌柜说,可这事儿与刘半拉子没啥瓜葛,这么整是不是有点亏心?
警备队长不耐烦地问,那你说咋整?
店掌柜的寻思半天,也没寻思出啥道道。只好说,也成。
警备队长是晚上带着人来到刘半拉子家的。刘半拉子和老婆已经躺下了。警备队长说明了来意,刘半拉子吓得哆哆嗦嗦地穿上衣服,哀求地说,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咋能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来?
警备队长说,别整那没用的,干这事有脑袋瓜子帖帖的吗?带走!
警察们上炕就扯刘半拉子,刘半拉子脚蹬着炕沿儿哭叽叽地打扑楞。
老刘婆子嗷唠一嗓子,慢着!
这一嗓子,如同燃爆的麻雷子,惊得警察们像傻狍子似的呆呆地杵在那儿。
老刘婆子一撩被子,白花花的大腿露出来。老刘婆子也不着急,慢腾腾地穿上棉袄棉裤,敞着怀儿坐在炕沿上,问,你们凭啥抓他?
听老刘婆子这一问,警备队长才缓过神来,嘎巴嘎巴嘴,心里也犯嘀咕,是呀,凭啥抓他?便支支吾吾地说,人在你家住,出事不找他找谁?
老刘婆子说,你没看见死者脸上有道鞭痕吗?
警备队长回忆着,在他的印象中,杨大肚子的脸上还真有道鞭痕,便问,有鞭痕,又怎么样?
老刘婆子卖着关子说,你不想知道那鞭痕是哪来的吗?
警备队长凑上去,挨着老刘婆子坐下来,眼睛顺着老刘婆子敞着的怀儿溜进去,瞅了一会儿问,哪来的?
老刘婆子风骚地用手把警长的脸扭过去,说,这是从娘家带来的。
警备队长一抺脸儿,什么从娘家带来的?我问那鞭痕!
老刘婆子说,你先把我们家掌柜的放了。
警备队长瞅瞅蹬蹬腿的刘半拉子,说,放了放了。
刘半拉子从炕上爬起来,把婆子的棉袄抿了抿,拣个布条子,扎了个严严实实。
老刘婆子笑骂着说,缺徳玩意儿,还怕他们吃了不成?
警备队长一本正经地说,别,别整没用的。那鞭痕道到底咋回事?
老刘婆子卖着关子说,让我想想,这事说好还是不说的好。
7
二麻子正在马棚里给马添草,见刘半拉子家来了几个警察。这肯定与杨大肚子的死有关,就觉着这事儿要坏。他妈的老刘婆子肯定得把杨大肚子的事儿抖落出来,这样警察狗子就会闻着味儿盯上门来,整不好会把他带走。那么,赵春霖的事咋整?那是大事儿。二麻子想是死是活总得有个交代。二麻子急忙回屋,对躺在炕上的梨花说,东院刘半拉子家来了帮警察狗子,八成要出事儿。
梨花问,能出啥事?
二麻子盘算着咋和梨花说好,问,你知道赵老弟是干啥的?
梨花说,不就是个道士吗?
二麻子侧过身来神秘兮兮地说,他是抗联的交通员。
梨花一下子坐了起来,啥?你说他是抗联的?打小日本的?
二麻子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梨花沉默下来,她想起了爹娘,想起了那俩兽性的日本鬼子,心里就悲伤起来。
二麻子说,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
梨花抬起头两眼盯着二麻子,问,啥事儿?
二麻子说,你记得赵老弟走后,我赶着马爬犁去过几次山吗?我说是蹓狍子,其实是替他做事儿。那天他临走时,在大门外跟我说,屯子人多眼杂,他来不方便,有事他会晚上派人来,在木杖子上插根野鸡翎子,见翎子就让我赶着马爬犁上山。
梨花问,做啥儿?
二麻子说,为抗联运送粮食,弹药。后来,不知杨大肚子咋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就要挟我。我把这事告诉了赵老弟,杨大肚子就出事儿了,我估摸杨大肚子是死在抗联手里的。
梨花说,没事儿,他人已经死了。这叫啥?这叫死无对证。
事情正如二麻子所料,正说着,门就被拽开了。警备队长走在前边儿,进门就喊,王二麻子!
二麻子近前说,长官,有事儿?
警备队长说,事大了!你知不知道杨大肚子死了?
二麻子说,听说了。
警备队长说,杨大肚子脸上有道鞭痕,你知道吗?
二麻子支吾着说,这个……
梨花说,是我抽的。
警备队长寻声一看灯下的梨花,不由得吸了口凉气,他就觉着奇怪了。这么个深山老林的小屯子,咋会有这么冷艳的女人?警备队长不由自主地凑到梨花跟前儿,问,你抽的?咋回事儿?
梨花说,那天,那个叫杨大肚子的来了,见二麻子没在家,就想占我便宜。我就抄起了鞭子抽了他一下。话说的简短明了,好像从骆驼峰的峡谷中刮过一团雪雾,忽闪地飘散了。
警备队长从“雪雾”里甩过头来问,就这么简单?
梨花说,就这么简单。
警备队长围着梨花转了个圈,突兀地问,然后,你就雇凶杀了他?
梨花苦笑着说,长官,玩笑了。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就是有那心思也没那个钱呢?
警备队长用手托起梨花的下巴,端详了一会儿,在他的心里怎么也不能把这美妙的女人和杀人犯联系到一块儿。就回头瞅瞅二麻子,心想这么个屌样的人咋会娶这漂亮的娘们儿?心里就有点酸叽叽的难受,就产生拯救她于水火的意思。便一挥手,喝道,把二麻子绑了!
二麻子没想到警备队长会来这么一手,就挣脱着,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警备队长冷笑着,王法?跟我讲王法?
梨花慢悠悠地说,他杨大肚子该死。
警备队长问,啥意思?
梨花说,他到处跑骚,还不该死么?吃着盆里的还望着锅里的,跑骚的男人都该死!
这句话,捅了警备队长的心窝子。本想把二麻子抓了,留下娘们儿慢慢消遣,没想到这娘们儿先把门堵上了。几乎在同时,他改变了主意。说,把二麻子放了。然后指着梨花说,把这娘们儿带走。
二麻子脚踩在门坎说,那不行!
警备队长淫威地说,这事儿由不得你。杨大肚子的死,你老婆逃不了干系,我们必须带回去审查。
二麻子把话拉回来说,队长,你大人大量,你抬抬手,我们就过去了。
警备队长说,过去?二麻子,我告诉你这个坎儿你是过不去了。你知道吗?那个杨大肚子是什么人?那是日本人的特务。我饶了你们,日本人也饶不了你们!
二麻子说,你把老娘们儿放了,我跟你们去。
梨花说,麻子,这事跟你没关,人不是咱们杀的,他们不能把我咋样。你好好在家待着,你还有你该干的事儿。
二麻子知道梨花说的是啥事儿,就没再言语。
就在梨花被带走那天夜里,二麻子病倒了。一连三天,倒在炕上捂着大被冷得直打牙巴骨。人都说二麻子结实得像石头,可那一刻他完全是个熊蛋包,外人看着十分可怜。二麻子知道,警察找上门来,定是老刘婆子使的坏,就骂,该死的骚娘们儿,你没让日本人日过,到成了东洋鬼子的走狗。
二麻子思前想后,还真的有点后悔了。给赵老弟做事,是为杀鬼子给老婆报仇,可仇没报,到头来把老婆倒搭了进去。
8
老客们听说要封大车店,就纷纷而逃。店掌柜的心疼得暴跳如雷,大骂警察狗子,拿人钱财,不为人办事儿。
二麻子躺了几天,也想了几天。他终于想明白了,要想好,不单单要和日本人斗,还要和中国人斗,准确地说是和那些个汉奸们斗。二麻子去了几次天增泉警备队,门都没让他进去过。只好在门口儿晃悠,见警察出来就打听,遇上好的摇摇头,碰上不好的就骂一声滚。
二麻子在绝望中“滚”回了林茂屯。刚进家门,见门旁插根野鸡翎。二麻子找不回老婆,索性横下一条心,噌一把拔下野鸡翎,调转爬犁进了骆驼峰。
二麻子见到赵春霖,并没哭诉老婆被抓的事,倒是赵春霖听说这个消息后,跪在地上给这个大哥叩了第二个响头。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二麻子把老客们遗弃在大车店外的爬犁拖到一块儿,用绳子连上,拖拖捞捞地运到了山上。据说赵春霖从姜家窑屯的姜大掌柜的家借了几匹马,套上这些爬犁给游击队送了大量的物资。有粮食,食盐,药品,枪支,弹药。
二麻子也毅然决然地挎上枪参加了队伍,从杨大肚子第一次拔下野鸡翎子,二麻子就对他恨之入骨,二麻子把野鸡翎子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进入队伍后,二麻子发誓,要把野鸡翎子插遍骆驼峰的前前后后,南南北北。
后来,听说游击队拿下了天增泉,袭击了警备队,有人见到了二麻子和梨花。没有几年,又有消息从林茂屯传出来,二麻子两口子都死了,死在了那场战斗中;也有人说,梨花死在那个警备队长的手里,警备队长又死在二麻子手里。
故事流传的很久,究竟谁死在谁的手里,无从考证。大家只是看到村村落落的野鸡翎子越插越多,一直插到一九四五年。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