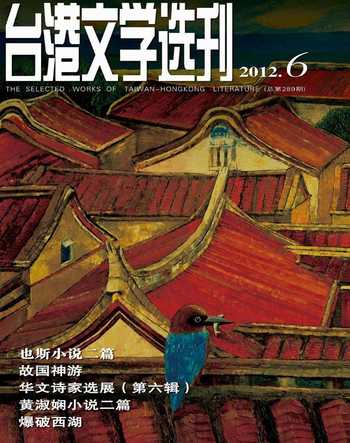移民的日子
林婷
楔子
岁月如水,当年华流逝无法挽留,当所有的憧憬成为往事,当幻想过盼望过期待过挣扎过实现过也幻灭过之后,生活才逐渐展开真实的一面。七年前的此时,手里握着“移民纸”,我们一家放弃国内的一切,收拾好行装,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茫茫然不知前路如何。七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七年间,所有的风雨沧桑,都化作了心中无字的歌。
用微笑替代所有的思绪。一些人来,一些人往,如一场幻梦。一些疏离,一些阻隔,一些接纳,一些交集,一些值得思考值得探索值得反省值得汲取的人和事。当那一年过去的时候,对自己说,淡然;当这一年来临的时候,依然如是。一些形式,越来越清淡;一些情谊,越来越游离。如若必定是要纪念,放在心上的自然记得,就算忘却了漠然了又如何?
平凡女子如我,如梦红尘中踽踽而行,独立寒宵,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可以遗忘现实烟火的滋味;或许,能够寻找一处安详和宁静的桃花源,于喧嚣红尘中做一个清梦,得一份慰藉,在山穷水尽处拈来柳暗花明的片刻愉悦,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时光像被无数细丝密密扎扎地裹束起来的茧,突围而出的后果是死路一条,化蝶而出的日子,却来日还渺。
在这静静的夜,思绪又开始游走起来,在清寂的沉默里,继续闪回……
风起
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就如大多数凡俗之躯一样。很多人都会问“为何要出国?”我也无数次问自己,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答案。其实,很多事是没有为什么的。
记不清是在1997还是1998的年底了,在家接了个移民公司打来的电话,说在人才库找到我先生的资料(我先生曾有去新加坡的念头),问我们想不想全家移民加拿大。那时的我,就连加拿大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不了解。或许,在机关上了七八年的班,平淡无奇,我又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就答应对方去见个面,听个讲座。没想到这一步迈出去,再也没有回头。一个星期后就跟移民公司签了合同,如同随便在张白纸上签个名那么简单,那时压根就没去想这以后的路该如何走。现在回想,自己在签这一纸合约之前,所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都太顺利了,即使有些风雨也都是父母给挡着,所以完全没考虑这个决定对自己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
接下来的半年里,先生还很认真地要学些英语(主申请人是他),半年后热情渐退,我们还是照常上着班,过着如常的日子,基本上当申请移民之事是个生活插曲了。那时办移民的人很多,我们是往菲律宾递的件,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三年,我们接到面试通知时已是2000年的夏天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往更顺畅的方向发展着。去菲律宾前,母亲一直说,不要去了,那几万元的申情、中介费就当是丢了罢了。我们也总觉得不可太儿戏,权当去旅游,再说了,就我们那英语水平,通过的机会太小了。没想到,世上总会有奇迹出现,我们竟通过了面试。接下来的日子,我历经了两次体检,初次在老家,复检在上海,之后就又没了消息。
转眼到了2002年初,移民签证还没收到,体检一年的有效期就要过期了,那样的话,又得再做一次体检,天哪,又要浪费一万多元的体检费不成?!说实在的,移民这事办的,已经让我们负资产了。问中介小姐,一问三不知,就让我们等,等,等。一气之下,我给加拿大驻菲律宾领事馆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概是:我们全家从申请移民到现在,已三年多,小孩从两岁等到五岁。每个人都有生活安排,若能给我们签证,请在孩子生日那天给他这份礼物(小孩的生日正是那年春节后几天)。这封信我分别以传真和e-mail的形式发出,那时,移民公司还威胁说,这样做一切后果自负。我说,有啥了不起的,最坏就是去不了吧,有啥了不得,我还不想去了呢。那时,跟我们情况类似的就有百来个家庭吧。我想,凡事总要有个结果。没想到,孩子生日那天,我的e-mail邮箱里收到了签证官的信,说移民签证已于四天前寄出,这是给我小孩的生日礼物。我是比移民公司都早得知签证通过的消息的。
我们的签证期限要求在四月底前登陆,也就是说,从收到签证起,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已经不能再选择去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那时才开始害怕未知的将来,可是,我们已没有退路。辞职,买机票,卖房子(我们那时已是身无分文,卖房的钱是我们要带往陌生国度的救命钱,以备不时之需)。
2002年4月26日,我们十几个家庭乘坐国泰航空的班机,飞往加拿大多伦多,从此,踏上了一条艰难的不归路。
风寒
那年的4月26日半夜,飞机经过了十八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多伦多。从空中往下望,多伦多的夜晚灯火闪烁,美丽而宁静。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里法律规定所有的单位机构、公共场所,夜晚都不允许熄灯。我们办好所有的通关手续后已是半夜两点了,走出机场,在寒风中等待移民接待站的人来接机,多伦多四月的天还是冷得如老家江南的冬天。五岁的小孩已在怀中睡去,夫妻俩的心也开始有了离开故土的悲凉,从此后,乡关千里万里了。
我们到达接待站,叫醒小孩,跟他说:“到了。”孩子睁开双眼,看看四周,冒出一句“为啥到乡下来啊?”真是童言无忌啊。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对他来说,外住应该是宾馆才是。在他的印象里,只有一年里两三次回乡下爷爷奶奶的家才是这样的啊。其实,移民接待站也就是一个私人的住宅,房主夫妻俩从中国到英国,又从英国到了加拿大,说是从事医药生意的,将一个好好的HOUSE每一层都隔了好多个房间,包括地下室不下二十间,他们自己一家三口只住一小间。我们的房间在他们的隔壁,就两个小床、一张小桌而已,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排队等着共用的厨房、卫生间,匆匆洗刷一下就将自己累得如行尸走肉般的身体抛到陌生的床铺睡去了,一切等明天再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就是忙着去移民部申请工卡、医疗保健卡、幼儿牛奶金等。等到周末,国内好友的加拿大朋友来看我们,给了我们一张多伦多地图,买了份报纸,我们一家就跟着他们去找房子租住了。几天里,我们受够了共用厨房、卫生间的痛苦,以及对孩子的限制(接待站房主一看到小孩走出房间,就冲他叫,别跑,走路要小声,不要吵了别人),那一层六十平方米左右的HOUSE,上下共四层住了几十号人,到处都吵得很。让我想起2000年搞人口普查时见过的民工的住区。
坐上开往唐人街的车子,我悲从中来,难道所谓的自由就是生活上共用厨房、卫生间?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哪怕是地下室,我也住——只要是独立的。
刚刚登陆的移民,如要租Apartment(单元房),首先要向公寓管理处申请,要提供工作、银行证明等一大堆材料;若没有工作,则要有朋友出面担保,再转给你住,这样的话,朋友是要承担信誉风险的;要么,须有足够的资金,一次交足一年的房租。这几个条件,对我们来讲都是奢求。很多来了好些年的中国家庭,租下二三间房的公寓,一家三口只住一间,然后做二房东,把其余房间租给新移民。但我的底线就是独立居住。
我们拿着报纸,给一个个看着合适的房东打电话,约看房的时间。唐人街给人的感觉是你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场景,马路上开着电轨车,窄小的地面覆盖着双向铁轨,一看就是跟路边的百年老屋一样历史悠久了。我们看了四五处房子。大凡一楼的房子,房东看你拖着五岁大的小孩都不愿意出租,因为这里的house都是木制的,房东的地下室也是出租的,都怕吵着租客;我也不想花钱租房还要让孩子像小猫一样蹑手蹑脚。多伦多自然环境好,到处绿草如茵,海鸥成群,很多地下室微小的窗户外就有很多鸟屎。我们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目标只能是还算干净的地下室了。儿子喜欢上有一个大窗户又没有鸟屎的三房一厅的地下室,就定了这户人家;其实,走了一天,大家都累得没有心情再比较了。
次月初,我们终于搬进了每月花六百三十加币租来的自己的空间。面对简陋的两张单人床,我竟然有了心满意足的感觉。那扇大窗足够让阳光进来一个上午,其他的两个房间一个做电脑房,一个做杂物间。
后来几天,我们买了大床、电脑、电话、传真机、电视及其他生活和找工作用的必需品,这个家算是安下了。后来认识的人都说我们太浪费,很多东西他们都用拣来的或从二手店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我想,大人可以努力平衡心里的落差,孩子何辜,不能让他有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
即使这样,孩子还是不时地问我:妈妈,我们家的大沙发哪里去了?直到今天,我们买了自己的房子,好好布置了各个角落,孩子对五岁前一直住过的房子却仍记忆深刻,我固执地认为是那一年的地下室生活给他的落差太大了,谁说小孩容易适应或是遗忘?!
几天之后,我们从后门出入,才知道我们租的房子,后面正对着一个公墓和公园。对我来讲,这没啥可怕的,后来去的地方多了,才知这也是老外一大特色,在繁华的地方,总会有一块墓地。想想也是,加拿大人太少了,这样的安排,活人跟死人都不寂寞吧。
五月的多伦多美得惊人,我们却无心享受,安排好孩子的入学,就投入了找工作的行列。
随着斗转星移,我越来越相信宿命的安排。登陆一个月后,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公司,三个月后就从车间转到了办公室搞设计。先生在国内念的是机械专业,可十年间都没干过跟专业有关的工作,对他来讲,一切都得从头学过,还得克服语言沟通的障碍,那种压力可想而知。可是,无论如何,总是比很多人幸运了,没有经历送PIZZA、搬运、装修、餐馆打工的劳苦,这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总算给我们苦闷的日子带来一丝安慰。
加拿大幼儿园每天只上半天的课,而且只有三小时,我就在家里一边带小孩,一边了解社区里的各种信息,考虑着自己的将来。在机关待了九年多,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家的对面就有一家麦当劳,每周都带孩子去吃一次,这里的麦当劳并不贵,套餐在3.99~7.99元之间,即使这样的价格,在移民初期的日子里也不是人人都敢去的。也许是每次都只买一份的套餐给小孩吃的原因吧,他总是问我:“妈妈,我们现在是不是很穷啊?”本不愿让孩子感受到太大的落差,可生活的点滴总是潜意识地给他一些印象。日子就这样继续着,人生活在最低层时,惟一的企盼就是平安了。
移民登陆的前三个月是没有医疗保障的,看病的费用要自己出。一个周六早上,孩子肚子疼得厉害,说实话,人生地不熟,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看病。问了房东,我们还没医疗卡、家庭医生,没有预约,就只好去“WALK IN”的门诊了。抱着孩子,找到房东说的那家门诊,外面有人排着队了,可诊所还没营业。这里的商场、营业机构,周六、日营业时间晚得惊人,十点或十二点之后才开门。我们在焦急中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诊所终于开门了,可这时小孩对我说:“妈妈,我不痛了,我们回家,不看了吧,别浪费钱。看,我都能自己走得好好的了。”说着就从我身上跳下来,自个儿往家的方向走去。这一刻,我那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的心终于崩溃,望着他小小的身躯,我站在异国的街道旁第一次泪如雨下。儿子从小到大,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可以说,他在国内时,连公共汽车都很少坐,出门基本上是打的或三轮车,可今天,带着他来到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未来的异国他乡,是不是对他太残忍?!
也许,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知足”。我们曾经生活在幸福里,还不断地抱怨,欲望无休止地膨胀,而此时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时候,才惊觉那过去的好时光朝着你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
今天,七年后的我,回首来时路,对上天给我的厚爱心存感激。先生撑起了养家的重负,我从来没有为生存去奔波。生活不可能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似乎也不会太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重回COLLEGE念书前,我打过三份工。第一份工是陪一个比我迟一个月登陆的朋友去的,她在国内是工程师,在外企干了很久,一家三口登陆的第一个月是在亲戚帮忙租的一间小屋里度过的。当我在那间小屋见到她时,她已经在小屋里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看到我的那一刻就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对彼此均无言。几周后,她让我陪她去职业中介找了一份在鸡肉厂打工的活,我们各交了80元的中介费,还得买安全鞋,又花去了60元,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就得起床,中介的车载着一车人在高速路上狂奔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个鸡肉厂,真有一种被卖掉的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工厂内是啥样的。五六月份的多伦多已是阳光灿烂了,如盛夏般地热,我们却要穿上棉衣棉裤,在零下十几度的生产线上串鸡肉串。冷气的白雾没过膝盖,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三天后,仅仅是将花掉的140元本钱拿回来,我就跟那串串鸡肉说再见了,同时在心里默默祝愿那一车间的工程师们早日脱离苦海。
第二份工是衣厂女工,就在距我住的地方步行五分钟的地方,那份工是某天路过,随便进去登记得来的。在那里,我认识了曹和王。曹跟我操作同台机器,第一眼见到她,憔悴无光的眼神让人感到恐惧。那时她来加拿大已经两年,先生原是西安交大的教授,自己也是该校的职工。两年来,她先生一边在一家超市当兼职上货员,一边努力找专业对口的工作。曹在这家衣厂做了一年多了,靠她微薄的收入养着家。她说,自己已经麻木了。王跟我一起进的衣厂,她跟先生在国内都是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那时也是她打工养家,先生偶尔在餐馆打打工,主要的目标也是找专业工作。那个衣厂里所有技术移民过来的女工都是相似的情况。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人人都已迷失了自我,看不到任何知识女性的痕迹。我于一个月后又离开了衣厂,那里的气氛只会让我感到绝望。后来,曹的老公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全家搬离了多伦多。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后来她学做修指甲,先生在一家公寓大厦里当管理员。她说,熬到她女儿上大学,就要回国了;为什么要移民?
第三份工是化妆品厂女工,那份工来得戏剧化,去得也戏剧化。我带小孩去医院看牙齿,在公车上听人说那个厂在招人,就带着孩子去面试了,没想到在那里旋口红盖旋了一个星期,就让人家赶回家了,本来他们招人就是临时赶工的。说实在,那是三份工中最好的一份了,可惜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茫茫移民人海中,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了。移民的第一年里,我有时间回望三十多年的前路,父母的荫护点点滴滴,先生的宽容让我自由从容地我行我素,现如今惟一悲伤的原因是远离故土家园和亲情。我清楚地知道,回头无岸,向前总是有希望的。
加拿大是个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被政府征去的税高得吓人,让人想到“苛政猛于虎也”。但对于刚登陆的移民来讲,那些福利给了他们许多帮助。
我在打过三份杂工之后,就进入了政府办的一个英语培训班学习,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为了第二年去念COLLEGE做些准备。这个学习班是给新移民开办的,学生按入学测试的不同水平分班。校内有托儿中心,学校还给所有学员及各人的小孩发公车车票,一切都是免费的。有一些省的这类学习班,政府还给学生生活补助,每月四百至六百元加币,而多伦多是没有的。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学校步行只有十五分钟,我跟孩子基本是走着去,省下车票做他用。我所在的班级水平高些,说实话,以技术移民身份来的,在国内都是上过大学的,英语的读、写都还凑合,就是听、说能力太差。即使是国内英语专业科班出身的,在听、说上也一样不行。老师总努力将中国人分散到不同族裔的GROUP里,逼着每个人都得开口说,无形中就培养了敢讲的勇气,口语有所提高。其实,加拿大是移民国家,人民来自各种族裔和文化背景,只要开口讲,能让对方听懂就行,在所谓的语法上他们并不介意。记得老师每天都会给大家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有次老师讲到加拿大的假期时很是得意,她认为加拿大的假期很多,其实就是基本上每个月有一天的公共假期而已,跟周六、日加起来有三天的时间,他们称为长周末。这跟我们国内的假期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中国的假期多,他们都不信,老师还要我去黑板上列出来,讲解给他们听之后,他们还将信将疑。在大多数的老外眼里,中国还停留在“东亚病夫”的时代,他们内心根本看不起中国,即使现在的发展有目共睹,在他们心中还只是“暴发户”的形象。这跟宣传是有关的,多年以后,我觉得加拿大人就如井底之蛙,天空只有加拿大的天。那天,也许扫了老师的兴,她问我在中国的职业,我跟她说是政府公务员统计师时,她和班上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学都有点震动(在加拿大,统计师是很高级的岗位,在中国却一文不值)。老师用那种不服气的口吻再问我:“Why you came to Canada?”记得当时我很大声地回答:“I am stupid,and many many of Chinese like me are stupid to choose coming Canada。” 那真是我当时的想法,被几个月的艰难压抑后的爆发。说完就哭了。冲进厕所后,跟进来几个中国同学安慰我,也是红着眼。我知道我触动了她们一样克制的情绪。再回到座位后,老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最有人性的话:“Take care.I knew your feeling;I landed here 25 years ago with my family.”我想,二十五年前的艰难同样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吧。
在那所学校,我认识了三个朋友,莹、欣和冰,三个人的老公在国内都是搞IT的。莹和欣的老公都在努力找专业工作,所以,她们俩都得肩负养家的重任。不久,她们都离开学校打工去了,莹在一家咖啡店,欣先是在一家面包屋,后来又去了一家一元店。冰当时因为怀着孩子,打不了工的,她老公就去学做西餐,想当厨师。人在不得已时,理想和追求就成空谈了。好在莹和欣的老公后来都找到了专业工作,她们也守得云开月明了。
我于2002年底,等不了登陆后的一年(登陆后一年,去念大专或大学,才会有政府的补助金),就递了COLLEGE的申请,准备2003年初重进校园,混个文凭去。
2003年的1月,在登陆加拿大八个月后,我跨入了CENTENNIAL COLLEGE的校园,主修会计。从前学的是工商企业管理,在统计局干了近十年,没想再干统计,因为统计在这里的门槛太高,一定是本科以上才能做的专业,我是不指望有那恒心、毅力及能力念下来的。对于移民来讲,女会计、男电脑,CNC是普遍的现象。会计在学习时,语言要求不是很高的,对当地人来讲,初级会计文员的工作,高中毕业生都能胜任。
大专的学费并不贵,一个学期四个月,选四门课免费送一门,一学期一千二百加币左右(对留学生就很贵,五千五百加币)。但这里的课本贵得很,每本都要一百多元,对新移民来讲,是没有人能付得起这书本费的,我们就买学姐们的旧书,还是几个人合买一本,然后再拿去复印,这样的话,一本书就十元左右。对我来说,提早四个月来上大专,还申请不到政府的贷款和小孩的托儿补助金,就更舍不得花这钱去买书了。学会计的中国人太多,英语水平根本提高不了,第一学期还挺认真听老师讲课,说实话,跟听歌一样,几乎都听不懂,倒是书都看得懂,这边的书编得真是好,没啥废话。
第一学期上课时,我还住在地下室,去学校要换乘三部公车、两路地铁,在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冬天,等车的煎熬历历在目。记得刚开学时,孩子出水痘,我待在家里照顾他,我们一家三口,一个上课,一个上班,还得照看小孩(这边法律规定,小孩12岁以下的,24小时要有人监护)。没有人能帮忙,先生就一直上着中班(下午三点至半夜十二点),他也是要换乘好多趟公车才能到上班的地点。我跟先生在一个屋檐下,却只有周末才能说上话,这种辛苦无法形容。这里的小学下午三点半就放学,等我下课回到家已是华灯初上了,所以还得从微薄的收入里拿出钱来请人每天代看小孩几个小时。也许,亲历过,才明白有家人、父母、朋友在身边的可贵。
那年四月,我们终于搬离住了一年的地下室,迁进了距先生公司只有十分钟路程的一套一房一厅的公寓。孩子的学校就在那栋公寓楼的背面,离我学校却是越来越远了,要换乘三部公车、三路地铁,单程就要两个小时。先生总是有太多的加班,再让他在路上折腾的话,就太辛苦了。那个区中国人很少,也没有中国人开的超市,房租也很贵,我们的生活费用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对我来讲,美好未来还遥遥无期。请了楼下一个白人老太太照看小孩,她可是严格要求在十八点必须接走孩子的。我总是每天在路上奔波着,精疲力竭,会计的就业状况并不是很好,真看不到希望所在。就这么艰难地修了一年半的全日制课程,我将三年的文凭转修成两年的文凭,修了二十门的课程,就差两门可以毕业了(在国内大学修读的一些相关课程在这里可以转学分,我因此少修了两门课)。
一年半的学习,共拿到政府的贷款、各种奖学金三千五百元加币以及小孩的托儿补助共三万加币左右,全职学生课程修完后就只还了政府一万五千元,所以说加拿大是高福利的国家。换句话说,不要羡慕在国内听到某某人到国外念博士怎么怎么,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将念书进行到底的,这样即解决了温饱问题,节约些还有剩余;没有毕业的全职学生,是不必还贷,也不算利息的。如念硕士或博士,这福利会更多些。
这一年,经历了SARS、北美大停电(美国一个发电站因线路故障,造成从美国到加拿大几十个大城市大停电,都以为是继9·11之后的又一次恐怖袭击。不过,大停电没有造成大城市的混乱,交通秩序城市治安等都有条不紊,让你不得不感叹加拿大的文明程度),先生最小的姐姐在国内因交通意外过世,我的父亲第一次从鬼门关里夺回了性命……一切的一切,让我们孤身在外的游子,怀想亲情的可贵和生命的不易,将所有的期许都搁浅,活着就是希望。
2004年6月,我搁下还未修完的两门课程,带着孩子回国探望父亲。父亲于四月病重住院,家人在他脱离危险后才告诉我。其实,那时我正在期末考期间,即使先得到消息,或许也无法回国,这就是离家的无奈和必须面对的背离亲情的痛苦。那时,姐姐还在日本讲学,她是在第一时间赶回国的。一直以来,姐姐总是尽着她作为长女的责任和义务,她为此付出了很多。而我,为自己的不孝承受着心灵的煎熬。“父母在,不远游”;“子欲养,而亲不在”。古人之云,总感切肤之痛。望着父亲苍老的脸,我明白出国的决定错得有多深,自己踏上的是一条怎样的不归路啊!一个半月后又无可奈何地回到多伦多,我必须完成学业和为渺茫的未来继续向前,再一次像飞蛾扑火般,不能回头。
很多移民在离开故土后,总是很多年都没有回国看看,那是出于怎样的无奈。很大程度是因为无法承受经济负担。一个人回国一个月,至少要六千至八千加币左右的支出,这是一个人辛辛苦苦打工半年的最低收入。来加六年里,我回了三次国,一次是探望劫后余生的父亲,第二次是给他过七十大寿,第三次竟是奔丧而回的,父亲已跟我阴阳两隔了。先生在这几年间,就只回了一次,是直接奔丧去的,他的老父亲也过世了。几年的时光里,很多亲人先后离开了我们,先生的姐姐、外婆、父亲、堂哥、表哥、姑母,我的父亲、大舅妈、姑妈、表哥。我们离亲情越来越远,异国他乡的友情又淡如水,我总游离于生存和情感之间,痛着。就如一个朋友在奔完父丧之后,跟我说的就是:“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是个孤儿。”是啊,我们已经一无所有,除了永恒的父子母女之情,我们还能守住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几年浪费太多的金钱在路途中,我却从没有为此后悔,即使如此,父女之情还是像断了线的风筝般再也回不来了。
2004年8月,回加之后,我就进入了找工的行列,同时修读未完的两门课程。简历发出无数,面试的机会少之又少,即使有,也都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加拿大企业大都固执地需要本地工作经验。留学生加移民,太多学会计的了,就业状况很不乐观,给的薪水也跟打苦力差不了多少。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一家TIMHORTONS当收银员,这是一家加拿大本土的大型咖啡连锁店,在第一年打了三份工厂工之后,我是再也不愿迈进工厂的大门了。服务性行业接触面广些,也有助于口语的提高。那时,因为房租太贵,我们再一次搬家,这个住处离我和先生上班的地方都很远,我们又开始了各自奔波的日子。2004年年底,买了第一部车,我和先生有一人不需要再带着疲备的身心在寒风或深夜中等车了。
在那个地方,我干了八个多月,每周五天的班,周六上课。总算在2005年4月修完了学业。就在我修完学业的那个月,一个朋友换了份工作,就将她先前干的那份会计活推荐给我,我终于在来加后的第四年,重新进入办公室职员的行列。
风平
人生有过对比,才知道如何去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移民头三年的辛酸苦辣,渐渐磨灭了我锋芒毕露的个性。当年,在国内时,对着刚买下两年的房子,就整天想着啥时可以换更好的。如今,瞪着地下室的天花板,只想着何时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哪怕是草屋,家徒四壁也好。眼下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屋,虽是贷款而来,可迈进家门的那一刻,就有了家的感觉,尽管,当两脚迈出家门,脚踩着加拿大的土地,都很清醒地知道,这块土地不是你的家。几代的移民奋斗着,可永远都还是黄皮肤、黑眼睛、持加拿大护照的华裔。每一个移民的脑海里都时时响着“是生存,还是毁灭?” 的名言。
回想在鸡肉厂的冷库中,膝盖疼痛的感觉,在衣厂曾经因高温下塑料放出的毒气而晕倒在厕所的日子,在咖啡店打工时被二百多度的高温咖啡烫伤的手,对着第一份办公室工作的简陋的场所,我却有了心满意足的感觉,虽然面对的是毫无文化的暴发户老板,冬天还得忍受因老板舍不得开暖气的冷,但比起那些和我一起在CENTENNIAL COLLEGE念书的同学们,她们大部分因找不到办公室的工作,重新又踏入了打劳力工的行列,或是去了赌场当发牌员,我还有什么可抱怨得啊!在这家公司上班的两年间,我学会了很多会计的实际操作,也看到了许多人情冷暖、世事无常。这家公司多是雇佣没有身份的留学生、偷渡过来的难民,以求减少成本。在仓库的戴,来加留学四年,因没拿到身份,学生签证过期,一直黑在这里,打着黑工。有一天在高速路上开着车,被警察逮着,直接送移民局看守处,两个月后被送回了国,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那些花钱办假结婚证的留学生们,倒是熬过两年后,都能将身份搞到;佳和欣是真正的一对,女的念书,男的打工,慢慢地为身份努力着,那年,他们结婚(也是为了能同时申请移民),我是证婚人之一,晚上下完班,匆匆忙忙去了公证处,就他们一对夫妻、两个证婚人、一个牧师,这个婚就结了。欣一直都没有笑过,我们也跟着辛酸。在国内,现在哪对新人结婚会如此冷清,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鲜花和宴席,仅仅有证婚人苍白的祝福?几个月以后,欣跟我聊天时说,她从十九岁离家,在这异乡土地上艰难求学,为了能拿到身份,不断地从这个学校念到那个学校,将近八年了,前面还是个未知数,从一名少女到一名少妇,谁为她的青春买单?!所有的父母一厢情愿地将子女送出国门时,是否真正明白少小离家的辛酸?也许他们只能为了父母的虚荣或父母自以为的爱子之心而无奈地任由青春流逝……另一个阿黄,是从美国偷渡过来的,他说,他在美国十四年了,也黑了十四年,再一次冒着风险来加拿大争个身份(据说,难民在加拿大比在美国容易拿到身份),人生何求啊!
2006年,介绍我进这家公司的朋友,因为2005年买房后的一个月先生就失业,她先生不得不带着孩子先去了新加坡工作,我的朋友苦撑了一年,也无法供养他们的房子,终于将他们的房子卖了,也去了新加坡,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这期间多少无奈可以言尽!我于2006年因母亲要出来探亲,也倾夫妻俩之所有,向银行贷了大额的款,买了一套小房,就为了不让我的母亲看到我们的处境而难过。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如果母亲没有出来探亲,也许到现在我都还没有买房,毕竟那债务让我们不能自由地呼吸,每时每刻都担心是否会失业,我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啊。那时,先生也刚刚换了份工作,离我们买的房子很近,但走路也要有三十五分钟的路程,为了每月能省下一百多元的公车费,他从春天走到冬天,风雪无阻,车一直是我开着上下班。2007年的春天,我因某种原因,下决心辞掉了这份我不喜欢的枯燥无味的会计工作,买了五月份回国的机票,再一次踏上回国的班机。回家了,为了能和父亲一起过他的七十大寿。这一次回国,已是持加拿大护照的名义上的加拿大人了,哪个是我的祖国,哪里是我的家?北京的机场从来没有哪个工作人员跟你说“欢迎你回来”,即使我第一次回国时持的是中国护照,也永远一副冷冷冰冰拒你千里之外的表情,虽然这是生我养我的祖国;倒是那次回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内的每一个检查证件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加拿大护照时,都跟我说“WELCOME HOME(欢迎回家)”,祖国和家都已经不再是心里的祖国和家了,从今以后我就只是个地球人了。
三年未见面的父亲,苍老得让我无法接受。2007年回国探亲,就一个目的:为父亲七十大寿而回。很多人都惊叹我的果决,没有为辞职后悔过,就如那年公公过世,先生刚刚换了份工作,试用期都还没满。我跟我先生说,“父亲只有一个,而工作还能再找,只要不饿死,一切都可从头。”公公过世时,只有先生一人回去奔丧;不是我们不愿回,真是没有足够的钱。在我的内心,我一直为这种无奈内疚。当时,我父亲为了这件事很生气地在电话里跟我吼:“是不是,我百年后,你们一家也就一个人回啊!” 很不幸的是父亲言中了一切,2008年父亲过世,也只是我一人回去。我知道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会难过的。此罪何时能赎?
我只在国内待了两周,实在是因我的辞职和回国,家里的钱都不够维持三个月了,我要回加拿大申请失业金和找下一份的工作。短短两周,我只是陪着父亲聊天,去西湖散步,好在当时拍了一些父亲的录像,让我现在还能时时看着这些录像,想象着父亲还活生生地在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待着。记得走前的那夜,父亲想跟我交待啥的,不曾想我的一个同学来送我,待得太晚,同学走后大概十点半了吧,父亲无奈地对我叹口气,说:“算了,去睡吧,明早还要早起啊。” 谁曾想到,第二天的清晨,跟父亲的拥抱竟是我们之间的永别。那一刻,似生命的定格永远烙在我心灵深处。
再一次回到多伦多,拿着失业金,一边在周末打点零工,一边发简历找工作。庆幸的是,我在只拿了一个月的失业金后,就进入了现在的这家日本贸易公司上班。一切又从头来过。这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总集团在日本,主要做北美业务,集团下我所在的这家总公司北美总部设在美国,在加拿大,就只有加西、加东各一家分公司,所有财务核算都归总公司。我的岗位是相当于销售经理的助手,负责处理加东分公司的主要客户,比枯燥无味的会计岗位好玩多了,又没有压力。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了手,也乐得不思进取了。我一直都很感激上天的垂怜,就我这不努力、不进取的态度,一路走来已经是很顺利了。不要以为在加拿大很容易找到工作,这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岗位是内部招工或朋友介绍的,他们称为“NETWORK”,跟中国没啥两样。我儿子在参加“领导人培训班”时,他的指导老师给他上的第一节课就是:你有百分之百的硬件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NETWORK。这就是为啥这边的小孩从小社会活动多的原因。
父亲给我灌输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让我可以在这里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到了2007年年末,先生却因公司重组而失业了。我们的日子又艰难起来。失业金是有的,但失业金只是让人不饿死罢了,供房供车还得靠自己。为了这个家,先生不得不去打现金工,CD厂生产线上的工人,给人做装修小工……我一直感激先生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是他默默地撑起这个家,让我们一家三口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一处避风的港湾。
山雨欲来风满楼,更让人伤心的事不期然而来,我的父亲在2008年过完正月十五后,再一次中风,这一次一去不返了,他老人家撒手走了……
对于生活在海外的人来讲,有节日也跟没节日一样,没啥区别。因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加拿大并不是法定假日,我们都照常上班,真是无法记起哪天是正月十五。2008年的那一天,下完班,因拿了太多公司的冰琪琳,我就送几盒给我原来的老板,离开时她回送了几盒广东熟食给我,我很惊讶她干嘛煮那么多的美食,这才知道那天是十五。心想着,真该死,忘了给父母打个电话了。那时,国内已是十六的早上了,父亲已经在医院抢救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回家后,一切忙完都快夜里十一点了,就想,算了吧,反正十五也过去了,明天再给家里打电话吧。第二天的清晨五点多,床头的电话响起,一听是姐的声音,我心就跌到了冰谷,父亲病危了。
那天是周五,我从放下姐的电话起,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哭着等着天亮,这一天,我得去中国领事馆办加急签证,得去买机票,还得回公司请假办交接。先生想着我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且我们就俩姐妹,便拿了一家三口的护照天一亮就跟我一起办签证去了。我们想着总该一家回去送父亲一程吧,哪怕回加拿大后这房子要被银行收回也得回去啊。先生在领事馆等下午才能取的签证,我则赶往旅行社定机票。最早的航班也就只有周六早上的,且只有一个位置了,我没得选择,只能是先买下自己的机票再说。先生下午拿到签证后,再帮我去取票。我下午赶回公司办交接,回到家已是深夜了。我不敢往姐姐处挂电话,怕听到坏消息,心里念着父亲能等我,让我看他最后一眼,哪怕能让我握一下他的手也好。先生那周刚刚得了份失业后的面试,还在等面试的结果,那夜,先生的电邮收到回复,他被录取了。那一刻,我心里已经放弃了先生回去的可能,为了活着,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虽然先生仍坚持如能买到周一的机票还要回去,我却已经不抱期望了,真是天意啊。
从来没有感觉从多伦多飞往香港的航程有这次这么漫长,十几个小时有如几天。我在香港机场等待转往福州的航班,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说,父亲走了,走了。我还是不敢先给姐姐打电话,我怕听到那个声音,可是我还是给先生通了电话,是的,是的,父亲他走了,没有等我,他就离开了。我蹲在香港机场,放声大哭。父亲啊,谁都不会知道,当我看到您静静地躺在冰棺里等待这个不孝女儿时的那份绝望,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下半夜在灵堂支开给您守夜的堂哥们,挪开了冰棺的棺盖,我抚摸着您的脸,握着您的手,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您的生息,才能和你对话。爸爸啊,我握着您的手跟您说,放心吧,所有您给我的交待我都会帮您办好。这是留不住您生命的女儿对您惟一的承诺。
三周后,我又飞回了多伦多,生活还是要继续。先生和我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且离开我们居住的城市,对着银行账户上所剩无几的位数,我们还是得有两部车才能正常上班,我终是再一次借贷银行的钱,买下了我们的第二部车。看着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债务也越来越高了,两个人的收入大都给银行打工了,笑对人生吧。无论是苦,是甜,总是要活下去的。你企盼着前路不再有风雨,金融风暴却如响彻着整个北美及世界上空的雷电,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风再起
2009年加拿大的冬天真的很冷,雪已经纷纷扬扬下了好几个月了。春节后的这两天,虽然阳光灿烂,却是冷晴天,零下二十多度,人也跟这气候般,外冷内热,是那种蚂蚁在热锅中的燥热。转眼今天又下起了雪暴,似奥巴马的誓言般,激起了人们片刻的期许,却仍挡不住金融危机带来的裁员浪潮。即使中国的牛年也带不来冲天的希望,每个人的心都跟这天气般冷到了极点。
今晨,开在路上的车都举步维艰。我停在线内等着红灯转绿的那一刻,望着车窗外茫茫大雪,看着从高速口下来的好几部车,因地上被雪覆盖的冰层而在拐弯处失控冲向路崖,我想着,裁员风暴下的人们,就像这行在雪天的车辆般,即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还是不知道撞向路崖的下一个会是谁。
听着CBC早间新闻不断播报失业率及某某公司裁员的消息,大脑有点麻木,心有点灰。新闻却也给了大家一个好消息:政府为了刺激消费,推出一个临时性举措,今年内进行房屋装修,金额在一千至一万元之间的,留下收据,政府将给予最高一千五百元的补助。我哑然失笑,真有点穷途末路之感,想着我家圣诞节后如雪花般飞来的账单,房子地税涨了、管理费涨了、保险费涨了、上网费涨了、车牌费涨了、菜价涨了、垃圾转运费也涨了,加币跌了、房价跌了,工资却没涨……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维持我的日常开支,哪来的钱搞装修啊!不过,今年的失业金增加了,可领取的期限也长了,但是领取失业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正应了国内春晚小品上的那句:人最痛苦的莫过于人还活着,钱花完了的台词。有多少人愿意加入这领取失业金的队伍呢?朋友春节打来的电话,除了第一句的问候,都是关心地问着所在公司的状况,细说周围的某某公司停产了、裁人了、只上四天班了、某某朋友被裁了……听着有点悲凉和无奈!这浪潮才刚刚开始,先是金融、IT、汽车业,现在是制造业,商业……艰难的路还在后头,加拿大的冬天再过三个月也就春暖花开了,可经济的冬天结束的日子还来日方长,遥遥无期。山雨欲来风满楼,总有一天曲终人散,人去楼空,或许留下就是幸运。
新闻上报道着中国民工返乡的热潮,不知他们春节后回到城市找工的还有多少?我担心着他们的将来。我们这些持着单程船票,乘上前往异国客船的人,都没有他们幸运,他们还可以背起行囊回到生他养他的家,而我们游走在万里之外,再也没有可靠的岸。就此抛锚了,雪继续下吧,纷纷扬扬……
回望这七年的移民路,含着多少的勇气和无奈。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且把经历的风雨化作绵远不尽的生命体验。就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漂泊最悲怆的含义是: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直到今天,无论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祝愿和告别中仍然隐含着这种悲怆的意绪。
且放下所有的烦恼,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希望在,明天就在。风继续吹吧,我不在乎,只要向前,就有希望。
有一首歌曾经这样唱:
“一天 ∕我不得已上路 ∕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 ∕为自我的证明 ∕路上的心酸 ∕已融进我的眼睛 ∕心灵的困境∕已化作我的坚定 ∕在路上 ∕用我心灵的呼声 ∕在路上 ∕只为伴着我的人 ∕在路上∕是我生命的远行 ∕在路上 ∕只为温暖我的人 ∕温暖我的人。”
责编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