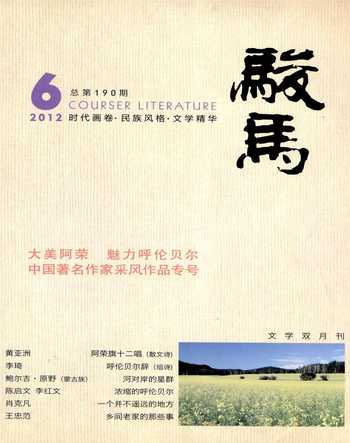呼伦贝尔草原寻梦
张成起
一
龙年盛夏。
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文联及中共阿荣旗委宣传部盛邀,我作为一位爱好而敬畏文学的业余“票友”,混迹于“大美阿荣·魅力呼伦贝尔”中国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大型文学艺术采风团,平生首次来到了令我神往魂飞的这片“一声雄鸡叫,三国(中、蒙、俄)起炊烟”的呼伦贝尔圣土。
夜宿于林密草深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卧听夜的深处传来杨、桦、松、榆相偎相依而眠静谧的鼾声和偶尔夹杂着的几声犬吠狼嚎;驰骋于一望无际芳草如茵的草原上,看碧海中羊群珍珠漫撒,望蓝天上云卷云舒。激动忘形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给草原一个拥抱,就醉倒在草原温柔的怀抱中。几缕出行时汗淋如蒸的烦躁和一丝挥之不去的无名隐忧一扫而空。
伴随着一碗浓香四溢的奶茶润喉下肚,悠扬的琴声在宽敞明洁的蒙古包里响起。马头琴那特有的低沉浑厚的音色,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诉说着草原昨天的灾难和祖先当年创业的艰辛;那金弓与银弦挟雷带电的撞击,再现着一代天骄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的所向披靡;那欢快跳跃的音符,荡漾着吹遍草原的改革开放的春风;那委婉绵长的旋律,情深深意切切地轻扯着您的衣袖——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
此曲只应草原有,闹市乐坊哪得闻?草原——只有草原,也只有草原上那勤劳坚韧、聪明智慧、淳朴善良的蒙古人灵巧的指间,才能飘出这种摄人魂魄动人心弦的天籁。
热情的祝酒歌响起。一群身着民族盛装、眼似清泉、面如满月的蒙古族少女手捧洁白的哈达飘然而至。金杯未举,而我的心已经醉了……
二
我是来草原寻梦的——是来寻我那个几十年未曾圆过的草原绿色的梦。
我与草原结缘,始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在那把“三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口号喊得震天响的“火红”岁月,按照当时省委提出的“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的要求,把我从张家口地直的一个单位,委派到地处冀蒙边界,北与太仆侍旗和多伦县为邻的坝上沽源县,并给我挂上了一个“县革命委员会第八副主任”的官衔。于是,正值而立之年的我,告别生活工作了八年的山城,只身来到了坝上,走进了梦幻中的草原。
第一次见到坝上草原,心中曾孕育已久的几分激动还没有来得及迸发,便目瞠舌僵,溺死胎中。
放眼望去,映入眼簾的虽不乏“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的空旷,但却极目难寻“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胜景。一片片泛白的碱滩,一洼洼干涸的淖泊,一群群追逐嬉戏的大眼睛褐鼠,几株朔风中有气无力摇曳的枯树,几声划破长空的乌啼……在极度的失望中,心中不免生出了几多悲凉哀叹——难道这就是我梦中的草原么?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上,曾有过一篇以《绿乎乎,黄乎乎,白乎乎》为题的报道。文章中讲到坝上这片草原,历史上曾是草肥水美的一片绿海。在“以粮为纲”的政治口号下,为了使塞外粮食产量“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开荒,异想天开地想把原本“绿乎乎”的牧场变成稷麦飘香“黄乎乎”的粮仓。结果,与天斗,事与愿违;与地斗,遗患无穷。在铁牛疯狂的吼叫声中,锋利的铁犁,犁碎了脆弱的生态——常年不足400毫米的降雨,年均不足90天的无霜期,上万年形成的薄薄的不足30厘米的宜耕土层,无论如何难现滚滚长江水浇灌出的“稻菽千重浪”。于是,“绿乎乎”绝迹,“黄乎乎”梦断,“白乎乎”的沙化盐碱化扑面而来……
年代已久了,这篇新闻报道撰稿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至今我仍由衷地钦佩当年这位新闻记者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敢于逆“以粮为纲”潮流而动的大无畏勇气。
一场也许并非恶意的梦游,带我们懵懵懂懂地绕行了四十年。好在在铁打的自然规律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痛定思痛,我们终于醒悟。于是,一个苦涩迟到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农还牧”的规划,从北京步履蹒跚地传到了坝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去年暑期,我回到二十年前曾工作生活过的山城,在几位老朋友的陪同下,驱车上坝,故地重游。
出山城北行,当年通往坝上的“九里十八弯”的山路,已变成一条平坦的高速坦途。蓝天白云下,一座座傲立山梁的乳白色的风力发电机的铁塔上迎风悠闲地摇着的巨型扇叶,热情地把我迎到了久违的坝上草原。停车驻足,凝望曾给我留下心底深深伤痛的这片土地,依旧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天苍苍”,但“野茫茫”的大地变了,昔日成方连片的一垄垄斑秃疥癣般的农田,又开始涂上了浓淡相宜的一抹绿色,变成了山草野花的家园。坡梁上迎风摇曳的一簇簇杨榆幼树,开始艰难地为大地撑开了一片片绿荫……我终于看到,昔日坝上的“白乎乎”开始向“绿乎乎”有了一个步履艰难但十分可喜的转化。于是,我心中便多了几分欣慰和期待。
亲吻着脚下这片芳草萋萋繁花似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飞回了千里之外的塞北。不知曾给我留下无限伤痛的那片草原,真正圆上那久违的绿色的梦,明天的路还有多长……
三
呼伦贝尔七日。采风归来,身返闹市,而我的魂却丢在了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草原上。高高的兴安岭,茂密的大森林;毡房好似白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晚风吹送天河的星,轻骑踏月不忍归;壮哉——父亲的草原,美哉——母亲的河……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绝、挥之不去。
生于长于冀中的我,站在大平原上放眼四野,尽管三里一庄、五里一屯的稠密村落遮掩得地平线难寻,但比起长居“一线天”的山里人来,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知道天宽地阔的。但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开始为我坐井观天的无知自愧不已。放眼远眺,微风下滚滚的碧涛,奔流不息地向天的尽头无声地涌动而去。人常言,“世间最大大不过天”。但我确信,即使走到天的尽头,呼伦贝尔大草原也会仍在地平线外无限温柔而顽强地延伸开去。
我蓦然悟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只有这样辽阔的大草原,才有了“怒行追疾风,忽忽跨九州”的蒙古千里马;只有这样辽阔的大草原,才容得下“悠扬传百里,高亢遏行云”的蒙古长调;也只有这样辽阔的大草原,才孕育了一个“宽厚容天地,威猛惊鬼神”的伟大民族!
漫步在松软如毯的草原上,陪同我们一路同行的当地文友及两位周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志愿者小姑娘,如數家珍地向我们介绍着草原上名目繁多的植物:这是碱草、针茅、羊草;那是苜蓿、冰草、隐子草;还有牛羊吃了最能增肥上膘而又能解除羊肉膻气的野韭、山葱。开满山野的洁白的银旋花,金黄的金莲花,翠蓝的溪荪,桔黄的斑百合,粉白的紫斑风铃……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凝视着脚下令人望而生怜的一株株小草,我想,盘古开天的千万年来,她们原本是没有姓氏的。也许她们从不知道自己昨天从何处来,更没有想过明天要到何处去。每年属于她们短暂生命的周期充其量不过百余日。但她们却一代接力一代地无声无息地践行着对人类的无私奉献。每当草原上西风乍起,鸿雁南飞,大雪飘落,百色归一的季节,她们把自己纤弱的身躯蜷伏于厚厚的冰雪封盖之下,年复一年地熬过了漫长冬季-40°C的严寒;当早春献媚的阳光贪婪地舔融了草原上的冰雪,肆虐的狂风掠走了草原上最后一滴露珠,她们又忍受着干旱,熬过了令人窒息的一场场沙尘暴。但她们从来无怨无悔。而只消一场春雨,一夜间,她们伸展身躯,又悄无声息地染绿了万顷草场。于是,千里草原上的盛大节日到了——一群刚刚降生行走脚步尚未平稳的小羊羔奶声奶气的欢叫声传遍了草原;几匹顽皮的小马驹耸耳甩尾,昂首扬蹄,一个蹶子一串屁地追逐嬉戏,天边的白云间,传来了几声清脆的“咴儿咴儿”嘶鸣……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我的草原,我的家。我的心爱,我的思恋……”把世道沧桑和对草原的挚爱写在脸上的怀抱马头琴的牧人老阿爸醉了。
四
草原上的夜是一种神秘少有的静谧。在这追名逐利钩心斗角的浮躁世间,似乎只有来到草原,才能寻觅到一片安放被滚木礌石明枪暗箭残酷蹂躏得千疮百孔的灵魂的净土。
夜深秉烛,细心翻阅着当地为我们提供的相关资料。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与我工作和生活过的张家口坝上草原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年均350毫米左右的降雨量,常年90天左右的无霜期,冬寒夏凉的典型大陆性气候,30厘米左右的宜耕土层……
而脚下这块生态如此脆弱的土地上,不仅在七百四十年前,走出了叱咤风云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疆土辽阔无二的蒙古大元帝国的一代天骄,而且还孕育出数个统一北方,建立独立封建王朝的鲜卑、契丹、女真等草原少数民族。即使从东北杀入关内统一中原,建立中国最后一个二百六十年封建王朝的满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仍可找到她们的原始祖先发迹的遗迹。
正是在这上千年的旌旗猎猎、剑戟铿锵的厮杀声中,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一次次猛烈撞击的雷霆闪电,推动着两种文明有机的大融合,演绎着波澜壮阔、斑斓绚丽的大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史。
如今,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草原民族特有的执著坚韧,在我们伟大祖国雄鸡啼晓的版图“鸡冠”处的北部边陲,为华夏芸芸众生,为全人类,守护住了地球上最后一片干旱半干旱区最美的原生态草原!
于是,我的心中,便生出了几多对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民族兄弟及其祖先们无限的敬仰。
查阅相关资料显示:呼伦贝尔市,面积25.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山东和江苏两省面积的总和;人口250余万,仅相当于山东和江苏两省总人口的1.46%。新巴尔虎右旗,面积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廊坊市总面积的4倍;而她承载的近4万人口,仅相当于廊坊市的近1%……
历史容不得半点假设——但恕我狂妄无知。
假设几千年前,这里的气候温润赛江南,土地肥沃如松辽,人口密度似冀鲁,今天我们还有这片宁静的草原吗?
假设这块草原有过那么一天,也开来了高擎“誓让北国变江南”大旗的垦荒大军,一阵铁牛轰鸣过后,上亿年形成的脆弱的生态一朝破坏殆尽,这片美丽的草原今天还复在吗?
假如没有草原上的民族兄弟“谁爱护草原谁就是神,谁破坏草原谁就是魔”这种世代不舍不弃、嫉恶如仇的顽强坚守,今天,我们又到何处去寻找草原的神话和神话的草原?
……
五
人似乎是一群极为少有的奇怪得不可思议的动物。
盘古开天地,人猿相揖别。当人类告别了采集狩猎的史前荒蛮,走出了茂密的山林,告别了茹毛饮血,创造了漫长的游牧及农耕文明,又尽享了近代工业文明及当代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带来的优越,暴殄过几乎所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物后,仰视被一幢幢插天刺云的高楼分割得七零八落的铅色天空,忽然觉得在钢筋水泥浇筑的森林中生活得无聊和乏味。
于是乎,城里人便又开始斥巨资,充分运用当代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和搬运工具,把祖先的祖先们曾经生活过的大山里的一株株百年老树,蛮横地搬到了城中新修筑的一条条笔直的沥青水泥路旁,极尽虚伪地炫耀着新城的历史厚重与古老。当大山里的人们把巨石林立、山高壑深、交通不便仍作为致富路上的拦路虎千诅万咒,急切盼望子孙们尽快走出大山时,城里人却把盘古开天时留下的一块块奇形怪状丑陋不堪的山中巨石,不远百里千里,辗转运到城中,垒起了一座座假山。更有甚者,以塑充石,喷涂障眼,几可乱真。当干旱尚在年复一年愈演愈烈地威胁着大半个中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老农,面对瘠薄干涸的黄土地盼水望穿干涩的双眼时,大都市里的一股股清泉却毫不吝啬地洒向了一块块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于是,汗流浃背的老农,望着卷叶枯黄的秧苗,喃喃地发出了“宁要城里的草,不要田里的苗”的愤愤不平和长长的哀叹……
行程途中,每当听到当地旗里的领导介绍本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往往是离不开诸如“南煤北油,东金西银”的矿产资源优势的。为了尽快摆脱“轻工业——擀毛毡,重工业——钉马掌”的落后局面,“工业富县”更是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是,我心中平添了几分自我难解的喜忧纠结和挥之不去的无名惆怅。
资源是发展之本。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科技,谁就占领了发展的制高点;而谁占有资源,谁就把握住了发展的主动权。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你的科技水平再高,若两手空空,巧妇是难为无米之炊的。放眼当前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凡有大国背后插手的硝烟弥漫的局部战争,几乎都与大国间争夺陆路及海上资源有关。为了更多地占有资源,一些大国已经开始把目光盯上了太空中的其他星球。欣闻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的地下,埋藏有煤炭、石油、黄金、白银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喜由心生——这不仅是草原走向繁荣之福,更是全民族可持续发展之幸!
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小小寰球带来的环境破坏,已接近地球和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矿藏采空区的塌陷,尾矿废渣的无序堆弃,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平原河道断流,阡陌间塘泊干枯,废水废气的污染,刺耳噪音的烦扰……假如明天茫茫草原到处立井架,处处机器轰鸣,蓝天上烟雾缭绕,半个世纪或百年后矿源枯竭,宁静的大草原将会在哪里?
古老的蒙古族历来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于世。在动车日行万里,神九傲然飞天,都市人尽享现代文明的今天,为了大都市的绿水蓝天,难道我们的蒙古族兄弟,就应该永远苦守这片祖辈赖以生存的草原,世世代代在马背上迎风冒雪挥鞭放牧吗?马蹄能刨出乌金的地方,为了保护已被人类破坏殆尽的生态,却让这方人捧着金钵去化缘,这公平吗?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地党委政府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明确地提出了“环保与开发并重,美丽与发展双赢”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凡是进入草原的企业,具有准入否决权的第一关是:首先要确定环境保护的明确目标,并有切实可行的防止破坏环境和有效治理污染的配套措施。
放眼望去,草原深处的一座座风电塔高耸入云。散落在碧海上白莲似的蒙古包前,小型的太阳能及风力发电机,为草原上的人们提供着绿色能源。蒙古包内的小型冰箱内,鲜肉如晶,冷饮如冰。电视机的荧屏上,正转播着神九飞天的清晰画面……
也许,也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