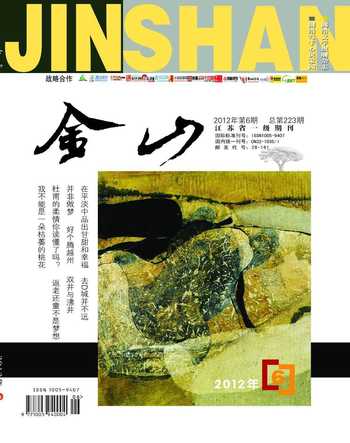我不能是一朵枯萎的桃花
兴隆枫叶
坐在四月的肩头,我成了一朵桃花,且是不折不扣地枯萎了。
五个月前,我还是闹在枝头的一朵红梅,山洼里那个爱美的姑娘,还把我扶上她的秀发。好一阵子,我得意得像一朵火红的山茶,恣情在水墨的江南。
一张纸,飘落在书桌的一角,好比一朵闲云飘荡在天际、一只野鹤漫步在水乡、一颗露珠摇曳在青荷。我端坐着,像极了一尊泥塑,任由时光从一月的飞红到二月的春鹃,从三月的海棠到四月的丁香,流得山花烂漫。我害怕拿起笔,零乱地涂下一些败草枯叶的字,糟蹋了百花的情分不说,还会让夏蝉悲鸣到秋,惊落一世的沉疴。我瘦了,瘦得比带鱼还难看,水边钓叟匆匆过,不忍回头耗精神。
我不能是一朵枯萎的桃花,我需要一把火,像费翔那把冬天里的火,熊熊火焰温暖我心窝。我不愿自己永远是一朵落花,清风懒得光顾,鸟雀懒得亲近。五个月来,我什么也写不出,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暮春零落,又被天风碾作尘,流浪在阳光的缝隙里。
我骨子里是厌倦这种漂泊的,像无根的蓬,找不到自己飞的方向。突然闯进头脑的,不是没有了头的就是没有了尾的,全都是硬生生拦腰斩断了的。你若有本事,可以半空里摘下一颗星来,紧握在手心。你能吗?
我没有这样的能耐,每天都万分地努力着,想码一行过得眼的字。有时,一个美妙的句子,像艳艳的桃花开在无人的山坡,满怀欣喜地追寻过去,那花又飞也似的闪在天际。有时似乎搭着一个梯子,靠了墙去摘云里的那朵花,可那是怎样的梯,又是怎样的墙,一切虚在我的想象里。
连续五个月,我就这样慵懒着,眼睁睁地看着美丽的阳光,吃饭的时候从碗里过去,洗手的时候从盆里过去,斜躺着的时候又从我身上伶伶俐俐地过去。咦,我还清醒着!分明觉着,这样子的话在哪里见过,一张口就顺溜而来。旋即,我又糊涂地可以了,什么子曰诗云什么魏晋汉唐,全是春困里的一阵哈欠。除了惬意地吼一声“爽”,一切的一切都是过眼的烟云。
有一次,我打算写一篇关于兄弟俩争夺土地的事。一忽儿在这张纸上涂一句,一忽儿在那张纸上抹半句,折腾了一个早上,还是那两个字最晃眼:《兄弟》。这个题目,是我花了N个晚上才捣鼓出来的。我坐在庭院里,在石桌上铺了张牛皮纸,拿了笔东涂涂西抹抹,不时地还敲敲笔杆,好让蹲在墙角唠嗑的人知道我还有写东西的能耐。有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老人,也是我最敬重的一个学者,看来是被我的奇特动作吸引了,慢慢地起身朝我这边来。我想象着,他会别一朵最美的桃花在我的头上,那我就有了可以炫耀子孙的资本了。老人走过我的身边,随便地抽了其中的一张,粗粗地扫了一眼,就一个劲地冲着我笑,比弥勒佛还弥勒佛。老人转身回去,迎着几个很是渴望的眼,“不咋地!”没有留给我动听的话语,却留给我一个心痛的背影。
我坐在那儿,守着我的作品,就像一尊佛守着自己的莲台。其实我清楚得很,自己已被踢出这个社会好久了。老人的话,又重新被我的耳朵拾起,一遍又一遍地碾压着我的心。我奋力地撕扯着,终于撕开了一个窟窿,吐出了压在心底的一句话:“我不能是一朵枯萎的桃花!”
我需要一把火,像费翔那把冬天里的火,熊熊火焰能温暖我冰冻的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