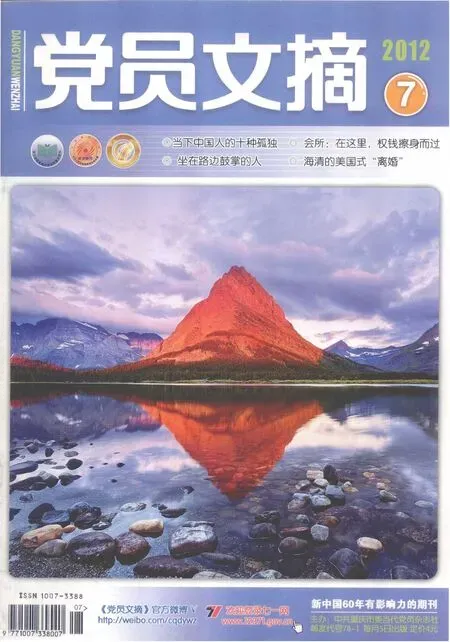“温州模式”蜕变
罗屿
“温州模式”已远远超越经济学、社会学最初对它的解释,它在发展中迷茫,在艰难中行进。这一次金融改革,能否助推“温州模式”完成新的蜕变?
今年4月13日,在央视主办的“探路温州金融改革”论坛上,出席人数最多的并非官员、学者,而是温州当地的草根中小企业家们。他们很多人甚至是站着听完了整场论坛。
惊喜,疑虑,乐观,悲观——面对3月28日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消息,企业主们的内心五味杂陈。
李建江是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的负责人,他坦言,在去年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买原料,他借了300万元高利贷,利息三分。有着同样遭遇的是刘顺峰,去年他的企业建设新厂区,他借了近亿元的民间资金,平均利息三分,“如果银行能解决,我要省掉3000多万资金”。
像李建江、刘顺峰这样热切关注此次金融改革的温州企业家还有很多。金改,关乎他们的命脉。
2011年9月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企业主“跑路”、跳楼自杀现象,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缓解温州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举措,但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
更让温州中小企业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开始出现罕见的“订单荒”。据温州海关数据统计,2012年2月温州外贸出口5.14亿美元,同比减少30.87%,环比减少更高达72.05%。
所有这些,都在为顶层设计传递一个信号:温州金改,迫在眉睫。
十年之后的重建
此次温州金改的重点是:如何解决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如何打通约8000亿元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路径。
“这是在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后未曾宣布取消——十年之后的重建。”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如是说。
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不仅提到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表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
然而,那一次的改革,却在是与非的种种争论中,无疾而终。
直至2005年,温州市银监分局和温州市体改委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还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温州十年前对改革的推进之所以顾虑重重,或许与民间金融曾经出现的疯狂与混乱有关。
温州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建立了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一方面,钱庄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可以在本区内从事金融事务,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得不到上级银行部门的认可,在法律上处于非法的状态,最终在坚持了五年之后自行关闭。
1986年,杨嘉兴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纽约时报》曾对此评价:“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紧随方培林、杨嘉兴之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在温州诞生。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却在温州爆发了“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就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元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老银行家曹尔阶回忆当年的事件,“由于‘抬会资金大部分脱离实体经济,无从产生利润,前边的‘抬会所获的高息,吃掉了后来者的本金,最后因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抬会终于倒会。”
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市信用社进行了清理整顿。
曹尔阶在回顾当年的大整顿时表示,“抬会”于民于国于社会都不利,金融监管应对其全面否定,进行打击,“但不应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出去,因取缔‘抬会而连同‘呈会、‘标会也一并取缔”。
如今,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建,映衬的正是温州在改革路上因恐惧风险而踌躇不前的十年光阴。
曾经的辉煌
恐惧风险,并非温州人的性情。不然,温州也不会成为中国改革的旗帜,更不会有“温州模式”的产生。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消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还配发了《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温州模式”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对于“温州模式”的昨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总结说:温州农民最早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大步闯向市场经济,包产到户,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一村一品,专业市场,供销大军,闹活了温州农村经济。温州最后形成了十万家庭工厂、十万供销大军、十大专业市场。费孝通将“温州模式”定位为“小商品、大市场”。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实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
但改革前行者,注定饱受争议。
股份合作制企业出现后,姓“社”、姓“资”的争议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松绑后的“温州模式”在20年间攻城克寨,把市场铺向了全世界。
政府的“有为”与“无为”
进入21世纪后,“温州模式”似乎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挑战。
倪云,温州乐清市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和他众多的亲族一样,他有着不大不小的一家厂子,有十几个工人。原料价格上涨,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他从信用社贷了20多万元,千分之八的月息算下来,自己几无利润空间。于是,倪云有了关掉厂子的想法。
当类似倪云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时,更多人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温州模式”。
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茶洪旺说起“温州模式”,表示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州区域文化有其突出特点,诸如温州人创业精神强,人人都想当老板,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般来说,温州老板大多都喜欢单打独斗,独立拼搏,但是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又会致使一些大集团、大企业难以形成,最终影响了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品牌企业成长。”
在2003年左右,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也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温州模式”终将变迁。在他看来,温州一直是以人格化有形市场为主,靠的是人缘、地缘、血缘、同学缘,人格化交易机制的强度太大。温州如果走不出人格化交易,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有很大难度。
史晋川还注意到,温州的人格化交易在向政府中渗透。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编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
如果将目光聚集于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估计温州各级政府官员基本上全面参与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活动。当地有人估计是100%参与,有人则估计为八成或九成不等的参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在几次深入温州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一批拥有公权力的人进入民间金融,势必给监管造成影响。茶洪旺认为,地方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寻租行为,是要靠法律机制约束解决的。“金融监管、法制建设,这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在茶洪旺看来,在推进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过程中,如何制订科学的实施方案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
众人期待,曾在发展中迷茫,在艰难中行进的“温州模式”,可否借助这一次金融改革完成新一次蜕变?
链接:温州金改数字
12条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12项重点任务,被称为“12条”。
25条 4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送审稿)》出台,共25条。浙江将以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民间财富管理中心”为重点,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创新。
30家 4月25日,浙江省宣布“十二五”期间将力推浙商银行、浙商证券、永安期货三家浙江企业上市。今后四年,拟每年新增30家左右上市公司。
100家 4月25日,温州宣布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
(摘自《小康》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