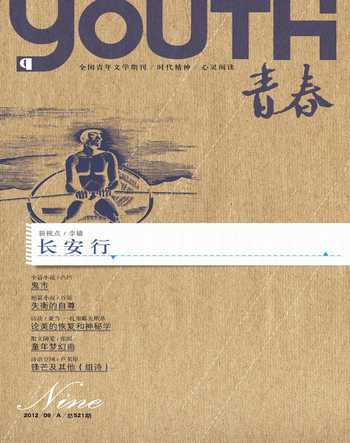童年梦幻曲
张闳
1968年的中国男童
男孩坐在火桶上,呆呆地望着祖母满是皱纹的脸。祖母手捧一只瓦质手炉,坐在对面。祖母的目光平静如水,凝视着遥远的某个地方,心中在盘算着什么。似乎是祖母的沉默感染了火桶上的男孩,男孩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沉思默想的祖母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喃喃自语,却没有声音。偶尔,祖孙俩也有简单的对话——
“奶奶,你在说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嘴唇为什么在动?”
“傻瓜。”
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火桶里散发出木屑和树叶焚烧的气息。四周寂静。只有祖母长长的指甲下意识地刮着手炉的边缘,发出吱吱的声音。
穿越笼罩着祖孙俩的巨大沉默,记忆的迷幻火车驶向动荡不安的1968年。历史在这一站发出伟大的嚣叫,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惊悚不已——巴黎:造反青年与警察进行街垒战;布拉格:捷克人为自己国家的政治春天而欢呼;纽约:马丁·路德·金牧师正带领着他的黑人兄弟向华盛顿“和平大进军”;越南:轰炸机和高射炮的大对决难解难分……
但对于一位6岁的中国男孩来说,这一切并不存在。他并没有听到历史沉重而又冗长的诉说,只有一些声音的碎片残存在他懵懂初开的记忆当中。
乡下祖母跟毛主席同岁,后来也活到跟毛主席同样的寿命。这是她的幸运。但她从衣着到观念,依然停留在有皇上的时代。她不知道在外面当医生的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走资派”是一個什么样的罪名。她只知道儿子有难了。当她的儿子将孙子送了她这里来的时候,她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在她看来,人生在世无论福乐还是灾难,都是上天的安排。服从命运,这就是她的人生律令。就这样,祖母成天忙碌着,挪动着她的小脚,喂鸡、喂猪、喂男孩。
村头百年的老樟树像祖母一样慈祥。它见证了贫困,见证了饥饿和寒冷。在冬天,它向地上的人民洒下了厚厚一层金黄的树叶。这些散发着芳香气息的树叶易于燃烧,是上好的燃料。但无所不在的公家,拥有樟树的所有权,包括落在地上的树叶。在那个“大公无私”的年代,村民必须忍受着冬天的寒冷,却无缘领承领这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值得庆幸的是,小孩子以一片一片地捡的方式收拾树叶,则不被认为是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样,来源丰富的樟树叶就成了男孩和祖母过冬的重要能源。它就是上天赐予的温暖的源泉。
“奶奶,我去穿树叶啦。”男孩说。
男孩踩在厚厚的树叶上,树叶立即愉快地唱起歌来。这些树叶认识男孩,认识村里的每一个人。整个夏天,男孩和他的伙伴们常常爬到树上玩耍。樟树总是以它粗大有力的枝条托举着、护卫着这些孩子们,以它黯绿、浓密的叶子为孩子们遮挡酷暑骄阳。
但树叶似乎并不太会唱歌,歌声支离破碎,不成调,只是一种窸窸簌簌的声音。男孩决定亲自唱一首刚学会的歌,但他也只唱了开头几句,便又忘掉了。只好听任树叶瞎唱一气。那些个儿大的叶子,唱得最欢,它们吸引了男孩的注意力。男孩拾起一片,闻一闻,樟脑的香气使他感到安心。男孩将树叶穿到事先准备好的针线上,再拾起一片,再闻一闻,还穿上。男孩很快就穿了长长的一串,一张张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又长又阔的叶子。他将树叶串按在屁股上,一路窸窸簌簌地拖回家去,远远看上去好像长了一条又大又长的尾巴。他喜欢这条尾巴。祖母也喜欢。
“真能干。”祖母说,“但是不用再去了。今天已经够烧的了。”
日复一日,时间在祖母的沉默和树叶的歌唱中缓缓流逝。那时节,巴黎红卫兵早已撤出了他们的街垒,“布拉格之春”也已落花流水,马丁·路德·金博士则在刺客的枪声中倒下,而中国红卫兵将被遣送到乡下去种地。而那些树叶也像男孩一样,对此一无所知。许多年之后,在他穿越幽深的时间隧道,回溯那个伟大的时代的时候,耳边却时时响起樟树叶瑟瑟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1968年,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这位中国男孩也将结束他混沌的童年。
一天,男孩背起兄长用过的书包,走向村头一幢破败的土屋。在那里,将开始他一生漫长的启蒙。
2001年的伊拉克女童
几年前的一天,我一边吃着午饭,一边看电视节目《新闻30分》。电视里正在报道伊拉克的情况,是中国记者在介绍饱受军事和经济双重制裁之苦的伊拉克目前的处境。我并非对此有特别的兴趣,也不怎么相信媒体的宣传,只不过习惯于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即使是看到一些伊拉克境内满目疮痍的镜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凭心而论,我对那个遥远的国度没有多少了解,对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我当然不会不恨他们,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爱他们。对于他们跟西方国家的恩恩怨怨,也不甚了然。看见街头上的伊拉克人,我甚至还这样想:他们看上去好像还不算太糟糕,无论是脸色还是穿着,比我小时候看见的中国农民处境似乎还要好一些。
我就这样边吃边看。我看见一位中国记者正在伊拉克的一所小学采访。记者开始询问孩子们的状况,然后检查他们的书包。一位小男孩打开自己的书包,可以看出里面比较空洞,只有寥寥几本破破烂烂的课本和练习簿,还有一支铅笔头。记者从书包的底部掏出这只铅笔头,向摄影镜头展示……这些都没什么。当初我们上学的时候,书包里的家当也不过尔尔。况且,根据我作为中国人的经验,这些镜头是特意安排的也未可知。所以,我依然是漠然地边吃边看。
这时,男孩身后的一位小女孩忽然哭起来。这一意外事件来得很突然,显然让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记者愣了一愣,然后转向小女孩,问她为什么要哭。小女孩一边啜泣,一边哽咽地回答记者的问话。翻译解释说,这位女孩哭,是因为自己连像同伴这样的一支铅笔头都没有。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魅力,这一新闻片断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突然哭泣的小女孩,带给我一种无可言状的强烈的内心震撼。我甚至至今还能准确地记得这则新闻播放的日期——1999年10月20日。
接下来记者开始发表议论,努力向我们证明对伊拉克的种种国际制裁的不合理性。但我所感到的内心震撼依然与伊拉克无关。我对国家之间的政治争端没有兴趣。我关心的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具体的个人的痛苦或快乐。而我关心的是一个具体的孩子因为贫困而遭受的内心委屈。是什么样的忧伤和委屈,是这位女孩突然会在一群陌生的外国人面前失声哭泣?
这个没有铅笔的小女孩,我相信她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姐妹。一个关于贫困、关于孤苦无助的小生命的永恒象征。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我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脆弱和无助。
对于一位成人来说,一只短短的铅笔头显然是微不足道。这么一点小事,似乎并不值得如此伤心,因为更沉重的生存压力还在后头。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更是渺小到了极点。国家政治往往只关心国家的利益和尊严。但对于这位小学生而言,却是她生活中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甚至就是她作为学生的全部。她的全部的快乐和忧愁、愉悦和焦虑,乃至她的个人价值和尊严,都维系于此。毫无疑问,在这个小女孩的世界里,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不仅是日常生活上的艰辛。她对于一支铅笔头的渴望,也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欲求无关。毋宁说,这是人对于自身权利和尊严的最起码的诉求。然而,贫困的“毒素”是如此之深地侵入到这个孩子的心灵深处,对她的情感和尊严构成伤害,成为她的噩梦。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也无法补偿的。
令我不解的是,我始終不能明白诸如国家政治的对抗、种族仇恨、领土纷争、文明冲突……这些严重的国家政治行为,究竟为的是怎样一个价值目标。我只能假想,如果政治家们能够抛弃那些冠冕堂皇的、空洞的政治理念,抛弃自身和集团的那些狭隘的蝇头小利,关心一下各自国度中的每一位公民具体的生存处境和情感,关心一下那些因为贫困或者其他原因而悲伤的每一位孩子,这个世界的面貌也许就大不一样。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这些一厢情愿的假想,自然无力付诸实践。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显然是在某个环节出了毛病。如果那些严重的国家政治行为,尚不足于消弭一位小女孩的眼泪的话,我不相信它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不相信它能够给全人类带来福祉和安宁。它很可能就是一些错误的、本末倒置的行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在这位小女孩的眼泪目前显得轻如鸿毛。
我相信,这样的孤苦无助的女孩、这样的突然哭泣的女孩,显然并不只是战火中的伊拉克的特产。她可以是黑人、黄种人,也可以是白人。她可以居住在阿富汗、索马里、阿根廷,甚至是美国,当然,也可能就在中国,在我们身边。
时间过去了。今天,恐怕没有人还记得那位小女孩,无论是记者还是观众。但贫困依然存在,孤苦无助的小女孩的眼泪恐怕还没有擦干。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事实,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这位无助的孩子。也不知道那位小女孩现在怎么样了。但愿她已经有了一支铅笔,哪怕只是一段短短的铅笔头。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