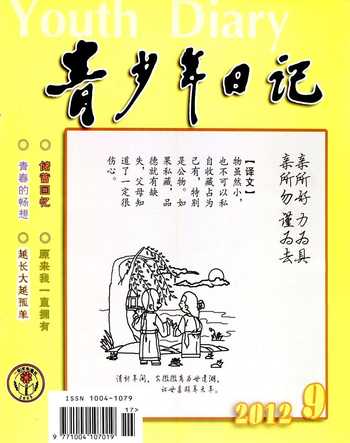父亲的逻辑
李建文
8月11日晴
在家中的床底下有一个很大的袋子,袋子是很厚实的那种,里面全都是父亲的宝贝。用父亲的逻辑来看,那里面就是他的命,也是我和弟弟的命。父亲是工地的工人,在那个袋子里面全是砌砖、抹灰的工具,其中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我们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用那些工具换来的。
几年前,父亲为了可以更方便地在城市打工,便领着我们来到城里。父亲租了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我们一家四口人便在城市里“扎根”了。
以前都是父亲在外打工,我和弟弟在外上学,母亲一个人在家收拾庄稼,我从来也不知道父亲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初来城里的日子,我看到了父亲的生活。每天早上五点多父亲便会起床,穿上满是石灰沫的衣服与一双永远也不会干爽的胶鞋。母亲为父亲买了好几双胶鞋,希望父亲可以轮着穿,可父亲总是有他的逻辑,他说在工地工作半天鞋子就全湿了。没必要天天换鞋子,也换不过来,没必要浪费那么多钱。有时候父亲还会穿上雨靴,父亲说虽然很热,但是也防水。父亲的衣服永远都是五十块钱一套的工服,无论母亲怎么清洗上面都会留着像火碱烧过一样的痕迹,看到父亲经常脱皮的脊背我就知道那些痕迹是石灰和水泥混合在一起的产物。穿上这身衣服,再背起放在床底下的袋子,父亲骑上自行车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
为了一天可以多干一些活,父亲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母亲说一袋馒头、两包榨菜、一小瓶白酒就是父亲的午饭。母亲也很多次劝父亲去买一些菜吃,父亲却又有他的逻辑,他说已经习惯了改不了了,工地的工友们都这么吃。我实在是不敢想象父亲在满是灰尘的工地上是怎么嚼下那些馒头的。
晚上,父亲总是比别的工人晚回家,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再多干一点儿活。父亲说晚上多干一点儿早上多干一点儿,时间长了挣的钱就比别的工人多了。我劝父亲说自己挣自己的钱和别人比什么啊?父亲总是说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别的工人挣钱也是为了养孩子,我要比他们挣得还多,我的孩子不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了吗?这又是父亲的逻辑!
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提前在门口备上两盆水,让父亲洗脸洗脚。每次父亲用完的水都是浑浑的,父亲说那水里全都是钙,是巨能钙。有时候父亲洗着脚就靠着门框睡着了。每到这时我都不忍心叫醒父亲吃晚饭。
父亲是16岁开始在外面打工的,现在已三十年了。父亲喝一点儿酒之后常对我说:“在工地我还可以干个六七年,等到那个时候你和你弟弟也该成家立业了,我也该享福了。”每每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会莫名地心痛。我实在是不敢想象那个时候父亲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父亲的左胳膊现在是弯的,是当初年纪小在工地打工伤的。母亲每每主张去医院给父亲检查,父亲总是说:“没事,又不是断了。”每天晚上父亲的胳膊都会痛,我半夜醒来总能看到母亲在给父亲揉胳膊,第二天父亲又像个没事的人一样去工地了。
父亲没有什么想要建造世界上最美高楼的想法,他的世界很简单,那就是只要用力气工作能拿到钱就可以。还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因为有一年被包工头骗了,没领到工资,父亲硬是过年没回家,去了吉林割芦苇。后来听父亲说,拿不到钱没什么脸回来看我们,也就是那一年冻坏了他的脚,至今每年冬天父亲的脚都会被冻伤。父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并且逐年增多,我知道在那些白头发里镌刻着他对家庭的爱。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去过父亲的工地,也看不到父亲一天的具体生活,父亲也很少讲,我大部分都是听母亲说的。假期的时候想去工地和父亲打工挣一点儿钱,可总是被父亲用“你的力气是用来读书的”的理由给强硬拒绝。
这就是父亲的逻辑!父亲凭他这固执而又简单的逻辑供养着我和弟弟,让我和弟弟从农村渎到城里,从小学读到大学。父亲,什么时候我能让您那宝贝袋子永远躺在床底呢?什么时候我能让您穿上一身干爽的衣服悠闲地在公园散步呢?什么时候我能让您每餐都能吃上热乎乎的炒菜呢?
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09级本科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