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镖
文/金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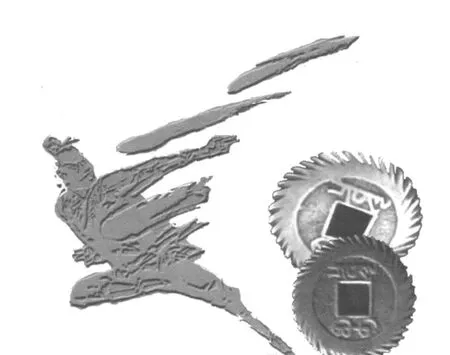
一、金钱镖之构造
金钱镖一物,为暗器中之最便利者,盖即用大青钱飞掷伤人也。亦可分为两种。
一为有刃之金钱镖,即将青钱之四围,用锉锉薄,更在细石上磨之,使锋利成刃。此物除用为暗器外,江湖剪绺者,亦恒用以为割划衣袋之具,而称之曰外口。故携带此种有刃之金钱镖,常易为公门中人所注意。且此物犹须仗边缘之锋而制人,其技固犹未臻精纯。
一为无刃之金钱镖,即用平常之青钱,信手劈出而制敌,固无借乎边缘之锋刃而伤人,完全用腕力而使钱如镖,则非有过人之力,与夫相当之功夫,不克臻此境也。即在今日,有孔之钱,已不多见,亦可以铜元代之,即用银元或小银元以代有孔之青钱,亦俱无不可,故极为便利。盖人之出也,绝无不带银元或铜元者,万一有惊,即可随手取出,用以击敌,随取随发,络续不绝。且带铜元或银币,实为普通之事,人亦绝不以此等物而指为暗器,故练得此种功夫,非但便利,且使人防不胜防也。
二、金钱镖之练法
金钱镖一物,若以手法言,只有阳手一种;以发劲言,则劈摔兼用,纯着力于腕,而钱之出时,完全平面飞去,如飞铙之横破。有时斜侧飞去,则如飞铙之斜破。唯直破一法,则非金钱镖所能矣。其伤人之处,虽云腕力,然亦半在旋转之功也。
所有各法,大略与飞铙相似,其不同之点,铙大而钱小,铙有把手而钱无。飞铙持其一边而摔掷之,发钱则以钱平贴掌之前部,约居各指节之中间,而按以拇指,掖腕蓄势,拨开拇指而使钱从小指之侧面横劈而出,钱出必平直而旋转不息,始能有效;否则不能旋转,而纯用直劲,虽能中的,其效亦至微也。其实此金钱镖较之飞铙为尤难。盖飞铙所占之面积较大,而分量亦甚重,持而发之,犹可仗其锋利之刃,与本身重量以制人,虽腕略弱之人,亦得有所借劲。此金钱镖即用银元代之,其重犹不及一两,若铜元青钱者,且不及一二钱,欲空手发此极轻飘之物,而之于远处伤人,其难可知;且又无刃可以借劲,实非飞铙所可同日而语也。故练习金钱镖者,入手之先,必须专练腕力,待腕力充足后,更进而练习飞掷之法,则始可有成。
练腕力之法,则可用沙包林,而以侧掌斫削劈击之,大约一年半即可应用。练金钱镖之靶,亦宜用土垣,由近而远,靶亦须逐渐收小。盖金钱镖之伤人,亦纯靠头面等处,若有较厚之遮蔽,则绝难透入,故所取之的较小。练时亦须注意于小靶,而不能如飞铙之专练中靶也。腕力充足以后,练习打靶,即较容易,若亦加上一年半苦功,其技固极可观矣。前后统计亦仅三年。
此种暗器,以其便利之故,江湖上练者极多,即至现在各种暗器衰败之时,犹有人习其技。飞钱击人之事,犹时有所闻也。
三、金钱镖之源流
凡一物之发明,有意研求者固多,然间亦有于无意触动灵机得之于偶然者,各种暗器中亦时有之,如铁蟾蜍等实其类也。而此金钱镖一物,乃亦得之偶然者。
山西有老武师景庆云者,擅拳棒,精内外功,生平所授徒,不下千人。景于夏日,恒垂钓河滨以为乐,且借以纳凉。一日,方坐柳荫下,适有群儿戏水滨,飞瓦削水,以远近分胜负。其力弱而不善飞者,瓦片入水即没,或仅能泛起跃一二尺。其善于此者,能泛起没入至数十次,而远于三四丈之外,且其在水面削过,嚓嚓有声,水花由近而远,由大渐小,竟如塔影横卧水中,甚有奇趣。
此事亦寻常小儿游戏之法,本无人注意也,景无意中见之,忽触动灵机,自思削水之瓦片,愈薄愈佳,稍厚即不能及远,其间固有至理焉,乃循其理而求之,竟发明金钱镖之法,试习之,果具奇效。
景固功力绝人者,稍事试演,即已大成,乃以法授诸徒,盛行一时。在乾嘉之世,有用金钱镖者,其人可不问而知为景氏之徒也。
景有戚王士成,听鼓历下者有年,某岁铨署峄县,闻其地为盗贼渊薮,颇不易治,计非有一武勇之士同往不可,乃寓书于景。景以年迈辞,命其徒沈继祖往,伪为幕客。盖沈貌固温文尔雅,状如书生,人或见之,亦不疑为武卫,而其技则在同侪中称独,绝不亚于其师景庆云也。
既至,王优礼相待,置诸幕中,同事数人,惟病其不善治事,徒以为王之乡人,亦相与交好,固不知沈之来,非为幕友而为卫士也。居久之,幸无意外,王心稍安。而沈倨居衙置,颇不自聊,暇恒一人游郊野,见飞禽止鸟,辄投石击之,贯以索,每归累累盈串,命厨役煮以下酒。朋辈以是异之,而其形迹亦渐露于外。
一日,值假辰,约同侪携酒游郊外,就林薄间踞石而饮。饮正酣,忽有四人至,皆短衣狭袖作武士装,且携刀械,一望而知非善类也。睨沈问曰:“众位中谁为山西沈姓者?”沈知其意,盖沈于二月前曾获一积盗,以案积如山,乃弃市。四人者当系盗党之谋复仇者。沈笑应曰:“余即沈某,汝曹素不相识,询余何为?”一人对曰:“子即沈继祖无误乎,今日者余侪盖欲与子一较生死耳。”言既拔刀猱进。
众客大惊,不知所计。沈笑语从容,似无其事者,从袋中出一钱,遥掷之,中盗执刀之腕,深入寸许。盗受痛,不能固握,刀铮然坠。三盗继至。沈连连发钱,盗急趋避,凡七发而不中者止三钱。三盗无幸免,且皆折腕,不能复斗。
沈告之曰:“汝曹欲在余手中讨生活,尚少练三年功夫也。实告汝曹,余乃山西名师景庆云徒也,今小使受创,尚体仁慈之意,使汝曹知所改悔。若不悛改,以后复相遇者,无生望矣。”盗闻言,皆投拜于前曰:“俗眼不测高深,景家金钱镖信绝技,今而后知所改矣。”沈挥之去。
众客台惊定,争道其能,至是沈亦不复隐讳,具以前事相告,众乃知其为幕宾者,实伪饰以掩人耳目耳。后其地盗风稍戢,终王士成之任,而未有巨案发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