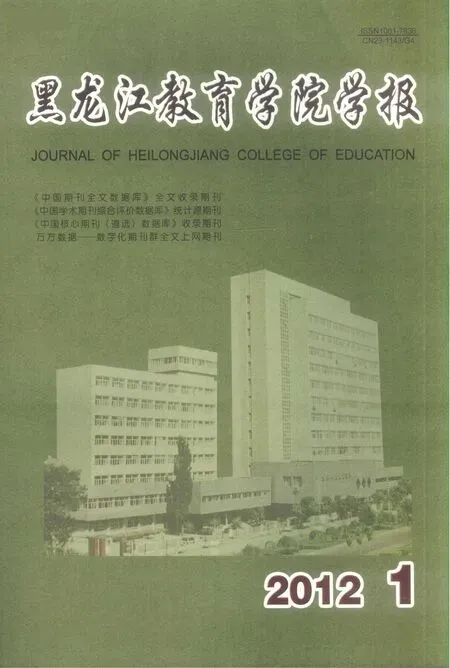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童话《小红帽》的演变
涂媛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上海200083)
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临精神文化领域的重大转折,以及整个哲学﹑文艺思潮急剧地政治化,“文体批评派”理论渐渐陷入了绝境,时代在呼唤着新美学。此时,康士坦茨学派青年理论家姚斯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他批判了过去种种文学研究中把文学与社会历史﹑对文学的美学思想与历史思考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姚斯认为,文学既有着自身独立的审美特质和形式的演变,又同时与“一般历史”,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休戚相关,并受制于“一般历史”的进程。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必须从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发展。无论是批评家、作者,还是文学史家,在他们对文学的反映关系变成再生产之前,也都是最早的读者。文学“事实”不仅包括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创作的特性和意图,还包括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与效果[1]54-59。在姚斯看来,文学是生产与接受的辩证过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2]339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
接受美学突出了读者的重要地位。姚斯认为:第一,文学史是效果与接受的历史,即“读者的文学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是为读者而创作的。第二,文学的社会功能应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加以探讨。文学作品首先会唤起读者由传统的流派﹑风格或形式而形成的期待视野,即在具体阅读中,读者对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之后,这种期待会随着读者的阅读一步步地被破坏[2]19-30。读者会把原先的视野与眼前作品所体现的新视野进行对比,原先的视野就会被“更动,修正,改变或甚至干脆重新制作”[3],新旧视野最终会达到一种“视野的交融”[2]347。阅读经验能帮助读者从一种生活实践的适应﹑偏见和困境中解脱出来,读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1]62,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
《小红帽》是许多成年人熟悉的一则童话,也是他们常常念给孩子们听的床边故事,小红帽是童年天真无邪的象征。然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数百年前,《小红帽》曾是成年人之间流传的色情故事。它经历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演变,故事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和寓意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变迁[4]3-5。从姚斯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则童话的演绎体现了不同时代对该题材的不同接受,反映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被打破,并建立新的期待视野的历史过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本文在此选择了《小红帽》法语版﹑格林兄弟德语版以及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时期的版本作为考察对象。
一、《小红帽》法语原始版——不为儿童而写的童话故事
根据民俗学者的研究,《小红帽》源自人们围在火堆旁传讲的民间故事。1697年法国艺术家,随笔作家,法国学士院成员佩罗(Charles Perrault)将这个带有色情内容的口传故事编写为童话,收入在《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一书中。17世纪法国的童话并非是为儿童所写,而是流传在成人之间﹑往往带有色情内容的一种故事体裁[4]10。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距离越小﹑越能满足流行趣味的作品越接近“通俗”艺术或娱乐艺术,因为这样的作品不能或很少能使读者产生“视野的变化”[2]31-32。而佩罗所写的《小红帽》并未迎合当时法国读者的流行趣味,而是去除了口传故事中的色情内容。故事中的小红帽因天真无邪,不知道与野狼交谈的危险,最终被野狼诱骗而丧失生命。
接受美学将伦理学领域内文学与读者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对道德反映的召唤”。文学“在伦理学领域里的社会功能,是根据接受美学在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上所采取的相同方式加以掌握的”[2]51。佩罗打破了读者对童话所熟知的审美形式,以小红帽的悲剧向读者提出了问题:“小红帽悲剧产生的根源或从中应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从17世纪开始,沙龙这种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谈论文学﹑艺术或政治的社会聚会在巴黎兴起,成为了当时文学界,艺术界和语言界神圣的殿堂,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沙龙促进了法国诗歌和小说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关于爱情﹑两性的论战。沙龙培养出的“女性主义者”们倡导爱情和婚姻自由,要求法律赋予女人权利,自行决定婚姻和生育问题。然而在17世纪的法国,中上层社会的妇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姑娘们到了14岁就要出嫁。她们的婚姻往往是“钱袋与钱袋的结合”,由父母出于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作出安排。女子的贞操是买卖婚姻中的筹码。根据门第的高低﹑嫁妆的多少,姑娘们要与门户相当或社会地位相当﹑但却从未见过面的男子成婚。不服从者将被送入修道院[5]。结婚后,生育小孩也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婚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国家带来国民,为教会带来孩子,为天堂带来居民”[6]。女性主义者们争取自身权利的要求显然与当时法国宫廷的道德观背道而驰。
身为法国皇室官僚的佩罗致力于维护“法国封建贵族的伦理秩序”[7],其创作的目的实则在于以《小红帽》来阐述和捍卫当时法国官方的道德观。他在童话后附上了一段题为《教训》的短评:“小女孩……永远不要信赖陌生朋友;……野狼可能用各种伪装,潜伏在你周围,它们可能变得英俊﹑和蔼,愉悦或迷人——当心!……最甜的舌头往往带有最锐利的牙齿!”[4]5在这里,文本向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妙龄少女们参加沙龙聚会时一定要警惕被“野狼”勾引的危险,保持贞洁。在佩罗笔下,《小红帽》成为了一则寓有道德训诫的故事。
二、《小红帽》德语版——宣扬家庭规范的家庭寓言
1812年格林兄弟编撰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问世,里面可找到不少佩罗童话集中的故事,其中包括《小红帽》。两版相比,内容上较大的不同在于:第一,德语版中添加了小红帽出发去外婆家之前,妈妈对她的一番告诫“不要走小路”。第二,小红帽被野狼吃掉后,猎人从野狼的肚腹中救出小红帽和外婆,给了她们第二次生机。第三,删除了佩罗版故事后附加的明显带有教化意味的“教训”。
童话是德国浪漫文学中艺术上最成熟的形式。德国浪漫诗人大量收集出版了民间童话或从事童话创作,即“艺术童话”的创作。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属于前者。民间童话的收集和艺术童话的创作在审美旨趣和出发点上截然不同。对民间童话的偏爱体现了浪漫派作家“对民族文学的重视和对民族历史的科学研究兴趣”[8]。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这个概念已深入公众的意识。18世纪末期,德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德国人也开始思考,是该效仿其他国家通过政治途径,还是另寻一条特殊的道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诺瓦利斯认为,当欧洲其他国家在忙于战事﹑空想和党派思想时,德国人在努力提升自身修养,以享受一种更高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的超前使德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具有优势。与此同时,席勒也提出了这种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思想。在他未完成的诗稿《德意志的伟大》中,席勒提到: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在德意志德国走向衰亡时,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仍被保存了下来,它存在于德国文化中[9]。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驱动下,浪漫派作家开始倾力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化遗产,研究民间文学,宣扬民族文化。
佩罗的讽刺寓言“字里行间紧系着17世纪法国宫廷﹑社会发生的事及上流社会的性爱政治”[4]10,将接受者定位于上流社会的贵族,意在通过小红帽的故事宣扬和维护法国宫廷道德观。而格林兄弟则致力编辑适合儿童和家长阅读的故事书,目的在于“让民俗故事中的诗意散发效果给人愉悦,同时教忠教孝”[4]33。
格林兄弟之所以选择儿童和家长作为接受者,与当时欧洲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姚斯所讲,文学的演变与“一般历史”的进程休戚相关。历史学家亚力士(Philippe Aries)指出,在19世纪工业革命大幅冲击欧洲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儿童期和青春期这个概念。贵族的“儿童”身穿燕尾服,头戴假发,俨然像个小大人。而中下阶层的男性“儿童”尚未成年便进入职场,女性很早成婚。工业革命使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都市中产阶级和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家庭。“儿童”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这才发现,儿童有其特殊的特质和需求。对儿童的教育、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教化逐渐为人所重视[4]29-30。
除了最初的愉悦性功能,此时的童话更多地发挥了对儿童情感的教育功能。弱小人物经历艰难困苦而获得幸福的故事成为了人们不懈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力量;人们富有正义感,惩强扶弱,最终善恶有报。虚实相生的童话世界为儿童提供了诸如勇敢﹑诚实﹑勤奋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10]。
格林兄弟版《小红帽》以儿童和家长为接受者进行伦理道德教化,是则宣扬家庭规范的家庭寓言。与佩罗版相比,故事中增加了“妈妈和猎人”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小红帽不听妈妈的告诫而落入危险,在猎人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其教育意义非常明显: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
三、60年代女权运动时期的《小红帽》——英勇,足智多谋的新女性形象
接受理论通过重新调整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文学及其历史。作品的意义被视作是历史的产物,它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作品实际上意指了不同读者类型,读者不同的主体规定也导致了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意义的实现既非全在于文本,亦非全在于读者的主观性,而在于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林树明认为,此观点使女性主义批评与接受美学处于同一层次,是两者复合叠加之处。由于父权文化一直将妇女排斥在外,“在一代一代接受之链上被补充与丰富的”审美感受(姚斯语)也是男性的,因而女性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便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那些带有偏见的作品[11]49-51。
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与第一次运动争取妇女选择权和教育权不同,第二次女权运动致力于消除两性之间的差别。男性中心主义把“与个人认同有关的属性﹑自我感觉﹑衣着形式及态度与兴趣等两性品质”之间的差异视为是“自然的”,从生物学意义上肯定了女性的被压迫地位[11]119。而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差异虽与两性生理有关,但更是历史与文化造成的结果。两性差别造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对性别气质的传统看法已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女人应克服自己的柔顺﹑被动﹑服从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12]。
女性阅读和创作成为了对“现存法则的挑战”和“抗拒”[11]51。在姚斯看来,作品持续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有“读者再次欣赏过去的作品,或有些作者力图模仿﹑超越或反对这部作品”[2]27。女权主义者将反对的矛头首先指向了童话,因为在他们看来,貌似天真稚拙的童话也参与了性别价值取向的教化[11]63。作为“小女孩人生中的第一本训练手册”,童话实际上一直在教导女孩要顺从,面对危险和虐待要“甘心受害”,因为童话故事中女主角的幸福结局往往是通过“逆来顺受”而获得的[4]113。小红帽面对野狼的侵袭却毫不进行反抗的顺服形象显然为女权主义者所不能接受。因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多颠覆传统版本的《小红帽》,如1972年由称为“默西塞郡女性解放组织”的四个女人共同撰写的《小红帽》;1985年夏普所著的《不那么像小红帽》;1983年罗纳德·达尔的《小红帽与野狼》;蕾克的《黛丽雅的小红帽》等等。在这些版本中,格林童话“小红帽;妈妈;野狼;外婆;猎人”的模式又重新还原为法语原始版的“小红帽;野狼;外婆”模式——没有了妈妈的教诲,也没有猎人的搭救。这些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将小红帽塑造成了一个英勇的“自救者”。在有的版本中,连外婆也不再是传统故事情节中年老体弱﹑卧病在床的形象,而被描绘成了一名身强力壮的老妇人。祖孙俩成为了英勇﹑足智多谋﹑有着男子气概的新女性。她们时而幽默,时而坚强;能识破野狼的伪装;面对野狼的侵袭,她们丝毫不胆怯,最终联袂将其制服[4]129-130。
姚斯认为,文学具有与其他艺术和社会力量同心协力“解放人类与自然﹑宗教和社会束缚”的功能[2]351。通过文学阅读,人们能够打破原有的生活实践经验的视野,对世界产生新的感觉和看法。女权运动时期的《小红帽》赋予了女性自信﹑勇敢的新形象。它能使读者产生新鲜感,改变对女性的传统看法。
四、结束语
三百年来,童话《小红帽》不断地被演绎。正如姚斯所指出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2]26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非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是永恒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作者意图与接受者的改变,《小红帽》的价值和意义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可变曲线,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1]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张廷琛.接受理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6.
[4]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M].杨淑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陈振尧.法国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99.
[6]弗朗索瓦·布吕士.太阳王和他的时代[M].麻艳萍,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109.
[7]李玉平.伦理话语与社会变迁——论《小红帽》童话故事的改写[J].外国文学研究,2010,(3):46.
[8]张玉书,等.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2.
[9]Rüdiger Safranski.Romantik[M].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2007:176 -177.
[10]刘文杰.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民间童话论略[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6(增刊):26.
[11]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2]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