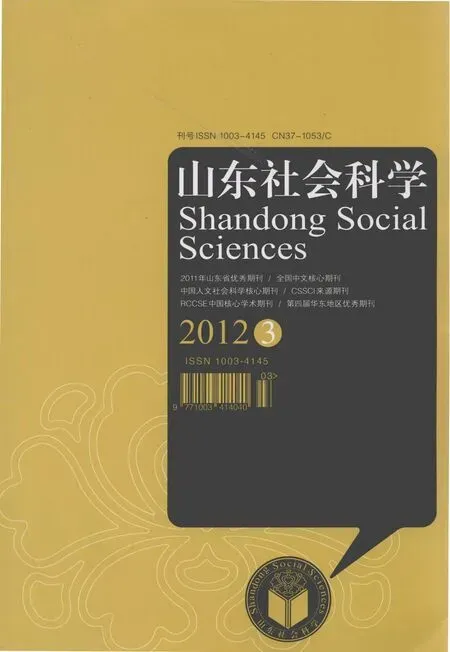文明冲突理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
张文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4)
文明冲突理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
张文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4)
塞缪尔·亨廷顿说自己是兼具爱国者和学者两种身份而从事研究的。由于爱国者本身是一个充满复杂含义的词汇,容易对学者的公正性与科学性造成侵蚀,加之亨廷顿呼吁西方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一步强化了其立场的偏颇性,这恐怕是人们对他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的回应,触及到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种种缺陷和弱点。如果说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拉美裔移民状况的分析体现了一名学者的敏锐,那么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拉美裔移民威胁论”则充分表明了他作为一名爱国者的偏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两部著作,都是通过树立敌人方式,以加强美国的身份认同为目的,实质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联合国呼吁抵制这种理论,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亨廷顿;文明冲突;身份认同危机
近二十年来,似乎很少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能如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这样的影响力。他提出了一种引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无数学者为之纠结不已的理论——文明冲突理论。从美洲大陆到欧洲腹地,从伊斯兰世界到东方世界,从尼罗河流域到恒河流域,数不清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或大力驳斥或为之喝彩。我们不仅要问,他是谁?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又如何能穿透文明冲突理论和种种讨论引起的泡沫表象,对他——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理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亨廷顿是谁?
他是谁,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1950~195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1959~1962年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回到哈佛大学,直至2008年去世,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1957)、《共同防御》(The Common Defense: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196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s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1991)、《文明的冲突与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2004)。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标准学者的经历。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其职务。亨廷顿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1957年出版的《士兵与国家》中,亨廷顿提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这本书一出版就引来评论不断。一个批评家指责这本书有军国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将亨廷顿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
20世纪60年代后期,亨廷顿撰写过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地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在这些过激的学生看来,他是支持战争的罪犯。
学生们攻击他,教授们也不例外。这其中就有著名的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1969年出版的《美国强权和新官僚》一书中,乔姆斯基认为,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政治学研究是罪恶。他写道,“当我们剥掉行为科学的术语外衣,我们看到暴露出来的殖民地公务员心态,即相信自己国家的慈善以及自我世界秩序观念的正确性。”他的靶子包括同在麻省的学者伊契尔·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乔姆斯基认为,像普尔和亨廷顿这样的新官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越南战争设计者和执行者。因为参与计划战争,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背叛了公共信任。”①[美]阿兰·沃尔夫:《教授参战:乔姆斯基和他的孩子们》,吴万伟译,http://chinaelections.net/NewsInfo.asp?NewsID=124807.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发表后,乔姆斯基再次祭起声讨的大旗。他说:“亨廷顿提出的为控制本国人民有必要制造错觉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纯粹的真理:理智的观察者不应相信领导人们坦言的所谓善意。这些表白是世界通用的,内容也不难想象,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些罪大恶极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苏哈托和萨达姆·侯赛因都曾用华丽动人的词章来描绘自己崇高的目标。”②[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白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29页。他感叹:“研究人类社会时经常会遇到障碍,所以研究者必须撕开官方宣传中的假象,那些制造假象的手段常与权力集中的过程如出一辙。”③[美]诺姆·乔姆斯基:《失败的国家》,白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29页。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亨廷顿即使不是罪犯,起码也是帮凶。
1986年,亨廷顿被提名加入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遭到耶鲁大学著名数学家朗(Serge Lang)的带头抵制。朗根本不相信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用数学方法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即60年代种族隔离的南非是“令人满意的社会”。朗详细考察了亨廷顿的论证过程,并专门到哈佛大学调查一年,此后得出结论:亨廷顿在书中所运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都存在着科学上的错误,亨廷顿歪曲历史记录并使用伪科学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亨廷顿没有对他的数学论证提出强有力的反驳。朗的看法得到其他投票者的认可。后来亨廷顿虽然又一次得到提名,但再次被国家科学院拒之门外,终其一生也未能进入国家科学院。1998年,朗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写入了他的著作《挑战》中,该书的前222页,便是亨廷顿的案例,题为《学术、新闻与政治:亨廷顿案例研究》。在朗等学者看来,他所从事的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
亨廷顿的同行们有时也并不客气。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问世后,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曾发表评论,说《士兵与国家》、《文明的冲突》是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我们是谁?》则显然不同,充斥着道德的热情,有时甚至近乎歇斯底里(bordering on hysteria)。④Huntington and Alan Wolfe,“Getting Me Wrong”,Foreign Affairs,Vol.83,No,5,(2004)pp.155 -159.亨廷顿去世后,哈佛大学学者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写了一篇文章《亨廷顿的意义》,称他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pariah)而去世的。他的《我们是谁?》出版后,“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哈佛及其他地方的贱民地位”⑤[美]埃里克·考夫曼《亨廷顿的意义》,吴万伟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079。。
为什么一个学者,却不断被人送上墨索里尼、罪犯、帮凶、伪科学、歇斯底里、贱民等这些带有不敬甚至侮辱的称号和词汇?他是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又的的确确成了一个大问题。亨廷顿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回答,他说自己是兼具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两种身份从事研究的。爱国者本身是一个充满复杂含义的词汇,这恐怕正是人们对他身份容易产生疑问的原因,也是他不断遇到麻烦的原因。
二、“文明的冲突”说了些什么?
毫无疑问,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冷战的结束。学者徐国琦有一段论述,说得非常清楚。他说:“1989年,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40多年的遏制战略因此过时。冷战时期许多熟悉的模式及规范应抛弃……许多学者及政客在1989年后……纷纷撰文,提出后冷战国际关系模式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前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是1989年西方朝野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心态的产物。”①徐国琦:《塞缪尔·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理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福山的乐观情绪很快被现实所击溃。
在1993年《外交》季刊上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并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之系统化。他所要“破”的一个重要对象,即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其他形式的普世主义学说。这构成了本书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在亨廷顿看来,福山的结论“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是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不符合事实。他说,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②[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他还批评其他形式的普世主义,如全球化和现代化。在他看来,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总之,“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③[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他说的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观点使他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社会的批判者,而不是维护者。他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
如果仅此,我们并不怀疑他的学术立场。但亨廷顿进一步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他自负地声称:“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④[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将他与其他西方中心论者作根本性的区分。
在对领土和人口、经济产值和军事能力等因素作量化分析后,亨廷顿得出结论: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权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⑤[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⑥[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在打破普世论和面对文明均势形势下,他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即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他还认为文明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有其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⑦[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5、63、87、102、141页。
亨廷顿认为,西方正在、并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至于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①[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30页。二者相比,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②[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30页。
三、中国学者的回应
中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有着数量庞大的回应文章,基本围绕文明、冲突、国际秩序三个主题讨论,侧重点各有不同。
第一个主题以强调文明的融合与交流为主,可称为找缺陷型回应。汤一介认为,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发展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如果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则是主导的。作者以佛教传入中国的三个阶段为例,说明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文化不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相反常常是促进不同国家、民族间互相了解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③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出,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可以引起冲突,甚至可以由冲突导致战争。但是,是否必然会引起冲突,能不能化解冲突,使之不因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战争,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可以使文明共存的资源,用以消解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引起冲突的文化因素。就中华文明而言,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的冲突提供有意义的资源。④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刘靖华讨论了文明的冲突以及相互影响。认为就文化适应性而言,一种文化或文明在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冲突可以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文明间的建设性对话和相互创造才是更有意义的。亨廷顿将冲突的一面推向了极致,而对文明间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相互影响却未置一词。文明从总体上是趋于整合的,这种整合是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样的变迁相对于整合来说就有如一种“蛹体”,文明间创造性的生命互动就在这种“蛹体”中诞生。⑤刘靖华:《冷战后世界冲突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2期。杜维明认为,亨廷顿的这个论说本身的建构非常不成熟,事实上很多杰出的西方学者已经看到其中的破绽,即一种狭隘的二分法:不是进步的就是落伍的,不是文明的就是野蛮的,不是西方的就是西方之外的。这个提法问题太大,一是世界上没有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二是非西方地区同样渗透到西方的各个领域。⑥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潘光同样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有时不同文明之间也可能发生恶性冲突,但主要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少数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且这类冲突均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尽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文明因素,特别是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是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努力解决这些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才能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⑦潘光:《浅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历史教学》2007年第5期。
第二个主题讨论冲突为主,可称为挖根源型回应。一种观点是挖冲突的根源,即承认冲突,但认为冲突的根源不是文明,而是利益。张顺洪认为,文明的冲突这样的论点可以说只是解释了冲突的现象,而不是实质。文化客观上讲是无辜的,文化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不同利益的矛盾,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国家群体利益。而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则是冲突的主要原因。⑧张顺洪:《我对文明冲突的初步理解》,《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钱乘旦也认为,人类的冲突,归根到底由利益引起。利益既有物质的利益也有非物质的利益。权力、信仰、社会地位、尊严、威望、文化享受等,都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成为利益的组成部分,但物质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利益,即使在最典型的信仰冲突中,物质利益也是时隐时现地存在着。①钱乘旦:《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是挖亨廷顿的思想根源,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别有用意的建构。如禾人认为,亨廷顿炮制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威胁论,出于三个目的:首先是为西方大国保持和巩固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支配地位服务,以所谓的威胁论作为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干预的借口;其次是为美国等西方大国保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强大的军力制造根据;再次是企图借此挑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②禾人:《“文明的冲突”主宰当今世界?》,《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徐国琦认为,在后冷战时期,西方权力的传统杠杆如军事、外交等逐渐失去效力,其他国家正致力于国家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现代化建设。使西方国家普遍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西方经济一直疲软不振,雄风不再,只好利用抽象的“文明”冲突来批评他国。文明的冲突理论未能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冷战术语“我们”与“他们”对立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实乃同出一辙,并无轩轾。因此“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和建树。③徐国琦:《塞缪尔·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理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李慎之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却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④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赵世瑜认为,亨廷顿的立脚点是要西方国家加强自身团结,使在文化上接近西方的东欧和拉美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促进和维系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一致对付伊斯兰与儒家文明。这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战略格局划分,未必不可能成为未来西方国家的战略指南。⑤赵世瑜:《未来的文明与文明的未来》,《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金灿荣的看法也类似。他认为从政治层面看,文明的冲突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一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中心的、排斥异己文明的西方中心史观,二是基于斗争哲学的、以寻找主要敌手为目的的冷战思维定式。亨廷顿对非西方文明力量的戒备与恐惧,其心理基础就是对内部问题的担忧和缺乏信心,其出发点则是寻找外部敌人,以凝聚内部力量。⑥金灿荣:《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启示意义》,《世界知识》1995年第9期。
第三个主题以讨论国际政治秩序为主,可称为有限肯定型回应。王逸舟认为,总体上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仍然会以国家关系及其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为中轴,种族的、民族的、文明的差异只会使主权国家产生更多的裂变而不是使其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间的冲突不会超过、盖住或压倒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国家间和地区间冲突。但亨廷顿以文明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从当代国际政治中最令人焦灼的冲突现象入手,仔细辨别暴力对抗行为背后的民族情绪、大众心理、文化特质、血缘标识、宗教基础、认同层次、角色意识、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力陈国际政治冲突将受文明冲突左右的论点,开国际政治的“大文化”研究之先河。⑦王逸舟:《国际政治的又一种透视》,《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邝杨也认为,亨廷顿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强调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那些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意识形态思维中纠缠得太久的人来说,变换一下视角,重新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大势,犹有必要。⑧邝杨:《变动中的世界途径》,《东方》1994年第1期。王缉思认为,把文明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有学术意义的。亨廷顿的问题是把文明提高到比民族、种族、经济利益等等因素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缺乏根据了。至于他一定要把世界各大文明的差异说成冲突,而且还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冲突甚至会引发战争,那就更加危险,误导性更强。⑨王缉思:《文明的冲突理论战述评》,《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1期。江宏伟认为,他创造了有别于“冷战模式”的新的理论框架,打破了过去从政治、经济、霸权的角度谈论国际文化的旧格局,而将“文明”作为自己论点的核心范畴来界定当今世界后冷战新格局,这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待西方和东方问题。⑩江宏伟:《冷战后美国外交的思维范式》,《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2期。以上都谈到了亨廷顿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引入文明视角的重要意义。不过徐国琦指出,这并非亨廷顿首创。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干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自1980年代初即尝试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政治,认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关系。他在1981年出版的《权力与文化》,以及1992年问世的《全球模式中的中国和日本》等论著都是在这方面探索的结晶。①徐国琦:《塞缪尔·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理论”》,《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应当说,以上各种论点及评论都非常有见地,触及到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种种缺陷和偏颇之处,但亨廷顿并未做出回应。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分析不同,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称之为帮凶,数学家朗斥之为伪科学,政治学家阿兰·沃尔夫批评其近乎歇斯底里,他们的论证要更有力、更深刻,令亨廷顿几无还手之力。
四、《我们是谁?》是《文明的冲突》的姊妹篇
我们可以暂时先搁置文明冲突的讨论,不妨来看看亨廷顿晚年的其他作品。亨廷顿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另一部著作。这本可被视为《文明的冲突》姊妹篇的著作,当年便在美国《外交》季刊引发一场亨廷顿与沃尔夫的互相攻击大战。该书的中译本于2005年出版,但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我们说《我们是谁?》是《文明的冲突》的姊妹篇,是基于这样一些理由:二者在设定的前提、论证逻辑、得出的结论以及应对策略上无本质区别,只不过讨论的对象从国外转移到了国内。
两者都是从身份认同危机——旗帜的象征意义开始讨论的。在《文明的冲突》中,作者这样开始了叙述:1994年10月16日,7000名洛杉矶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游行,但却是倒举着。②[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在《我们是谁?》中,作者开篇便写道:星条旗似乎成了一种宗教偶像,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其意义之深更甚于别国的旗帜。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到2000年时已不如此前百年间那样举国一体。在美国人各种特性/身份的旗杆上,星条旗似乎是处于降半旗的位置,而另外一些旗帜却在更高处飘扬。③④⑥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148、216页。
在对认同危机作夸张性描述后,作者设定了批判的目标。在《文明的冲突》中,批评的对象是普世文明。在《我们是谁?》中,批评的重点是多元文化。作者认为,多文化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是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挑战,可能导致美国陷于分裂。④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148、216页。批判普世文明和多元文化作后,作者开始强调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文明的冲突》中,他从八个方面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在《我们是谁?》中,他用全书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分析美国文化的特性,其中特别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
以上这些都是铺垫性工作,并非两本著作立论的主导思想。两本书的核心都在于,在身份认同危机下树立敌人,用新的意识形态维系国内的团结,在《文明的冲突》中是“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在《我们是谁?》中是“拉美移民威胁论”。
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在《文明的冲突》开头部分,作者引用了一段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作者在引用完之后,意味深长地加上如此评述:“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⑤[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也许觉得在该书中说得还不够直白透彻,在《我们是谁?》中,作者再次为树立敌人的意识形态辩护。他说,“社会学理论和历史表明,没有外部敌人或对立面,容易出现内部纷争。因此毫不奇怪的是,随着冷战的缓和及结束,美国和别的许多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国民身份之外的身份更加感兴趣。没有重大的外部威胁,国家对强有力政府和国民团结的需要也就降低了。”⑥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148、216页。现实情况也正如作者所言,20世纪末民主制度失去了有分量的世俗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失去了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竞争者。失去了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目标。作者随后写道,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冷战结束时说,“国家是需要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是这样的敌人。①[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2页。这可以说是作者对“文明的冲突理论”写作动机的最好说明。
如上文所述,在《文明的冲突》中,作者将中国的崛起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我们是谁?》中,威胁来自拉美裔移民。作者危言耸听地写道:“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移民继续不断地处于高水平,他们同化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水平又很低,这就有可能使美国变成一个两大民族、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国家。”②[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2页。
由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称《我们是谁?》与《文明的冲突》为姊妹篇毫不为过。如果说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与伊斯兰世界的复兴、拉美裔移民的状况的分析体现了一名学者的敏锐,那么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拉美裔移民威胁论”则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爱国者的狂热。两者都是出于同样的加强身份认同的目的,将事实渲染夸大为鼓动民众的意识形态。
五、树立敌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下的意识形态
亨廷顿亲自告诉了我们,《我们是谁?》与《文明的冲突》两部著作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他也笑纳了沃尔夫送来的“本土主义者(nativist)”称号。毕竟以他四面树敌的做法,本土主义者已经是比种族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宽容得多的称号了。对于文明的冲突理论而言,“本土主义者”也正好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理解视角。亨廷顿是一名爱国者,是政治学教授,他知道在众多学者和民众心中,某些词汇比如“意识形态”,是招人厌的东西。所以他把所批判的对象统统加上意识形态的帽子,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多元文化是反对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他自己的文明冲突理论,何尝又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与斯宾格勒、汤因比与布罗代尔等人不同,亨廷顿不关心如何界定文明,也不关心文明如何发展变迁,所以专业学者很容易看到其中的自相矛盾与漏洞百出之处。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亨廷顿去纵论文明的冲突。因为他不是以学者,而是以爱国者的身份去讨论的。美国《旗帜周刊》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曾说过,对美国政策持原则性观点并不一定需要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他说自己根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观点出自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亨廷顿难道不是如此么?
恐怕没有人比亨廷顿自己说得更为直白了。在1997年《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中,他梳理了美国以“树立敌人”来构建自我身份的历史。他写道:“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身份。只有弄清楚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在与讨厌的‘他者’相对立的基础之上构建其信条身份的。美国的对手们总是被界定为自由的对手。独立时,美国人无法将他们从文化上与英国区别开来,因此就从政治上着手。英国是暴政、贵族和压制的体现,美国则代表了民主、平等和共和。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将自己看作是欧洲的对立面。欧洲代表了过去:落后、不自由、不平等,有封建主义、君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特性。美国则相反,代表了未来:进步、自由、平等和共和。到了20世纪,美国登上世界舞台,逐步将自己看成是欧美文明反对新兴挑战者如纳粹德国的领袖。二战后,美国将自己看成民主自由世界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领袖。”③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Vol.76,No,5,1997.p30、pp30 -31、p48.但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暂时失去了敌人,亨廷顿对此充满忧虑。他说,冷战在美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培育了共同身份。冷战的结束似乎要削弱或起码改变了这种身份。一种可能的结果是逐步反对联邦政府,然而,这正是美国国家身份和统一的制度显现考虑到国内力量推动美国朝向异质性、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和种族分裂发展,美国或许比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来维持其统一。公元前84年,罗马人完成对希腊世界的征服时,苏拉曾提出过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敌人了,共和国的命运将会怎样?”答案很快出现,共和国不久崩溃了。美国似乎不会有类似命运,然而在缺乏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今天,美国信条到底多大程度上能维持其吸引力、赢得支持并保持强劲的生机?假如出现历史的终结与民主在全球的胜利,这对于美国而言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不安定的事件。④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Vol.76,No,5,1997.p30、pp30 -31、p48.正如亨廷顿所言,寻找并树立新的敌人,是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威胁对于美国产生新的国家身份与目标而言足够了,虽然这还不会立刻发生。”⑤Huntington,“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Foreign Affairs,Vol.76,No,5,1997.p30、pp30 -31、p48.
将中国列为敌人的做法,并非亨廷顿独占。20世纪90年代,许多美国右翼人士都在散布“中国威胁论”。1992年秋,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Munro)在《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声称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但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说食品的短缺伴随着经济的不稳定,其对安全的威胁远比军事入侵大得多。1997年,《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Munro)发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做出夸张的描述。1998年,中央情报局前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William Triplett II)和共和党前国会对外政策助手爱德华·廷珀莱克(Edward Timperlake)合写《鼠年:克林顿如何为获中国现金出卖美国安全》一书,危言耸听地把一批卷入美国政治筹款活动的华人都说成是中国特务。次年他们又发表《赤龙腾飞: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一书,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从以上同一时期的其他人物言论可以看出,亨廷顿的结论和他们如出一辙。只是作为政治学家的他,对身份认同危机感受得更为深切,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罢了。在1997年瑞士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亨廷顿继续阐述他的感受,“一个国家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认同危机,而整个世界似乎也陷入了全球性认同危机之中,人们仍按照传统的方式,以祖先、宗教、语言、历史、风俗、体制来解释自己,用文化集团、部落、民族、宗教身份、国家和最广泛的标准——文明来区别身份。”①[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国外社会化科学》1998年第6期。在1999年,在纪念科罗拉多学院建校125周年的发言中,他再次谈到认同问题。在他看来,世界各地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②[美]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到此时为止,《我们是谁》已经呼之欲出了。
“9·11”事件使亨廷顿为之一振。他高兴地看到,“美国国旗又重新高高地飘扬在旗杆顶上”。只不过,这种高兴情绪并未持续多久。细心的他注意到,查尔斯街的17面国旗,到2001年11月减少到12面,12月减少到9面,2002年1月为7面,3月为5面,到了一周年时,只剩下4面。③[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218-219页。外部威胁未能使团结维持多久,他于是以一名爱国者的热情和责任感,重新从内部找挖潜力,迅速完成了《我们是谁?》,试图使美国长久地获得万众一心的团结。尽管《我们是谁?》讨论的是内部威胁,但亨廷顿还没忘记重新强调一下《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将中国列为美国主要威胁的结论。他声称,20世纪中,美国有两次受到最大的威胁,一次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敌人二战期间结成的轴心国,另一次是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共产主义敌人50年代结成的同盟。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威胁,其核心将会是中国。④[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218-219页。
2006年11月,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在第一部分第三条专门分析了“文明的冲突”理论的负面影响。报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由‘文明的冲突’理论所造成的忧虑和混乱扭曲了(distorted)对于世界面临困境之实质的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战争与对抗的历史,同时也是建设性的交换、互相促进与和平共存的历史。用一成不变的文明界限来区分内部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不同社会,妨碍了(interfere)人们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动机、行为这类问题。与这种文化类型模式相比,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裂痕,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的裂痕,不同政治团体、阶级、职业、民族之间的裂痕,会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事实上,这种模式只会强化(entrench)早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promote)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助推为(help)萦绕于大众想象中的看似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因此,必须抵制(counter)这种加深不同社会之间敌对和不信任的成见和错误概念。”⑤UN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Report of the High - level Group,November 13,2006.http://www.unaoc.org/content/view/64/94/lang,english.该权威报告不仅揭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的缺陷和危害,而且呼吁人们抵制这种理论。这个报告,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KI091
A
1003-4145[2012]03-0005-08
2011-12-15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在职博士后。
(责任编辑:蒋海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