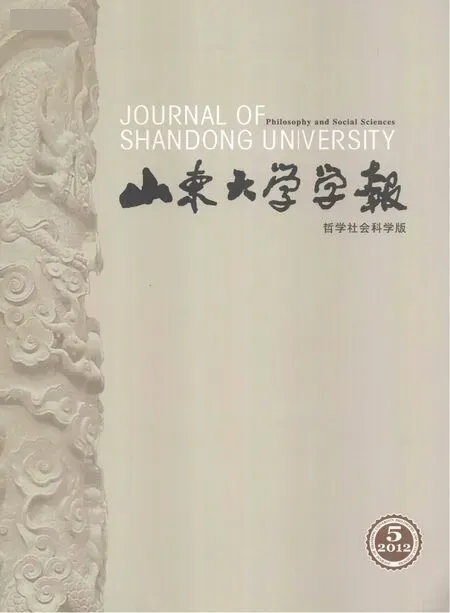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中国特色”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杭州310027)
[责任编辑:贾乐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从1996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从53.4%下降为39.7%,同期企业营业余额占比从21.2%上升为31.3%,而政府财政收入占比从10.4%上升为20.6%。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存有疑虑,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做了重新估算,但即使剔除2004年统计口径变动等影响,重新计算的结果仍旧表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存在,只不过幅度有所不同而已。如白重恩等重新估算的结果是,在要素成本法增加值中,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2006年间从59.1%逐渐下降到47.31%①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张车伟等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出的结论是,劳动报酬占比“仅仅在近几年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①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可以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或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不在于对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事实的认定,而在于对其发生机理的剖析。只有真正弄清楚了原因,找到了根源,才能采取有效对策予以矫正。近年来,一些学者高度关注这一现象,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此作了探讨。罗长远把现有文献的理论探讨概括为四个层次:一是从要素替代弹性角度考察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深化的关系;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考察技术进步和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三是从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中寻找动因;四是从全球化角度对不同要素的不对称变化进行分析②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1期。。有些学者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进行总结,探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一般规律。如李稻葵等就提出了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U型规律”,认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时,劳动收入份额会开始上升③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深入交换意见,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观点,增进了对该问题的认识。
“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收入分配历来被认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但收入分配与整个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割裂。“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社会形式决定分配的社会形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今天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生产方式又有生产的物质技术关系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分别作用于这两个层面。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的作用更为重要,而目前我国对于劳动报酬占比问题的讨论中,似乎对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体制背景缺乏足够的重视,上述罗长远概括的几个层次的讨论,大多属于生产结构的技术性变化或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对导致这种变化的体制性根源或政策形成的机制过程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在多重经济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经历着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从计划经济向双轨经济再向现代市场经济、从公有制经济向混合经济、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等多重转换过程,工业化、城市化、民营化、市场化同时展开。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市场结构、社会结构同时经历急剧调整。在这样一种剧变中,不仅假定要素报酬比例长期稳定的“卡尔多特征事实”在中国不存在,而且还有着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中国式“特征事实”:
1.中国式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伪城市化”为中国所独有。
2.中国式的身份等级制度,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不同于基于能力差异的国外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中国干部、职员、工人、农民相互间泾渭分明:即便农民做工人的事,也只能叫农民工;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待遇各异。而且在区域、行业内部还有很多制度性差异。
3.中国式的区域竞争机制,从“财政大包干”到“分税制”,地方利益主体的角色没有根本性变化,“增长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各地区之间为率先增长而争夺投资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笔者曾收集长三角40多个县市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现基本上都在做土地和财政补贴的文章。这种区域尤其是县域之间的招商引资竞争确实产生了某种内生增长机制,因而被张五常教授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谜底”所在⑤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10年。。但这种千方百计降低投资者商务成本的亲资本行为,无疑强化了资本地位,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
4.中国式抑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体系。计划经济时期以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为指导,以“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为口号而实施的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短期放松后又重新成为政府制定工资收入分配政策的指导思想。劳动工资管理部门一直把“企业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国工资总额增长不得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教条奉为圭臬,把抑制工资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对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绩效挂钩办法或工资总额包干进行计划控制,而且延伸到非国有企业,如国办发(1993)69号文《转发劳动部关于加强企业工资总额宏观调控意见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各地区、部门的全部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和各种经营方式的企业,均应按要求认真编制本企业的工资总额计划,报送主管部门和同级劳动部门。”直到21世纪,国家仍通过对各省下达工资指导线对工资增长予以控制。如2002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对浙江省的工资指导线审核意见中规定:企业货币平均工资增长基准线为12%,上线为17%,下线为零增长或负增长。这种控高不控低的规定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对工资增长的态度。尤其荒唐的是所谓“计税工资制度”,即只有部分工资能进入企业成本(最初为800元,后来增加到2000元),超过部分企业要另外交33%的所得税,而个人拿到工资又要去交个人所得税,实乃“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可见,政府不但不鼓励企业给职工多发工资,反而要加以惩罚。
从以上事实中,人们不难体会中国劳动报酬增长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可以说是由三种力量打压造成的:一是市场供求力量对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每年千万以上的新成长劳动力,还有国企改革释放出的数千万富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劳动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工资谈判能力。二是歧视性制度安排和社会保障缺失,造成相当部分劳动者得不到应有保护。一个显然的例证是工资拖欠的大量存在。在《资本论》中有大量剥削压迫劳工的例证,但没有拖欠工资的描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少有。即便如此,许多劳动者仍不得不在“饥饿纪律”驱使下接受“生存工资”和奴役劳动。三是抑制性工资政策体系,人为压低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增长,使劳动者报酬难以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亲资本的政策导向进一步扩大了两种要素报酬的差距。
由此可见,在我国转型经济的体制背景下,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要从两方面结构变动中去分析。一是生产要素组合的技术性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市场供给结构等;二是经济主体的权力结构,包括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劳工、劳动与资本等。如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明确的界定和有效的保护,即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创新仍然难以解决劳动报酬占比下降问题。
上述中国模式“特征事实”多数是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遗产。改革开放30多年,虽有所松动,但远未解决。究其根本,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这种扭曲的体制环境中追求投资驱动的高增长,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低成本竞争优势,必然造成分配格局失衡。
实践证明,靠采取某个单项措施或颁发法律、政令,难以矫正这种失衡。耐人寻味的是,1996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之时,恰逢《劳动法》于1995年颁布实施。2003 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急剧下降,而此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连续5年超过10%的高增长时期,而且此时已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因此,要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一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功能,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消除不同群体劳动者之间的制度性歧视,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二是要深化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尤其要矫正亲资本立场,建设对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同等保护的“中性政府”;三是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从物质资本驱动转向人力资本驱动,在提升劳动要素贡献与地位的基础上保障劳动报酬占比上升。
-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关于劳动份额U型规律的争论
-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问题(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