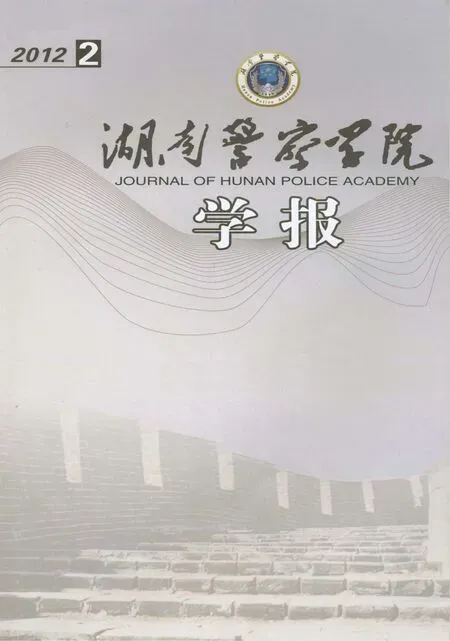“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李竟芬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李竟芬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扒窃;扒窃入刑;公共场所;随身携带
前 言
《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全国各地都相继有抓获因扒窃而涉嫌盗窃罪的行为人,有部分地方法院也最终对扒窃行为人做了定罪处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处理轻微扒窃案的做法不一致,扒窃入罪的标准不统一,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公检法机关对《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的新规定认识不统一。一些地区的公安检察机关认为一旦扒窃案件一律都入刑,那么案件将会成大量激增,使得原本就很紧张的司法资源越发紧张,所以对于扒窃案件持谨慎的态度,轻微的扒窃案不会进入司法程序,而是给予行政处罚。有些地方则认为所有的扒窃案件都应入刑,虽然这种案件发案量较大,但通常案情简单,处理起来难度不大,司法部门可以对这类案件启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短期内都可以办结,即使盗窃有些许增多也不会造成公检法系统的运作负担。其实,《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扒窃犯罪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扒窃犯罪的定罪量刑给予了清晰的标准,全国在处理扒窃案件时应参照执行。对于实践中的不同认识可以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准确解读和相关的法理解释来进行提高,以下笔者试将对执法中出现的对于扒窃犯罪定罪量刑的几个困惑进行厘清。
一、“扒窃入刑”的必要性分析
“扒窃”,是在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增加的进盗窃罪的条款的,刑修八草案一次审议稿仅仅涉及盗窃罪死刑的废除,并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将“扒窃”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有的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扒窃”行为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且这类犯罪技术性强,多为惯犯,应当在刑罚中作出明确规定。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扒窃”就出现在了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的草案稿中,并由《刑法修正案(八)》最终确认了这一规定。[1]据有关媒体报道,“扒窃入刑”,确实有考虑到扒窃行为对公众安全感的损害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2]也就是说“扒窃入刑”主要原因是立法者认为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盗窃罪大,达到了将它规定为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的相当程度。笔者认为,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是就一定比一般的盗窃行为大,这点有待研究。
但现实中,扒窃确实具有以下几点特征:(1)扒窃的社会危害性确实很大,它直接极大地损害社会公信度,对社会风气影响极坏。在现代社会,大部分要人经常地出入公共场所,如果扒窃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每个人都是潜在被害人,且扒窃是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这样不仅被害人损失了财物,很多社会公众都可能受到恐吓,一旦不幸遭遇扒窃将蒙受长期阴影。(2)对于扒窃案侦破的难度很大,扒窃的取证很难。扒窃都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很难留下证据,且一般是团伙作案,而且扒窃的对象一般体积微小,犯罪所得容易快速转移。(3)目前对扒窃案的处理明显打击力度不大。由于一般只能在扒窃行为得手后方可对行为人进行抓捕,在行为人被抓捕后被害人还通常不敢作证,扒窃案件举证难度较大,很多扒窃只好抓了就放,得不到有效及时处理。就算能证明也只用社会治安的办法来处理,给予轻微行政处罚对于频发的扒窃案来说打击力度太小。[3]况且扒窃行为人多为惯犯,且改造难度大,如果不一律入刑,等同于放纵犯罪,破坏刑法的刑法的威慑力。当然,扒窃的上述特点并不是说要成立扒窃犯罪必须要具备以上所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只是大多数的扒窃案的外在特征,这些特征帮助我们更好地衡量“扒窃入刑”的立法成本和立法价值,但成立扒窃犯罪并不要求具备以上所有的特征,《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对扒窃做过多的限制,在给扒窃犯罪定罪量刑时主要考虑是否符合扒窃的内涵,而不是从起特征上做入罪的考量。
因此从构成要件上来探究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是因为扒窃行为的特殊性。盗窃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成立的构成要件有三个,①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②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方法;③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数额较大,是盗窃行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如果盗窃的财物数额较小,一般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不需要动用刑罚。但对于一些特定的盗窃行为,只要实施了该盗窃行为,即使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条件,因该行为本身的特殊社会危害性,也构成犯罪。所以认定扒窃构成盗窃罪的关键是正确理解扒窃的内涵。
二、“扒窃”的内涵
“扒窃”一词,产生于反扒实务中,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前它只是在侦查抓获犯罪以及治安管理法规中的概念,并非严格的刑法学用语,但是如今进入了刑法学领域,就应当对其含义进行准确界定,且《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扒窃”是一个空白的罪状,为了保证准确定罪和一致量刑,也必须让这个概念内涵清晰。
(一)历史解释
“扒窃”一词,产生于反扒实务,以前仅限于侦查学和犯罪学中使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徐久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扒窃的定义是:“扒窃”一词不是法律用语,而是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民警在工作总结时常用的词汇,是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从他人身上获取财物的行为。”[4]地方治安管理法规对“扒窃”也有过定义,如1990年《长沙市惩治扒窃的规定》第二条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车站、码头、商场、集贸市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这个定义有一定借鉴性但其合理性不充分。
经过这次刑法修正后它将转化为刑法学上的一个术语。需不需要司法解释来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二)文义解释
我国现代汉语将“扒窃”解释为:从他人身上偷窃财物,[5]写出了扒窃的明显特征,但是没有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进行必要界定。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教程中定义“扒窃”也有三个条件:①扒窃指的是近身盗窃;②窃取应是对方紧密控制的财物;③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
(三)学理解释
权威学者张明楷将“扒窃”定义为: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且认为扒窃成立盗窃罪,客观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②所窃取的应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③所窃取的财物应是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6]
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去给“扒窃”下定义,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就是怎样去界定公共场所和随身携带,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是可以影响到定罪量刑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例一:行为人在红绿灯处,趁被害人不备,从其放在电动车脚踏板上的背包内窃取其钱包一个(价值人民币5元),内有人民币108元及身份证等物品,后被当场抓获。红绿灯处算不算公共场合?被害人电动车脚踏板上的背包算不算随身携带,被害人对被窃取的钱包是不是紧密控制?
第一,关于公共场所范围的界定。刑法中没有对“公共场所”的明确解释,行政性质的《公共场所管理条例》也没有对“公共场所”进行定义。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中出现的“公共场所”,学界多定义为“对公众开放,供其从事各种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带有公益或商业性质的场所。”[7]有观点认为所谓“扒窃”,一般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在车站、码头、商场等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确实,说到“扒窃”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共汽车、车站和商场等地方。因为“扒窃”一词本来就产生于第一线广大干警的反扒工作中。但是采取列举式的定义方法将限制“公共场所”的范围,一旦没有被列举,比如红绿灯下、停车场、学校食堂等人流量不是特别大的地方算不算公共场所呢?
笔者认为,对“公共场所”的定义,不应采用列举的方法,采用列举的方法不仅影响刑法的简短的价值,我们也无法穷尽列举,况且越详细越具体的规定可能漏洞越多,因为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往往难以被人们认识,而合理的使用模糊性的概念时任何法律都不可避免的,[8]所以在定义的方法上不要执着于列举。
在阐述“公共场所”的性质上,也有不同观点:张明楷教授认为公共场所是不特定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而且只要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即使公共场所的人不是很多,也不影响扒窃的成立。例如,在公共汽车上只有少数几人时,行为人实施扒窃行为的,也应认定为盗窃罪。[9]反对的观点认为对公共场所的含义应结合刑法条文做个别的解释,认为扒窃行为侵犯的是财产权利,在凌晨空无一人或仅有数人的车站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就不应认定为扒窃。[10]
笔者认为公共场所不应在场所的人流量和场所的性质上进行严格限制。公共场所的认定不能单单从人流量的大小来考虑的,不特定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以及有多数人在内的场所都应算公共场所,只要有可能出现人流量较多的地方都可以算公共场所。也不是单从场所的性质来考虑的,娱乐、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质的公共场所都可以认为是刑法里的公共场所。综上,笔者将公共场所定义为:不特定人多数人可能进入、停留的场所。那么以上的例子中,行为人在红绿灯处行窃也算在公共场合行窃。
第二,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多数论者认为对随身携带应做扩张解释,包括他人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的财物。例如,在公共汽车上窃取他人口袋内、提包内的财物,在火车、地铁上窃取他人置于货架上、床底下地财物的,都属于扒窃。也有论者认为,既然是“扒”,对象就应当是与他人紧密联系并受他人实际控制的物品,如贴身衣服口袋里装的钱包、随身携带的手提袋等。在火车、长途汽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与被害人分离的行李箱里的物品就不属于扒窃了。
笔者认为,随身携带包括置于身边的财物。要求一般公众在公共场所都将自己的财物握在手中或绑在身上是不切实际的,在很多公共场所大部分人都会将体积稍微大点的财物放在目光可及或容易照看的地方,窃取这种财物也将造成民众的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且难以取证,所以将这种行为也认定为“扒窃”是符合《刑法修正案(八)》的精神的。所以笔者笔者认为,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和近身放置的财物。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占有的近身物品的行为。那么以上的例子中,被害人电动车脚踏板上的背包也算随身携带。
三、“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和手段限制
在明确了扒窃的内涵后,还是会有人对扒窃是否一律入刑存在疑问。先分析一下以下案例:
例二:行为人在马路上看到一名女子单独行走,看见该女子兜里露出来一个MP4,就跟着这女孩身后走,趁该女子不注意的时候,把该女子兜内的MP4偷走了,行为人被警察抓抓住,警察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起获了MP4,经物价部门认定该MP4价值50元人民币。行为人窃得的财物数额太低,手段太平和,社会危害性也不大,还应不应该承担盗窃罪的刑事责任?
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扒窃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要么是扒窃所得达到盗窃罪法定的犯罪数额要么是扒窃三次以上。也就是说在扒窃行为没有独立成盗窃罪的一种行为前入罪是有数额和次数的要求的。数额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3号]对“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作了明确的规定,“数额较大”,以五百元至二千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五千元至二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三万元至十万元为起点。而多次的要求体现于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42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扒窃”的规定,使得这两个司法解释关于盗窃罪数额和次数的标准不再适用于扒窃犯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项,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仔细分析这个条款,可以发现,“扒窃”通过“或者”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并列,可见“扒窃入刑”是没有数额要求的,“扒窃”通过顿号与多次盗窃并列,那么“扒窃入刑”是没有次数要求的,同时也于“携带凶器盗窃”,说明“扒窃入刑”也没有作案手段的特殊要求,只要符合扒窃的内涵就可以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非常合理的,可以避免现实操作中的不少问题。比如“扒窃入刑”如果还用次数来限制,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对于次数的认定是采用主观认定还是客观认定不好选择。只主观上去认定,如果行为人不记得自己是第几次扒窃就不好定罪了,这样可能记性好的行为人就被认定为犯罪而追究刑事责任而记性不好的就不能成立犯罪。如果采用客观标准去认定,扒窃行为本身不好被证明,在现有证据只能证明行为人有一次的扒窃时候,即使行为人交代自己有几次扒窃的行为,也不能光依靠口供定罪。所以说“扒窃入刑”采用各种限制是非常不利于打击扒窃的,这也是实践中为何对于扒窃行为人抓了就放,得不到合理处理的原因。用次数去限制犯罪的范围是不合理的,同样地,如果在数额、手段上进行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好操作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扒窃入刑”的规定没有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确实合情合理、易于操作。回到案例中,既然没有数额限制,行为人所扒窃的财物虽然价值只有50元,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的情节,那也是成立盗窃罪的。当然,如果行为人是初犯、偶犯、少年犯或者有其他的显著轻微的情节可以用刑法第一十三条的规定来出罪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主要是从行为的客观方面进行分析的,可以说“扒窃入刑”客观上对于扒窃所得没有数额的要求,但盗窃罪是财产性犯罪,是故意犯罪,不法获取他人的财物是盗窃罪的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扒窃入刑”,在主观上是要求行为人有意欲窃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的。
笔者对“扒窃入刑”的简明规定,持赞成态度,《刑法修正案(八)》这样的规定体现了对盗窃罪构成要件的适当扬弃,同时也符合长久以来我国犯罪论所要求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也使得现实中扒窃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对于完善我国刑法典,有效地实现刑法的目的和任务不无裨益。
四、“扒窃”既遂与未遂的争议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前,扒窃案因为其行为与抓捕的特殊性,取证的难度,大多地被认定为未遂而被搁浅,大量扒窃行为人都是抓了只能放,这样造成了警力资源的浪费,扒窃案得不到处理,又使得扒窃行为人更加地猖狂。当然,《刑法修正案(八)》增加扒窃型的盗窃罪后,扒窃未遂的也要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提高了打击扒窃的有效性。
(一)普通盗窃既未遂的标准
普通盗窃罪是结果犯,其既遂与未遂认定的标准有很多学说,至今也存在不少争议。常用的区分标准主要有接触说、转移说、控制说、移动说、失控说、失控加控制说等几种学说,现在理论界的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失控说和控制说上,并且失控说在理论界更为流行。[11]笔者认为失控说更为合理,因为失控说更多的是从被害人的角度去考虑既遂的标准,刑法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法益,其次才是惩罚犯罪,失控说更符合这个目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了控制说是区分盗窃罪未遂与既遂的界限标准,所以,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控制说,而以失控说为补充。
(二)扒窃犯罪的既未遂标准
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既然扒窃犯罪是没有数额限制,就不管窃取金额的大小甚至没有金额都可能成立既遂。但是这里应注意,扒窃行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时间点,并不是说行为人一触及被害人财物就成立既遂。盗窃罪是财产犯罪,既未遂的标准应该看财产的占有是否发生了转移。扒窃的既未遂认定时,可以将扒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小件扒窃,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体积较小的物品,以行为人的手或者作案工具接触到被害人身上的背包或口袋的外侧时为着手,在取的过程中出现了其他情况是可以成立中止和未遂的,但一旦行为人取出钱包、现金或其他财物,不管财物的价值大小,也不论行为人是不是马上逃离了现场都算控制了财物,成立盗窃既遂。第二类是大件扒窃,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近身放置的体积较大的物品,以行为人的手或者作案工具接触到被害人的放置在身边的或者在一定固定空间的财物为着手,一旦行为人有效转移了被扒窃的大件物品就算控制了财物。比如扒窃火车架上的行李包,如果行为人提着行李包还没有出本车厢就被抓获了就只能认定为未遂。普通盗窃罪的既遂认定是以控制说为标准以失控说为补充的,按照这样的标准,确定犯罪人是否已经控制所窃取的财物,也应当根据盗窃财物本身的大小、空间和环境条件以及监控条件的不同具体情况分析。对于扒窃大件而没有效转移的情况,按普通盗窃处理时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没有实际控制财物,是未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将扒窃犯罪与普通盗窃认定既未遂的标准差异也不大。
笔者认为,还应该注意扒窃犯罪的不能犯未遂。不能犯的未遂是指行为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其犯罪行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达到既遂。未遂是法定的减轻量刑情节,认定既遂与未遂对于行为人的量刑影响极大。扒窃犯罪在不能犯未遂的情况下,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也可以起到均衡量刑的作用。《刑法修正案(八)》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扩大犯罪圈的、增加处罚面。一种行为是不是值得动用刑罚去规制,要综合地是看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这两个犯罪构成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二者的齐备和内在统一,决定了行为具有值得刑法处罚的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扒窃犯罪的不能犯未遂也应综合考量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统一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当然这里的对象不能犯并不是扒窃金额的大小去认定的,而是看行为人有没有取得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例如,扒窃他人口袋内的餐巾纸、名片、廉价手帕等物品的,不应认定为盗窃罪。
五、“扒窃”出罪无需依赖于“但书”的适用
回到本文例二中的问题,行为人的扒窃行为可不可以用刑法第13条来出罪?以往我们常用民事或行政的手段来处理扒窃案件,扒窃未达到较大数额的或达到3次以上的,一般给予行政拘留或被报送劳动教养。但是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一旦被认定为扒窃就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哪怕最后判决只是被判处拘役或罚金,都与之前的行政处罚有天壤之别,因为前科制度对个人的发展影响极大,行为人一旦被追究了刑事责任,那么他的人生履历就永远地多了一个不可抹去的污点。“扒窃”出罪和之前的“醉驾”出罪问题是一样的,《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第二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应与行政处罚注意衔接,称醉驾如果行为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是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考虑确实是考虑到醉驾一律入刑之后,醉驾案件一下子激增,给公检法、监狱系统都造成极大的压力,而有些醉驾行为人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即被抓获也确实情节轻微,如果不区分情节一律认定为犯罪会导致法益保护的过度前移,刑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就值得质疑了。虽然各国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沿着“风险刑法”理论预设的轨迹在前进,但“风险刑法”理论的劣势更应该令我们警醒,每一次犯罪圈的扩张都应当经受得起更多的正当性诘难。[12]成功的一点是,虽然醉驾入刑本身没有情节恶劣的要求,醉驾却并非不区分情节一律入刑,而且出罪的方法也并不仅仅依赖刑法总则13条的规定,有论者认为在认定是否醉驾的时候可以给醉酒的血液酒精含量值解释在一定的幅度内,给予警察和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13]相对于“醉驾入刑”,“扒窃入刑”没有次数、数额、手段的限制,无法设定一个可以自由裁量的幅度值。扒窃犯罪是没有罪量要素的,“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罪量要素的犯罪,并不表示只要行为一经实施就一概构成犯罪。因为刑法总则关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同样也适用于这些犯罪,因而司法解释对这些犯罪规定了罪量要素。”[14]所以,扒窃犯罪,如果行为人在主客观两方面都符合情节显著轻微的条件,可能会适用但书来出罪。但笔者并不支持运用但书来出罪,因为刑法分则条文在制定时就受到了但书的约束,但书的作用更多的是立法上的指导,那些显著轻微的行为在立法时就被排除了,不会成为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如果一个行为本身已经符合刑法分则的犯罪构成,再用但书来出罪,是严重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逻辑的。但是要注意,扒窃入刑,对行为客观上虽然没有数额、具体情节、手段的要求,但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扒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所以,行为人客观上窃取的财物极少,主观上又没有窃取较大财物的故意,是不构成盗窃罪的,也就不存在如何出罪的问题了。而对于那些初犯、偶犯、少年犯或存在被胁迫、被控制等情形的可以改造的行为人实施的扒窃的未遂和窃取的财物极少的行为,应综合犯罪的事实、情节和数额、悔罪表现、认罪态度等多方面因素判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视具体情况做定罪免刑、缓刑、减刑等合理处理,使刑罚最大限度发挥其预防和矫正犯罪的作用。
六、结论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盗窃罪就有了五种类型的盗窃行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单独作为盗窃行为的一种,“扒窃入刑”是没有数额、次数和手段的限制的,但是在认定扒窃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公共场所”和“随身携带”的内涵。“扒窃入刑”并没有对盗窃的既遂标准构成较大冲击,反而使得未遂的扒窃行为得到刑法的规范,这为实践中打击未遂的扒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公检法机关必须准确把握“扒窃”内涵,统一执法尺度以消解“扒窃入刑”的各个争议,使得“扒窃入刑”确实有利于打击扒窃犯罪,保护人身财产权,维护社会秩序,提高社会安全感。
[1]高铭暄,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与思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9.
[2]周婷玉等.拟明确“扒窃”行为入罪[N].北京日报.2010-12-21(2).
[3]李振林.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 39条的规定为视角[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3).
[4]陈平.对扒窃入罪的理性思考[J].政法论坛.2011,(15).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1014.
[6]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7]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8]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7.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
[10]陈家林.论刑法中的扒窃——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与解读[J].法律科学.2011,(4).
[11]阮齐林.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616. [12]于志刚.“风险刑法”不可行[J].法商研究,2011,(4).
[13]曲新久.醉驾不一律入罪无需依赖于“但书”的适用[J].法学,2011,(7).
[14]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91-192.
Resolution of Several Disputes about“Pick-pocketing Crime”
LI Jing-fen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China,100088)
The reason of writing pick-pocketing crime into criminal law is mainly because of its special hazards.Pickpocketing crime break through the ideas that larceny conviction is usually based on th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and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tandards of pick-pocketing crime from the two following aspects:objectively,there is not limits as to the amount of money,the times and the means of stealing;subjectively,there must have a purpose to steal larger public or private property.The standard of accomplishment of the pick-pocketing crime and general larceny is similar,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re are penalty for theft even though the pick-pocketing crime is not accomplished.In short,the provisions about pick-pocketing crime in“Criminal Law Amendment(eight)”did break the dilemma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against pickpockets.
pick-pocketing;pick-pocketing crime;public place;portable
D924.35
A
2095-1140(2012)02-0099-06
2012-02-25
李竟芬(1987-),女,湖南宁乡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刑法研究。
叶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