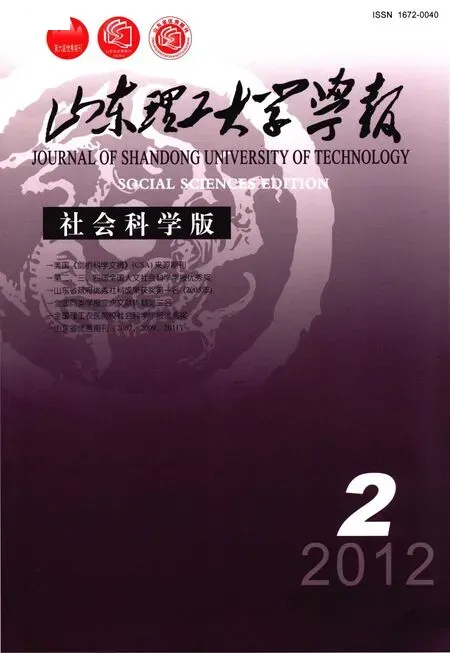中国当代先锋戏剧语言比较研究——以20世纪80与90年代比较为例
胡志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返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戏剧语言,大量流行的文学语言掺杂着浓厚的政治宣传说教成分的解说和说理,还有不少语言离生活本相甚远且缺乏审美的意味,而给人以明显“假、大、空”的感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时期,它严重地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先锋戏剧发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门户开放后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以及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失落,故80年代先锋戏剧的主旨在于引进西方现代主义以“重建”戏剧发展道路。80年代前中期阶段的先锋戏剧语言中,对个体的生存关注、情感婚姻关注,体现了一定的人性关怀。但从总体上说,先锋戏剧语言仍然保持着浓重的文人或精英人物的语调,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语言修辞是严肃的、有雅化倾向。
一、8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语言:严肃修辞和雅化倾向
新时期戏剧引起第一场轰动的《屋外有热流》,所发出的“回来吧,弟弟、妹妹们的灵魂”振聋发聩,在新时期的戏剧中具有不可磨灭的特殊意义,但它的语言仍然一如既往地沿用了严肃的政治说教的理性套路。
你们既然睁大眼睛看得那么仔细,为什么坐着一动不动?不吭一声?我们不应该在责备生活中生活下去啊!噢,我看出来,你们在思索,在痛苦,和我一样在呼唤,在寻求:回来吧,那发光发热有生命的灵魂!
〔仿佛呼应一样,从空间、从四面八方传来男女老少的声音:“你们缺少热量,还不冷静想一想吗?你们没有热量,还不冷静想一想吗?你们失去热量,还不冷静想一想吗?”〕
这种语言,和教导员口中的政治说教式语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以一个先知的、领导的、高尚者的身份,语重心长地言说落后的消极的冷淡的人生态度是多么可怕,应该立即摒弃这种错误的低级的观念,重新回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你们看,走出屋外,站在高处,和人民在一起,你们就不会冷;只要为国家,为大家做点事,你们就会有热量。
这和当时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以及日常政治生活中流行的语言结构以及逻辑都很相似,将事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教育弟弟妹妹向政治的、人民的高度看齐。当然叙述人并非真正有意“扣帽子”,政治思维的惯性和审美的迷失,使得他有意无意地将政治性话语穿插到语言中。这种政治话语的无意识嵌入,使得戏剧语言增加了严肃性、失去诸多韵味,遮蔽掉戏剧语言的丰富和鲜活。
在《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探索戏剧选萃》的序言中,编者讲,“新时期的文学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理解所指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态度,而从说话者和社会思潮的关系来看,在总结80年代先锋戏剧的发展时,说话者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政治术语,从隐含的一面可以看出,戏剧语言与社会语言的密切联系。
中国80年代先锋戏剧中前期,戏剧语言中渗透着国家和集体的意识,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红色词语出现频繁,“你”的教导性词语出现,正体现出这种浓重的精英立场上的教育姿态。
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语境中,精英文化从主流政治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寻根文学”的出现,昭示了精英文学摆脱依附性的趋势。无论寻根寻的是“优根”还是“劣根”,都是对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突破。[1]37几乎与“寻根文学”同时并存的“先锋实验文学”——先是刘索拉、陈村,后是马原、格非、余华、苏童,他们极度张扬个性自我,调侃“意义世界”及其寻找的努力,其实内中也包含了对主流文学崇尚的理想道德的深刻怀疑和消解的成分。精英文学一旦打出“先锋性”、“实验性”的旗号,就意味着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大众话语的脱离,变成了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进行“大众化”的、自言自语的话语。这种趋势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先锋戏剧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作为80年代先锋文学一支的先锋戏剧文本语言,在80年代前中期更多继承了五四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传统,担负起启蒙任务,充满理想主义的崇高精神;80年代后期出现了先锋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分离,修辞中随之出现了90年代先锋戏剧的戏谑和庸俗化倾向。
二、中国90年代先锋戏剧语言:戏谑修辞和庸俗化倾向
中国90年代先锋戏剧语言,在修辞词汇和语言技巧方面表现出庸俗化和戏谑化的突出特征。修饰词汇庸俗化表现在污言秽语、身体语言和俗话题的大量出现,甚至语言描写有审丑癖倾向;技巧的戏谑化、游戏化,体现在对抗与颠覆、极度夸张、混杂与拼贴等方面。
(一)修饰词汇庸俗化
在以往的戏剧语言中,本着真善美的原则,相应地出现了一种共识,即剔丑扬美、去恶扬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要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2]483戏剧语言也在这种共识指导下,形成了葱郁的诗意。
而在90年代的先锋戏剧中,垃圾、厕所、臭虫、屁、生殖器、尸体、凶杀、死亡等丑陋的意象进入戏剧语言中,并且出现得那样自然顺畅、仿佛戏剧语言的“自我”冲破了“超我”的束缚,“本我”呈现出完全自然、原始化的本相,携带着充溢丑陋的意象冲破束缚,肆意释放着狂欢化的快意。如同巴赫金在解释狂欢式的“粗鄙”范畴时所言:“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等。[3]177
90年代中国先锋戏剧在语言组合上呈现的审丑化,包括宣泄式的污言秽语、与人体的生殖能力相关的身体语言、以及诸多的俗话题。
90年代先锋戏剧剧作中,“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你丫出来!孙子!你出来!姓无的!”这一类骂人的粗口俯首即是;“金刚金刚转转,拉屎让我看看”,“猪吃我屎、我猪吃屎”等脏话更是见怪不怪。《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以众人齐说“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展开戏剧的第一部分——“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崩到了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了这个屁,很不满意”。低俗的开场白,一下子将观众内心中对舞台的神殿形象预期摧毁,落入到低俗、甚至相当不文明的生活中。
90年代先锋戏剧的私人化袒露,可以说比80年代更为大胆。在80年代的《WM》中,有很隐讳的经期中女性身体不适、心情焦躁的舞台表现;而在90年代中,身体用语已经如同家常便饭,成为一种完全私人的公开表达。
《我爱×××》中,“我”的爱成为一种泛爱,爱某某事件,爱某某时间,也爱身体——“我爱你的肺的海绵体/我爱你的腰/我爱你的胃/我爱你喷香而干净的肠子/我爱你的肚子/我爱你的脊椎/我爱你的尾椎/我爱你的臀部你美丽的半圆”。《思凡》中本应在庙里安心念佛的小和尚偷下山来,见到了同时逃出尼姑庵的尼姑,萌生出“将她搂抱在山凹,管取一场戏弄”的想法。《恋爱的犀牛》中,众人的歌队语言齐声说起,“我是强壮的黑犀牛/我的皮有一寸厚/最喜欢的地方是烂泥塘/我那玩意有一尺长/……我是性感的母犀牛/我的角用来做春药/远近闻名的大波妹/我们的爱情是天仙配”;推销牙刷者喊,“早晨刷牙出门体面,晚上刷牙刺激性欲”,以宣传牙刷的特别身体功能。
肠子、肚子、臀部、下体、春药、性等与身体相关的语言,彻底从80年代前期的“心与灵”转变成为“下半身”,人的身体存在所具备的社会性质、道德性质,通通被剥离,完全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的身体本身、肉体欲望本身。
俗话题的出现,则不仅仅是一两个词语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个问题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和谈论的范围。对俗话题的乐此不疲和津津乐道,同样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庸俗性。《与艾滋有关》中,演员在不是舞台的舞台上“做他们自己的事,说他们自己的话,展示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4]随意言说着文革、性、艾滋病,每一次的表演都没有一定的模式和话语,但对性的言说总是乐此不疲;《坏话一条街》中,神秘人对要跟随自己的耳聪提出的要求,荒诞又低俗:
神秘人:是处女吗?
耳聪:这有什么关系?
神秘人:真正的土匪只要处女。
耳聪:我刚在上海做的再造手术。
神秘人:那就行了,无非是面子上的事情,土匪没有不要面子的。
这些污言、身体语言以及俗话题等审丑语言实验,一方面,丰富了戏剧文学语言的多样性、复杂性、开放性和非规范性;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审丑倾向过犹不及,就又会使戏剧语言的功能价值从丰富多样滑向简单划一,那就值得人们注意了。
(二)语言修辞游戏化
语言修辞方面语言组合的庸俗化,呈现出游戏化、戏谑化倾向。戏剧语言通过采用多种语言游戏的手法,包括对抗与颠覆、极度夸张、混杂与拼贴、无意义重复,去达到嘲讽、戏谑、反讽的目的,和充斥大量俗文字、丑文字的戏剧修辞话语相匹配。
对抗与颠覆可以说是先锋戏剧的品格,就语言修辞手法方面,实际是对通常意义上的常规话语的对抗和颠覆。具体说,有如下几种表现:个人语言的自我矛盾与无意义的重复;降格与升格,语法上悖反常规、常识、常理以及既定的价值观念,不循陈规习俗到亵渎的程度;混杂与拼贴体现出的后现代品格。
1.个人语言多自我矛盾与无意义的重复。
《非常麻将》中四儿对三儿和老大的真面目进行了激愤地分析和批判,认为他们是懦夫,并揭示了他们内心的黑点。
四儿:你们怕与活人打交道,你们怕看见那些表情丰富、奇怪庄严的面孔,你们怕与那些活蹦乱跳、张牙舞爪的活人打交道。你们只喜欢品尝一切都在想象中的生活,十三张牌就像十三个人在你们面前站着、摆着,你们喜欢把它摆来摆去,拼装组合,以满足你们自己的欲望和占有。所以你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
四儿接下来的行为,按审美期待应当是在和三儿、老大的辩论下,义正严词地表明自己要离开麻将的决心,以证明自己比三儿和老大都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原来四儿也是个没本事的人,没出息的人,也还是离不了麻将。
四儿:我不离开这个屋子,……我就在这等二哥,我那儿也不去。我要在这实现我的理想。打完最后一局牌。
在《三姐妹·等待戈多》中有相当大的语言篇幅是在进行无意义的重复,“咱们既然很快活,那咱们得干点什么?/咱们在等待戈多。……咱们走吧!/咱们不能!咱们在等待戈多!……有人在喊救命,我们去帮帮他!/我们不能!我们在等待戈多!”。“等待戈多”重复出现,将所有事情的原委都归结到等待,突出戏剧对生活无意义和荒诞的表现。
部分语言的重复,导向认知和理解的混乱。重复的一个常用的方式,是一个固定词句在一出戏中反复出现,就像是音乐中的主旋律不断反复一样。重复性对白还能够加强戏剧紧张气氛,表现人物情绪的逐渐激动,直到极限。《雨过天晴》中,关于“干什么”的一问一答,杂乱拗口,甚至最后连言语者都不晓得所云何事何物,无意义的语言增强了戏剧所反映的现实的无意义感。
读书人B:你不要干什么,又没有想干什么,那你在干什么?
某男:我没有干什么。
读书人B:你没有干什么那你在干什么?
某男:……什么什么什么。
…………
某男:是什么,是什么。我不是什么。我是什么。不,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学习;学习是什么;看书是什么;椅子是什么;桌子是什么;灯是什么;天是什么;地是什么;海是什么;走路是什么;你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剧场是什么;观众是什么;脸是什么;呼吸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我……我谁也没说,我什么也没什么,我说我自己。对,我自己,我自己。嘿!……〔静场〕。
如此的词不达意和重复“什么”,实际和贝克特《等待戈多》的“我们在等待戈多”如出一辙。这样一种语言策略,体现出语言已经很难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同时,通过语言也已经找不到解决人类生存苦恼的办法。语言作为戏剧表现的重要工具,先锋戏剧即通过杂乱无序的文字、无意义的无休止的重复去努力表达那些无法表达清晰的对世界的理解。
2.升格与降格。
语言修辞方面的一系列的“狂欢式”,是通过一系列的错位达到效果的。这种错位包括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崇高”转成为“卑俗”的降格;一种是将“卑俗”转成为“崇高”的升格。这两种方式又都体现出夸张的特征。
语言修辞上的降格,同巴赫金所言“俯就”同出一辙,“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团结起来,订下婚约,结成一体”。[3]177降格巧妙地通过语言变形,沟通崇高与鄙俗的联系,使“崇高”者降格而为“卑俗”者。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转到肉体上去;或一个人却给我们以物的形象,从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大写”的人转到“反英雄”的“小写”的人;从美本位转到丑本位等。这都可以称之为降格。
先锋戏剧语言随着80年代以来对红色语言的逐渐脱离,在90年代走到了政治红色语言的反面,红色语言成为可以玩味的猎物,失去了红色的庄严与正统感,波普手法在不少90先锋戏剧语言中得以应用。
波普①栗宪庭认为:“政治波普,系指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陆续并普遍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艺术潮流。这个潮流借用波普样式,多在对西方商业符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形象的处理中,以呈现某种幽默与荒诞的意味。”见文章《政治波普——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收于《今日先锋》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是英文POP的音译词,波普艺术利用两种以上的现成艺术品为材料,加以组装和拼接,以达到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效果。政治波普经典作品《列宁可口可乐》,成功地利用了反讽修辞,实现了对政治乌托邦主义和商品消费主义的双重讽喻和戏谑化,同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解构的机制。这种批判性机制的建立,正是波普艺术魅力的来源。
鲁迅的“吃人”两字从《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道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二字,借疯子之口讲出历史的真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残酷本质的概括可以说是力透纸背。而在90年代先锋戏剧中,当我们再一次亲密接触“吃人”时,它已经完全面目全非。
《我爱×××》中,鲁迅的“吃人”一说成为无意义可谈、无力度可感的“集体舞”。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集体舞”
《雨过天晴》中,演员某男和女扮男装的商人讨论,将“吃人”替换成为骂人的语言——
某男:虽然每天背的词不一样,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说得再多,只有两个字……
商人:翻开几千年的履历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只有两个字……
某男:什么字?
商人:吃人。
某男:错了。
商人:那是什么?
某男:傻B。
由对封建社会批判入骨的“吃人”成为“集体舞”、用现在社会中流行的骂人语“傻B”置换“吃人”,此类语言以接受者忍俊不禁收场。原本“吃人”所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在这类语言中已经荡然无存,徒增了一种荒诞感、滑稽感。波普手法恰恰是利用这种强烈对比、反差,将红色、政治、经典、正统等所附着的光环一律剥掉,并且将它们刷上不和谐、滑稽的颜色重新出场,在接受者的笑中给予解构和颠覆。
升格,则是将“卑俗”升格成为“崇高”,将常人心目中卑微的甚至不值一提的事物或者现象,推崇为自己心目中的神、理想甚至毕生追求。在《棋人》和《非常麻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类精神的人,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简单活动赋予无限大的意义,下围棋、打麻将成为了生命的意义、世界的意义,棋停人亡,甚至还给这个活动增添无限的人生哲理和含蕴。
“围棋为什么是一门艺术?”“因为围棋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才是艺术”。“棋盘在我的灵魂里”。“棋子的黑白两色像是阴阳两界,这四个角像是春夏秋冬一样。……你活了才能往复,不让别人活就会鱼死网破。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旦失去平衡就翻了天”。这是棋人对围棋的推崇,除了会下棋什么别的也不会。何云清同司炎下完最后一盘棋后,司炎以失败和死亡告终,“我死了,终于和我父亲一样成了一个游魂了,我终于自由了”。棋成为生命的依据和支持,除了表现人物的病态心理之外,同时也是将棋的意义极度升格。
《非常麻将》中,老大对麻将的理解更加出神,普通的麻将牌在他和老二、老三等人的心中是神、是无冕之王。
老大:麻将有一百四十四张牌,一百四十四张牌张张可成“将”,一百四十四张牌张张可成“佛”,所以真正准确地应该是叫“佛了”。十三张牌,必须有“将”才能“佛”,换句话说,要想成“佛”,你手里即心里必须要有“将”,无“将”钓“将”方成“佛”。就是说无“将”不成“佛”,成“佛”必有“将”。佛家语:佛无处不在,我佛即我身,我心即我佛,犹如大千世界人人可成佛。麻将亦是如此。一百四十四张牌张张可成“佛”。
老大用深奥的哲学语言解释打麻将通常用的“胡了”,将胡了说成是对成佛的一种愿望表达——“佛了”。
降格和升格都有一定夸张性,将内涵夸小或者夸大的同时,达到颠覆和瓦解的目的。运用夸张来达到喜剧效果,在接受者看到“变形”后以瓦解性的笑复之。
3.混杂与拼贴。
后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被人们称为“工业文化”,具有标准化、复制性、大批量的生产特征。在90年代先锋戏剧中,语言手法的游戏化和大众文化的特质有关联,语言的混杂与拼贴体现出强烈的复制性。混杂是将乍一看似乎完全相异的事物拉扯在一起,其形成的倒错与乖讹,使人感到怪诞离奇。混杂与拼贴,如同工业时代电影制作中的剪辑加拼贴,将有蛛丝马迹联系的两三种甚至更多的语言混杂、拼贴,将故事情节剪辑和拼贴。
混杂与拼贴,小到词语的置换、句子的经典套用,大到故事的拼贴、情节的穿插。前者如《我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有对多种文学作品中语句的拼贴和混杂;后者如《三姐妹·等待戈多》、《思凡·双下山》、《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都使用了剪辑、混杂和拼贴故事结构的手法,将两个故事拼贴、穿插在一起。
《我爱×××》中,对《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雨巷》、《荷塘月色》、《论语》等正统文学经典的经典语句,进行了工业化的剪辑、混杂与拼贴。
中国,我的集体舞丢了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集体舞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集体舞
子曰:三人行,必有集体舞
梁小斌、戴望舒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孔子的哲理等经典语句中所包含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等主题,都在句式套用、混合后被解构和摧毁。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跟警花楼上看风景,想再下楼看楼上看风景的警花”,套用了卞之琳《断章》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结构;“德国的瓶儿,英国的奶,两个强国伺候我一个人,这福分还浅吗?”套用了《茶馆》中的经典对话。
将不同戏剧出处的故事和情节,围绕一个相关点揉在一起,是90年代先锋戏剧混杂与拼贴手法最为常用的一种形式。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不同,戏剧语言呈现出多声部现象,语言面貌也呈现出不同风格、多种形式的穿插,使得语言显得纷繁。
《棋人》的语言由两部分语言重合与穿插而成:一是围棋高手何云清和他的棋友、司慧、司炎的对话;二是大量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场景对话,如消防检查、安全检查时的对话。
《三姐妹·等待戈多》把俄国戏剧《三姐妹》和法国荒诞戏剧《等待戈多》以等待的生命母题名义,拼合在一起。这样不仅形成了同一主题——“等待”下不同人物的人生选择,——或者无休止地“我们在等待戈多”,或者喊着“到莫斯科去”,而且形成了多声部的效果。人物在戏剧演出中穿梭、交互使用,人物的语言也在两个剧本中穿插。
《思凡》将中国明朝无名氏传本《思凡·双下山》及意大利薄伽丘《十日谈》有关章节拼贴起来,分成四部,不分场次,连贯演出。一头一尾是中国传统戏的故事:仙桃庵内小尼姑色空度日如年不忍寂寞,思恋凡间生活,碧桃寺的小和尚本无也不堪忍受谨遵五戒,逃下山来——小尼姑色空和小和尚本无在下山路上相遇,在萌动的爱意和情欲驱使下双双返俗,成了“披红结彩的一对新人”;在《思凡》和《双下山》两部分中间插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两个故事:两个青年皮奴乔和阿德连诺在老实人家过夜,半夜里皮奴乔和主人的女儿尼可罗莎私会,女主妇错把阿德连诺当作自己丈夫,偷情的事实险些被男主人发现,众人一起扯谎总算蒙骗过去——暗恋王后的马夫,学国王的举动占了王后的便宜,为逃脱惩罚给其他的侍臣都剪去一把头发,国王无奈没有证据捉拿罪人,只得说“下次,就别再……干啦!”作家以人的自然“欲望”为纽带将四部分内容拼贴组合在一起。
1995年孟京辉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合作,根据德国剧作家乔治·毕希纳的作品改编并导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就是将中国现代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德国剧作家格乔治·毕希纳的经典名剧《沃伊采克》拼贴在一起。而且,还遵从《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的感觉,先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办公楼前演出,然后才回到室内继续演出《沃伊采克》。
先锋戏剧语言通过故事的拼贴和经典作品语言的恶意修改和拼贴,一方面做得好,可以在故事情节的相互注解和阐释中,实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特殊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很容易出现语言的混乱,造成接受的困难。
尽管庸俗化带来的戏剧语言词汇,较以往语言的使用更加多样化,美的丑的、善的恶的、纯的脏的都集于一堂,走的是80年代文字的高尚化、精英化、人文化的反方向,但庸俗化倾向照此发展,必难逃媚俗、世俗、趣味低下的困扰,这是不利于先锋戏剧继续发展的。修辞手法上的游戏化、戏谑化,是对经典结构、正统修辞的解构和反叛,也同样增加了修辞功能的多样性,但要把握好尺度、掌握好结合点还需要不断地尝试和探索。形式上的突破,还应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相结合,毕竟以旧瓶装新酒总不是长久之计,也不会走得很远。
[1]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俄]M.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牟森.写在戏剧节目单上[J].艺术世界,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