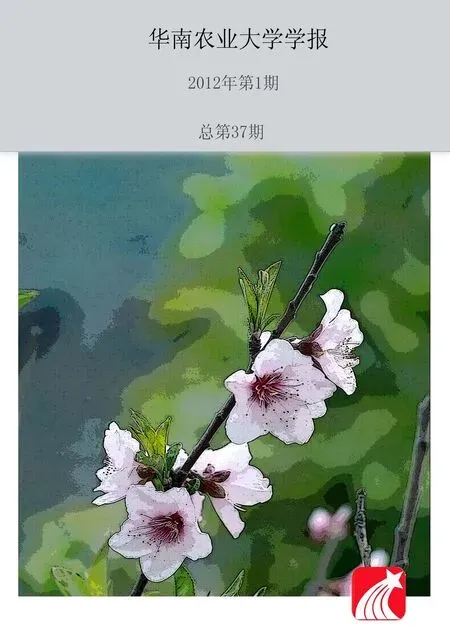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透视
罗衍军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日益受到中外学界关注(中国近现代的时段划分,是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将1840—1949年划为中国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为现代[1])。笔者在此以三种西方代表性的中国研究期刊《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为中心,透视20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乡村研究,以期对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中国研究》(半年刊),原名《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年创刊,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自1995年7月起改名为《中国研究》;《中国季刊》1960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联盟出资创办,1968年起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编辑,现任主编为朱莉(Julia Strauss);《近现代中国》(季刊),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于1975年创刊,自2009年起改为双月刊。上述三种英文期刊为西方研究近现代中国的代表性刊物,在2008年发布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分类排序中,分列区域研究类期刊第一、二、四位,所刊文稿充分反映了国际学界中国研究的主流观点。据笔者初步统计,1990—2010年间三种期刊共刊载有关中国近现代乡村的论文200余篇,研究的领域较为广泛,研究范式亦发生了明显转换。
一
在研究领域方面,20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的研究,从过去集中于乡村民变、乡村革命、乡村改革拓展到乡村日常生活、乡村妇女、乡村人际关系等更多领域。
(一)革命运动、社会治理与乡村社会变迁
革命运动、社会治理与乡村社会变迁向来是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1990年以来这一领域受到一些学者的持续关注。
萧邦奇(R. Keith Schoppa)以1910—1930年代浙江杭州湾地区的农民垦荒为个案,探析国家、社会、民众三者互动关系,认为民国政府虽加强了现代化新机构的建设,但这些机构任意、威逼式的统治手段却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2]246-271。周锡瑞通过对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年共产主义革命历程的阐述,指出乡村革命乃是党的不同层面以及党和社会不同力量间不断互动的嬗变过程[3]。吴应銧以河南“杜八联”抗日组织为考察中心,阐述传统伦理、人际网络、文化资源等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4]。朱爱岚从对中共边区民间艺人的考察透视革命运动对乡村文化的重塑[5]。洪长泰通过描述中共及其知识分子对以延安盲书匠韩起祥等为代表的民间艺人的改造历程,阐释中共对民间文艺的重塑主要基于其政治宣传功用而非文艺本身,指出在中共对民间文艺的改造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张力[6]。
在中共革命逻辑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剖析。黄宗智考察了从根据地土改到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阶层分层的构想及乡村阶层的真实表达,指出在革命过程中,乡村社会的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了文革中的灾难性后果[7]105-143。刘瑜的研究则聚焦于中共的革命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如何激发革命情感,她将革命言说划分为三项主题:苦难主题、赎罪主题、解放主题,探究不同主题的内容、对象及运行策略[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级政府在乡村的政治、法律、文化运作,政府与基层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日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史林通过对安徽一个乡村县城的政治策略的阐述,阐明在地方干部选拔和评价方面,如欠缺公民的参与,良好的政治运行是难以实现的[9]。麦宜生对当代乡村纠纷的解决策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对申诉者更多通过上层而非基层获得依靠和补偿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对乡村民众而言,通过基层方式(经常包括村庄领导人)解决纠纷远比上层方式更能获得认同和更有效果,这既源于向上层申诉通常即意味着基层解决的失效,故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下层相较而言,通过上层方式的成功率较低;同时亦在于与城市相比,乡村民众更重视维护人际关系,不愿进行法律解决而倾向于经由非正式途径协调解决纠纷[10]。黄宗智基于所收集的乡村民事案件档案资料,系统考察了当代中国离婚法实践的起源、虚构和现实,指出离婚法实践中的毛主义调解和好或许是最具特色和启迪作用的,调解和好所运用的毛主义调解诞生于一段独特的离婚法实践的历史,那些实践融合了多种要素,涵盖了一系列的实践和观念:它运用道德劝诫、物质刺激,以及党——政国家和法院的强制压力来压制单方面请求的离婚;其构造性的观念是感情,视夫妻感情为婚姻和离婚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其实践逻辑是既要结束没有良好感情的旧式婚姻,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有良好感情基础的新式婚姻[11]151-203。张卫国对计划生育政策在现代中国的实施与影响进行了个案剖析,认为乡村计划生育状况的演变取决于农民、村干部、县乡镇干部的多边互动,在执行具体计生措施时,村干部要维护与村民的关系,村民亦与村干部形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不同家庭应对计生措施的方法和效果亦各有不同;对上级政策,村干部亦有其应对之策,并不完全执行上级的规章[12]。邝泽倩从中国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的视角,对北京地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分析,认为面对政府的压制取缔,学校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与一些政府官员和单位搞好关系,并借助公众和媒体的力量,取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些学校的存在发展,显示了市民社会的成长[13]。
1949年后,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文化重塑,亦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重视。曹诗弟通过对云南某县的田野考察,剖析基层政权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中对乡村文化的引导和控制[14]。穆葛乐描述了云南楚雄彝族“赛装节”的演变历程,在集体化时代,少数民族往往代表着处于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落后阶段,他们的许多文化实践象征着落后与迷信,在改革开放后,这些文化实践则被赋予了“少数民族传统”的新形象。对“赛装节”演变过程的考察,正阐明了国家通过对传统节日的长期改造以重塑地方社会的努力[15]。
(二)乡村改革与民众生活
中国于1970年代后期开启的乡村社会新变革对乡村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过程中出现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民工潮”现象,这些都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重视。
有学者对1970年代末起的乡村改革历程进行回顾,指出目前乡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难以充分调动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热情,频繁的土地调整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有机肥的施用也因之减少[16]。但龚启圣、蔡永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通过对乡村有机肥施用的实证考察,认为改革开放后有机肥的绝对施用量并未减少,只是在全部肥料中的比重降低,此种相对减少并非缘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周期性分配,而是化肥广泛应用、劳动力价值提高等农业自身发展因素所造成[17]。
罗伯特·阿什分析了1950—1970年代乡村农业生产与粮食消费问题,认为国家的汲取严重阻碍了农民生活的改善,乡村发展的停滞成为1970年代末乡村改革的重要推动力[18]。阎云翔以黑龙江省下岬村为研究个案,剖析改革开放对乡村社会分层的影响,阐明改革开放减少了原来潜藏于村庄内部的不平等,乡村下层因之受益[19]。班乃迪克·J·克弗列特和马克·赛尔登比较了自1945起的中越农业转型,认为中越两国都经历了两种农业转型过程:1945—1970年代末的土地分配和集体化过程、1970年代末之后的的土地承包和乡村企业发展过程,并就两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20]。
白威廉和折晓叶等通过抽样调查和个体访谈,探究农民的非农工作与乡村市场化的内在关联[21]。对外出务工者的主体,原来观点认为他们多系文化程度较低的“盲流”,或认为他们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精英。近年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均提出质疑,认为乡村的外出务工者既非乡村下层亦非乡村上层,而是那些文化程度中等者[22]。
(三)乡村农产品加工业与乡村市场
中国近现代乡村的农产品加工、手工业等的发展演变是在外部刺激和内部社会制度、经济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并因所处时空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面相。艾仁民考察了19世纪台湾蔗糖制造业的变迁,认为传统造糖工艺在新的造糖技艺的冲击下逐渐萎缩以致消失[23]。雅克布探讨了1935—1978年四川夹江县乡村手工业的演化,描述集体化时代乡村手工业的衰落,透视改革开放后政府支持力度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阐明对地理位置不利区域发展路径的压制加重了区域间的不平等[24]53-73。苏珊以对四川红薯加工业的考察为中心,探讨“龙头企业”、“乡村合作社”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的影响: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工作机会的同时仍存在着进入障碍和不平等的交易权、利润分配等问题[25]。罗思高等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国乡村集市向现代超市的演变,认为改革开放后乡村定期集市活动未能如施坚雅所预测的下降,其深层缘由乃是税收政策、土地规章、资金短缺等制度性因素制约了定期集市向长期市场的转变[26]。
(四)乡村妇女研究
伴随着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的剧烈嬗变,乡村女性的状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乡村妇女的研究因之日益受到西方学界重视。夏明德对近代妇女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近代乡村妇女更多卷入劳动的现象并不必然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而是与家庭生存压力加大、人口增长和乡村商业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妇女劳动与否、从事何种劳动的选择权较为有限;男性控制了近代棉纺、蚕桑等的生产、销售过程,妇女赚取的资金通常由丈夫掌管,妇女自身却难以掌控;乡村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男性更易于离开家庭从事非农业生产,妇女被局限于家庭种植和生育,收入远低于男性;涌入城市的乡村妇女,往往自身的保护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伤害[27]180-210。弋玫以档案资料和在河南、江苏两省的调查访谈为中心,描述大跃进时期中央和妇联的马克思女权观念与一些基层妇女领导者的革命平等主义妇女观的差异,指出一些基层女性领导者以牺牲妇女自身健康来动员妇女从事农业生产,以在生产中的贡献大小衡量女性的价值而非依据女性生理等原因而给予必要照顾,这与这些女性领导者的出身、家庭、人际网络、所受政治教育等密切相关[28]。
温苑芳通过对一个移民社区女性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地位、生活变迁的考察,揭示改革开放后女性所面临的生活满足感增强与现实中仍遭遇歧视的矛盾处境[29]。帕特里克等从对两个乡村区域的实证研究入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女性所采取的两种策略:从经济利益优先的考虑出发,号召妇女回归家庭,延误甚至损害女性地位;将妇女地位的提升视为社会整体目标的一部分,高度赞扬女性的贡献,促进男女地位的完全平等[30]。王梦惠通过对泸沽湖畔一个村庄的研究,探析旅游活动对摩梭文化生活、两性关系的影响,揭示在此过程中女性生活和地位的变化[31]。
(五)乡村家庭与人际关系研究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乡村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亦发生了重要嬗变,对此西方学界亦给予了一定关注。黄树民以对一个华南村庄——福建林村的个案考察,探析建国后家庭类型的演变[32]25-38。孔迈隆则对1949年后大陆与台湾乡村的分家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33]。任柯安和阎云翔分别以山东邹平冯家村和黑龙江下岬村为研究个案,探讨乡村实践中的社会关系运作过程。任柯安重点探讨乡村中的礼品交往关系,认为乡村礼品交往奉行“怎来怎往”原则,礼物的给予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4]。阎云翔的研究则重在阐明由礼物交换所建构的乡村人际关系具有的社会支持功能和政治功能[35]。斯科特·威尔森分析了上海郊区一村庄的金钱交往和人际关系,指出其社会交往已金钱化,金钱逐步取代非现金礼物和劳动,人际关系亦逐步超越村庄甚至城镇界限。村民还情多比别人的给予更多,这与任所描述的“怎来怎往”显然不同。村民的跨村社会交往,亦较阎的描述更具工业化和市场化特征[36]。
二
20年来西方学术界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具有如下鲜明的趋向。
其一,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从“有事件”到“无事件”。以往西方学界的主流研究路径为采用由上而下的视角,聚焦于对乡村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阐述,重在描述各类政权的乡村政策、政权成员在乡村的活动及乡村民变事件等,至于乡村普通民众在时代变迁中的具体思想和行动则多欠缺深入的探究。1990年以来,西方学界日益重视对普通乡村民众的研究,将近现代乡村政治、经济等的变迁历程与民众的具体行为、观念变革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重在阐释二者的多元互动。其研究视角由从上而下描述乡村、将乡村自身演变看成国家和社会宏观演变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自下而上阐释乡村,深入透视乡村经济状况、民众生活、观念嬗变、村落文化等以往视为“无事件”的乡村面相,以之完善、质疑甚至重构以往的宏大叙事结构。普通民众由素来漠然无声的“被述者”转变为鲜活历史的“讲述者”,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如萧邦奇以1910—1930年代浙江杭州湾地区的农民垦荒事件为个案,从区域视角透视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2]246-271;雅克布从1935—1978年四川夹江县乡村手工业的演化历程透析集体化时期同一国家政策对不同微观区域所造成的不同影响[24]53-73等研究论文,即反应了此种转换。
其二,连结经验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自二战后至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经历了由“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趋向的转换历程,前者主要包括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和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强调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作用,后者以施坚雅、柯文等为代表,突出强调中国在自身发展演变中的主体性,注重从区域个案研究中探寻中国社会演进的动力和诸相关因素。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中国研究则愈益趋向于以黄宗智的连接经验与理论、从实践出发认识中国社会的研究范式。黄氏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在中国经济社会史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研究中所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和一系列悖论现象,倡导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37]。他此后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中国研究必须超越西方化和本土化、理论和经验的两种对立,连结经验和理论,将学术理论置入具体的社会和历史之中进行检验,走向从实践出发的对近现代中国的重新书写[38-39]。《近现代中国》在1990年代专门刊出4期论文专号(1993年第1期、1993年第2期、1995年第1期、1998年第2期),刊载黄宗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周锡瑞等学者的文章研讨“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其中1993年第2期“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和1998年第2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专辑的中文版由黄宗智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3年以《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的书名出版)。就黄宗智本人而言,其研究兴趣经历了1970年代前期的梁启超与晚清思潮研究、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革命研究至1980年代的中国近代农民经济与乡村发展研究、直至1990年之后的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等互动关系研究的嬗变过程,从中可看出其研究中心主要在于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并且愈益注重对一手档案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运用,从纷乱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过密化”、“内卷化”、“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等学术理论,力图从中透视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演化的内在规律,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7]105-143、《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11]151-203等研究论文便是其乡村研究范式转换的典型例证。以黄氏为代表的从乡村实践出发的新型研究范式在20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中显居主导地位,学者大都通过对乡村客观实际的深入考察,由微观诠释透视宏观变迁,完善甚或改写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理论。专著有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论文有黄树民《对中国乡村社会大家庭的重新审视:一个福建村庄的发现》[32]25-38、夏明德《更好,更坏:中国乡村妇女和世界市场》[27]180-210等。
其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因更多档案资料的开放、统计数据获取的便利及田野考察机会的增加,使得西方学界的中国乡村日益建立在翔实的史料之上。因之,在研究中,学界愈益重视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在西方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研究领域中,集合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如黄宗智、周锡瑞等历史学者,阎云翔、萧凤霞等社会学、人类学者,萧邦奇、弗里曼等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学者们并非拘于一隅,而是注意将各学科的优长糅合融汇。他们将历史学的重视挖掘原始文献、社会学的重视实地调查、政治学的注意理论阐释等学科特色方法有机结合,从而大大丰富了相关史料,深化了对乡村社会的阐释力度。
当然,在西方学界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需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是多只进行某一时段的研究,未能从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进行纵深考察,如能更重视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将1949年前后的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考察,深入探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嬗变轨迹,当更为全面。二是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还有待深入。已有研究多是对某一乡村场域的个案考察,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广大内陆乡村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近现代中国乡村研究无疑需要更广阔的区域视野,如何在区域社会研究中赋予总体性关注,仍是学界此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三是囿于原始档案资料的限制,对乡村革命运行、集体化时期民众经济文化生活等的考察还有待深入。
三
对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国内学界给予了相当关注,如对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国内学界给予了详细介绍,《史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研究》等期刊并就黄氏的理论组织了专门学术研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等学术期刊直接刊发或转载了多篇黄宗智、杜赞奇、裴宜理、阎云翔等学者的乡村研究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学界的乡村研究,但对于西方学界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其它大部分学者及其成果,国内学界的了解尚不深入。同时,一批社会史研究和乡村研究机构亦在国内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如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乡村研究所等。国内学界在乡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提升,对于西方学界重视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基层乡村社会的真实状态等学术特色,国内学界给予了充分重视,行龙等学者即大力呼吁进行“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研究[40]。当然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理论也并非一概吸收,而是根据乡村现实进行再思考。对于国内外学界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学者也进行了深入剖析,赵世瑜即提出在进行区域社会研究中,时间和空间多元性的重要意义[41]。在一些研究课题的阐释力度上,国内学者则已超越西方学界,如王奇生、李金铮运用原始档案文献对中共革命政权与乡村民众互动关系的考察,行龙等运用大量基层档案资料和地方文献对集体化时期山西乡村的研究等。
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主持人户华为对学者赵世瑜、行龙、常建华的访谈,学者们提出在社会史研究中应采取多元开放的态度[42],可以说多元的学术方法、开放的研究心态已成为国内外学界从事乡村研究的共识。“乡村研究和乡村学要发扬光大,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中国”[43],相信作为近现代乡村研究主力的国内学者在占有翔实史料、掌握先进研究方法、批判性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N].人民日报.2009-11-20.
[2] KEITH R, SCHOPPA. State, Society, and Land Reclamation on Hangzhou Ba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J]. Modern China, 1997,23(2).
[3] JOSEPH W, ESHERICK.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J]. Modern China, 1998,24(4).[4] ODORIC Y K,WOU. Community defens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hhenan’s du eight-neighborhood Pact [J].Modern China, 1999,25(3).
[5] ELLEN R JUDD. Cultural articul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1937-1947 [J].Modern China, 1990,16,(3).[6] HUNG CHANG-TAI. Reeducating a blind storyteller: han qix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orytelling campaign [J].Modern China, 1993,19(4).
[7] PHILIP C C, HUANG.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Modern China, 1995,21(1).
[8] YU LIU. Maoist disciurse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motion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J].Modern China, 2010,36(4).[9] GRAEME SMITH. Political machinations in a rural county [J]. The China Journal, 2009,62(2).
[10] ETHAN MICHELSON. Justice from Above or Below? Popular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Grievances in Rural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2008(193).
[11] PHILIP C C, HUANG. Divorce Law Practices and the Origins, Myths, and Realities of Judicial “Mediation” in China [J]. Modern China, 2005,31(2).
[12] ZHANG WEI-GUO. Implementation of Stat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in a Northern Chinese Village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157).
[13] JULIA KWONG. Educating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4] STIG THOGERSEN. Cultural life and cultural control in rural china: where is the party? [J]. The China Journal, 2000(44).
[15] ERIK MUEGGLER. Dancing fools: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place in a “Traditional Nationality Festival”[J]. Modern China, 2002,28(1).
[16] JEAN C, QI. Two Decades of Rural Reform in China: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J].The China Quarterly, 1999(159).
[17] JAMES KAI-SING KUNG,YONG-SHUN CAI. Property rights and fertilizing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evidence from northern Jiangsu [J]. Modern China,2000,26(3).
[18] ROBERT ASH. 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188).
[19] YAN YUN-XIANG. The impact of rural refor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2(27).
[20] BENEDICT J, TRIA KERKVLIET,MARK SELDEN.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and Vietnam [J]. The China Journal,1998(40).
[21] WILLIAM L. PARISH XIAOYE ZHE,LI FANG. Nonfarm Work and Market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 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3).
[22] LEI GUANG,LU ZHENG. Migration as the Second-best Option: Local Power and Off-farm Employment [J]. The China Quarterly,2005(181).
[23] CHRISTOPHER M, ISETT. Sugar Manufacture and the Agrarian Economy of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J]. Modern China, 1995,21(2).
[24] JACOB EYFERTH.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Handicrafts and Development in Jiajiang (Sichuan), 1935-1978 [J]. The China Quarterly,2003(173).
[25] SUSANNE LINGOHR. Rural Households, Dragon Heads and Associations: A Case Study of Sweet Potato Processing in Sichuan Province [J]. The China Quarterly,2007(192).
[26] SCOTT ROZELLE, JIKUN HUANG, VINCENT BENZIG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Periodic Markets [J]. The China Journal,2003(49).
[27] LYNDA S, BELL. For Better, for Worse: Women and the World Market in Rural China [J]. Modern China, 1994,20(2).
[28] KIMBERLEY ENS MANNING.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J]. Modern China, 2006,32(3).
[29] YUEN-FONG WOON. From Mao to Deng: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an Emigrant Community in South China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25).
[30] PATRICA D. BEAVER, HOU LIHUI,WANG XUE. Rural Chinese Women:Two Faces of Economic Reform [J]. Modern China,1995,21(2).
[31] EILEEN ROSE WALSH, FROM NÜ GUO TO NÜ’ER GUO. Negotiating Desire in the Land of the Mosuo [J]. Modern China, 2005,31(4).
[32] HUANG SHU-MIN. Re-Examining the Extended Family in Chinese Peasant Society: Findings from a Fujian Village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2(27).
[33] MYRON L, COHEN. Family Management and Family Divis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1992(130).
[34] ANDREW B, KIPNIS. The Language of Gifts: Managing Guanxi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J]. Modern China,1996,22(3).
[35] YAN YUN-XIANG. The Cultre of Guanxi in a North Village [J]. The China Journal,1996(35).
[36] SCOTT WILSON. The Cash Nexus and Social Networks: Mutual Aid and Gifts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Villages [J]. The China Journal,1997(37).
[37]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J]. Modern China, 1991,17(3).
[38]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9] 黄宗智.连结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
[40] 行 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4).
[41] 赵世瑜.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阀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几个区域社会史的例子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42] 户华为,等.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的回顾与前瞻[N].光明日报.2009-03-24.
[43] 彭 伦.中国乡村研究有望领先世界[N].文汇读书周报.2004-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