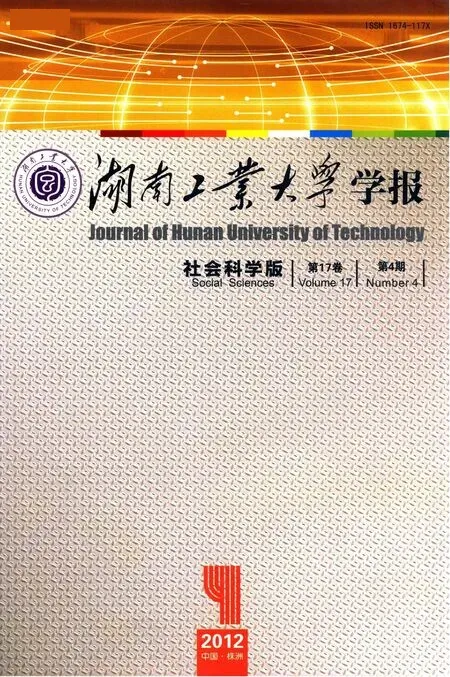王尔德悲剧童话叙事的深层意蕴*
程瑜瑜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广东广州511363)
王尔德悲剧童话叙事的深层意蕴*
程瑜瑜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广东广州511363)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创作了不少悲剧童话故事,以独特的叙事风格赋予悲剧作品深刻的内涵与意蕴。他在故事中融入丰富的想象与情感,抓住物质与精神矛盾的两极进行叙事布局与铺陈,以先“扬”后“抑”的叙事基调、静默的隐含作者、二元对立的叙事视角、宗教的救赎精神,以及暗合的同性恋观讲述悲剧主人公们无法圆融的爱情与人生。这些悲剧作品无疑潜藏着王尔德个人的人生路线,预言着他的最终归宿,并验证了他对生命与艺术本质的探索与追求。
奥斯卡·王尔德;悲剧童话;叙事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童话作家,他的笔触如诗如歌,对悲剧情节的叙事与悲剧形象的塑造极具感染力,其作品集《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与《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中不乏悲剧童话。故事中融入了丰沛的想象与深邃的情感,但语言层面上奢华的美只是一种假象,文字背后暗藏着生命的疼痛如影随行,表达着“不完满才是生命极致的美”的悲剧主题。王尔德以独特的叙事风格讲述走不出悲剧宿命的爱情和无法圆融的人生,主人公们往往依托死亡以寻求宗教式的救赎与安宁。这些故事仿佛也巧合地潜藏了王尔德本人的人生路线——对爱情的期待与幻灭、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与探求——验证着他的情感轨迹与精神归宿,投射了他对完美艺术的向往与追求。
一 悲剧童话的叙事基调
王尔德在给道格拉斯的信中曾说:“悲怆是一道伤口,除了爱的手,别的手一碰就会流血,甚至爱的手碰了,也必定会流血的,虽然不是因为疼。”[1]对于“悲”,他见解独到,借助童话形式诠释悲剧故事,美的希翼与痛苦的现实、爱的理想与死亡的命运互为观照,因此并不真正适合孩童的阅读。[2]他惯于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来讲述核心人物与事件,以物欲之爱与精神之爱二者的冲突作为悲剧叙事的一个重要契机,通过先“扬”后“抑”的叙事基调来呈现人物内心的精神之爱与物质之爱的战争:开篇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各种情思,爱恋,友谊……而后这些美好的事物终归化为泡影,无论主人公们对爱情的渴望,对深情的眷恋,精神之爱程度有多深,总是无法圆满,《夜莺与红蔷薇》(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中夜莺真诚地表示:“爱情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它比绿宝石更宝贵,比猫眼石更价值。用珠宝也买不到它。它不是陈列在市场上的,它不是可以从商人那儿买到的,也不能称重拿来换钱。”[3]
她不求回报地用生命染红玫瑰,只为了成全她所认为的世界上最弥足珍贵的东西——“爱”,然而得到玫瑰的少女却说“谁都知道珠宝比花更值钱。”玫瑰甚至被扔进路沟让车轮碾过,而学者也放弃了爱情。《西班牙公主的生日》(The Birthday of Infanta)中的小矮人初见小公主便产生深深的爱恋,他内心唯一的渴望是给小公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在想象的思绪里弥漫出无穷的勇气,像一朵从未绽放的鲜花想用尽全部的力量去绽放第一次生命:“他会把他的小床让给她,自己守候在窗外守着到天亮,不要叫长角的野兽伤害她,也不让面目狰狞的豺狼走近茅屋。天亮后他会轻轻敲着窗板,唤醒她,他们一块儿出去,跳舞跳个一整天。”对他而言珍贵的珍珠也绝不能代替象征爱情的玫瑰:“他不肯拿他的蔷薇花来换华盖上的全部珍珠,也不肯牺牲一片白花瓣来换那宝座。”小公主却只为了他的滑稽面容而笑,让他不堪自尊的重负心碎而死。《打鱼人和他的灵魂》(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中年轻的打鱼人原本让人鱼替他歌唱可以给他带来满网的鱼,可当他爱上人鱼之后,便再也不在乎渔网和鱼:“她的声音是那么美好,他听得连他的网和他的本领都忘记了,他也不去管他的行业了。金枪鱼成群地游过他面前,朱红色的鳍和凸起的金眼非常显明,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它们。他的鱼叉搁在旁边不用了,他那柳条编的篮子也是空空的。”为了和人鱼生活在一起,他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灵魂,抗拒“灵魂”的百般诱惑,最终却被陆地上一双“光着的小脚”(naked feet)所吸引,无法重回爱的怀抱。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通过先“扬”后“抑”的叙事基调足以令读者随着人物的情绪变化而变化,精神爱恋“扬”的程度越大,对情感的描写越浓烈,叙事结尾物质与世俗层面所产生的“抑”以及“抑”所达到的“毁”的力量就愈大,恰如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当中的评价:“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展现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曾经顶礼膜拜的道德信仰坍塌,人们在物质愈发充裕而精神却愈发空虚的窘境中挣扎,在道德与伦理体系崩溃的边缘犹豫不决,王尔德悲剧童话以美丑善恶的对比尖锐地揭开虚伪的面孔,拷问世人的价值观念。
二 唯美悲剧的二元视角
在整个“扬”与“抑”的叙事中,王尔德虽然既是讲故事的“叙述者”,也是观察事件的“感知者”,但他始终是静默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藉由前后反差的微小细节和有鲜明对照的人物视角进行较为曲折的悲剧叙事,从不提前说明,亦不会在半途中植入自己的眼光;从不亲自指涉人物,更不参与其中。显然,王尔德通过众多“第三人称”的人物眼光来进行全知叙述,无论是作为叙述者抑或是隐含作者,他均跳脱故事本身,仿佛只需负责陈述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他个人的情绪与立场是收敛与克制的,哪怕藉由第三人称的悲剧人物在文末说一句抱怨或责难的话语、哪怕连一点对悲剧人物是否有同情之意的暗示都完全没有,即使是获悉真相的小矮人(他几乎是众多悲剧童话中唯一因了解真相而产生悲剧效果的人物)最后痛恨的依旧是自己的丑陋:“为什么他父亲不杀死他却卖他出去丢丑呢?”丝毫没有对嘲弄他的以公主为首的王宫贵族进行任何指责或批判。至于作为叙写悲剧故事的隐含作者与作为唯美主义代表的真实作者王尔德是否一致地认为丑陋如斯的小矮人从来就不应该存在世上?直接的答案无迹可寻,读者无法确实地把握王尔德作为隐含作者的态度,更无法具体地捕捉他本人对故事中人物的真实情绪,却反而会在这种尤为“客观”的、毫无干扰的叙述中倍感痛苦,产生对悲剧人物强烈的同情心。此外,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是“全知叙述者直接告知读者‘真相’,使读者在认知能力和范围方面远远超过人物本身。同时由于全知叙述者对于人物内外两个世界的观察和描述通常代表了某种叙述立场或道德判断,这种叙述方式使读者容易倾向于接受叙述者的态度。”[4]而作为故事外视角的全知叙述者王尔德却往往徘徊于“全知叙述”与“有限全知叙述”之间,他一边讲述着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一边又通过不同人物的眼光和视角来呈现他们各自的感知和感悟,搭建二元对立的叙事视角,呈现二元对立的意象;一旦人物开始所探讨各种人生命题时,王尔德便“放弃了自己的眼光,转为采用人物的眼光来叙事”,[5]继续做“静默的隐含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相对视角的二元对立产生叙事的不同层次。由于每一个人物的叙事视角只属于自己并孤立于对方,令双方无法求证事实真相,唯有读者才能清楚地知道人物自身无法知道的事实,知晓人物眼中的彼此,掌握人物每一个念头,因此人物悲剧命运的痛感亦才显得无以伦比的昭然若揭。如夜莺视角所见之学者:“这的确是一个忠实的情人,我所歌唱的,正是使他受苦的东西。在我是快乐的东西,在他却成了痛苦……”她对爱情的理解是“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来报答我,就是你做一个忠实的情人,因为不管哲学是怎样地聪明,爱情却比她更聪明,不管权利怎样地伟大,爱情却比他更伟大……”在学者眼里夜莺却是:“她长得很好看,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她有情感吗?我想她大概没有。事实上她跟大多数的艺术家一样;她只有外表的东西,没有一点真诚。她不会为着别人牺牲自己……”他的爱情观是“爱情是多无聊的东西,它的用处比不上逻辑的一半。因为它什么都不能证明,它总是告诉人一些不会有的事,并且总是教人相信人一些并不是实有的事。总之,它是完全不实际的……我还是回到哲学上去,还是去研究形而上学吧。”一个感性而忘我地付出,一个理性而冷漠地评价,同一作品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视角与眼光,构建出无法调和的悲哀。同样地,西班牙公主眼里的小矮人因丑陋而滑稽,小矮人眼里的公主因美丽而可爱,他们对彼此的“喜爱”由来全不同,他们对彼此“微笑”的原因天差地别:小矮人在获悉公主笑容背后真正的意义时痛苦万分,“原来那个畸形怪状、驼背的丑八怪就是他。他自己就是那个怪物!所有的小孩都在笑他,他原以为小公主在爱他,其实她也不过是在嘲笑他的丑陋,拿他的拐脚开心。”大大加剧了“悲”的效果。打鱼人和自己的灵魂建构着爱欲与禁欲、神性与人性的矛盾,憨厚的汉斯与狡黠的磨坊主成为真诚与虚伪的两极,表达着相反的立场和价值观。王尔德恰到好处地组合了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外视角与体现对立冲突的内视角以展示失落的人生,一切矛盾是他妙笔生花的武器,生命观感中的热烈与冷漠,外在的华美与内心的丑陋,爱与悲的两极叙事充满了张力,令这些故事犹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忧伤。
三 悲剧宿命与艺术诉求
王尔德诗一般的措辞搭建了故事的唯美叙述,无一不表现着他对完美艺术形式的不懈追求。然而,形式上的辞藻越华丽,装饰性和感官性越强,越无法掩藏内容上的悲凉意蕴和悲剧宿命。故事人物的情感是投入生命水波中的涟漪,而死亡,是涟漪消失后永远的宁静。失意的感情依靠死亡成全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达成了追求爱和美的极致。或为爱,或为尊严,被踩在脚下的生命仿佛在死亡中得到解脱与新生,主人公以到达天堂彼岸的方式实现救赎,投入最后唯一而温暖的怀抱获取心灵的寄托与慰藉。小矮人对西班牙公主的爱恋,是对美的期待和追求,当他洞悉真相,他用尽一切想象和希冀付出的真心和尊严被无情践踏,若人们憎恨他或打骂他也一定远比这种带着嘲讽的喜爱更容易接受,他的“真心实意”输给了人们对“美”肤浅的认识,这既是爱的幻灭,也是美的假相,唯有死亡才能让心灵得到恒久的安宁,死亡成为爱的挽歌和寻求慰藉的方式。主人公们在现世的受难还潜藏着基督的原型,并成为王尔德悲剧叙事的一种理想模式。快乐王子为了穷人献出自己的每一份财富、夜莺刺穿心脏用鲜血孕育爱情,是耶稣基督式的牺牲,以肉体的消亡换取爱的成全,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世界;小汉斯因为磨坊主口中的一句“真朋友应该分享一切”而无私奉献,对磨坊主所有要求照单全收,是死亡使他不再疲于奔命。痛苦的悲剧主人公们通过死亡获得救赎与归宿,打鱼人丢弃灵魂,拥抱着人鱼的躯体死去,一直反对人鱼恋的神父最后一刻改变了给人们讲解上帝的愤怒的初衷,“他讲解的不是上帝的愤怒,却是那个叫做“爱”的上帝......他祝福了海,以及海中的一切野东西。他也祝福了牧神和森林中跳舞的小东西,以及从树叶缝中偷偷张望的亮眼睛的东西。在上帝的世界中所有的东西他都祝福了,人们充满了快乐和惊奇。”王尔德的悲剧童话可谓打上了很深的宗教烙印,而且在他看来,基督不仅仅是信仰与精神的依赖,还是真正艺术的化身:“基督是最高超的自为主义者。谦卑,就像艺术接受一切经验一样,不过是一个表现得方式而已。基督一直在找寻的是人的灵魂。他把这称作“上帝的国度”,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他把这比作小东西,一小粒种子、一小团酵母、一颗珍珠。这是因为,只有在摆脱了所有与之不合的情欲、所有习得的文化、所有的身外之物,不管是好是坏,然后人才能领悟自己的灵魂。”[1]
不论于情感还是艺术,他始终是个矛盾者,内心的摇摆与探寻在其创作中也留下了痕迹。同时也符合王尔德的创作观念及其作品达成了一种隐喻互证:“文学创作被视为实现自我的两种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和质量靠的是加强作者的个性、靠的是它实现了作者自我的这一事实。”[6]他也亲自承认:“当然,所有这一切在我的作品中已有先兆,已有预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每时每刻的做人,不但取决于他曾经怎样,也同样取决于他即将怎样。艺术是一个象征,因为人是一个象征。”[1]他曾不止一次借叙事作品中人物之口来颂扬爱情:夜莺由衷地认为:“拿死来换一朵红蔷薇,代价太大了,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可是爱情胜过生命……”打鱼人也掷地有声地说:“爱比‘智慧’更好,比‘财富’更宝贵,比人间女儿们的脚更漂亮。火不能烧毁它,水不能淹没它。”他虽然强调爱情的价值,但似乎异性恋在他笔下从未完满,总呈现一种“眼望着却无法得到”的煎熬与痛苦。同性的爱恋观在他的悲剧童话中也有所体现。在《快乐的王子》中有着这样的对话:“亲爱的王子,再见罢!”小燕子喃喃地说,“你肯让我亲你的手吗?”“小燕子,我很高兴你到底要到埃及去了,”王子说,“你在这儿住得太久了,不过你应该亲我的嘴唇,因为我爱你。”小燕子的代词为“他”(he),可见同性恋观的端倪。但按照上帝的意旨,燕子在天堂的园子里(garden of Paradise)歌唱,王子则住在金城里(city of gold),他们死后仍旧分开。灵魂对打鱼人的爱,除了“灵”与“肉”的隐喻,似乎也潜藏这种莫名的同性情感,且打鱼人和人鱼的结局也和所有的异性恋爱情故事一样不能善终,尽管神父为一切祈祷祝福,埋葬他们的地方始终再也长不出鲜花来。情爱的不完满体现了王尔德人对爱情的胶着与矛盾。这种胶着与矛盾同时也体现了他唯美主义式执着的艺术追求:“你知道我的艺术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宏大的首要的意旨,使得我以向自己,而后向世界,展现我自己。它是我生命的真实的激情,它是爱。拿别的爱同这种爱相比,就像拿泥水比醇酒,拿沼泽地里的萤火虫比长空里的皓月。”[1]
由此可见,尽管王尔德的悲剧童话作品不论故事背后暗藏的是同性还是异性的情愫,他所用的语言词藻对情爱的修饰近乎一种浮华的美,但这种美对于世俗之爱的爱情最终的幻灭与消逝无济于事,能够达成完满的唯有博爱的基督和至上的艺术。
正如王尔德自己所言“艺术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真实,而是复杂的美。”他以的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示唯美主义风格的悲剧故事,打造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比起希腊悲剧大气磅礴的因果宿命,莎士比亚戏剧人文主义者孤独的痛苦,海明威笔下永不言败的悲剧英雄精神,他记叙的是生命里的美丽与哀愁—平凡生活里的爱,精神世界中的美,以及这两者的毁灭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痛苦,突出了基督神性的救赎与归宿。王尔德不再重复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一百年的陈词滥调,也不表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美好愿望,只用一种淡然超脱的口吻来讲述悲剧,借助人物交错的视角与眼光让读者听见打鱼人长长的叹息,夜莺最后命若游丝的歌声,小矮人哀哀的哭泣和他的心破裂的声音。作为隐含作者的他始终对故事人物沉默不语,让基督感召中的死亡成为人物告别悲剧命运最好的完结仪式。他以不完美的童话反复叩问生活中处处存在的矛盾与悖论、影射现实社会的困顿与复杂,以曲折的方式展现他对艺术、爱情及人生完美而纯粹的追求,亦用自己的作品预言了他独特的人生路线:生前走在享乐主义与感官主义的边缘,摇摆于物质与精神之间,对爱情既渴望又绝望,临终前于孤寂中皈依了天主教,投入基督的怀抱,和他笔下的悲剧人物一般,得到他真正的心灵安宁。
[1]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M].朱纯深,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58-89,88-89,41,94.
[2]Peter Raby edit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97.
[3]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1卷[M].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348.
[4]申丹.王丽娅.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6-67.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1.
[6]杜吉刚.世俗化与文学乌托邦:西方唯美主义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3.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 in the Narration of Oscar Wilde's Tragic Fairy Tales
CHENG Yuy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Zengche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511363 China)
Oscar Wilde,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aestheticism move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th century,had created many fairy tales with profound connotation and tragic implication by using a unique narrative style.He endowed these fantastic works with rich imagination and emotion,carrying out his elegant narrative layout and elaboration by using two contradictory poles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In addition,he created many successful tragical characters and narrated their unhappy life and sorrowful love stories with a changeable narrative tone.As a silent implied author who never involved the process of 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ies themselves,Oscar Wilde made good use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o make sad stories which really showed the spiritual intrinsic of religious salvation and a hidden view of homosexuality.To some degree,these tragedies seemed to have pointed out the clue of Oscar Wilde's personal life,the prediction about his ultimate fate,and the reflection of his explor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art.
Oscar Wilde;tragic fairy tales;narration
I106.4
A
1674-117X(2012)04-0148-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4.028
2012-04-18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课题“王尔德文学作品叙事研究”(XJKT2010C003)
程瑜瑜(1979-),女,广东湛江人,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