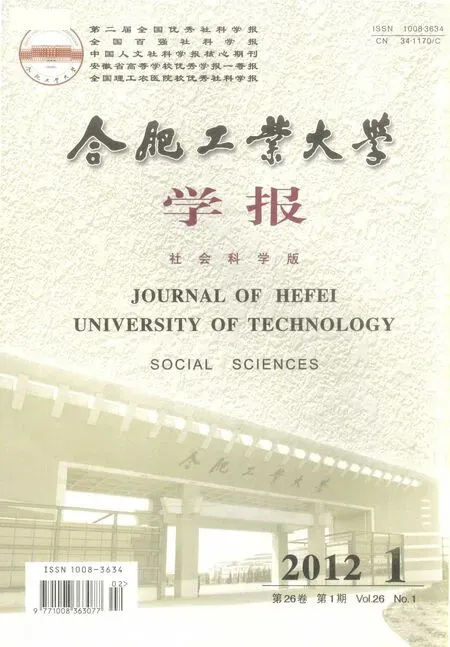土地伦理从可能到现实——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环境特质
陈绪新, 李荷君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09)
土地伦理从可能到现实
——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环境特质
陈绪新, 李荷君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 23000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伴随着“自然的分割”基础上的“自然的异化”,除非采取实际行动来一场基于生态伦理的道德革命和社会革命,否则,自然资源枯竭的悲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危险就在所难免。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他者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野。
土地伦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者与共体;积极伦理学;生态革命
正是因为内蕴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性思维模式的首要原则是分离和征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伴随着“自然的分割”基础上的“自然的异化”,这种分割和异化是“经济简约论”[1]的前提假设与必然结果。除非我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一场基于生态伦理的道德革命和社会革命,否则,自然资源枯竭的悲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危险就在所难免。
土地伦理原先是从环境和生态伦理的视角延展而来的,是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ry Almanac)一书中首次倡导并提出的。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需要新的突破,其演变的下一步,就是扩展为包含生物共同体——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为“土地”——的非人类成员在内的伦理观,是“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2]。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一、土地伦理何以必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德审察
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待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即当下中国语境的“三农”问题)上所遵循的几个原则[3]80,从道德的层面来观察和审视,其导致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几乎所有的灾难和风险,具体如下:
1.农场或森林应该与工厂同样对待
也就是说,用来耕作的土地以及用来采伐利用的森林可以像现代化的工厂一样,按照不同标准或用途进行细化或分割,然后使其标准化,进而能够像工厂一样源源不断地为投资人赚取利润。土地和森林被标准化成为农场或木材加工厂的过程,就是自在存在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生态系统被人为地分割和开发利用的过程,使得作为人类生存和居住条件存在的“生态系统”变成了由人类任意分割、支配、控制和掠夺的“自然资源”,进而简约化为“自然资本”。
2.对待土地只需要最小限度的关照
与人类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或人类所谓的幸福生活相比较,土地只需要人类最小限度的关照。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人类的当下利益对长远利益、当代人利益对后继者利益、人类自由对其他物种的自由、人类的利益对其他物种的利益的侵占和掠夺。然而,缺少关照的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人居条件,反过来会因为蜕化或肥力减少而对人类产生消极的影响;被肆意砍伐的森林反过来会以沙漠化以及因为森林对二氧化碳吸收的减少所产生的气温上升而对人类进行灾难性的报复。
3.与土地打交道情感因素毫无必要
文艺复兴以降,人类在现代化及道德谋划的过程中,过分强调理性的认识和改造作用,而忽略了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情感因素的一面。事实上,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类现世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都是依靠真实的情感来维系的。这种情感除了具有真实性特质以外,还具有道德性和整体性的一面。从道德层面上看,土地不仅生育万物,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我们不仅要去呵护它,更要从心灵深处去敬畏它,要怀着感恩之心去回馈它。
4.地表土壤是惰性的和没有生命的
从表面上看,土地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正是这一看似没有生命的土地却构成了人类乃至地球上任何一种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或最原始条件。土壤并非是惰性的,而是生生不息。它的这种生生不息来自于自然界所有生物构成的多样性存在的生态系统,最直接的就是生物圈系统。这种生物圈系统主要是通过食物链系统来完成养分和能量的传输,进而实现各种生命体或物种间的比例协调且丰富多彩的生物圈生态。那些持守土壤是惰性甚至是无生命的观点的人们,他们拥有和主宰着包括土壤在内的一切自然物,对待无生命的土壤来说,他们拥有着绝对话语霸权。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类对土壤及以其为存在条件的一切生命存在的“强权”包括话语霸权不是绝对的,对于默默无闻不会反抗的土壤及其生物来说这是暂时的。自然会苏醒,大地会震颤,灾难在累蓄。
5.土壤生物可以安全可靠地由土壤化学取而代之
土壤生物通过食物链形成了肥力、养分和能量的有效传输,因此建构了生物多样性的有机生态——不同物种间比例协调,在竞争与合作中展现生命的生机勃勃和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土壤本身也是多样和有机的。对于农业生产及其基础上的相关产业来说,土壤生物条件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之“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的本性要求,土壤化学出现了。人类希望通过化学分析来了解土壤的元素构成,然后对土壤的有效成分作最大化利用,对不利成分通过化学肥料的施用来加以改变以实现产出最大化而不是土壤生物条件的最优化。这是人类对待土壤的极其短视的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要尽可能地窄干土壤肥力条件,为了眼前利益而无视土壤的退化或蜕化,无视化学肥料的无限制使用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潜在和显在的威胁,无视因为土壤的退化或蜕化而可能或业已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连锁反应。
6.任何地方的自然与生态都与它的开发利用没有关系
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发现这句话和这一观点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人类自有史以来一直在对自然和生态进行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却又说这种开发利用与自然和生态没有关系。其实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的出现,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人类对自然和生态存在的漠不关心,在人类驾驭一切、主宰一切的世界里,自然和生态为资本家的“榨汁机”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水果和蔬菜,可是资本家却因为惟利是图而故意地对自然和生态的承载能力不闻不问。
二、土地伦理何以可能——他者伦理学或共体伦理学的视角
劳动分工的细化必然伴随着“自然的异化”,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几乎所有类型的系统的整体性被人为地分割和肢解,然后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用二元函数进行标准化,进而估算出每一个系统要素可以利用的最大经济价值。这种标准化的过程,在为资本家加速度地最大限度利用一切有限资源创造无限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加速度地分割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现代资本主义把整个自然纳入它的损益表中,美其名曰为“自然资本”。这种概念下的所谓进步就是通过不断的劳动分工和所谓的“征服”自然而获得的。秉持掠夺式思维的生态帝国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们把地球作为人类居所”的那种情感的破坏;“居民”或生态系统居民被现代意义的人口或公民所取代,从而沦落为“流浪的君主”。
如果前面所述正确的话,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建立新的生态文化或生态道德,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更具体地说,人类必须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居住,这是关键所在。人类要重新学会在地球上居住,就必须重新全盘思考和定位人类在自然界或生态系统中的位置,重新思考和定位个体与人类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即社区和邻里关系[4]。人类要真正地走出目前对待自然甚至对人类其他个体或群体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走出传统的关系定位或伦理实体定位的人伦关系的单一性,走出自我为中心、人类为中心的狭隘立场,以更宽泛的视野,站在整个生态系统文化的高度,将人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各种关系从生态的角度构设为人与自然(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身与心(个体生命存在之肉身与灵魂的关系)的完整性,进而实现伦理学的新突破。
众所周知,个体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关系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使我们意识到了“自我”,并且同时意识到与“自我”同样存在的许许多多“他者”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他者”的意识往往先于对“自我”的认知,换句话说,对“自我”的意识或规定是建立在对“他者”存在的承认或认知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理性的“自我”不是孤独或孤立的存在,“自我”存在于由“自我”与“他者”共同寄身于其中的共同体之中,故而,“自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无不关涉着“他者”的利益和感受。这样一来,“伦理”就产生了。所谓的“伦理”,就是处理与人有关的各种关系的原则或规范。以“自我”为中心可能引发的关系有很多,但概括起来无外乎三种,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范畴)、人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社会伦理范畴)、人与自身的关系(生命伦理范畴)。
从“伦理”的意义上讲,“自我”与“他者”是一个竞相生长、同存共荣的有机体,他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不容分割。一个有理性的人类生命个体如果能够做出上述关系定位并建构自己的人格的话,他就会在追求自我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同时,时刻告诫自己行为的“合宜性”,他会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善待自然界其他生物,善待社区和邻里关系中的其他人,维持生命体存在的同时善待或照顾精神的存在。他不再视自然、他人和社会为客体,视为与自我对立的“他者”,而是将“他者”摆到与“自我”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而自觉地意识到,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具有这样一种人格和生命体认的人,他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有意伤害其他生命物种,不会因为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有意甚至是无意伤害其他人,不会因为自己的肉体幸福和快乐有意或无意造成自己心灵的伤痛或成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正如福斯特所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长期分割,“使人们产生了人类只生活在消费场所而不是生产场所的幻觉,因为自然可以被视为外部环境,一个从中索取资源并向其倾倒废料的区域,而不是像人类‘外部躯体’一样作为人类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3]。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呼之已出。“我们滥用土地,是因为我们将它视为自己拥有的商品。如果把土地视为我们归属的共同体,我们就会怀着爱戴之情使用它。”[3]81
利奥波德认为,与建立在个人主义占有基础上的支配型西方道德哲学不同,以土地伦理关怀为出发点的新的道德情感主要是对道德共同体的敬重。这种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情感之上的道德诉求,将道德伦理从单一的人类个体和社会关系共同体扩展到更大更宽泛的关系领域。因是,人类历史的道德观将被视为是以人为中心,融摄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的关系共同体之“道德序列”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土地伦理或生态理论的提出,使伦理实体的规定从个体经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世界扩展到包括人类个体及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生态共同体。土地伦理虽然不能限制对囊括了土壤、水源、植物和动物在内的整个土地“资源”的变更、管理和使用,但它却告诫人类必须确保土地持续存在的权利。简而言之,土地伦理改变了当代人类的角色,使其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成它的普遍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要尊重同类,同时也要尊重共同体。从土地伦理的角度评判,“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结果如果是否定的,那就是错误的。”[3]81
土地伦理的实质性意义不仅仅像利奥波德所言称的那样,“仅仅扩大了共同体范围”,更重要的是,土地伦理把人类道德情感和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个体自我和人类社会扩展到了人类以外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物。人类开始学会如何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支配者和掠夺者的角色中走出来,并努力将自己视为自然系统的一个部分;开始学会如何尊重自然界其他物种持续存在的权利,并将囊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物种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视为人类自身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人居条件。虽然到目前为止,像土地伦理这样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规范还有些模糊,像“完整、稳定和美”这样的术语还需人类共同体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给予规定,但是利奥波德等人提出的崭新思想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建立在对财富的利己主义追求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是同包容了更大生态共同体的土地伦理直接对立的”[3]82。
三、土地伦理如何实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德革命
如果说利奥波德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建构一种区别于传统的人与自然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支配型关系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土地伦理的可能性,那么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则进一步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更高的不道德”与当今世界最严重问题之间的一种质的关联。
1.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
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秉持着“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分”价值原则,“以自我为中心”,漠视“他者”的存在及意义,使得“自我”与“他者”出现分离,标榜着“自我”对“他者”的征服、侵略和掠夺。在“资本无限扩张与积累”的号角鼓吹下,演绎着赤裸裸的“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金钱逻辑。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他者”的利益侵占和掠夺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态危机”,身与心的分离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人格分裂和“心态危机”。生态、人态和心态的三大危机,吁求一种全新的伦理观,一种走出传统的“人伦关系”的单一性同时融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为一体的新型伦理观;一种走出“非此即彼”或“主客二分”的狭隘立场同时构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的新型伦理观;一种摒弃“自我利益最大化是以他者利益最小化为前提”的传统思维模式同时倡立“自我与他者合作共赢”的新型伦理观。
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市场机制已经成为具有如此支配性的理念。譬如说在对待地球生态危机时,它要求我们接受“进一步延伸生产关系会给所有环境问题提供技术解决”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在超越一切控制的生产秩序中,逐渐被所谓的技术理性支配着,市场利润操控着,政治工具宰制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这是当初马克斯·韦伯在觅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间内在关联的时候,没有预见或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这么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资本家以世间万物“看守者”(上帝造人的真正目的)的名义,主宰着自然界的命运;以“获得上帝救赎”为藉口,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打上“上帝允许的”合理合法的烙印;以“上帝选民”的身份,在经济扩张、资源掠夺、环境商品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地通过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甚至环境等方式,试图主宰其他异域文明[5]。
也正如米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按照市场规则,在一个大资本和大企业以“盈亏底线”实现专制的社会里,“金钱是成功的明确标准,并且这种成功乃是美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相对这种价值观,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已经下降,所以人们很容易在追求来之轻松的金钱和开发迅速的房地产当中表现出道德上的冷酷无情”[3]。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厚颜无耻地崇拜财富,而对其引发的贫困和环境破坏通常置之不顾。实际上,正因为它在社会中得到如此高度的制度化,所以几乎显示不出任何不道德的本性。因此,所有其他道德标准和共同体基本规范被迫在它面前让步。“如果作为人类与地球基本联系的土地蜕变成最高出价人可以随意买卖的纯粹地产,如果将公地围圈,然后不受任何公共制约和限制随意开发,就注定会导致一切都蜕变为经济价值。”[3]的确,问题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它是所有幸存事物的基本物态,同时也是所有事物的社会产品。在这种社会里,人们被迫将与其有关的一切——地球上的土地、河流、自然资源以及他们自身的劳动力都作为单纯的商品,都可以为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加以开发利用。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不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主导下的市场规则的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就不可能在地球保护方面取得任何持续进展。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所有将生态和人类福利简化为单调的生产过程)进行生态批判的崛起。这种批判基于三项主张:第一,一种制度如果追求无休止的几何增长和无限度地攫取财富,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角度(如果不是短期的话)看都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目前这种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已被推向极端),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6]。
2.农业的可持续与生态公正
伴随着现代土壤科学——研究农业与化学之间关系的科学——的兴起,合成肥料被逐步引入。在土壤中使用单一的废料(如磷)的努力虽然最初产生了显著效果,然而不久,因为土壤的整体肥力总是受养分单一的限制,土地的肥力便开始迅速下降。
人工合成肥料和农业产业化,不仅导致物质和能量从初级生产者(植物)经由初级消费者(动物)再到高级消费者(人类)的传送和转化的链条的断裂,而且也使得物质和能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初级的动物和高级的人类——之间的养分循环或反馈链断裂或消逝。早期农业阶段,物质和能量从植物经动物再到人类的传送和转化的过程,也是一部分物质和能量会以养分的形式从动物和人类那里返回土壤,成为植物可以吸收的养分。这样一来在植物——动物——人类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物质和能量传输以及养分循环的完整链条。而对于那些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的社会来说,大量人口——高级消费者——集中在大城市,他们已经与物质和能量的初级生产者(植物)和初级消费者(动物)的耕作、养殖或饲养完全脱离,这导致了伴随着物质和能量传送过程的人类与初级生产者(植物)之间的养分反馈链条出现断裂,仅仅有很少一部分的养分会通过污染物的再利用而回流到土地,而且还要承担污染物残留威胁人类健康的风险。到了农业产业化阶段,初级生产者(植物)和初级消费者(动物)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也变得间接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发展因标准化和产业化而在异域同时进行。这样一来,人类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植物和动物那里分别获取物质和能量,而且效率提高了,品种增多了。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动物和植物之间、人类和植物之间的那种养分循环再利用的链条全都不存在了。农业生产过多地依赖人工合成肥料(富含人类自身无法消解的危害健康的化学元素以及农药的残留)的大量和广泛使用,畜牧业生产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合成饲料(富含影响人类健康的激素和有害物质)。就现代社会的农业产业化而言,维持土地的肥力只能依靠合成肥料,而不是制定有利于环境健康的土地长效使用机制和农业及畜牧业发展管理战略。
今天,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依赖合成废料给生态环境和土壤造成的危害,开始呼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旨在最终避免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种认识使人们对可持续农业产生了新的兴趣,而在可持续农业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是土壤养分循环问题、发展生态农业,人们正在重新发现人与土壤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生态健康的关系。
可持续的生态农业观强调的是“适度”,而不是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抛弃那些处于世界体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底层的人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应该使社会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受益——罗尔斯正义之“差别原则”即促进“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不仅是生态道德或土地伦理应该关注的重点,也是社会公共理性或道德应该关注的焦点。的确,正如汤姆·阿塔纳修在其《分割的地球》一书中所言的那样,“历史将通过绿色组织是否站在世界穷人的一边来判断他们的功过”[3]。近几年的世界环境公正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关注生态公正实际上就是关注社会公正,因为生态系统是不同历史发展进程和不可消弭的文化或道德的差异性的各个民族国家共同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和最原初动力。人类社会生活层面的形形色色的不公正往往都是以对包括土地、水源、自然资源、动植物等在内的稀缺性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多寡或不公为现实表征的[7]。那些旨在捍卫生态与文化多样性及促进和代表社会公正的人们,正在试图唤起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意识和更强烈的生态道德责任,正在激励那些代表特定生态系统及其所寄身于其中的生态共同体的人们,与现行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资本积累的逻辑)及其“大量功利主义残忍行为”展开斗争。这场全人类有关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道德革命和社会斗争,正在唤醒全人类对于当下的所作所为作出全新的文化选择和伦理抉择。
四、马克思的土地改良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19世纪40至50年代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非理性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脱胎而来的城乡对立紧密相关的。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马克思在阅读了李比希、约翰斯顿和凯里等思想家著作的基础上,就土地肥力危机问题开始将研究的重点直接转到了土壤养分循环及其与资本主义农业的剥夺特性的关系上。因此,他在《资本论》第一卷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大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对资本主义农业和有机化肥循环利用的这种思考使马克思形成了生态可持续性的观念——一种他认为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社会关联极为有限,但对一个由生产者联合而构成的社会却至关重要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个由生产者联合而构成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产条件和再生产条件进行自觉的合理的经营”。他继而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下一代。”[3]秉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后续的思想家如考茨基和列宁,深受李比希和马克思关于农业可持续性和循环利用有机肥料必要性的观点的影响,认为养分返回土地是社会性变革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他们那个时代肥料供应量已大幅度提高。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考茨基主张:“辅助肥料,可以避免土壤肥力的减少,但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肥料,只能给农业增添更大的负担——它并不是强加给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负担,而是现行社会组织的一个直接后果。通过克服城乡之间,或至少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与荒凉偏僻的农村之间的对立,从土地取走的材料就可能完全回流到土地。那时辅助肥料至多发挥着肥沃土壤的作用,而不是用来避免土壤的贫瘠。耕作方式的进步意味着在不必增添人工肥料的前提下使土壤的可溶性养分增加。”[3]同样,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写道:“人造肥料代替自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替代(部分地)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下述事实:把自然肥料白白抛掉,反而污染市郊和工厂附近的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就在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周围也有一些土地利用城市的污水,并且使农业获得很大的好处,但是这样能够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污水。”[3]不仅如此,即便是对这很少一部分的污水的再利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它会使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着因污染物的残留而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
改变土地承包和租用制度,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改良土地肥力和发展循环农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的佃农因为租种地主的土地,故而倾向于避免任何的耕作改良与保护土壤肥力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土地改良方面的任何付出在其土地租种期间得不到任何回报[8]。新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在今天的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使用权已经通过法律的形式为农民租种使用。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我国农民改良耕作方式以保持土壤肥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长期性和一贯性,尽可能地延长和扩大农民对土地使用年限和权限。只有这样,租种土地的农民不仅有了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因土地租用的短期行为对土壤肥力的破坏。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而是类似于封建社会的佃农的话,他们就不会为改良土做出任何一点努力,并且大量使用化学合成废料以提高自己租种土地的生产率,从而导致土地肥力急剧下降,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人为设置障碍。农民害怕自己改良土地的努力会因自己正在耕作的土地的使用权限的变更而化为乌有。每一个农民都会避免为下一个租种者“坐食渔利”而进行耕作改良以保护土地。土地承包的短期行为无疑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果要么是维持低效率的传统耕作方式,要么尽可能多地使用合成化学肥料,追求土地租用的短期效益的最大化。总之,任何一个农民都不愿意自己租种土地期间的改良付出因为土地变更而自动转让给其他农民。保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通过法律明确农民对土地租种使用的长期性,这样一来,每一个农民就会摒弃农业生产中的短期行为而立足于长远,最大程度地改善耕作方式、保持土壤肥力,积极投身于生态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某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因为人为因素而获致的与人的关系的紧张以及因为过度开采或滥用而导致这一领域的实际问题和价值危机,当且仅当这一领域出现的矛盾、问题和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的时候,这一领域、该领域与人类的关系才会被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一领域本身存在的尊严和意义、该领域与人类关系及价值的重要性才会进入人类关注的视野。
土地原本就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然而,正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使用,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土地问题,人地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我们才不得不在道德层面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土地,按照伦理的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利用土地、如何改善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伴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土地伦理”才应运而生。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几近被消耗殆尽、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灾难性报复,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经济原本关乎伦理,或者至少是以伦理为皈依、为觇标、为视阈的。而经济伦理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经济行为逐渐背离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变成了纯粹“二元函数式的经济模型”,经济行为不再需要伦理或道德约束,蜕变成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当经济学家的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当这匹“脱缰的野马”变成了一头“跛足的驴”、“一头犟劲十足可能拉也拉不回来的驴”的时候,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才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被经济学家、企业家、资本家、政治家提上议事日程,“经济伦理学”这个消防队员的身影才会出现。但也只能起到一个暂时的消防队员的作用,火灾被消灭之后会不会再发生、问题被暂时解决之后会不会再重演那就很难说。
面对大地和自然,我们呼唤一种积极的伦理学,一种视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而且还为人类提供寄身于其中的人居环境的伦理学,一种人与自然本该是和谐共生的伦理学。改变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传统思维方式,不要为了人类即时性的欲望的满足,而无限度地改变自然生态原有的内在发展和繁衍的趋势,逆自然规律而行;无限度地开采自然资源,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和统一,自然被分割;无止境地向自然环境丢弃生产废料和生活垃圾,环境被污染。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综合治理与保护、维持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与和谐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伦理考量、道德关怀和制度创设必须成为实业家、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们的行为自觉[9]。
我们呼唤一种积极的土地伦理学,就是希冀人们不再当且仅当现实问题和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时候,土地作为独立的有生命的机体才会被关注、被尊重,人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才会被重视,诸如土壤肥力的保护与提升、还原和保持土壤的内在平衡、确保生态系统的物种平衡与食物链完整、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及风险规避、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开发利用的有序规划以及对土地的应有尊重或敬重等价值问题才会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话语和政治家们决策的关键词。
我们呼唤一种他者立场或共体视域中的土地伦理学,是因为诸如土壤肥力、转基因技术运用、生态系统物种平衡、食物链的完整以及粮食安全等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的窘境与话语。笔者担心的是,土地伦理会不会像其他应用伦理学一样是个“迟来大仙”?放放“马后炮”,做个“和事老”,或者仅仅是“案头摆设”,顶多也是个“自我安慰”的“花瓶”。它能够起到多大的道德实践力量?土地伦理——与其他一切应用伦理学一样——能不能摆脱“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后致性命运?更进一步讲,伦理学是否应该回归到基于人性固有的善端、人类社会共享的普适性价值以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内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等本源意义上来?伦理学应不应该走出黑格尔的消极和被动命运[10],真正发挥其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充分发挥其以人性固有的善断和共体内部自然形成的共同善为基始和践行力量源泉的、积极而又主动的创造活力与感召力?
[1]陈绪新.后金融危机时代必须究诘的几个伦理问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
[2](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译者序言[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美)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0.
[4]陈妙玲.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审视——论<啊,拓荒者>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外国文学研究,2010,(2):127-134.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6]T Eric,Freyfogle.Fostering a Culture of Land Commentary on“Agrarian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Ethics”[J].Sci Eng Ethics,2008,(14):545-549.
[7]Cafaro Philip,Primack Richard Zimdahl Robert.The Fat of the Land:Linking American Food Over Consumption,Obesity,and Biodiversity Loss[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2006,(19):541-561.
[8]F Magdoff.Ecological agriculture:Principles,practices,and constraints[J].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2007,(2):109-117.
[9]Jennifer Welchman.Hume,Callicott,and the Land Ethic:Prospects and Problems[J].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2009,(43):201-220.
[10](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37.
Land Ethics from Possibility to Reality-On Anti-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CHEN Xu-xin, LI He-jun
(School of Marxism,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natural partition”based on the“natural alienation”.Unless a moral and social revolution is set off based on ecological ethics,there is an inevitable danger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ased on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tragedy.Land ethics is to transform the role of human as a conqueror in the community into an equal member of the community.Other ethics provides us such a moral vision.
land ethics;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other and community;positive ethics;ecological revolution
G829
A
1008-3634(2012)01-0050-08
2011-11-1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8CZX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7JA20008);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一般项目(2010sk020)
陈绪新(1970-),男,安徽六安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