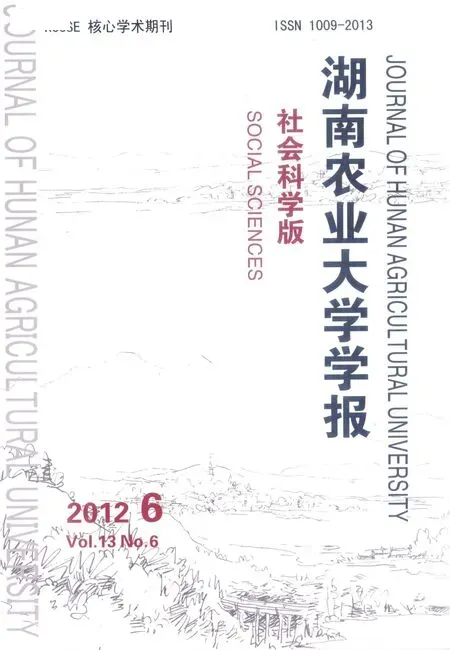关于传统集体主义的若干观点辨析——与刘天喜教授商榷
陈 云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同时又尊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正当权益、发挥个体创造性潜能,并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全面协调发展。刘天喜教授公开发表的《不应该用传统视角理解现代集体主义》一文认为:“传统集体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既不科学,也不适应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现实。”[2]同时,以“传统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价值、游离法律之外、局限狭隘群体”的三个分论点进行了论证。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苟同,本文拟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传统集体主义是否科学的问题进行考辨并顺承就传统集体主义的三分论点与刘教授商榷,最后以传统集体主义的辩证性视角略谈结语旨意。
一、传统集体主义的科学性问题
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某种理论命题是否科学,一直是众人研究的热点。在此,笔者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的视角对传统集体主义的科学性问题进行考辩,以期纠偏刘文总论点的表述。
1. 命题科学与否在于其是否有意义
这里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客观内容,而在于它是否属于逻辑的和纯数学的命题,或者可由经验证实的经验科学命题。一些既不能用逻辑证明的命题,也不能用经验证实的命题,必然是伪命题、假命题,不科学的命题。在此,以卡尔普纳的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为例,他提出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必要条件是:“假定‘a’为任何一个词,是‘s(a)’为这个词出现在其中的基本句子,那么,‘a’具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用如下各种表述表现出来:1.同一事情‘a’在经验中的标准已知;2.‘s(a)’可以从某种基本的观察语句中推断出来;3.‘s(a)’的真值条件已经确定;4.证实‘s(a)’的方法已知。”[1]57从中可知,判定某个命题是否有意义,既要看这个命题中是否为有意义的词,也要看这个命题是否符合逻辑句法,否则无意义、不科学。
就刘教授“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不科学”的总论点来看,其基于对“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说明,从而得出了传统集体主义是不科学的结论。因此,如果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看,“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因此才所谓不科学。然而,如果我们假设“a”为集体主义,则其有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作为‘a’在经验中的标准已知,作为‘s(a)’的‘传统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命题可以从某种基本的观察语句中推断出来,‘s(a)’得真值条件已经确定,证实‘s(a)’的方法已知。”事实确实如此,纵观刘文陈述,“a”的标准的确已知:个人价值、法律保障、全面集体;“s(a)”命题的确可以某种基本的观察语句中推断出来:“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法外开恩……诛不仁……家族”等观察语句中推断出来;“s(a)”的真值条件的确已经确定:史料分析、观点论证;证实‘s(a)’的方法的确已知:传统社会“否定个人价值、缺乏法则规约、局限狭隘群体”的归纳分析法。以此分析,刘文“传统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命题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有意义的命题,因此也就科学了(注意:逻辑实证主义不深究命题内容)。从这个意义讲,刘文所持“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是不科学的”命题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论证的结果互为矛盾。因此,刘文对传统集体主义的科学性阐释从逻辑形式上看缺乏严密性,有待商榷。
2. 理论科学与否在于它的可证伪性
这里的“可证伪性”是逻辑上的可证伪性,即从理论推导出来的陈述在逻辑上总可以有某种事例与之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一个理论是可证伪的,那就是科学的,反之则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在此,以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理论为例,他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四 段 图式: P1(问 题 1)→TT(假 说)→EE(证伪)→P2(问题2)。换言之,科学发展的核心是假说,而所有假说都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P1 的假说,假说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使结果被证伪,被证伪的原因是在实践检验中的假说不能解决新的问题P2,为了解决新问题P2,则又须提出新的假说。因此,某一理论问题的科学性也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证伪,不断发展的。相反,无法证伪的则无科学意义。
站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可证伪性角度,就刘教授“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是不科学”的总论点来看,要确证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集体主义观念不科学,就必须证明“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无证伪性。在波普尔看来,不可证伪的理论主要有逻辑学和数学、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命题、经验之外的宗教神话,占星术等伪科学。简言之,波普尔认为无法证伪的理论命题即为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这样的才可称为不科学的。在此,反观“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的命题,实际上其并非是脱离经验的空洞表达,而是扎根于传统社会且对传统宗法等级社会的经验是非的深刻反思。正如刘文也有所揭示:“传统集体主义是从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中生长出来的。在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个人不能成为自由的独立主体,只能依附于群体而存在。因而,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没有个人,只有群体;没有个人主体,只有社会主体……在自然经济和传统经济时代,分工和交换不发达,人们以血缘、地缘、职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联系与合作范围就很有限,由此构成的群体、集体也很狭隘。”[2]基于此,刘文所述的“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的命题的确并非经验之外的行上表达,而是立足于传统社会的经验观察,且刘文也一直在对该命题的中心意旨进行论证式证伪,即论证传统集体主义不科学。但是,如果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该命题的可证伪性却已经表明其称得上是科学的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文对其命题的证伪性论证与该命题的不科学实际上已陷入矛盾境地。
3. 理论科学与否应立足不同时期的范式形成
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历史主义认为评判某一理论的科学与否并没有绝对的真理标准,而应该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范式形成。库恩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理论在成为真正科学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从“前科学到科学”的过渡与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某一历史时期已获得一种共同的范式。而这种范式即为划分某种理论科学与否的标准。正如库恩说言:“他们已获得一种证明有可能指导整个集体进行研究的范式。除了事后认识到这种好处,很难另外找到什么标准可以明确宣布某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3]18正是如此,不同范式下的不同理论之间不存在一种客观的超越于二者之上的绝对评价标准,即前后两种相继的理论之间是没有通约性的。这种不可通约性可表述为: 根据范式P 或在P的条件下,T 被认为是科学的,但根据范式Q 或在Q 的条件下,T 则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因此,科学历史主义否认绝对科学(或真理)的绝对存在,而认为某种理论的科学与否应取决于不同范式下的各种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
就刘教授的总论点“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传统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是不科学”的内涵来看,可以发现刘教授的定论的确过于绝对。如果站在库恩科学历史主义的视域下来考察,刘教授在现代集体主义与传统集体主义之见构架起了一座方便二者可通约性的桥梁,即建构了一个二者绝对化的对比标准。在此,笔者不反对就二者做通约性比较,但是,这种层面的通约性意义不可作为判定谁是谁非的标准性理由。因为,二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完全不一样且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环境也完全不一样。正如刘文所述意涵: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和传统计划经济的时代,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时期;传统集体主义是否定个人价值、缺乏法则规约、局限狭隘群体的集体主义,现代集体主义是尊重个体价值、重视法律维护、力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全面协调发展的集体主义。既然刘文又已经明确揭示了集体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那就已经提供了说明某一理论科学与否的范式启发。换言之,其已启发人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在传统社会必有其科学性,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在现代社会也定有其科学性,不存在传统集体主义的不科学性表达,只存在现代集体主义对传统集体主义的范式打破而取得的主导地位的常规科学性表达。
综上所述,对于某一理论命题的科学性与否的表达的确不能妄自定论,否则必然遭到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即便三大主义自身可能存在其固有缺陷,但是其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对于人们分析某一理论命题确实具有很深的启发。至少,这已让笔者领悟到了对于传统集体主义的科学性问题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言说,并就所谓的“否定个人价值、缺乏法则规约、局限狭隘群体”的狭隘集体主义到底能否真正证伪需做进一步确证,而非妄自定论。其实,集体主义本是一个伦理上的价值原则,其本身并无“科学”可言,将“集体主义”当成“科学”来表述,确实是混淆了以“科学”为指征的“事实”和以“集体主义”所体现的伦理“价值”之间的区分。
二、传统集体主义的三大分论点辨析
刘教授在文中对“传统集体主义是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片面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是缺乏‘守法’规范的与法分离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是局限于狭隘群体的狭隘封闭的集体主义”分论点的论证过于片面,缺乏说服力。在此,笔者拟通过对传统集体主义三大向度的确证来和刘教授进行商榷。
1. 传统集体主义以个体为基点
刘教授认为,传统集体主义因为处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都不发达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不能成为自由的独立主体。因此,“……这个时代的集体主义也必然具有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特征”。[2]
实则不然,中国传统社会在讲集体主义的同时,同样注重对个体价值的塑造,更甚者,传统集体主义的展开可以说就是以成仁之己为基点的。诚如《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等称得上是最完美的注重个体价值塑造的集体主义,即只有以修身培养起仁义礼智信的个体基本善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主义逻辑理路才得以展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集体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样态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说没有忽略对个体人性的重视与塑造。例如,当古代孔子强调个体对集体有不可回避的责任之时,让子路见隐者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第十八》)与此同时,孔子并不忽视对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成……”的“正名”个体德性教导。当古代孟子挥扬“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公孙丑下》)的集体主义气概时,同样也不忽视对“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个体善端价值的重视。当古代朱熹强调对“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语类七》)的集体主义公私辨明时,同样不代表朱熹丢掉个体自我人格:“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六)当近代梁启超坚定“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地与诸行星群,日与诸恒星群,相吸相摄,用不散坠”(《说群一·群理一》)的集体主义信念时,同样也注重“人人对于人而有当尽之责任,人人对于我而有当尽之责任”(《新民说》)的集体主义个人责任互担。当近代李大钊强调自由联合体的集体主义大同理想时,同样着重阐明“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略与干涉……在这样的平民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人”[4]421的彰显个体自由的集体主义。
可见,传统集体主义并没有忽视个体价值意义的存在,反而特别强调在家国同构的宗法集体主义中,要重视对人价值属性的开发与塑造,要实现人作为与低等动物有着根本区别的类存在的自由平等。然而,基于宗法等级的传统社会性质,传统集体主义个体价值意义的这一层面似乎屡屡处于挣扎阻滞之中,以致就有了刘文对传统集体主义不讲个体利益与价值的误解之说,其实这是两码事!
2. 传统集体主义以礼法为保障
刘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法制经济,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国家只能是法治国家。以此为基础,‘合法’、‘守法’就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基础性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5]此言固然有理,然而,其却因此反批传统社会的人们基于生产和交往的空间局限性而对国家集体之法则并不太关注,以致传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法律分离。换言之,其言传统集体主义是缺乏“守法”规范的与法分离的集体主义。
实际上,尽管人们基于小农经济的浓厚传统社会色彩而大都注重本族群内部的礼法规则,但是在等级森严的传统封建社会,人们怎能不守集体之大法,国家怎能不重权势之礼法!纵观传统社会,宗法性质之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及实践推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礼法之外。即便儒家倾向于重视家族小集体的礼法地位,其也没有忽视国家之大集体的礼法保障,诚如《唐律疏议》所载“谋反、谋大逆、谋叛”之践踏国家(圣王)集体利益的三大恶行,将给予“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其谋大逆者,绞”的重惩。毋庸赘言,法家更是强调集体利益的礼法保障,《秦律》明确规定,对君王(代表国家集体)“不忠”、“不孝”,不分贵贱,必处以死刑。诚如司马谈在《六家要旨》说言:“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矣,故曰严而少恩。”(《史记·太史公自序》)再如,清代江南宁国府太平县《馆田李氏宗谱》规定:“家法引:尽子道第一;笃友于第二;宜室家第三;睦宗族第四;立族长第五;别男女第六;严规则第七;锦茔墓第八;供赋税第九;澄忤逆第十;禁乱伦第十一;禁嫖娼第十二;戒邪淫第十三;禁赌博第十四;禁盗窃第十五;禁诈伪第十六;附:削不入谱。”[6]215通领其意,其主要揭示对两大集体利益的维护,即家族小集体利益和国家大集体利益。
所以,传统集体主义并不是缺乏“守法”规范的与法分离的集体主义。在传统社会,不论就家族之小集体还是代表圣王之意的大集体而言,人们基于对自身或家族利益的迫切考虑,都不得不守家族之仪则、尊圣王之礼法,从而融大小集体之共长之中。即便中国传统社会着重强调德主刑辅、以德配天,也强调格物致知、心性修养,但谁又能说,在森严等级的社会中,传统集体主义会游离于“法”之外呢?诚如《尸子·分》所揭示的:“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上下兄弟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另行,正名也……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3. 传统集体主义以天下为己任
刘教授认为,每个人既是家族的成员,也是国家的成员,他不仅应爱护家族利益,同时也应博爱他人并关爱整个国家利益。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所强调的“仁爱”只施于具有同一血缘的“自己人”。而对其他派别的“外人”,既谈不上“仁爱”,也不讲“人道”……对于远离“自己群体”的国家来说,更谈不上责任和义务。[2]换言之,其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也只是局限于这种群体和范围的狭隘集体主义,这种狭隘的集体主义缺乏“博爱”精神和“公德”意识。
其实,传统集体主义并不是只论爱己(家族),不论爱他、爱国的狭隘集体主义。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占据着主体性地位,中国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伦理原则,它强调家国一体的集体利益,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职责和义务,以追求家国安邦、天下太平为己任。这一价值观的展开,从根本上说遵循了爱己、爱他与爱国(天下)的逻辑主线,而并没有缺乏“博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可从儒家重要思想家的论述中得到诠释。当孔夫子主张“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精血,无权自残,毫发不可损伤”的“爱己”观时,也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的“爱人”观,更强调“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的“爱国(天下)”观。当董仲舒强调“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的己他仁义观时,也强调“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天下己任观。或者,撇开儒家集体主义价值观来看,墨家同样也没有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框限在个人或者家族小集体内部,而是诉诸于天下(亦称国家)。例如墨子通过强调尚贤的重要性来表达国之天下的发展道路,有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尚贤上》)再者,即便在中国近代社会,基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劣根性以及人们迫于建立一个富强之国的迫切性,有志之士仍怀着“杀身以成仁”的精神,抛头颅洒热血,为的绝不是小集体之家,而是将来能给全体国民带来福音的大集体之国。诸如,不论洪秀全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康有为的“平等自主,世界大同”的大集体主义理想追求,还是孙中山的以“民权、民族、民生”实现天下为公的现实努力,都寄予了建立平等、自由、博爱之和谐社会的集体主义伦理内涵。
因此,传统集体主义并不是局限于家族群体或其他行业范围的狭隘集体主义,也并没有缺乏博爱的精神因子。刘文观点对传统集体主义的阐述很大程度上只是站在传统社会固有的制度缺陷以及圣王君主的残暴昏庸立场上考虑的,而却没有看到人们骨子里怀着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精神对家国天下的孜孜以求。
三、传统集体主义的精华与糟粕辨识
纵观对刘文《不应该用传统视角理解现代集体主义》总论点的论理性商榷及分论点的事实性商榷可得知,传统集体主义并非是全然否定个人价值、游离法规之外与局限狭隘群体的不科学的集体主义,因而对传统集体主义应进行辩证理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 传统集体主义的精华及意义
传统集体主义不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近代社会,都凸显了其积极成分,值得现代社会汲取。古代孔子所倡导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第十八》)的集体主义意识揭示出人与禽兽的区别,表明人是社会的动物,应该过集体生活。这对于现代社会存在的人们个性过度张扬、私欲恶性膨胀、追求个体自由、贬低集体主义且与鸟兽有何异的部分现象不无启发意义。韩非子所强调的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八经》)、“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安危》)的集体主义规约揭示出国家集体利益的维护应该靠法律来保障。这对于打击现代社会存在的侵害他人、社会以及国家集体的犯罪分子,保障人们合法权益,推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墨子所强调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揭示出大爱无疆的时代精神。这对于建设富强文明之国家,促进与他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世界和谐具有重要启发。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提出的“群则强”[7]195、“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变法通议·论学会》)的集体主义信念;严复特别强调的“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能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8]1347的集体主义态度等对处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应对他国的恶意挑衅、如何缓解周边紧张局势、如何体现国家的凝聚力等具有震撼性启发。
2. 传统集体主义的糟粕及危害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处于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时代,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因此传统集体主义必然表现出与现代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的消极成分。这里侧重指出古代集体主义平等的缺失及近代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泛滥。古代集体主义是在宗法等级制度的历史框架下孕育生长的,其最显著的消极成分就是家族小集体内部或者家国同构的大集体外部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子民天子等之间差序明显、地位失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古代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以致上位者肆意夸大其权威、下位者无奈忍受压制。正如戴震激愤之言:“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孟子字义疏证》)反观现代社会,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平等,人们自身特有的种属尊严将被剥夺,现代社会将因缺失其应有的人性内涵而分崩离析。因此,现代社会应警惕古代集体主义人性不平等的消极成分回光返照,警惕其在现代社会制度建设中的不时渗透,警惕其被现代社会某些利益集团恶意强加。在近代社会,集体主义的内涵尽管有别于古代社会,其更加关注人的平等,要求集体成员“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然而,近代集体主义却因对“平等”的唯心向往而陷入了平均主义的境地,它抹杀了劳动报酬上的差异性,否认了按劳分配原则,把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无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利于竞争性团队集体的壮大,更不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综上所述,通过对传统集体主义科学性的考辩可知,对传统集体主义这一理论命题是否科学的定论不仅要符合基本的逻辑理路,也要经得住证伪的多重挑战,更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求范式证成。同样,通过对传统集体主义三大分论点的阐述可知,对“传统集体主义是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片面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是局限于狭隘群体的狭隘封闭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是缺乏‘守法’规范的与法分离的集体主义”应提供足够的证据,更要保证这些证据足够的可靠。否则,就应该站在辩证的立场来看待传统集体主义,批判摒弃传统集体主义的消极成分,弘扬发挥传统集体主义的积极效用。
[1]尚智丛,高海兰.西方科学哲学简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2]刘天喜.不应该用传统视角理解现代集体主义[J].兰州学刊,2004(3):73-74.
[3]库 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4]李大钊.李大钊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5]刘天喜.论集体主义的现代涵义[J].攀登,2004(5):37-38.
[6]朱 勇.清代宗族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7]康有为.康有为全集(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严 复.严复集:第五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