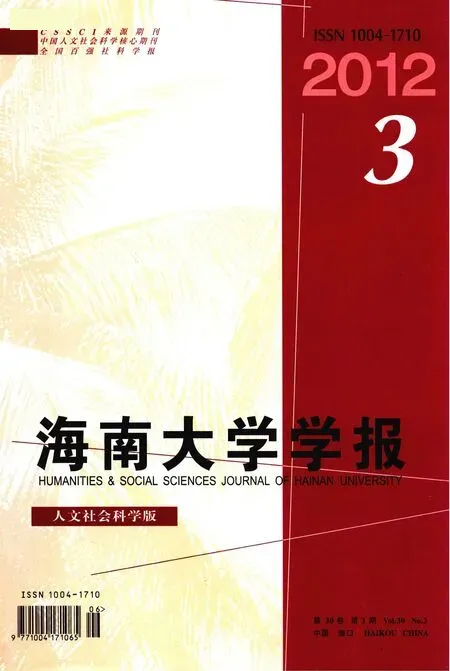于民间大地慨然挽唱——论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
周会凌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ZHOU Hui-ling
(Depar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于民间大地慨然挽唱
——论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
周会凌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迟子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关于历史题材的写作占重要位置。作者以北国故土这一特定的地域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以民间立场与浓厚的悲悯情怀去观照历史,其作品显现出历史背幕下气韵生动的民间人物形象、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美学、灵魂挽唱中的死亡哲思的创作特征。在其小说冲淡温厚的文字深处是对于民间大地与生命存在的慨然挽唱。
民间;日常生活;死亡叙事
对于历史的书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这是文学对消逝的历史的一种深刻缅怀与永恒追忆。王德威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小说夹处在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1]历史并非只是史册中一个个僵死而堂皇的文字符号,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构成的,是对于人的存在的生命纪录。文学之于历史,就是让人们超越那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历史年份,以具象的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呼号来触摸历史之脉搏动的温度,倾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对于历史有质感的理解与领悟。
历史题材的写作在迟子建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中占重要位置,从她2000年的《伪满洲国》到2005年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2010年的《白雪乌鸦》,无论是书写一个区域的时代历史还是一个民族的演变历史,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迟子建的创作中都显得格外厚重。
一、历史背幕下气韵生动的民间人物形象
迟子建在近年来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用文字去逼近历史,低吟咏叹民间大地,为无数小人物的挣扎困顿的灵魂挽唱,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文学性的体认,是对传统历史叙事机制的一种叛逆与超越。因为文学的一大价值就是去言说那些散落在固化历史缝隙中细屑而鲜活的生命存在,去勾勒与描摹那些民间小人物在宏大的历史面前的各式生命姿态与灵魂呼喊。而这需要作者有一种既宏大又绵密的想象力,需要在民间与历史之间打通一条精神通道,聚焦于历史时代下的民间个体存在以及他们的多舛命运,这是文学对于历史遗忘的抵抗,推动着历史叙事由宏大转向细节,从而获得生命的温度。
“民”,即小人物,是民间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社会的主体力量。学者陈思和的“民间”理论认为:“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的审美功能”[2]。他认为“民间”有着巨大的包容性,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相处,有光彩照人的内容,又有藏污纳垢的形态,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由此可见,“民间”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空间与视界。迟子建的文字始终紧贴民间大地,以一种真挚的民间情怀,始终关注那些民间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理想追求与精神困境,处于对民间底层生命景观与精神气质的温情观照中。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在鄂温克族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塑造了大批民间人物群像,在他们身上凝聚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伊莲娜是鄂温克族第一个大学生,成为了有名的画家,当她彻底厌倦城市之后,回到家乡却发现一切都已经溃败,她倾力创作了一副妮浩萨满祈雨图,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深切情感。伊莲娜面对着人性的困境,有一种处于城市文明与故乡自然之间的灵魂撕裂感,其身影背后折射出鄂温克民族对于自身为现代文明侵蚀与消解而趋于衰败的一种民族心理的巨大焦虑感。《伪满洲国》中,作者在深宏的历史背景下,作者没有将笔墨集中在像皇帝傅仪、王妃等历史中的显赫人物身上,而是致力描摹民间人物群像,有手艺人、商人、土匪、乞丐、农民、劳工、奴才、小知识分子,也有对于细菌试验极其狂热的日本军医与厌恶战争的日本军官……展现了一个个面容生动血肉丰满的民间人物,表现这些生命个体在历史风云变幻下的独特生命形式与灵魂律动,着力于去发现湮灭于历史深处的民间小人物卑微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的幽微。
《白雪乌鸦》以民间视角去重现历史中的“东北大鼠疫”,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这座城成为作者吟唱悲楚而悠远的灵魂挽歌的悲悯大地。面对疫灾与死亡,真正的承受者原本就是生活在这块黑土地上的民间小人物,正是这些卑微的底层小人物用自己的肩膀承受命运,直面死神。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历史时空中边缘化的卑微个体,民间独立的个体成为了承载历史与诠释历史的主体。由此小说中那些民间三教九流的小人物有着一种灵动的性情,作者以白描写意之法,于点染勾勒之中使人物意态尽显,神韵流动。如外表冷艳如冰但内心却情痴意酽的陈雪卿,因自己爱的红胡子男人死去而托孤殉情;有着胜过须眉的文思才情的厨娘于晴秀,醉意之下更显其本真纯然的心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翟芳桂,最终与俄罗斯鞋匠相惜相怜;能酿好酒的热血汉子秦八碗,因疫情而不能送老母灵柩返乡竟以死殉母,堪称至孝;还有散尽家财为乡邻,与于秀晴心有灵犀的义商傅百川;嬉笑活泼,生性纯良的报灯名的少年喜岁;一生怯懦窝囊,却对俄罗斯歌唱家谢尼科娃有着深切而无望的恋慕之情的车夫王春申;还有那个在宫中受尽屈辱变得阴鸷无赖,可怜又可憎的太监翟役生,面对死亡时那沉痛而又疯狂的自我剖白,直指人性中的阴暗。作者给予种种庸常而没落的人生一种深切的悲悯,去言说每一个怀抱俗世理想的小人物背后哀切的故事与伤痛的呼号。这些淹没在庸常人生的人们,在灾难与死亡的冲击之下,仍然能聆听到自己心灵深处的呐喊。
风云变幻的历史往往是作者笔下的苍茫背幕,她并不执著于去刻画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伪满洲国》中的杨靖宇的描写,作者淡化了英雄人物身上的浓墨重彩。还有《白雪乌鸦》中的伍连德这个人物,历史中确有其人,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在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的国危之下,他主持当时东北防疫工作并取得成功,堪称为英雄。作者在小说最后虽较多着墨于伍连德,但其始终显得形象模糊了些,远不如作者笔下那些民间的性情汉子与灵秀女性来的那般气韵生动。这不失为遗憾之处。此人物是一个可以在历史中承载“历史决定性瞬间”的人物,也是能让这部怆然而大气的作品更具历史沉郁之神的一个人物。也许是作者无意塑造“英雄”的形象,更执意于那些沉凐于历史尘埃中的民间百相,从人性的视角去刻画民间人物群像。
迟子建始终以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去关注历史背幕下的民间底层人物,在残酷而庸常的民间生活细微处去捕捉人性善的存在,并将其作为这些小人物对抗厄运与苦难的精神力量,从而展现民间历史背后丰富而复杂的生命景观,它是与丰饶的民间大地血缘相连的,让人们感受到民间血脉强有力的搏动与温润的生命热度。
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美学
真正好的小说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有深刻而宏大的主题之外,无不以真实、准确而丰盈的细节与材料来支撑。正如评论家谢有顺之言:“小说是由经验、材料、细节构成的。如果小说的物质外壳(经验、材料、细节)失真了、不可信了,那整部小说的真实性也就瓦解了”[3]。在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以东北大地的地域文化为背景来构建自己独特的艺术空间,并以细腻而温情的笔触进行日常生活美学的书写,使其小说有着丰厚而坚实的生活质地,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也许正像迟子建说的那样:“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浸透着我对历史的思考,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孤立的和割裂的,它与现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我总觉得仅仅凭吊历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能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4]正是在作者这种对于日常生活图景的重视,成为作者对于历史的民间化书写的物质基点,由此产生了一种真实而厚重的历史感。
《白雪乌鸦》中,作者准确洞察到历史中最为恒常而丰厚的底子——民间日常生活,小说中生活实感层面的细节以坚实的史料为依托,温情的书写民间日常生活的寻常巷陌与纷繁百态,再现百年前的那个破败不堪而又烟火蓬蓬的傅家甸,重现历史中东北边地的民间俗世生活景观。小说让读者跟随着王春申的马车,将1910到1911年“东北大鼠疫”期间小城傅家甸的世情画卷徐缓展开,这里杂居着中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集聚于此,柴米油盐、买卖送往与生老病死每日都在发生。王春申家的三铺炕客栈、翟桂芳家的粮栈、周耀祖家的点心铺、罗扎耶夫的鞋铺、傅百川的傅家烧锅……各色人等轮流登场而又相互联系,以片断连缀的方式呈现出鲜活的民间世情百态。其独特之处是将民间日常生活放置在灾难与死亡这样宏大而残酷的背幕下来书写,猝不及防的灾难性死亡与琐屑恒常的日常生活相并置与反衬,散发一种独特的悲情与残酷意味,以一种日常性生活“实”的丰厚底子来透出一种突发性死亡“虚”的凛冽冷光。由此而呈现出灾难与死亡到来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如何由常态渐趋扭曲与变形,突显人们灵魂上的惊悸、恐惧与绝望。以一个个生命个体的覆没,铺展了一个历史瞬间的惨烈与悲怆。
《伪满洲国》讲述了从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到1945年傅仪退位的十四年历史,但作者并不热衷于对战争进程与场面的书写,而是着力于用绵实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在日本控制的伪满傀儡政权下中国城乡底层百姓的世情画卷,如伪政权皇宫、民间百姓杂院、极乐寺、日军监狱、哈尔滨的妓院与大烟馆、奉天的当铺还有杂货铺,让人们在王金堂、狗耳朵、王小二、紫环等民间底层人物的一粥一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与生老病死中,在这些丰盈的历史物质形式中,看到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痕迹,使作品具有了历史的深邃实感。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对于鄂温克民族近百年的苦难历史与文化变迁都是通过对其日常生活与民族习俗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展现,弥散出原始自然的浓郁民族性,如驯鹿放养的方法、狩猎活动前后的仪式、锯鹿茸与挤鹿奶的场面、“希楞柱”的搭建、妇女分娩时搭建的“亚塔珠”,等等,展示了民间世界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常态、行为方式和民族文化形态,以此而展现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在这种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美学书写中,迟子建小说中除了对于北方民间的衣食住行的描摹之外,还对其节日习俗、民族婚丧礼仪有着细致而丰富的描写。如《伪满洲国》中展示的鄂温克民族的独特丧葬风俗:将安放着死者的桦皮棺材吊在粗壮的樟子松树上,一周年忌日之时,亲人再为死者举行正式的祭悼仪式。还有《白雪乌鸦》中周耀祖一家人在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一处,作者笔触细致的描摹了北方民间祭灶时的饮食讲究、仪式程序与民间传说。像这样对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细部描摹在小说中多处可见,作者温情的描绘着民间生活的细碎、零乱、平淡与鲜活,于杯水微澜处发现生活中温情的一瞬,使得小说创作浸染了一种冲淡的美学风格,即使是处在灾难性死亡的阴霾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停留在对于历史物质层面的书写,而是在其中寄寓着深刻的人性哲思与精神指向。福斯特认为:“不管哪种日常生活,其实都是由两种生活,即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我们所作所为也要显示出具有双重的忠诚。”[5]这里的“双重的忠诚”意为写作者不仅要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日常生活秩序本身,还要将其内蕴价值挖掘与提炼出来,以期突显出它内在的精神价值。迟子建小说中对民间日常生活细部的关注与呈现,除了描绘北国边地的世情画卷或民族百年变迁图景,淋漓而鲜活而渲染出了民间那烟火缭绕的俗世生活之外,还于温厚而琐细的日常生活美学中具有了哲学思辨的意义。恒常的世俗生活与常态的人生被到来的不可知的“变”所打破,这种不可知的“变”可以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历史进程中无可拒避的现代文明,也可以是《伪满洲国》中历史的滚滚车轮,还可以是《白雪乌鸦》中猝然而至的灾难与死亡,从民间立场来看,深刻展示了民间大地的生之艰辛与生命苦难,于历史、灾难与死亡的深邃、猝然与残酷中,去哀唱伤咏一曲曲民间生死哀歌,展现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民间万千生命的生存与寂灭,体现出在历史的延展之中,民间丰饶大地所集聚与沉淀的大智慧。
三、灵魂挽唱中的死亡哲思
迟子建执著地用文字回返历史,抵达民间,但这并不是作者惟一的精神姿态,“死亡”是其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写主题,她善于用一种温情的笔触去描绘死亡,试图在死亡濒临时绝望而宏大的苍凉感中,将死亡作为生命的图腾来记忆与纪念那消逝的历史与生命。并以一种民间视角,在死亡叙事中呈现出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与对生命存在的哲思。因此,作者始终以一种悲悯的眼神来凝视死亡的冰凉与黑暗,意图去驱散它们,淬炼成为一种由死而向生的信念,凸显出人性的光辉与坚韧的精神品性。
哲学家傅伟勋认为“每一个人的实存主体面对死亡的态度有其俨然不可(由他人态度)替代的独特性、尊严性。”[6]《白雪乌鸦》中灾难性死亡的突然到来,猝然而持续的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生活行为,从而让每个人内心被死亡这巨大的黑色阴影所裹挟,一下剥落了附着在个体生命上种种庸常卑俗的欲望,而让潜藏在深层自我中的灵魂凸现出来,让人们清晰的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呻吟。作者正是在死亡阴影下去展现民间生命个体各式的生命姿态与灵魂呼喊,从而探寻生命的光辉与人性的闪亮。鼠疫最猖獗时,周济全家义务为被隔离的染病者每日运送饭食,最终祖孙三代都染疫身亡的善行;在疫情面前医官伍连德力主焚尸切断感染源,宁愿掉脑袋也将为之的只为天下苍生的勇毅;商人傅百川在疫灾中散尽自己的家财来支持防疫工作的义举;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带着女儿娜塔莎在教堂为鼠疫患者募集善款,最终母女二人都感染疫病谢世……当死亡呼啸而来狞笑着碾压过众人如草芥般的生命时,还应看到另一种死亡方式的存在,那就是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自杀。小说中陈雪卿向翟桂芳托孤之后为爱殉情、秦八碗因孝而剖腹自尽。一为爱情一为亲情,这是民间底层的生命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的选择。也许,在死亡面前留存下来的东西才是生命所真正完成的东西。作品以猝然的死亡来折射出民生的艰难、无奈与惨烈,但“死亡”只是一个切入点,是对民间现实生活与生命个体的存在作一次切片式的凝思与感悟,其终极意义是对于“生命”的抚慰与哲思。
《伪满洲国》中的手艺人王金堂,原本靠弹棉花与老伴过日子,却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离家十年,在劳工营中经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让他恐惧的是他亲见身边年轻的同胞一个个被折磨而死,他在死亡的巨大阴影下以自己的毅力与智慧奇迹般的渡过了漫长的十年,最终重见天日,在他对于死亡与命运的绝望反抗中,让人对其坚韧甚至是强悍的生命而感叹不已。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尼都萨满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跳神的方式杀死日军的战马来保护自己的族人。后来的妮浩萨满运用自己的神力与仁慈之心去一次次挽救他人的性命,却不得不面对着自己的孩子接连死去的残酷现实,最后她用自己的生命祈来倾盆大雨,用以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保护家园,面对着死亡与生存的抉择,让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感,但最终人性中的善良与仁慈击败了与生命随行的苦难,也展现出来自民间的不息生命强力与崇高精神,也是民族精神与深层文化心理的展现。同时,妮浩萨满的死亡还有一种深刻的隐喻意味,鄂温克族最后一个萨满死去了,也许鄂温克族的民族文化和萨满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也面临着“死亡”的结局,这也展现出作者对于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命运的深刻而沉痛的思考。
迟子建的作品中从来都不乏苦难与死亡,但其并不迷恋关于死亡的书写,并未浓墨重彩的渲染死亡的血腥与烈艳,对于死亡主题的执著书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种真实可感的直逼生命真相的凝视方式。她的笔触中始终弥散着一种温情与敦厚,执著的于黑夜中去找寻人性的点点星光,为的是驱散生之悲凉与死之绝望。作者正是在这些平实而卑微的民间生命面对死亡的精神姿态与灵魂呼喊,敏锐的捕捉到民间的“集体无意识”,譬如善良、坚韧、亲情与爱情,从而来阐释民间生活与文化中某些永恒而坚实的精神魅力。这是文学对于生命的凝视,是对于生命存在的真诚悲悯与深刻哲思,从而获取超越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在充满嘈杂与琐屑的生活中,也许正是死亡让人们开始对生命存在进行一种思考与反省,正因如此,死亡具有一种对于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意义。
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会上,诗评家谢冕宣读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辞是“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7]其实这些话语同样适用于迟子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她始终以温情的眼神与悲悯的情怀来凝视与书写历史背幕下处于苦难与死亡阴影中的人们,用文字来承担与命运相随而至的灾难、来铭记历史纵深处那些被忘却的生命,以此来抵抗生之艰辛与死之绝望。
如果说《伪满洲国》是一段殘山剩水的沦陷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一部鄂温克民族的秘史,那么《白雪乌鸦》是一曲对于笼罩在鼠疫阴影之下的东北大地的悲悯挽唱。作家对于东北大地有一种执著的情结,也许这即是她精神上的原乡。作者保持一种民间立场,以伤怀而深情的目光去凝视这块广袤黑土,将那湮灭于时光之中的历史还原其鲜活生动的民间生活原貌,描绘出边地生活的风俗民情,释放出其中孕藏着旺盛而坚韧的生命强力,呈现出一个烟火蓬蓬而又勃然生机的边地世界。作者着意去刻画历史中的民间人物群像,在或悠远或沉痛的历史背幕下,在人性、命运与历史存在的种种冲突中,将民间人物的俗世生存景观凸显出来,将他们的生命轨迹勾勒呈现,于民间大地为已然逝去的历史与灵魂慨然挽唱。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3:1-2.
[2]陈思和.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J].福建论坛.1999(3):44-50.
[3]谢有顺.小说的物质外壳:逻辑、情理和说服力[J].当代作家评论,2007(3):36-46.
[4]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J].艺术广角,2006(3):34-35.
[5]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6]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M].台北:正中书局,1993.
[7]谢冕.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奖辞[J].小说选刊,2007(12):24.
Singing Tragically a Dirge in the Folk Land——on CHI Zi-jian’s Novel Writing
Historical subject takes a major part of CHI Zi-jian’s novel writing in recent years.Taking her north homeland as a given set,she constructs her art world and observes history from folk standpoint and with compassionateness.Her works characterizes with vivid folk images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aesthetics of daily life with local culture,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death by singing incorporeal dirge.Hidden in her placid and rich words is a dirge tragically sung for folk land and life being.
folk;daily life;narration of death
I 206.7
A
1004-1710(2012)03-0036-05
2011-09-05
周会凌(1982-),女,湖南洪江人,中山大学中文系2009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林漫宙]
ZHOU Hui-ling
(Depar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