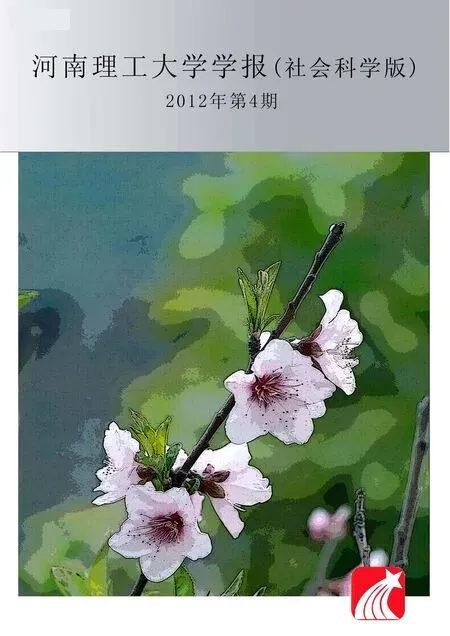抗战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高等工程教育
周志远,张尚字,洪振涛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焦作 454000)
抗战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与西北高等工程教育
周志远,张尚字,洪振涛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焦作 454000)
抗日战争时期,私立焦作工学院西迁陕南,与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东北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不仅保存了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的文脉,而且以雄厚的师资设备、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优良的办学传统,鼎力支撑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融入了抗战救国、传播文明、开发西部的时代洪流,为巩固和发展抗战后方的高等工程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救亡;焦作工学院;西北联大;高等工程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始建于1909年、地处中原的我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私立焦作工学院奉命西迁,与当时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开启西北工程高等教育之先河,在陕南古路坝度过了八年峥嵘岁月,巩固和发展了后方工程教育,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灿烂篇章。
一、勇挑国难:私立焦作工学院西迁办学的始末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焦作工学院西迁办学,是中国抗战期间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和勇挑国难、抵御外侮的民族气节,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高等教育根基的图谋,开启了我国战时高等教育迁移内地、保存实力、服务西部、抗日救国的壮丽实践。
(一)西迁办学:救亡图存的非凡壮举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汉铁路继续向南进犯,迅速把战火燃烧到豫北,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为了不使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沦入敌手,院长张清涟迅速呈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慨前车之可鉴,允宜未雨而绸缪,拟在紧急时期,择定安全区域,预将图书、仪器、机械、文卷、表册等件之一部或大部,迁移保存,以备将来之用。”在征得同意后,中福公司总经理、常务校董孙越崎权衡迁校地址之利弊,命令学校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和实习工厂的机床等教学用具,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一并迁往西安。10月20日,院长张清涟率师生将160吨仪器设备和图书全部搬上由孙越崎亲自安排的铁路车皮,假道郑州,举校西迁,于24日抵达西安。为了不使教务停顿,遂租借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部分教室及西京机械修造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西北高等教育由此新增一支重要力量。次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军攻占风陵渡,开始派军机侵扰轰炸西安。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学校决定再迁甘肃天水。由于当时陇海铁路刚通至宝鸡,公路运输力量极其薄弱,全校师生自陇海铁路虢镇站起,长途跋涉500余里,“峡谷寒风,陇州暮雨;关山晓月,驿路晨霜;山泉冷饮,冰河盥漱,行歌道山,谈笑峰巅”,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完成迁校任务,成为天水最早的高等学校。不久,学校以天水南郊水月寺为临时校舍开始上课,并在天水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祭出了“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设,当前责任不让人”的楹联,演出了抗日救亡话剧。这年暑假,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在天水毕业。
焦作工学院的西迁办学,不仅为战时西北高等教育发展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而且在西部地区播撒了科学文化的种子,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敌后的深入开展。尤为重要的是,焦作工学院并没有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和省内各学校一起迁往豫西南,而是撤迁中国大西北,从而减少了战火袭扰,免受当时如河南大学“潭头血案”之劫,保全了中国第一所矿业大学的文脉,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奠基保存了实力。
(二)合并改组:抗战救国的教育实践
在焦作工学院西迁天水之际,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的西安临时大学,也奉命迁往陕西城固,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由北洋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组成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独立建院。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集中师资和设备,巩固发展后方工程教育,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并附发《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办法》、《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简章》,对筹委会的组成、经费支配、院系编制、教职员、学生、校址、校产等事宜作了原则规定。8月10日,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任筹委会主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文华和教育部代表张北海等为筹备委员。之后,相继通过筹委会组织大纲(草案)、学校组织规程和计划大纲,并确定校址暂设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意大利天主教堂,设置教务处、总务处、训育处等管理机构以及矿冶工程学系、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工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水利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系和工科研究所、学术推广部、矿冶研究部等教学科研机构。10月,招收首批学生。11月,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院长张清涟的率领下,从甘肃天水乘汽车迁入国立西北工学院,图书、仪器及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分别从西安、宝鸡、凤翔、天水运往城固古路坝。11月12日,西北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西北工程高等教育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实现了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四所名校的强强联合,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工科大学。如1948年《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院史概略》所载:“四校在战前,办理完善,声誉素著,本院集四大工程学府之精萃而成立,虽经乱离,而教授人选,图书仪器,亦复蔚为大观。”焦作工学院也由此开始了八年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
(三)洛阳复校:情系桑梓的薪火传承
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焦作工学院随校西迁的师生主要分布于矿冶工程学系和土木工程学系。他们在古路坝潜心执教、发奋学习的同时,仍情系桑梓、心怀故土,时时怀念在焦作工学院的美好时光。特别是共同奋斗经历所熔铸的焦工精神,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把焦作工学院的师生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但与此同时,“过去之历史,日久不彰,未来之重任,事浮莫属”的担忧也时常在原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涟的心头萦绕。为“联络情感、砥砺学行,辅助母校发展”,负起继往开来之使命,在张清涟倡导下,1939年6月12日,原焦作工学院师生在陕西城固五圣山成立校友会,通过《焦作工学院校友会总会简章》,推举张清涟为校友总会会长。校友会最初下辖西康、甘青、西安、城固、重庆5个分会,并设计制作了校友徽章。1942年10月,编印《焦作工学院校友录》,张清涟在序言中勉励校友:“如何发扬旧精神,如何树立新生命,皆为本会之职责。愿与诸校友共同策励之!”这些举措,对于加强校友联络、凝聚焦工师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后来焦工复校奠定了基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西北工学院内载歌载舞、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复校大计也开始在焦工师生心中酝酿。8月31日,私立焦作工学院复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孙越崎等联名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尽快复校并由张清涟参加全国教育复员会议。信中指出:“焦作虽属小镇,地处晋冀豫三省工矿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良。本院设置于此,允称最为适宜。”10月15日,教育部批令国立西北工学院将原属焦工的图书、仪器、设备归还,以利焦作工学院在原址复校。但受时局影响,焦作工学院先是落脚开封,与国立河南大学互助合作,继续筹备复校大计;后最终于1946年在洛阳关林复校,当年招录新生232名,11月15日正式上课。至此,辗转飘零九年之久的焦作工学院得以浴火重生。
焦作工学院的成功复校,既是战后教育复员的大局使然,更是焦工精神凝聚、校友极力斡旋争取的结果。它不仅使得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文脉延传,“其灵光巍然,弦歌未尝一日辍”,更激励着广大师生和校友“提起精神,创造青出于蓝的新牌子,建设新焦工”,并在后来孕育出河南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矿业高等学府,成为我国矿业高等教育的发源与中坚。
二、矢志不渝:鼎力支撑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发展
在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年代,焦作工学院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雄厚的师资设备、丰富的办学经验、优良的办学传统,鼎力支撑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办学,为巩固和发展抗战后方的高等工程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同舟共济:开启西北高等工程教育先河
早在焦作工学院筹备西迁之时,常务校董孙越崎即明令学校:“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西北工学院筹建时,西北联大工学院和东北工学院经多次迁徙,图书、仪器、设备几乎损失殆尽。而焦作工学院至1935年物理、化学、地质、采矿、冶金、试金、测量、材料、水力等仪器设备、矿物标本、土木模型总值已达125 479元[2],西迁办学时,除个别特大型设备外,其图书、仪器、设备及实习工厂机器几乎是完整西迁。运抵古路坝时,雇用汽车约87辆次。1938级校友师昌绪在回忆西北工学院时曾说:“那时我报考矿冶系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那时实业救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开矿炼钢当属首位;二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福中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到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因而报考了矿冶系。”此外,西工的图书馆藏书主要也来自焦工,1940年馆藏的15 257册图书中,来自焦工的图书就达13 101册。以至西工筹建时,他校师生但凡见到焦工师生,言必问:“焦工图书来了没有?”正如孙越崎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3]
事实上,焦作工学院对西北工学院的贡献,远非仅限于仪器、图书等硬件条件的支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校已汇聚了一大批“留学欧美,在彼邦有工程经验,在海内有教书成绩”的师资队伍,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西工筹建时焦工教授不下15人(四校共有教授62人);在三组共5人的接收委员会中,焦工就占了3人。特别是后来担任西北工学院事务主任、训导长等职的张清涟院长,为我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冶金学家,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毕业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其“学识优良,经验丰富”,“颇能兢兢业业,锐意精进,处理校务,亦擘划有方”[4]。他们将焦工的丰富办学经验和优良办学传统带到西工,与其他三所高校风雨同舟、戮力同心,终于使得西北唯一工程高等学府放射出灼灼其华的耀眼光芒。
(二)作育栋梁:打造高等工程技术人才基地
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后,焦作工学院的教职员大多留任于各学系、研究所(部)及管理部门。张清涟、胡季纯先后任事务(总务)主任;任殿元、马载之、李余庆、石心圃、朱端、张卯均等任教于矿冶工程学系,任殿元教授为该学系主任;谢光华、徐百川、胡季纯、许继曾、沈季良、杨大金等任教于土木工程学系;彭荣阁、余立基等任教于水利工程学系;张景淮等任教于航空工程学系;马书润、唐绍宗等任教于化工工程学系;杜春山等任教于机械工程学系;王允升为公共学科体育副教授。王洪涛、王魁元、李振亚、曾冀泉、王喜麟、李树栋、胡昌来、樊宝莲等任职于各事务部门[5]。由于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他们只有租住在天主教堂附近当地人喂牲口或堆放杂物的房子,白天忙于授课,夜晚则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教授月薪500元左右,1942年8月,每袋面粉也涨至500元左右,其窘况不言而喻。”[6]但他们依然刻苦钻研,严谨执教,颇受学生敬仰。如马载之教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讲课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启发有术,是著名的授课名师。西工合组时,筹委会主任李书田得知马载之由汉中启程,步行出校远迎40里;他校师生凡见焦工师生,必询问“马载之教授来了没有”。李余庆教授“嘉惠后学之精神,极堪敬仰”。青年讲师袁耀庭学业基础深厚,教学内容娴熟,分析问题透彻,思路敏捷,讲授得法,效果出众,深受学生推崇,被誉为当时西工的“四大金刚”之一[7]。由此可见焦工教员在当时的影响。如张清涟所言:“自是本院教务暂告停顿,前途发展,不无影响;然本集中力量之原则,以辅助战时教育计划之实施,其作育人之精神,初无二致。”[8]1-2
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初期共有8个学系,其中矿冶工程学系为焦工采矿系和北洋矿冶系合组而成;土木工程学系为焦工路工桥梁系与东工、北洋土木系合组而成。当时,学生虽然只能挤住在教堂的桶仓式房子里,依靠政府发给的菲薄“贷金”维持学业,但他们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在艰苦的环境中练就了坚毅品格,以至于古路坝和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处处闪烁,“古路灯火”遂成战时高校一大奇观。这一时期,西北工学院先后招收学生2 330人,原焦作工学院8个班的学生共97人分别于1939年至1942年毕业。孙越崎曾深情地回忆说:“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抗战后方新兴的工矿企业和交通发展提供技术力量。很多毕业生被聘到甘肃玉门油矿和四川天府、嘉阳及威远等煤矿工作,其中不少人至今尚在国家重要企业中负责煤矿技术工作。”[3]
(三)考工致用:探求抗战建国之需工程学术
焦作工学院以“教育英才,备物质建设之先锋;从事研究,求吾国学术之独立”为使命,向来重视学术研究。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学校因抗战救国和西北地区生产事业的现实需要,成立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和工程技术推广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工矿技术改良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任殿元主持矿冶研究部工作期间,积极推动调查研究工作。1939年,工程学术推广部附设的化工实验工厂研制成功肥皂、蜡烛。1942年,矿冶研究部的石心圃教授经过调查研究,撰写出《关于调查沔县、略阳一带煤铁等矿并采集矿物及岩石标本的报告》,指出:“沔县民生公司所产之煤,经试验所炼之焦(炭),为全省之冠,沔县窑沟及略阳一带铁矿质量均佳。”同年,教育部拨款15 000元,指令矿冶研究部调查西北矿产,研究部指派石心圃、马载之教授为该课题的实际承担人。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时半年,撰写了《佛坪县铁矿调查报告》,认为佛坪铁矿“矿质纯洁,硫磷极低,为炼钢之上品”。1943年,任殿元、石心圃教授到汉中调研略阳一带之土法炼铁之改良问题,并草拟了《改良土法炼铁之说明及试验计划》。此外,1941年,矿冶系李余庆教授被聘为青海西宁西北区采矿处总工程师,技术服务近一年,1943年,他与图书馆王洪涛主任在陇南主持金矿开采。这些科学研究实践,为扩大抗战时期战略物资的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奠定了西北工程学术的基础。但由于受研究经费、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所开展的研究大多面向生产现场,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高层次基础理论研究不多。
1939年6月,学校成立了编译委员会。鉴于焦工创办学术期刊的经验,编译委员会三级领导全由焦工教职员出任:张清涟任主席,杨大金任专门委员,李振亚任出版组组长。张清涟主持通过了《编译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委员会以“编译书报,发扬工程学术及有关自然科学”为宗旨。9月,编辑出版《国立西北工学院季刊》,栏目分论著、计划、调查、设计、特载、杂俎等,刊发“富研究性之工程论著,或调查及与抗战建国有关之具体建设计划”。院长赖琏在《发刊词》中指出:“吾国工程刊物,无论数量与质量,均难与欧美各国相比衡。在此抗战建国之大时代中……工业人才已感供不应求,工程刊物尤有尽量扩展之需要。”“今更编纂定期季刊,发表本院师生研究考察之所得”,旨在“增进全国技术人员研讨工程学术之兴趣”,为西北开发“树之风声”。学校编译委员会还编辑出版了《国立西北工学院丛书》、《国立西北工学院通俗工程丛书》。1940年,学校创办期刊《西工友声》,刊登“服务社会之经验,研究学术之心得,以及改革事业之建议”等方面的论文。这些刊物的创办,对于提高学校的学术知名度及追求学术研究之独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文化长征:高扬在西北高等教育的焦工精神
焦作工学院西迁之前,已有近30年的办学历史,在“实业报国”思想的激励下和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孕育的独特文化品质,熔铸形成了焦工精神。西迁办学不仅是一次人员和物资的迁徙,更是一次文化的长征,焦工精神对于西北工学院的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矿魂斯扬:办学宗旨之坚守
焦作工学院的前身焦作路矿学堂,最早是在“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下,为“培养路矿专门人才”而创立的。及至后来“养成采矿冶金专门人才”、“教授工程学术,养成建设人才,以应社会之需”,再到“研究高深学术、培植专门人才”,无不体现了学校服务工矿的办学宗旨与方向,彰显了“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的办学目的与价值。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焦工的矿冶高等教育不但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壮大。据1948年6月《国立西北工学院概要》记载,从1939年至1946年,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学生394人;矿冶工程系毕业学生165人,其中采矿组107人,冶金组58人,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沛霖、李恒德、师昌绪、刘广志、傅恒志等是这一时期矿冶系的杰出校友。矿冶研究部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石油地质组,这也是焦工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践。1939年张清涟在《七一志游并赠毕业同学》诗中写到:“遄来古路坝,弦歌满山丘……煤田问疾苦,生产羡美欧”,显示了学校培养矿冶专门人才的办学宗旨已延续至西工。这一时期,西北工学院确立了“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及发展西北地区工业”的宗旨,这与焦工之办学宗旨,既有传承,亦有创新。学校在西北地区开展的陕南煤矿勘测、广元和昭化等地金矿调查、两当山硝矿设计等一系列科考与研究活动,也充分彰显了服务于国家工矿业发展的崇高追求。
(二)通专并重:教育思想之传承
在西迁之前的近30年办学历程中,焦作工学院形成了“学富”和“学贵专精”、“学重专门”相结合即通专并重的教育教学思想。张清涟主校时,曾针对课程设置提到:设置国文、经济等普通课程,是要“培养工程师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并授以发表意见之技术与实际工作之境地,范围广博,用意精微”;设置算理化图等基本课程,“所以起工程学术之宏规,验学生个性之适宜与否,乃解决择业问题之最后阶段也”;设置土木、机电等辅助课程,“所以辅助采矿冶金各项工程使有实现之可能也”。西迁办学时期,“通专并重”的教育教学思想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全校九个学系一年级公共课程和基础课设置完全相同,学生不分系科混合编班,二年级各系课程完全相同,三、四年级分专业精心进行课程设置,这与20世纪30年代焦作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如出一辙。1940年,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在对第二届毕业生的训词中指出:“工程人员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更应有充分的普通知识;否则,一旦观感幼稚,判断谬误,小之被人讥为坐井观天,大之就可影响毕生的事业……纵有专门技能,也难成为健全的工程人员。所以,你们对一门自应精通一切,对其他部门,也应略知梗概。”[9]这一教育教学思想,对于西北工学院的人才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这一时期毕业生中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荟萃、名家迭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学用结合:教学理念之发展
作为一所培养工矿人才的大学,焦作工学院坚持学用结合、尤重达用的教学思想,把学生实验和实习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务校董李文浩认为:“研究科学,专从书本上用工夫,犹如闭门造车,难以合辙,隔靴搔痒,不得要处,结果不能成功,必须要于研究科学的时候,同时对于自然界的有机体无机体,作实际的考察,俾理解其现象与原理,则科学的知识才能充分。”[10]在焦作办学时,学校充分利用与中福公司矿厂关系密切之便利,组织学生深入矿厂实习,着力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以使学生“朝夕渐摩、易有心得”,“学理与应用互相证明”。合组西工后,这一教学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学校把实习和实验视作“创作和发明的祖先,有了它,才能造出宇宙间的奇迹来”[11]。尽管抗战时期经费紧张,学校还是尽力补助路费,鼓励学生利用暑期到工厂实习,以使“学生在校时,一面课以书本,阐明理论;一面授以实际工作,供其揣摩,二者互相引证,事半功倍,俾将来服务社会时,一切问题,均能得心应手,而无格格不入之苦”[9]。学校依此原则鼓励学生深入生产一线,以工程技术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验证所学知识。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专业基础知识扎实,而且实践动手能力强,科研探索意识浓,毕业后能很快胜任工作,广受社会欢迎。
(四)人格涵育:公诚勇毅之源头
焦作工学院历来十分重视学生的人格修养教育,提出了具体的修养标准,如:“抱定力、爱名誉、服勤劳”;“力戒懦弱苟安,养成勇敢奋发之精神”;“力戒依懒敷衍,养成自立负责之能力”;“力戒轻躁盲进,养成审慎周密之思考”;“力戒浪漫奢靡,养成刻苦勤朴之习惯”;“力戒虚伪涣散,养成精神团结之意志”;“力戒自私自利,养成爱国爱群之观念”[12]。特别是常务校董李文浩关于“我的观念”训育思想,认为要“在切身处所尽力为国家服务,为国家维护元气,为国家制造实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努力用功”[13],对于焦工师生的人格培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些精神的感召下,焦工师生积极参与或领导了反帝保矿运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南下请愿抗日救亡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在风雨洗礼中铸就了独特的精神品质:“本院同人,素具同舟共济之精神;本院同学,向有朴实耐劳之习惯。”[14]“本院学风醇朴,来学者多刻苦求学之士,课余之暇,率多游览矿厂,参观工程设备,绝少浪漫奢靡之风。”[15]“为国家争人格,为母校增光荣”[18]早已融入焦工师生的精神血脉。合组西北工学院之后,焦工的文化精神与西北联合大学“公诚勤朴”校训相结合,逐步发展成“公为天下、报效祖国,诚实守信、襟怀坦荡,勇猛精进、敢为人先,毅然果决、坚忍不拔”等精神特质,形成“公诚勇毅”的校训,这不仅成为西工师生在抗日战争年代的精神支柱,更激励着历届学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它不仅保全了焦作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四大国内高等工程学府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而且推动了西北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战时急需人才,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西北工学院留下的丰富教育思想和优良学术传统,仍值得我们在新时期继续传承与发扬。
[1]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民国廿七年发汉教字第6074号教育部训令[M]//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438.
[2] 私立焦作工学院一览·设备说明[M].北平:中华印书局,1936:47-60.
[3] 孙越崎.抗战时期焦作工学院西迁[Z].1983.
[4] 戴夏.河南省私立焦作工学院视察报告[M].视察河南省教育报告,1933:31.
[5] 王少安.河南理工大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16.
[6] 《西北工业大学发展概要》编写组.西北工业大学发展概要(1938—2002)[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8.
[7] 陶秉礼.西北工业大学校史[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38-41.
[8] 张清涟.焦作工学院校友录·序[M].汉中:西北文化出版社,1942.
[9] 赖琏.敬告本院第一届毕业同学书[J].国立西北工学院季刊.1939(1):2-4.
[10] 李文浩.李监督在工学院开学演讲辞[J].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1931(3):附录18-20.
[11] 母校矿冶陈列室概况[J].西工友声,1941,1(3-4):14-16.
[12] 入学须知[J].焦作工学院周刊,1932(26):6.
[13] 李文浩.李董事长在工学院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演说[J].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1932(6):7.
[14] 焦作工学院之展望[J].焦作工学生,1933,2(1-2):特载2-6.
[15] 私立焦作工学院采矿冶金系概况[J].焦作工学院周刊,1935,4(5-6):5.
[责任编辑 谢定均 位雪燕]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3卷,第 4期,2012年 12月
ThePrivateJiaozuoInstituteofTechnologyandEngineeringandNorthwestHighEngineeringEducationinAnti-JapanWarPeriod
ZHOUZhi-yuan,ZHANGShang-zi,HONGZhen-tao
(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454000,Henan,China)
During Anti-Japan war period, the Private Jiaozu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moved to the south of Shanxi province and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college of the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the Northeast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Northwe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he National Northwe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kept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the first mining university in China, it helped a lot in northwest high engineering education with its qualified teachers, advanced teaching equipments, rich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good schooling tradition; it also devoted itself to anti-war, saving our nation, the spread of civiliz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est, etc.
anti-Japan and save our nation; Jiaozu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he Nor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high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2-06-28
周志远(1963—),男,河南南乐人,河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mail:hongzhentao@hpu.edu.cn
G527
A
1673-9779(2012)04-048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