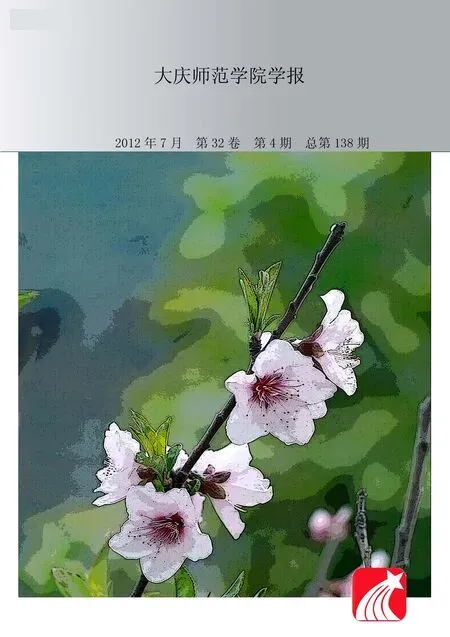桃花源与瓦尔登湖:虚实之间的隐逸诉求
徐玉红
(大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隐逸是文人面对社会所做出的一种异于常人的生存抉择。在中国,从上古的许由、伯夷、叔齐,到中古的陶渊明,都是这一道路的践行者。在美国,19世纪出现的作家、思想家梭罗也走了一条近于中国隐者的道路,他在瓦尔登湖畔诗意地栖居,并刻意拒绝现代文明对生活的渗透,表现了他对自然的理解,对隐逸的诉求。对比梭罗栖居的瓦尔登湖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我们会发现颇多饶有兴味的问题。二者都是作家追求自然、追求隐居生活的场所,并且都寄托了作家的终极精神追求;二者的出现对于他们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二者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实境,可以生活栖居;陶渊明的桃花源是虚境,可望而不可即。虚实之间,二者精神实质也有着巨大差异。
一瓦尔登湖与桃花源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二者的产生都是知识分子面对芜杂的社会所做出的理性思考。追求平淡、追求隐逸、追求自然,是二者共同的外部特征。梭罗的生命历程正是人类走出古老的农业生活而逐步走向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过程,他出生于1817年,于1845年春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一座木屋,开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生活。同时,他对这种生活进行了哲学式的思考,面对人类日益喧嚣的世界而探索的一条异于大众的隐逸之路。应该说,他在瓦尔登湖畔的栖居是尝试性的,瓦尔登湖是他栖居的试验品,他并未在此度过终生,而是于1847年离开了瓦尔登湖。但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考以及他的散文体小说《瓦尔登湖》,却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日益现代化的人类社会里,梭罗的行为与思想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在动机上与梭罗有很大的不同。《晋书》及《南史》都说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解印去县,赋《归去来辞》”。而陶渊明自己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是在公元405年,此后他生命中的所有岁月,都没有离开田园。关于《桃花源记》创作的年代,逯钦立先生认为是晋义熙十四年[1],袁行霈先生认为是宋永初三年壬戌[2],学界关于其创作时间虽不能详考,但大都认为是陶渊明归隐之后的创作。这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对归隐的生活是认可和赞许的,并通过这篇虚拟之作予以升华。
梭罗与陶渊明虽然面对的社会现实不同,身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做出的选择却是相同的。对于梭罗而言,他行走于湖畔,自己建筑房屋,自己种植农作物,细心体察湖畔一年四季的变化,然后进行种种关于生存的思考;而对于陶渊明,他的生活终于脱离官场,几乎进入一种孤寂之中,他在《归园田居》中云:“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陶渊明身体力行地从事农事劳动,他自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可以说,梭罗与陶渊明的隐居,都是真实而具体的,他们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他们物质生活本身,然后才是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他们隐逸行为本身所带来的自然精神,追求本真的独立人格,也是颇有相似之处的。
探究梭罗与陶渊明关于隐逸行为的共因,我们可以说,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一种文化趋同行为。农业是人类由原始蒙昧走向文明开化的必由之路,它绵延了数千年,在社会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积淀。陶渊明自幼在柴桑农村长大,耳濡目染的农业生活,贯穿他生命意识的始终。“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可以说是他田园意识的真实写照。而梭罗是一个孤独而追求安静的人,他的一生都在都市与田园中徘徊,并且更倾向于孤独的田园。他在1837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要孤独,我们必须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着一堆一堆的堆放柴火。”[3]对田园世界的天然追求和默契,是梭罗与陶渊明共同的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共同的阅读对象也是梭罗与陶渊明走向田园、追求隐逸的重要原因。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梭罗引用了《论语》及《大学》中的儒家语句共十处,由此可见,他对儒家经典是比较熟稔的。在《瓦尔登湖》的“经济”篇中,当思考“行”与“知”的关系时,作者引用了孔子的话:“知之为知之,是知也。”在“隐居”篇中,当讨论人的生存环境时,梭罗引用了孔子的话:“德不孤,必有邻。”在“更高的法则”篇中,作者谈论饮食时,引用了曾参的话:“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当然,由于翻译及个性化的阅读等原因,梭罗的引用并不贴切,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极大的误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梭罗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对儒家思想是有所体认的。儒家也有隐遁意识,《论语·公冶长》中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中也有楚狂接舆以及长沮、桀溺等隐者的形象。儒家经典里所传递出的隐逸精神,对梭罗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而陶渊明对儒家的接受、阅读及体认则达到了更高境界。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一文中,据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4]陶渊明对儒家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同时,他也兼具道家的思想,儒道会通或者援儒入道的精神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桃花源记》是表达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精华之作。它有着复杂的创作背景,儒家精神的影响,是其中之一。梭罗与陶渊明,通过对儒家的理解而产生了共鸣,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当把桃花源和瓦尔登湖这两个场所放在一起比对时,我们发现更多的是他们的不同。桃花源是一个虚境,在现实世界中,它是不存在的,但它却极具象征性,非瓦尔登湖这一可以触及的生活场所可以比拟的。它表现了陶渊明隐逸精神的终极性追求。瓦尔登湖是一个实境,在梭罗笔下,它是一个隐者的居住场地和思考场所,它更具有实验性。梭罗力图通过一种切身栖居湖畔的体验,来探求人类在简化的物质环境中生存的可能性。将桃花源和瓦尔登湖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前者是虚幻的超世精神,后者代表了真实的入世精神。从哲学层面来考察,桃花源的象征意义则远远高于瓦尔登湖所代表的精神实质。
桃花源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处处充满着神秘与浪漫,它象征着陶渊明最高的隐逸诉求。就陶渊明的现实生活而言,他辞去彭泽令回到柴桑之后,并非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他在精神上达到了完全的自由,如羁鸟归林,池鱼入渊,但生活却每况愈下。虽然他秉承着儒家思想,“忧道不忧贫”,但穷困且劳苦的农耕生活,仍然带给他巨大的压力。在归隐之后,陶渊明已经从他在为官时不断怀恋田园转变为在田园里思考如何过一种更优越的、更富有诗意的躬耕生活。由此,我们看到了《桃花源记》中的场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在现实的田园世界中,我们很难看到这幅优美自然的画面,更难以追寻那种“怡然自乐”的精神生活。看似简单质朴的生活,却只有依靠想象的文字才能实现,这既折射出陶渊明现实生活的窘困,也表现了它对隐逸世界的终极追求。陶渊明有大量诗歌描写归隐后的窘困,如《乞食》、《戊申岁六月遇火》等。正是由于这种现实和理想的不平衡,才促使陶渊明对隐逸生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相对于陶渊明,梭罗的现实生活与主观理想则无限接近。他追求的是平淡的隐居生活,这正是瓦尔登湖畔的栖居;他力求在平淡生活之中获取深入思考,《瓦尔登湖》中有多处富有智慧和启示性的文字;他放低物质生活的需求,甚至是居无求安,食无求饱,通过在湖畔的劳动来自给自足。因而,作为实验性的瓦尔登湖,满足了梭罗的所有需求,梭罗的思考也因而到此为止,而不像陶渊明一样,超离于这个世界。在《瓦尔登湖》一书中,充满了梭罗的思考,但大多只是对现实场景的议论,这种议论很少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哲学。如在谈到生活的真实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时,他说:“我每天的生活的真正收获触摸不到,难以描述,好比早上或者晚上的色彩。”当论及人对本性的认知时,他说:“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体里有一种动物性,一等我们更高级的天性昏昏欲睡了,它便乘机醒过来了。”可以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思考,是随感式的,它没有体系,甚至不需要体系,但这样,也就无法把问题展现得更深刻。
基于上述对梭罗的分析,我们再阅读《桃花源记》,它深邃的哲学式的思考与表达,则更加深刻而富有象征性。渔人进入桃花源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无意识则是进入桃花源的唯一途径,处心积虑、潜心经营的人,无论采取多么精妙的方式,都是无法进入桃源的。后来的太守以及南阳高尚之士刘子骥都是如此。这种写法一方面象征着陶渊明理想的隐逸方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或者说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更重要的是,这种“进入桃源”以及“无法进入桃源”的方式,本质上也昭示了老子的“无为”思想。真正的“自然”是一种本源的、自然而然的、无任何外界因素干扰的意识,这既是陶渊明的隐逸观,也是陶渊明的哲学观。
所以说,桃花源的虚境,是一种理想的真诚和哲学的真实,但很难在现实生活中获取;瓦尔登湖的实境,则是理想的平实和哲学的现实,也正是如此,梭罗的隐逸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实现。通过对二者的对比,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与哲学,追求的是“得意忘形”或“得鱼忘筌”的精神实质;以梭罗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与哲学,则往往通过大量琐碎的实证,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和哲学的本真。虚实之间,陶渊明与梭罗对隐逸的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分野。
三陶渊明与梭罗不仅哲学的思考方式不同,而且对物质生活的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瓦尔登湖在隐逸上具有实验性,它必须满足现实世界中隐者的所有需求,这种需求首先表现为一种物质,然后才是一种精神。桃花源作为一个虚幻的隐者乐园,物质已经消弭在精神之后,良田、美池以及桑竹与其说是生活所需,不如说是田园美景的点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陶渊明却饱受物质之累,即使他的物质欲望极低;梭罗却达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契合,表现为一种悠闲、安适和恬淡。
《瓦尔登湖》一书的首篇即以“经济”命名,简单而又明了,这是梭罗对隐逸生活的初步认知,也是最基本认知。他知道,谋求最基本的生活资源,是一个隐者能够生存下去的前提。在开篇中,梭罗说:“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接着,他发现,他只有“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维系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在梭罗的眼中,他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一定会需要必备的物质资源,他力求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这种物质的自足。他当然不需要奢侈品,但接下来的物质生活,他仍然是兢兢业业、节衣缩食。他精心计算着自己的生活,如何耕种,如何收获,再将获取的农作物进行变卖,来购买旧砖、钉子、门闩及板条等建筑必需品。在“经济”一篇中,他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农作物出卖的价格以及购买建筑用品的价格,还精确地计算出两者之间的差价。梭罗对经济生活是极端重视的,这种重视体现在数额上的极端精确,如在记录购买建筑材料费用时,他购买木板花费为8.035块,而总计则为28.115块,精确到千分位。在记录购买石灰花费2.40块时,他额外标注:“买贵了。”这种精确计算表现了他对自己物质生活的苛刻程度,他力求将物质生活降至最低,只需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即可。
应该说,梭罗的物质生活与物质需求是一致的,他也因此而获得自由、安适的心境,并能够在如画般的瓦尔登湖畔进行安居和思考。相对于梭罗而言,陶渊明的经济生活和对物质的需求则复杂得多。
陶渊明年轻时代,即受到物质生活的困扰。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多有记述,史传中也屡有记载。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陶渊明自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出任参军以及为彭泽令期间,他的经济生活有所好转。回归田园之后,他又陷入穷困之中。遇到旱年或是蝗虫横行之年,他颗粒无收,几有乞食之举,在《乞食》一诗中,他言:“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晋书·隐逸传》与《南史·隐逸传》都记载,陶渊明隐居时,他的朋友颜延之前去探望,临行,“留二万钱与潜”,此处亦可见陶渊明生活的拮据。陶渊明的物质欲望亦很低,否则,他不可能会“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的俸禄,即使再低,也会比陶渊明亲自耕种所获收入要高、要稳定。陶渊明始终处于贫困之中,是有原因的:其一,他是庶族,没有祖上的遗赠,他的曾祖虽为东晋大司马陶侃,但至陶渊明,这一族支早已败落下来;其二,他自己很难适应世俗社会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其三,陶渊明家庭负担较重,他共有五子,仅靠耕种,着实难以维持家计。陶渊明对贫败的感叹,是生活的写实,而绝少情感的沮丧与灰暗。他在思想上,早已超越了物质生活,达到“安贫乐道”的境界。另一方面,贫苦生活确实引发了陶渊明更多的思考,他所走的隐逸之路是需要勇气和意志的,如何拥有更轻松、更自然的隐居生活,他在《桃花源记》中描绘出了理想场景。
陶渊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能为力,“未见其术”,在理想图式中,他则选择超越。桃花源中经济足以自给自足,桃园中人没有衣食之忧,到处充溢着满足、快乐和祥和。陶渊明的终极物质理想不过如此,这实是对物质的超越。与梭罗相比,陶渊明的物质观更接近一种精神的、乃至于宗教的层面,他用一种高妙的理想光芒去除了物质世界的繁琐。而梭罗则始终立足于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中,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密切关注下,他用一种可操作性手段证明人类离群而居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均表现了陶渊明与梭罗的隐逸诉求,但加以辨析,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前者是虚境,却表现了一个隐者的最高隐逸理想,它是陶渊明追求自然理念的一个实践,是他安贫乐道的理想场所;后者是实境,是西方思想家摆脱喧哗、走向自然的一个真实世界。就所表现的隐逸思想而言,相对于瓦尔登湖,桃花源则更深邃、更精粹、更凝练,它是中国士大夫精神安息的一个场所,也是他们走向社会的动力之源。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8.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2.
[3] 亨利·戴维·梭罗.寻找精神的家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4]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