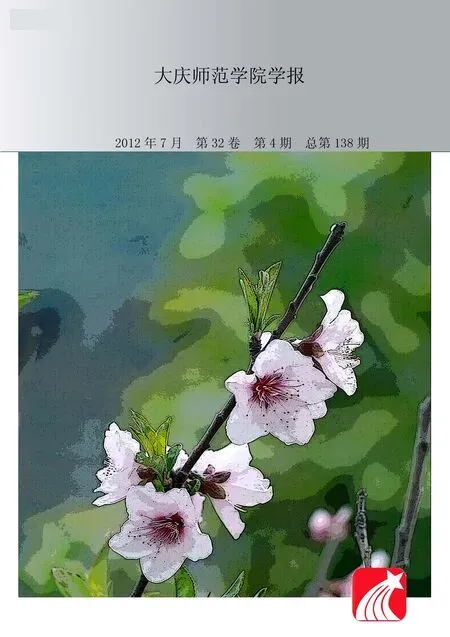人口增长和土地改革
——中国地主阶级为什么消亡
马 跃
(淮北市委党校,安徽 淮北 235000)
一、社会结构和群众动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地的不平等占有制度,确立了平等占有的土地制度。这次土地变革是对商鞅变法的否定,是从来没有过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变革。20世纪为什么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
传统观点认为,土地革命或者土地改革之所以发生,是由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造成的。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指出:“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占90%以上贫、雇、中农只占有20%-30%的土地,这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落后的根源。”毛泽东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拥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1]。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观点,指出古代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的剥削率并没有传统观点认为的那么高,近代土地分配不是更加集中,而是更加分散了。秦晖说:“几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认为,以前的那种地主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的土地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结束封建社会、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志,是没有根据的。”[2]对这种观点,也有学者持有异议[3]。当然,没有人否认土地不平等占有的事实,黄宗智说:“我们无须怀疑这些一致性: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1/3,富农掌握了另外的15%-20%。”[4]
高王凌说,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额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所谓50%是指“正产物”而言);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5]
当地主占有土地比重并不高、地租率实际很低的结论出来后,一些人认为,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共产党的作用,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出于某种动机和目的,比如吸取资源,重新建立基层政权组织,通过行政手段或群众动员发动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群众动员论。张鸣说:“中国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而随着战事的烈度和规模急剧扩大,社会动员演变成功利性极强手段特殊的战争动员,正因为如此,革命才取得了迅速的成功。”[6]秦晖说:“杜润生同志最近的回忆录讲,他说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土改,土改的意义不在于分地,而在于重建基层。他说,实际上土改的时候,农村可分的土地并不很多,地主和富农合计占地肯定达不到一半,可能还不到40%。”[7]
于建嵘认为,土地改革几乎完全是外部输入的结果。他说:“毫无疑问,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的外部性力量,是当时乡村社会发生变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时强势国家的强制性进入下,那种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乡村传统就变得无能为力了。”[8]
传统观点的确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中间经过了数次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每个王朝末期,几乎都有比较严重的土地问题,并且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不比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更平均,为什么没有土地改革或革命,甚至某些农民出身的皇帝也没有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而是保留了这种制度,并且使自己及其政治集团成为新的地主。他们通过剥夺敌对集团的土地,招抚流亡,便实现了天下安定。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是现在不合理的,而是早就存在并且延续了几千年,都没有出现平分土地的改革。就是说,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并非必然带来土地改革,肯定还有其他条件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
用群众动员论来解释土地改革的成因更加不能让人信服。从土地改革的过程看,许多村庄甚至大多数村庄的土地改革都是由共产党派出工作队,从外部进入村庄发动起来的。群众动员在土地改革,甚至在共产党的大部分工作中,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革命无法离开动员,但我们能否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动员的结果?这个理论把共产党与农民作为两个社会主体,好像共产党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殊不知,共产党大部分来自于农民,本身就是农民,共产党闹革命搞土改,就是农民闹革命搞土改。况且从吸取资源的角度说,古代农民战争同样要吸取资源,为什么没有废除这种土地制度?关键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能动员起来?乱世出英雄,为什么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人物?进行社会动员,肯定要有动员的社会前提,这种社会前提或客观条件为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这么大的动员力量。“外界煽动导致骚乱和革命的保守主义观点,只包含有一半的真理性;如果忽视了使煽动充分有效的社会条件,这半个真理就会变成谎言。”[9]对于土地改革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仅仅归结为主观动员,未免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
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必须有来自社会深层的巨大力量。李自成被洪承畴剿得只剩十八骑,三年后又聚集几十万众,号称百万。共产党在八七会议意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作出以土地革命、武装暴动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决议后,短短几年就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河南、陕西、山西、四川等省吸引和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加,并用了20多年就推翻了蒋家王朝。如果农民没有平均地权的诉求,共产党花言巧语的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动员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投入到这场革命中。没有山东和中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60万人民解放军后面就不会有500万农民推着小车抬着担架支援他们打败80万美式装备的国军[10]。张鸣说:“如果没有几十年来社会和阶级关系的恶化,没有那么多不公和罪恶,那么任凭共产党人再有宣传技能,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11]
现代中国历史上,这种土地制度被废除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我认为,不仅是这种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也不仅是群众动员,肯定是碰到了古代改朝换代时所没有碰到的因素,正是这个因素,促使这种土地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那么这个新的因素是什么呢?
二、人口增长与中国革命
韩非早就认识到人口与社会动乱的关系。他在《五蠹》中说:“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从秦至明末,中国人口大致保持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呈波动式增长态势。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接近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改制以及绿林、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人口达4500万人,经过群雄混战的三国时代到西晋,降到1600万人。唐天宝十四年人口达到5291万人,经过安史之乱,760年减少到1699万人。公元960年的宋初,人口只有2000多万,南宋鼎盛时达到7000多万。17世纪初达到6000万,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12]。
人口的增减变化与王朝的治乱循环肯定有一定的相关性,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同步现象。农业社会中,主要的资源就是土地,人与自然的平衡就是人与土地的平衡。当人口超过一定规模的时候,人地之间就会严重失衡,越来越多的人口就从土地中游离出来,便发生战乱、饥荒和瘟疫,使人口大规模减少。新建王朝通过消灭军阀地主,没收敌对集团的土地,招抚流亡,注意与民休息,就可以实现天下安定的统治目标,那么就没有必要变更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清朝垮台以后,中国再次进入军阀割据状态,使用传统方法能否实现天下安定呢?实现共和与民国就稳定了吗?建立一个强大的军政权力系统,像国民党那样,就稳定了吗?北洋军阀或国民党夺取政权后,天下依然处于不安定状态。国内社会为什么老是不稳定?怎样才能稳定?问题到底在哪里?
艾奇逊较早注意人口增长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问题的诺言。”[13]
曹树基等人说,19世纪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和民族冲突都含有人口压力的因素,连串起来时,它们表现出19世纪的中国很深切地感受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这些战争和冲突的规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频率都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在这一个世纪之内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因为如此,这100年间不断的战争和造反才都覆盖了广阔的地区,它们吸引着众多人口并不仅仅因为它们信誓旦旦允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还因为它们能更现实地填饱肚子,哪怕以生命为代价[14]。
裴小林认为,中国暴力革命的发生就是由于土地争夺导致的市场失灵,人口饱和时土地私有权会伤害他人生存,市场失灵引发了农民起义和革命造反。暴力革命、土地改革和建立公有制经济,就是贫困人口对人地矛盾冲突的合理反应。土改的原则是与市场经济正相反的平均主义原则。平均分配是使福利最大化的唯一方式[15]。
三、资源、制度和土地改革
清朝以后,因为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广,中国人口增长态势出现巨大变化。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2],清康熙时人口10170万,清乾隆二十七年20047万,清乾隆五十五年30148万,清道光十四年40100万,民国八年(1919年)50600万。汉朝到宋朝,人均耕地在10亩以上,从明朝开始,下降到10亩以下,嘉庆以后,下降到3亩以下。嘉庆十七年为2.19亩,光绪十三年为2.41亩。从1650 年到1850年的200年间,人口增长两倍多,耕地仅增加63%。
古代人口问题远远没有近现代历史上这样严重,人口增长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度稀缺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冲突的激烈化。裴宜理通过对淮北捻军与红枪会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这一地区两种集体暴力(或曰生存策略):一是掠夺性策略,二是防御性策略。不同的人群围绕着这少得可怜的资源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在这些活动中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基本经济结构或者政治结构的意愿。要重新设计淮北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得不等到那些充分摆脱地方关系羁绊的革命者的到来,只有他们才提供革新的办法。当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规则的时候,这些策略被证明失去了吸引力[16]。
社会稳定是政治统治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亨廷顿认为,对那些土地占有不均衡的后发达国家来说,土地改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关系到这些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也是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改革是这类国家迈向现代化所必须经过的门槛[17]。稳定与发展是左右现代历史背后的绝对精神,一切个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而已。如何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呢?不稳定的根源是什么呢?
国共“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18]。林伯渠说:“土地解决,万事冰释,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19]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20]
邋遢道人对杨奎松在《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文章中提供的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大约130万农户的调查资料,进行了重新分析和计算。该时期中国不是大地主所有制,中小地主和富农才是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同时,农村人均耕地(按每户5人计算)与同期其他统计和调查也接近,即3.08亩。118万户下中农和贫农拥有585万亩耕地,按最低生活标准,这些土地只能让60万户维持生存,大地主拥有的275万亩和中小地主和富农出租的342万亩土地顶多租给31万户农民,中小地主和富农直接经营的800万亩土地可以为11万户无地农民提供做工机会,16万户农民(占全部农民的12.3%)失去耕地机会。这个比例不高,但全国加起来就是六七千万,闹起来一样天翻地覆。一旦天灾人祸、外敌入侵、官吏腐败、苛捐杂税相互叠加在一起,势必加大流民溢出的比例[10]。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论述了人口增长与土地改革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在结论中又否认人口增长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非常让人感到遗憾的。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无序人口源源不断地从农村社会中被游离出来,成为游民和流民,成为军队和盗匪的补充来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也有人口问题,但没有任何一次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即使晚近的明清之交,王朝更替时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减少了大量人口。新的王朝通过没收敌对上层集团的土地,招抚流亡,在不长的时期内就能使社会安定下来。然而,现代历史上,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不管是否没收敌对上层集团的土地,都无法安置那么多的流亡人口,无法阻止从农村社会中不断分离出来的大量流亡人口。
人口的巨大量变,使革命的内容发生变化。要使广大农民安定在农村和农业上,延续数千年的农村土地制度非来一次彻底变革不可,非触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可。不实行土地的平均占有,就不能实现人人都有一口饭吃的目标,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不平等的农村土地占有制度和依附在这种制度上的乡绅地主阶级就成为实现农村稳定的障碍,这种制度和这个阶级的灭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有必要承认,在像醴陵县这样(醴陵地权集中主要是一些大地主和乡村劣绅占有)的南方地区,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是比较强烈的。民主革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革命运动向农民个人提供了物质利益,才换取了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21]土地改革有效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假如没有这种人口数量的变化,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完全可以同以往任何朝代一样,通过没收敌对集团的土地,招抚流亡,或者领袖及军功集团本身占有土地,也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但这样的条件对共产党来说是不存在的。共产党面临的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压力,只有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以及反霸反匪、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等配套举措,实现了嘉庆王朝以来一直没有实现的天下安定。
正是人口这个因素,在古代历史上,虽然有农民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没有促使土地制度的根本变动;也正是人口这个因素,促使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在现代历史上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就是说,人口的巨大增长,加上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正是促使土地改革和地主阶级消亡的根本因素。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3-625.
[2] 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J].中国农村观察,2007(3).
[3]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45.
[4]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经济、社会与法律的历史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6.
[5]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3).
[6] 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EB/OL].(2003-06-30)[2005-06-07].http://www.cuhk.edu.hk/ics/21c.
[7] 秦晖.历史和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EB/OL].(2007-09-12)[2008-05-03].http://www.southcn.com.
[8] 于建嵘.岳村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0-231.
[9]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6.
[10] 邋遢道人.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EB/OL].(2009-07-29)[2010-01-05].http://www.wyzxsx.com.
[11]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33.
[12]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0.
[14] 曹树基,等. 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J].历史研究,2002(1).
[15] 裴小林.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M]//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42-244.
[16]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4,254.
[1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49-355.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7.
[19] 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M]//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4.
[20] 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 王恩光 申葆青,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47.
[21] 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