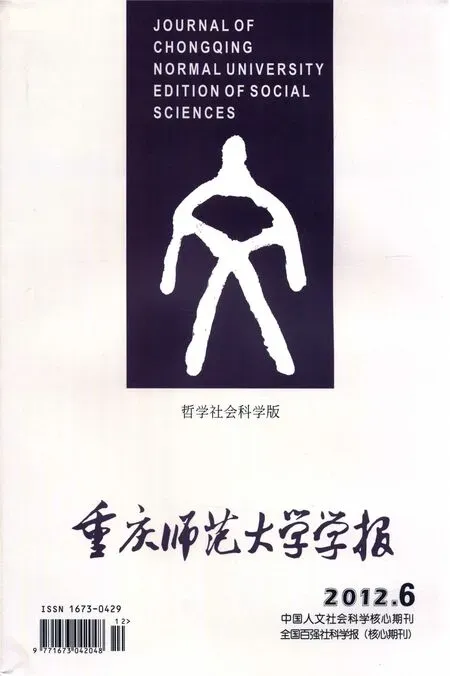文学社团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方法创新——评李光荣、宣淑君著《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李文平 向 立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朱寿桐先生曾说:“文学社团的出现及其历史性的存在,是中国现代文学极其重要甚至相当精彩的现象。”[1](10)而校园文学社团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文学社团研究的多样性,而且开拓了文学社团研究的新领域。
李光荣先生与宣淑君女士历经数载的默默耕耘,为学术界贡献出了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专著——《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版)。作为国家社科项目的结题成果,该书以全新的视角、扎实的史料对西南联大九年间的文学社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后方校园文学社团系统研究上的历史空白。
阅读此书,受益匪浅。这本厚实而具有历史感的著作,给此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颇多的启示。
一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老实人做老实学问”的治学精神。
原创性是作者在项目申报之初提出的学术目标——“事实上,进行此项研究,即使想不原创也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在此领域做过专题研究。”[2](368)正因为没有人在此领域做过专题研究,也没有人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做过系统的梳理和描述,所以材料的搜集与整理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原创性决定了研究者只能从筚路蓝缕的基础性工作起步。在现有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撰写一部如此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其间所经历的收集史料的周折与艰辛绝非亲历者所能体会。在本书的《跋》中,作者有这样的描述:“在研究中,花费精力最多的工作是搜集材料。我们用了两年多时间,查阅报刊,访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成员及其家属,购买书籍,并广交朋友,从多渠道获取国内外相关信息和线索。通过以上多方面旷日持久的努力,掌握了大量有关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用了很大的功夫来甄别材料”[2](368),以至于“为寻找一则材料寝食不安,为求证一则材料费时费月的事是常有的”[2](369)。上穷碧落下黄泉,在这段艰辛而又快乐的旅途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用生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严谨学者。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老实人做老实学问”的学术研究精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2](2)这种踏踏实实“做小事”的“泥土”精神,对于一直坚守在西南地区默默研究的学者而言是可贵的,更是值得发扬和学习的。
二是研究方法新颖独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虽然一贯注重作家作品研究以及流派研究,但真正的文学社团研究似乎长期处于某种缺席的状态。“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来看,历史上关于文学社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与文学社团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极其不相称。”[3]当文学社团研究开始被研究者所重视的时候,“一个极为便当的处理办法便是从流派的研究切入社团,最终是将社团研究成了流派。”[1](44)很显然,过去通常以流派的角度研究文学社团的方法存在着局限性,社团与流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学社团是文人的集合体,文学流派则是风格的集合体。文学社团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研究文学社团既要看到整体的普遍性,又要关注作家个体的特殊性,以某种“主义”概括作家或社团的创作风格,往往容易遮蔽社团文学的丰富性。文学社团研究以人事关系为主导,关注社团成员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社团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以社团的研究方法研究社团,是朱寿桐先生乃至学术界一直以来期待已久的实践,《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为今后的社团研究提供了典范性的案例。
研究文学社团,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尊重历史的学术勇气。朱寿桐先生在《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中指出,社团研究应尽可能在文学史基本格局中去定位,辨析社团基本历史状貌,包括人员范围、出版物、内部结构及其复杂性等等,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对社团进行总体把握和学术概括。“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从弄清‘基本事实’入手。”[1](4)《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秉承“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不以“孤证”立论的原则进行书写。“在材料的运用上,我们尽量使用第一手材料,第二、第三手材料仅供参考或作为线索使用。”[2](369)对于所获得的“口述历史”,都要核实考证,绝不轻信使用。书中独立成章的七大社团在人员组成、主张追求、创作情况、活动开展、特点贡献等方面都得到真实的呈现,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显现出各有千秋之态。
《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跳出了以流派切入社团的研究局限,将社团研究回归到了文学的原生态,让读者更加深切地触摸到现代文学史上生动而丰富的校园文学现象。
三是历史梳理清晰明了。
西南联大的历史从1937年夏到1946年夏,共计九年。九年间,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学生社团。以学科而论,有政治的、历史的、戏剧的、音乐的……其中属于文学的社团有十多个(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诗社、冬青诗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要梳理、呈现十几个文学社团的历史面貌,并不是一件易事。作者采用了宏观把握和微观透析的方式,将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社团综论,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文学社团的历史分别进行爬梳。联大的历史,依据政治事件分为五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皖南事变”以前、“皖南事变”以后、爱国运动高潮期、反内战时期。而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则根据各个社团的消长情况,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937年秋—1941年春)、中期(1941年春—1943秋)、后期(1943秋—1946年夏),各个时期的社团又分综合社团、戏剧社团和纯文学社团三类。很显然,作者采取这样的梳理方式,关注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的确,政治对联大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决定着联大的“命运”。但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余七章是对七大纯文学社团(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诗社、冬青诗社、文聚社、文艺社和新诗社)的分论,内容涉及各文学社团的人员情况、创作主张、地位影响等。综观其框架,由面到点,点面结合,全面、系统、深入地展示、分析、评价了西南联大九年间文学社团的活动面貌。
除了宏观上的统筹把握,在处理七大社团的演变、消长及其复杂关系时,条理依旧清晰。例如本书在对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三大文学社团进行介绍时,作者对其消长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并用发展的眼光将三大社团串联在一起。高原文艺社是南湖诗社的延续,南荒文艺社由高原文艺社转化而成。在整理创作材料的时候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西南联大的师生在谈到高原文艺社和南湖诗社的关系时,使用的词语是“改名”而非“重组”。而南荒文艺社又是在高原文艺社的基础上,接受了当时《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的建议而组成。因而,本书将之处理成一个社团的三个发展阶段。
社团与社团之间成员的交织是常有的事,可在作者的笔下各大社团面貌清晰,杂而不乱。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唯有对联大所有文学社团的史料有全局性的把握和细心的钻研,才能做到如此的系统全面。
四是文本解读细致精当。
文学社团是文学创作者的集合体,必然离不开文学创作。《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不但展现了七大文学社团丰厚的创作成果,而且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做出了细致的艺术分析和精当的学术评价。例如对南荒文艺社时期林浦诗歌《乡居》的解读:“阶前/看山茶花/含蕾,一朵朵/慵懒地开,谢/猫儿蜷伏门槛外/对九月嫩阳/垂盖瞌睡的眼/无暇规计天边时日/白鸭子(扁嘴代手)/摸捉鱼虾/屋角打谷声/减轻了禾堆的重负/灰色牛,蹲池畔/阔大的芭蕉叶/张着,圆圆像雨伞/通城的大路/人影踏人影/来了,又走了/昨夜水凫/留下的足印/斜挂云端/补红萍空隙/铺舒静止的/湖面”。全诗用散文的情愫勾画乡村生活的图景,俨然一幅闲适宁静的中国画卷,在完美和谐之中传达出林浦对生活的情趣,一种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生存境界。本书作者用“散文美”和“中国化”来概括其诗歌的特色,毋庸置疑,这样的评价十分贴切。“慵懒”的花、“瞌睡”的猫、鸭子、水牛、山茶、芭蕉、红萍……从字里行间的揣摩中作者准确地定位出林浦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上的“现代化”和浓郁的“中国味”。又如评价文聚社时期汪曾祺的散文创作:《花园》是《汪曾祺全集》散文卷所收最早的一篇散文,文章回忆作者老家的小花园,记述“我”在花园里的种种趣事,在客观介绍小花园的同时又倾注了作者浓浓的情感。本书将之与鲁迅的百草园进行比较赏析,同样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字,同样有着各种可供赏玩的植物和动物,而汪曾祺的散文却更见“散”和“淡”的文风。本书作者认为“散”和“淡”是《花园》的两大特点,文章无统一的结构。板块拼合式的构造是“散”的体现,语言风格上的“说话”方式则是“淡”的意味。从汪曾祺《花园》的赏析自然过渡到其后期的散文特色,追其本而溯其源,合情合理之中更显作者的睿智。诸如此类的例证,本书中随处可见,如若没有高水平的文学鉴赏力,是断不能做到如此精当的。
五是本书以扎实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空白,对文学社团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进行了有力的开拓。
《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以社团入手研究文学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作家荟萃的集合体。读者从中可寻绎出众多作家成长发展的足迹,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闻一多、穆旦、林浦、赵瑞蕻、杜运燮、秦泥、汪曾祺、郑敏、刘北汜、向意、祖文、陆嘉、吴风、王佐良、闻山、萧荻、何达……他们中有业已成名的大家,也有初登文坛的新星,群星闪烁,异彩纷呈。
群星荟萃、材料详实,如此丰厚的资源,不但为进一步研究联大文学社团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深入研究穆旦、汪曾祺、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著名的文学家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和研究线索。例如穆旦、汪曾祺的早期创作情况在本书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将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穆旦和汪曾祺的宝贵资源。从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诗社、冬青诗社和文聚社的文学创作情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诗人穆旦的成长历程。南湖诗社时期以浪漫主义为主调,高原文艺社时期开始向现代主义转变,南荒文艺社时期基本实现转变,但尚未出现十分成熟的作品。直到文聚社时期,《赞美》的诞生,将穆旦诗歌的艺术风格推向了成熟。众所周知,汪曾祺师承沈从文,他在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将人性置于江苏高邮美丽的山光水色中尽情地演绎,而本书则对汪曾祺早期文学创作中的多样探索做了详细的介绍。关于汪曾祺的早期创作,李光荣先生也曾在《当年习作不寻常——汪曾祺初期小说校读札记》中发表过独特的见解。与此同时,他还提供了四篇汪曾祺的早期作品(《翠子》、《寒夜》、《春天》、《谁是错的?》)以便读者参考。而本书在搜罗过程中发现汪曾祺早期的十多篇小说创作,这些散佚的原始资料,无疑对研究汪曾祺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治学“三境界”,正可用来描述李光荣先生与宣淑君女士在撰写此书时的心路历程,没有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执着追求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辛勤付出,便燃烧不起这异彩纷呈的“季节的花朵”。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2](5)笔者以为,这是对此书价值的最大肯定,也是对同行研究者在学术追求上有力的鞭策。
[1]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李光荣,宣淑君 .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M].中华书局,2011.
[3]孙宜学 .社团研究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J].文学评论,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