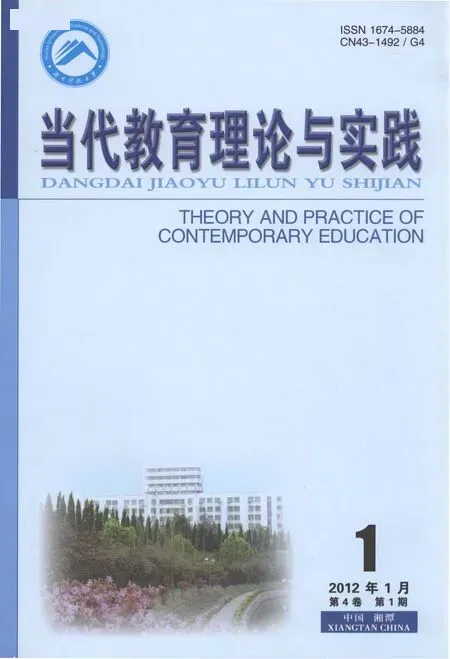论教育和游戏的融合
许丽珍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论教育和游戏的融合
许丽珍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从柏拉图至今,无数的教育家研究“教育”和“游戏”的关系。有的认为游戏是教育的一种手段;有的认为教育和游戏有着原初意义上的融合。大家一致认为游戏对教育有促进作用,然而,为什么游戏和教育不能达到本质的和精神上的融合?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教育和游戏的融合反映在教育中就是把游戏看成教育的内在结构持续,即教育就是一种游戏,把教育当作一种游戏来做,以游戏的精神和态度重塑教育。
教育;游戏;融合;教育即游戏
众所周知,游戏对教育有很重要的意义,而教育实践中游戏的“身影”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包装教育的“糖衣”。为什么教育中缺少游戏因素和游戏精神?这主要因为大众对游戏的偏见,以及日益严重的教育功利性。分析及研究教育和游戏的关系有助于二者的融合进而可以缓解教育的功利性。
一 教育与游戏的关系
在希腊语中,游戏(Paidia)和教育(Paideia)这两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都指称儿童(Pais)的活动。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时代以及不同的学者中不尽相同。教育和游戏的关系大致可分为3种:
1.游戏与教育相对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游戏的实质是“享乐”,教育的实质是“发展”。二者性质不同,不具有共存的可能,反映在教育中就是排斥游戏活动,追求效率和纪律,坚持知识接受的“苦学观”。
2.游戏是一种教育工具或者手段。第一个研究二者关系的柏拉图(Plato)言称教育包括游戏成分,以游戏帮助教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游戏是7岁以前儿童教育的一种方法;《论语·雍也》中“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就把孔子所提倡的乐学表现的淋漓尽致。古今中外有很多学者持此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
3.游戏是教育的本质之一。胡伊青加在《人:游戏者》中提到人造就的各种文化形态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也应该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导论》一书中曾说过“既然人人都是游戏者,人人都生活在游戏之中,那么教育本身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人类多种多样游戏活动中的一种……”[1]他在谈到人的形象时,就把“游戏人的形象”、“文化人的形象”和“制造人的形象”作为三大类。
游戏是教育的本质之一,是二者关系新的突破。张正江教授提出了“教育即游戏”。他认为“游戏是教育的本质之一……本真的教育也是游戏,是教育工作者的本真存在方式。”[2]这里的“教育即游戏”并不是“Education is Play”而是“Education as Play”。所以我们应该以游戏的精神和态度来办教育,把游戏作为教育的本质和过程,而不仅仅是教育的内容和手段。这样才能达到教育和游戏的真正融合。
二 教育与游戏融合是教育发展之需要
雅斯贝尔斯曾说过“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和技术。”[3]
“沦为苦役”的教育是当今我国教育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家提倡的“素质教育”以及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各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各种措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沦为苦役”的教育主要表现在:学生的厌学、教师的厌教。
(一)学生厌学
压力过大是现在学生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首先,学生体会不到获得知识的快乐以及探索知识的兴奋感。其次,学生没有意识到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而是觉得在为家长学习,所以来自家长的压力远大于学习知识的压力。可见学生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是厌学的主要原因。
(二)教师厌教
经调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体会不到成就感反而有强烈的疲惫感是厌教的主要原因。现在教师大多处在一个纠结的位置,教育任务日益增加,学生厌学。久之教师的教育信仰以及热情被冲击,没有自我充实、提高的动力,更不用说搞科研以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恶性怪圈中,社会大众感觉到我国教育出了问题,开始崇洋媚外,所以迫于形势压力我们的教育不断地改革。
石钟英先生曾说“教学活动中游戏状态的缺乏是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游戏’意味着‘人的诞生’和‘人性的复归’”,“人们应该‘在教育中游戏’(playing in education)‘通过教育游戏’(playing by education)‘为了教育而游戏’(playing for education)。参与教育游戏,享受教育游戏所给予的愉悦,是人类参与教育活动的另一种目的。”[1]
三 阻碍教育和游戏融合的因素
(一)对游戏的偏见
受维多利亚时期基督教清教伦理的影响,工作往往“被认为是上帝的工作的延伸,而游戏却被认为是魔鬼的领地(如‘悠闲的双手是魔鬼的作坊’,de Grazia,1962)”[4]所以传统的人们认为游戏就是纯粹的玩、打闹,究其实质是享乐,学生以一种享乐的心态去学习不仅不利于学习反而起了阻碍作用。比如:以游戏为基础的幼儿园课程受到家长的质疑:“我们送孩子到幼儿园是来接受教育的,你们为什么老让孩子玩?”可见,“幼儿园小学化”是游戏从根基上不能融合于教育的最好例证。
人们对游戏之所以有偏见,首先,忽视了游戏是人的本性。游戏是人的一种最为本真的存在方式,人们只有在游戏中才能充分和全面的发展自己。席勒曾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5]其次,把游戏和工作(学习)完全的对立。然而,从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游戏和工作有某种“交叉”的可能;皮亚杰从他的认知理论出发提出“游戏和工作之间依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而可以相互的转化”;到杜威提出的游戏和工作并不是完全分裂的,只不过是二者兴趣的指向不同,“同一项活动可以是工作,也可以是游戏”。
(二)实用理性观念的根深蒂固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6]
实用理性观念在教育中主要表现在其功利性上,席勒曾说“‘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现在教育功利性日益严重主要是因为,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自己而是想通过教育获得更大的利益,让自己更“有用”。顾明远先生说“教育质量不光表现在考试分数上,还表现在各种能力上,如:创造力、思维力、观察能力”。但是教育评价为什么不把创造力、思维力、观察能力作为评价标准?是因为这些能力不如分数更能证明自己“有用”。尽管教师很清楚创造力、思维力、观察能力的培养可以促进学生充分、全面的发展。而教育和游戏融合能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但迫于分数的压力他们“义不容辞”给学生提供灌输式的教育。这正如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说“尽管灌输式的教学和被动吸收式的学习普遍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是为什么它们在实践中仍旧那么的根深蒂固?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和建设的过程,这个几乎在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无人不违反。”[7]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投入和产出的斟酌,使学生家长关心的不是学生本身有何发展,而是学生的分数以及排名。尽管学生在创造力、思维力、观察能力等方面表现优秀,但是分数不高,家长就会质疑教师的水平以及学校的管理。迫于入学率以及家长的压力,学校为迎合社会的期望会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这样一来,“让游戏融入教育,把教育当作游戏一样来做,以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思维力;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进而让他们感觉学习是“第一需要”的美好教育境界就会被搁置。
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的目的不是谋职或赚钱,当一个人沉浸在体育锻炼和音乐活动中时,他完全是为了身心愉悦。如果他将自己的技能孕育实际用途,也就是说,他利用他们来赚钱,那么,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缺乏修养的猥琐小人。”[8]所以我们不要让教育的功利性异化了教育,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其在受教育过程中以最本真的自我方式去探索知识、获得知识。
四 促进教育和游戏融合的途径
(一)观念的更新
观念左右人的行动,如果一些关于教育的社会主流观念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么促进教育和游戏融合,把教育当作一种游戏来办,以游戏的精神和态度来办教育也将成为教育革新浪潮中又一股还没形成即被打碎的浪花。
首先,改变对“人才”的观念。何为“人才”?目前大众认为考试分数高、读高等学府、工作好就是人才。顾明远先生认为“只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9]社会大众拥有正确的人才观对当今功利化、制度化的教育是一个很好的缓冲。这并不是说让大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平等的、在自由和限制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宽松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就会更加主动的学习,在无形中也更好地发展了各方面的能力,也充分印证了老子“无为”的观点。
其次,建立教师充分信任学生的观念。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而不是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让师生之间进行对话性、生成性的交流,就要求教师对学生有充分的信任!只有相信学生“行”,自己仅仅为其提供辅助型指导。他才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开放、宽松、无压力的学习环境,在无形之中就把游戏精神融合到教育过程之中。
最后,改变“分数至上”的教育评价观。游戏能不能成为教学的组织形式,取决于教育的评价方式。如果教育评价还是以“升学率”、“高分率”为标准,只会加剧教育的功利性。教师迫于压力不可能也没精力以游戏的精神和态度进行教学。改变“分数至上”的教育评价观为考察学生各方面能力尤其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等发展的教育评价观,将有助于教育和游戏的融合。
(二)明确教育的游戏性
众所周知游戏对教育具有深刻的意义,教育的游戏性被大家忽视,吴航博士在其论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教育具有游戏性。胡伊青加认为人造就的各种文化形态:语言、教化、法律、知识等都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形态,也应该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产生而发展出来的,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游戏。
1.教学的游戏性。从古至今很多教育家都在教育过程中体现了教学的游戏性,从孔子的乐教乐学思想到当今的愉快教育思想,无不利用教学的游戏性。冯季林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教学的游戏性研究》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教学的游戏性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给学生提供游戏般的情景,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时情感的愉悦性以及整个过程的和谐性。
2.师生间的游戏精神。石中英先生曾说:“既然人人都有游戏的冲动,人人都喜爱游戏,人人都是游戏者,那么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是游戏者和游戏者之间的平等的关系。”[1]而“平等”是游戏精神的核心。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以游戏精神进行对话,共同创造游戏气氛,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其游戏性。在教育过程中不一定要采用实体游戏,关键是师生间要具有游戏精神。伽达默尔曾说“游戏并不是在意识或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获得其存在的,而是相反地在游戏领域中培养出游戏活动者并使之充满精神的。”[10]
教育和游戏的融合不仅是对制度化教育的一种抵抗,更是缓解了当今教育的功利性;有助于减轻师生的压力;促进了教育的良好发展。教育和游戏的融合不仅有浓厚的文化基础,更是现实教育之要求。期望教育家以游戏精神、游戏特征来办教育!教育策略者以游戏精神、游戏特征来制定教育策略和制度!教师以游戏精神、游戏特征来进行教育!这样有助于促进教育和游戏的融合、促进教育的良好发展。
[1]石钟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张正江.教育即游戏[J].教育导刊,2011(6).
[3](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 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4]瞿葆奎.教育学文集·课外校外活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5](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7](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8](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出版社,2000.
[9]顾明远.我的教育探索:顾明远教育论文选.[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10](德)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G424
A
1674-5884(2012)01-0051-03
2011-10-21
许丽珍(1985-),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
(责任编校 晏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