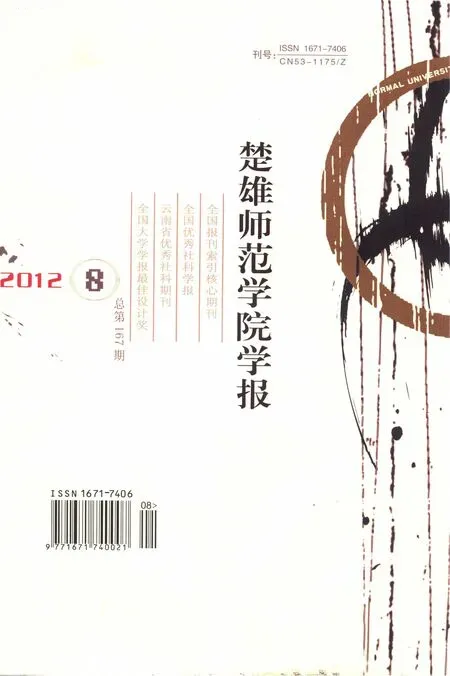双音词词汇化研究模式的特点及思考*——以“月亮”的成词为例
谢永芳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双音词词汇化 (以下简称“词汇化”),是当前汉语词汇历史研究的热点。在前辈时贤的大量实践中,该研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模式:首先从历史文献中找出与今双音实词同形的词组或跨层形式,然后分析这一词组或跨层形式大概在何时、如何演变成词的,即从今上溯到古,再从古下推至今。在这一研究中,大家有一种做法和认识比较突出。
一种做法是:单个词语单线式上溯下推,即在研究中始终只关注双音词及其同形形式,不管其他。这样做留下些问题:第一,历史文献中的同形形式与双音实词是否有直接的源生关系?许多语言事实和研究证明“不一定”。而现在有的研究者拿到一个双音词,直接就进行词汇化研究的操作,即使文献中同形形式用例极少也硬作分析,很少见在这一点上进行更为全面和多样化的考察甄别。第二,由于汉语汉字的特殊性,文献中存在许多和研究对象结构相同、构成成分意义相近的家族成员,其中不乏和研究对象同义者,为什么发生词汇化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研究对象如何从这些家族成员竞争中脱颖而出?例如,据《汉语大词典》和北大古汉语语料库 (以下简称“大词典”、 “语料库”),与“月亮”一样的“月+单音节明亮义语素”还有“月明、月光、月皎、月皓、月朗、月白、月霁”等,其中前两者有月球义作通称,今天方言中仍然保留,②本文方言材料,都出自参考文献 [1][2]。最终“月亮”成为普通话通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如今的词汇化研究揭示的只是双音词和其同形形式之间的纵向发展历程,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双音相邻单位发生词汇化而不是其他双音相邻单位,双音词如何从家族成员的聚合系统中竞争而出等问题,基本不涉及。
一种认识是:双音化是词汇化过程中韵律方面的制约因素。即在解释词组或跨层形式变成词的时候,认为是双音节的韵律要求,促使连续相邻的双音单位重新分析或者粘合在一起。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文献中有数量众多的词组“月+明”和“明+月”,后来“月明”有月球义作通称,“明月”却没有。如果说是双音节的韵律要求促成前者词汇化并作为通名的,为什么没有对后者造成同样的结果?具体原因是什么?双音化除了作为韵律因素在具体词语的词汇化进程中起作用外,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词汇化研究大量开展以来,前辈时贤多致力于微观层面具体词语的词汇化分析,宏观层面的研究则侧重在探讨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联系与区别上等,并未专门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有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上述问题虽有所涉及,但零星分散,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为此,本文打算通过对“月亮”成词的再分析,着重就当前词汇化研究中单个词语单线式上溯下推、双音化是具体词语词汇化中的韵律因素这些模式性做法与认识进行讨论,并对与上述模式性做法、认识紧密相关的三个问题:词汇化在词汇学知识体系中的归属、双音化在词汇化中的作用及两种研究的关系、汉语词汇历史发展演变的研究方式等进行探讨,希望引起大家对词汇化研究适用对象的重视,在进行单个词语单线式上溯下推前注意考察甄别是否适用;同时,希望重新引起大家对已被边缘化的汉语词汇特有的双音化研究及系统式研究传统的重视,共同探讨这些优良传统如何在深受国外研究和表述影响的当代语境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月亮”成为普通话通称与词汇化无关
(一)前人认定文献中的同形形式是“月亮”的来源欠妥
“月亮”是普通话中极其常用的核心名词,它的结构和来源一直很受关注。大家的结论不同,但研究思路却基本一致,即都认定历史文献中的同形单位是今天“月亮”的直接来源,差别只是在于所认定的直接来源的出现时间和结构类型不同。仔细分析,这或者有待证明,或者值得商榷。
1.唐宋主谓式“月+亮”是“月亮”的来源需要再证
董秀芳认为月球义的“月亮”是由唐宋时期出现的主谓词组“月+亮”词汇化而来,不过因为仅有两处用例,于是暂时先类比推测,她说:比照相似类型的演变,笔者相信“月亮”从主谓词组词汇化为一个名词,从逻辑上讲是很可能的。[3](P78)
高频使用是词汇化的重要动力,谭代龙指出:此类用例太少,而且缺乏过渡痕迹,不能充分说明其结构上的来源问题。[4]此外我们认为,从方法论上说类推属于演绎,还需其他证据来证明。
2.明代定中式月光义的“月亮”是“月亮”的来源值得商榷
谭代龙认为,月球义的“月亮”是明代出现的月光义的定中结构“月亮”由部分指全体而来。[4]谭文认定文献中一共有六处“月亮”有月光义,限于篇幅,下面列出其中有代表性的三处加以分析:
①只见月亮地里,原是春梅打灯笼,落后叫了来安儿打着。(《金瓶梅》四十回)
②那楼上有方便的桌椅,推开窗格,映月光齐齐坐下。只见有人点上灯来,行者拦门,一口吹息道“这般月亮不用灯。”(《西游记》八四回)
③丽卿到阵里下了马,解去了裙子,女兵接去收了,露出大红湖络单叉裤,盘膝坐在月亮地上。(《荡寇志》八八回)
对于①,谭文通过引用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的解释“月光下的地面”,来明确“月亮”有月光义。而词典释义受主观、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制约,引释义确定词义应该慎重。清代文献和今天方言中有“太阳地”,后者方言词典解释作“太阳光下”,[2](P531)不能据此说“太阳”有太阳光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词语单位整体的意义未必一定要由构成成分坐实,“月亮地”的整体意义中有“月光”,并不等于其中的“月亮”就是“月光”。
对于②,谭认为前面说“映月光齐齐坐下”,后面说“这般月亮不用灯”,故“月亮”就是“月光”。而《西游记》中“月亮”只出现这一次,根据上文,“这般月亮”理解为“月这般亮”或者“这样的月亮”也可以。说②中的“月亮”就是“月光”,是仅凭一个孤例和一段上文得出的,难以让人信服。
对于③,谭文没有论证,直接说其中的“月亮”就是“月光”。《荡寇志》中“月亮”出现11次,其中9次是非常明确的月球义 (如“今夜的月亮镜子般滚圆”),剩下两次就是③中的“月亮地上”和另一处的“月亮地下”。而这两处整个词组可以解释作“月光地上”,并不等于其中的“月亮”就是“月光”。
综上可见,很难说“月亮”有月光义,因此,认定月光义的“月亮”是月球义“月亮”的直接来源并不妥。“月亮”下面《大词典》只列了月球义,没有列月光义,非常正确。在几千年跨度的文献中,非月球义“月亮”的用例只是个位数,①汪维辉补充了两条清代的主谓结构“月+亮”用例,[5]加上董秀芳和潭代龙文章中的,去掉重复,总共4例。固然这可以存疑,等待新文献出现再查找;另一方面,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既然用例这么缺乏,是不是说明同形单位就不是今天“月亮”的直接来源,“月亮”成为普通话通称自有其他途径?
(二)“月明”有月球义作通称的根本动因是“月”的双音化
文献中“月明”也有月球义,可以作通称,《大词典》列作义项,出例④,语料库中像⑤这样的则比较明确,今天方言中继续使用,如⑥。
④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唐·李益《从军北征》)
⑤秋玩月明冬赏雪,一生好景莫蹉跎。(元·刘唐卿《白兔记》)
⑥今黑间月明 (月亮)明得太 (很)。[2](P2213)
有月球义作通称的“月明”是如何成词的?能否借助弄清“月明”的成词来弄清楚“月亮”的成词?
1.词汇化不是“月明”有月球义作通称的根本原因
调查文献可见,与非月球义“月亮”用例只有个位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月光明亮”的主谓词组“月+明”非常活跃,从汉代到清代一直都有,按今天通行的做法,一般多从词汇化来考察分析:“月”、“明”分别符合主谓词组词汇化过程中主语名词的条件和谓语动词的条件,二者紧紧相邻、高频使用,当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时 (如“月明在天”、“未见月明”)被“重新分析”。②也可以认为是“月”和“明”直接组合而来。这种“组合说”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要组合成“明”在后的“月明”,而不组合成“明”在前的“明月”?这种“词汇化说”需要解释:语料库中“明月”是“月明”的两倍,“明”和“月”分别符合定中词组词汇化的条件,二者同样紧紧相邻、高频使用,为什么“明”在前的“明+月”没有词汇化为通称?像“明月”这样的定中“性状+事物”结构的作为月亮的通称,既有语言事实方面的证据 (如今天方言中叫“亮月”、“亮月子”),又符合汉语定中式词法结构的表意特质。[6]另外,词汇化之后的双音词一般会有一个大量使用的阶段,与此不同,月球义作通称的“月明”在唐宋、元明清文献中陆续出现,始终没有一个大量使用的阶段,这又是为什么呢?
2.“月”的双音化促使“月明”有月球义作通称
从普通话的词法结构看,像“月明”、“月亮”这样的“名1+形=名1”的,无论是历时发展层面还是共时应用层面,都非常特殊少见。我们曾经对“月亮”中的“亮”为什么在“月”后进行研究,从约定俗成、语音、词法、句法、语用、词汇化、亲属语言接触等多角度考察后很难解释,考虑到“月亮”这样双音单位明确地是顺应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发展大势,用来分化“月”不太常用的月球义而出现的新的能指形式,于是联系原单音词来进行解释,发现用“月+单音明亮义语素”形式来分化“月”的月球义,应该不是偶然的,明显的比叫“太阴”、“月子”、“亮阴”、“月爷”、“明月”有优势:(1)保留原单音词,显示新双音词与原单音词之间的关联,便于人们凭借对原单音词的熟悉,尽快地掌握和使用新双音词;(2)原单音词置于最显著的首位,更易引起人们注意;(3)“明、亮、光”等单音明亮义语素直接反映月亮夜晚最显著、为古人最需要、最期盼、最关注的重要的明亮特征,增加了词形的透明度。至于月球义作通称的“月明”在文献中不多见的原因,也和它所源出的单音词有关:“月”自甲骨文起一直就只有两个义项,时间义和月球义不容易混淆,完全不必双音化。后来顺应双音化发展大势,出现分化月球义的双音能指形式,但“月”是千年传承的核心词,加上文言的保守性,一直都在大量使用,甚至保留在今天的书面语中,致使分化月球义的双音节能指形式没有大量使用。[6]
(三)“月亮”取代“月明”等成为普通话通称
语料库中除了“月明”有月球义用作通称,“月光”还有月球义用作通称,今天方言中保留,此外今天方言中还有叫“月皛”的。因词义特征不同,这些通称中的明亮义语素,分别反映的是月亮呈现在人们眼中的三种最典型的明亮状况:亮得耀眼(“亮”、“光”)、亮得清晰(“明”)、又白又亮(“皛”)。从理论上说,这些通称虽然产生、使用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既然被汉语社团所创造使用,意味着它们都有成为普通话通称的潜在可能,甚至其他结构相同、构成成分意义相近的“月+单音明亮义语素”如“月皎”、“月皓”、“月朗”、“月白”等也都有可能,如藏语月亮叫ta12wa12,ta12是“月”,wa12是“白”;为什么普通话最终选择的又是“月亮”?
调查《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语料库发现,古汉语中“明”是明亮义的通用词,后来“明”因义项过多发生分化,明亮义交由“亮”,最终“亮”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明亮义的通用词。[7](P16)“皛”、“皎”、“光”、“白”、“皓”、“朗”等或者因为本身在古代就使用频率低,或者因为它们的明亮义项不如它们的其他意义 (如“光”的光线义、“白”的颜色义、“皓”的白色义,“朗”的开朗义)常用,因此,普通话叫作“月亮”不叫“月明”,也不叫其他的“月+单音明亮义语素”。
三、对词汇化的归属、双音化在词汇化中的作用等三个问题的思考
(一)词汇化在词汇学知识体系中的归属
前人对“月亮”来源的研究始终从同形形式出发,单个词语单线式上溯下推的做法是词汇化研究的惯常做法。如一所述,词汇化研究的这一模式性做法面临的问题是:历史上的同形形式是否和双音词有直接的源生关系?双音词是否都是由历史上的同形形式直接词汇化而来?
不少学者在对常用双音词来源的聚类和个案研究中已对此做出了回答。如丁喜霞指出,占并列双音词绝大多数的同义并列双音词主要是词法演变的结果。[8]刘晓然调查《太平经》100个高频词中来源于词汇化路径的双音词只占27%,大量的双音词是通过词根复合法产生的。[8]董正存在仔细考察语料后指出,情态副词“反正”不是由正反对立的并列短语“反正”语法化来的,它没有经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因而也没有一个词汇化的过程;普通话和方言里的“反正”类情态副词基本上都不是语法化的产物,而是一种构词现象。[9]由此可见,大家的观点很一致,即词汇化不是双音词的唯一来源,词汇化只是双音词的来源之一。
早在二十多年前,刘叔新曾经谈到,把一个固定语转化为一个词的“词化型转化法”,是和换素型改造法 (引者按:即类比造词法)、语素直接组合的结合法等造词法平行并列的一种方法。[10](P104)尽管刘先生讨论的是现代汉语造词法,“词化型转化法”和词汇化不完全等同,但对于我们认识词汇化在词汇学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归属很有启发。词汇化属于汉语造词法体系中的一种类型,主要存在于历史范畴,现代汉语共时平面中也有,但很少。[11]
有的综述性文章在梳理有关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历史时,把赵元任等前辈学者关于构词法的研究也大量概括进来,[12]这恐怕不妥。因为在汉语词法研究中,构词法和造词法互相区分,已为大家所认同。刘叔新指出,前者是静态研究,后者是动态研究,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区分很清楚。[10](P69)“词汇化”既然叫“化”,无疑属于动态造词法;造词法有多种类型,词汇化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在词汇化研究时,一定要注意考察、甄别古代的同形形式是否一定与今天某词语有直接的源生关系。而如何考察甄别,可以进一步研究,就目前实践看,遇到用例少的情况,最好不要猜测类推或者硬性分析。总之,在研究过程中增加这样一根弦,有助于保证出发点的正确。
(二)双音化在词汇化中的作用及两种研究的关系
如一所述,一般认为双音化是作为韵律因素促使词组或跨层形式重新分析或者粘合在一起,近来也有学者在研究中看到双音化在词汇化中的其他作用。如晁瑞指出:“容易”的词汇化发生在表示“许可”义的“容”双音化之后。[13]这里,基于单音词义项而来的双音化是词汇化发生的先决前提条件。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发现,如果说有月球义作通称的“月明”是由词组“月+明”词汇化而来,那么决定相邻的“月+明”而不是“明+月”词汇化为通称的是,单音词“月”的月球义顺应双音化发展大势改用最有优势的双音能指形式所要求的。这里,基于单音词义项而来的双音化,是决定相邻的A和B发生词汇化而不是其他相邻单位发生词汇化的根本原因。由于词汇化研究始终只是关注同形的非词单位到词的演变,不考虑双音词与单音词的联系,就很难看到双音化的这些作用。当然,作为汉语词汇非常重要的发展演变,双音化在词汇化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词汇化研究大举开展以来,“双音化”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再谈似乎很落后、过时。诚然,双音化中的一部分类型,如双音节词组或跨层结构变成双音节词、四个以上音节压缩为双音节,词汇化研究都能将其涵盖并拓展。不过,明显的还有一些类型,如基于单音词一个义项而来的双音化、语素合成新生双音词等,是词汇化研究所涵盖不到的。从研究内容看,基于单音词一个义项而来的双音化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这种类型的双音化是为已经存在的所指寻找一个新的能指。而单音词的哪个义项被分化出来改用双音词、新的双音词为什么最终是AB而不是其他的AC、DB、EF等,AB又是如何从众多可能候选单位中被选择出来的,其中的制约因素、机制是什么?它和今天汉语词汇的选择机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关涉汉语词汇发展规律,词汇古今“大同小异”本质特点的根本问题。由于词汇化研究始终只关注双音词及其历史上的同形形式,对于双音词和与其所来的单音词之间的渊源,对于上述双音词选用的问题一概不涉及。因此,词汇化研究与双音化的研究虽然有交集,但二者还存在许多不交叉的地方,前者不应该也不能完全取代后者。
(三)汉语词汇历史发展演变的研究方式
十多年来,词汇化研究的大量开展,促使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演变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多是开展词汇化研究,不知不觉中词汇化研究似乎成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演变研究的全部,显然这是不对的。
首先,如一所述,词汇化只是一小部分双音词的来源途径,对于大多数不是经由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须采用非词汇化研究的研究方式。其次,即使对于经由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如果仅仅开展词汇化研究,可以显示该双音词从历史上的同形形式到今天形式的单一纵向发展状貌,至于该双音词在其他方面的重要发展演变则无法显示。比如按一般模式研究“太阳”的词汇化,虽然有可能揭示词组“太+阳”成词的时间段、句法条件、成词后意义“由性状转指名物”等,但是对于为什么是“太+阳”而不是其他相邻双音单位如“极+阳”等发生词汇化,①“极阳”指称太阳,《大词典》出条例作义项。为什么普通话从那么多太阳的同实异称中,唯独选择“太阳”作为分化单音词“日”的天体义的新双音词,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制约因素、机制又是什么等,都不能很好地回答。众多研究实践显示,词语单位并非孤立存在,总是处于与其他词语单位发生的各种各样聚合、组合的关系结构中,彼此之间互相制约影响;汉语有许多不同于印欧语的地方,比如用表意汉字记录因而不同时间长度和空间分布上的各种单位都能被记录、保存下来,音衍成词、义衍成词、单音词双音化,言文分离、言代替文等等。即使是经由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也很难说词汇化是该双音词在从古到今的发展演变中所经历的唯一变化。而如果只是开展词汇化研究,导致对该双音词其他发展演变情况的屏蔽,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此,已有学者对仅开展词汇化研究的做法提出了异议。如许小颖经研究发现,今天浙江平阳闽南话中“阮我们”失去指称意义的“我阮我们母”、“我个的阮我们母”中,“阮我们母”类词语词汇化的动因是与亲属称谓的亲密度,语用中面称、背称严格区分等有关。受此活语言启发,她指出:近代汉语中大量产生的“乃X”类称谓的来源,和当时亲属称谓与其先行代词的使用系统有关,仅从先秦的“乃祖乃父”、“乃祖”用法来判断近代的“乃×”类称谓的来源和释义是不够的。[14]我们理解,从先秦的“乃祖乃父”、“乃祖”到近代的“乃祖”,就是一种单个词语单线式上溯下推的研究,而许文所说的从“当时亲属称谓与其先行代词的使用系统”考察,则属于一种着眼于特定词群的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的系统式研究。
实际上,汉语词汇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将词语置于各种系统中进行研究。如对各种语义场、结构组织、特定词群 (如亲属称谓、职事称谓、颜色词、眼睛活动词群等)内部成员之间互相影响制约、此强彼弱、此消彼长的研究;对同实异称词语之间互相竞争、共存的研究;对词语形、音、义之间互相作用、影响的研究等。这些优良传统为众多研究实践证明是符合汉语词汇发展实际情况的,但是近来由于词汇化研究盛行而被边缘化。于此,我们应坚持和发扬汉语词汇系统式研究的优良传统,把词汇化研究和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演变的综合研究态势,以便多方位地立体地呈现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复杂的发展演变状貌。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采用基于英语研究文献而来的学术体系和话语表述,日益成为汉语研究比较主流的做法,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传统的系统式研究因为为汉语所特有而很难直接搬借于国外,那么,如何借鉴新体系、新表述整装待发,是它面临的一大难题。
[1]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全卷本)[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4]谭代龙.“月亮”考 [J].语言科学,2004,(4).
[5]汪维辉.〈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评价 [J].语言科学,2006,(3).
[6]谢永芳.“月亮”的词素序——兼论A—AB式双音化对词素序的制约 [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1年第八辑.
[7]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刘晓然.双音短语的词汇化:以〈太平经〉为例 [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9]董正存.情态副词“反正”的用法及相关问题研究 [J].语文研究,2008,(2).
[10]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1]李惠.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化基本特征探析 [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2).
[12]刘红妮.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5).
[13]晁瑞.“容易”的词汇化与“容”表“许可”义 [J].汉语学习,2007,(1).
[14]许小颖.平阳闽南话中“三身代词+亲属称谓”格式——兼谈“阮母 (我们妈)”类词语的词汇化 [J].励耘学刊 (语言卷),2011年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