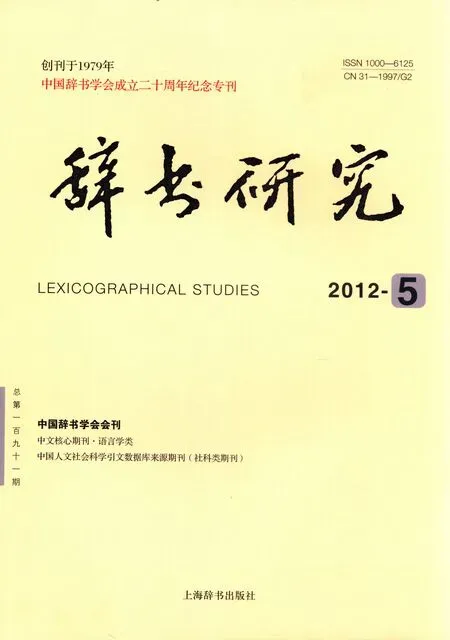继续努力,把学会的事情办得更好
曹先擢
中国辞书学会成立20年了,这在辞书界是件大事,值得纪念。最近我的身体不是太好,不能动笔,但还是愿意把学会成立和后来的活动说一说,我有这个责任。
中国辞书学会是1992年成立的。成立之前的酝酿、准备从80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辞书事业发展很快,1979年《辞书研究》创刊,团结了全国一大批辞书编者、研究者、出版者和读者(我就是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之一),它的作用很大、很好。后来上海、陕西、福建、安徽陆续成立了地方性的辞书学会,学术活动、学术交流逐渐开展起来,在上海、武汉、成都召开了几次有各地代表参加的会议。大家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辞书编纂出版的学术团体,来促进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于是就开始着手筹备成立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学会可不容易,得层层报批,颇费了些周折,多亏汪耀楠、韩敬体他们几位下了不少功夫,学会终于办起来了。开始的时候考虑一南一北设立双会长,可是民政部不允许,后来因为我在北京,就由我来担任会长,由巢峰同志担任第一副会长。以我的本心,是不爱出头露面的,而担任会长是一种责任,不能推脱。巢峰同志很早就参加新四军,是老革命,又长期在出版社社长的岗位上,组织《辞海》的编写,有经验,有水平,我们两个人思想一致,步调一致,团结得好,合作愉快。以后几年我曾到国外讲学,他代会长,学会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学会成立大会上,罗竹风先生说“学会的生命力在于活动”,我非常赞成。我们不仅一直坚持召开学会的年会,下属的各个专业委员会也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得早,会议的论文也多;参加双语词典研讨会的除了辞书的编者、出版者,还有许多大学的外语教师,又开了国际会议,黄建华副会长还出任第一届亚洲辞书学会会长,影响很大;编辑与出版、专科词典、辞书理论与辞书史以及后来成立的辞书编纂现代化、百科全书专业委员会都搞得不错。我们尽量发挥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会议多,论文多,学术交流一活跃,学会就有了凝聚力。这里还要说说中青年的会(注:即中国辞书学会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有特点,年轻人多,议题集中,一些老同志也参加,讨论得比较深入,很有朝气,富有生命力。我们不断地进行学术活动和研究,辞书学的地位也逐渐明确了,过去对辞书学到底是属于应用语言学下的一个分支,还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学科,看法不一致,现在我们是国家一级学会,也就是说我们辞书学的地位比过去提高了。
1994年,新闻出版署批准设立中国辞书奖。他们主办,学会承办。后来又有一些别的奖。那时评奖比较频繁,我们把住一道关,那就是不允许谋私利、走后门。有时候也有些人来送礼,我们也不怕驳面子,都拒绝了。人家虽然觉得面子上不好看,但是心里也还服气。这样搞辞书评奖,坚持了标准,评出了好书,顺利地配合出版署完成了任务。
辞书评奖就是评好的,树立榜样,引导方向。那些抄袭的辞书、不好的辞书我们也进行批评。当年王同亿找过我,向我请教如何编辞书。我说:“你不要向我请教,最好是找语言所,他们编辞书有经验,特别像吕先生。”他说:“我找过吕先生了,吕先生说我不合适编。”我说:“那比谁下的结论都正确。”我觉得王同亿他没有可肯定的,要明确他在语文词典这一块,没有值得肯定的。
辞书学会成立以后,辞书研究和辞书编写出版的队伍逐渐组织起来,辞书事业的发展才有了组织保障。我坚持这两条原则,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老一点的不说,年轻一点的像苏宝荣、章宜华、周荐、苏新春、李尔钢等等,都做得不错,有建树。我们这个叫广纳天下贤士。哪个学会都要有一些活跃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活动才能搞起来,李志江跟徐祖友我觉得就发挥了作用,我们放手,他们配合得也很好。
到了70岁的时候,我说照章办事,学会领导应该换届换人了。换届也要找到接班的,后来我就找到了江(蓝生)老师。我说:“你很合适,语言所有一个《现代汉语词典》,辞书学界有两大权威,一个是丁声树,一个是吕叔湘。你是吕先生一手培养的。”江老师比较爽快,这样就顺利地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她。她接着做,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退下来了,我仍然支持和参与辞书学会的活动,这点毫不含糊。凡是需要我出来讲话的,需要出来支持一下的,我尽力而为。办辞书班,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都参加讲课,讲的都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学员听了反映很有收获,因为那些材料都是我从现实生活里头、辞书编写里头、自己所用的辞书里头捞出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从书上抄过来的。
光阴荏苒,一晃学会已经成立20年了。这20年也是我们国家辞书事业飞速发展的20年,学会的学术活动跟辞书事业是紧密相关的,如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辞书学会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作用。我很高兴,愿意今后跟大家一道继续努力,把学会的事情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