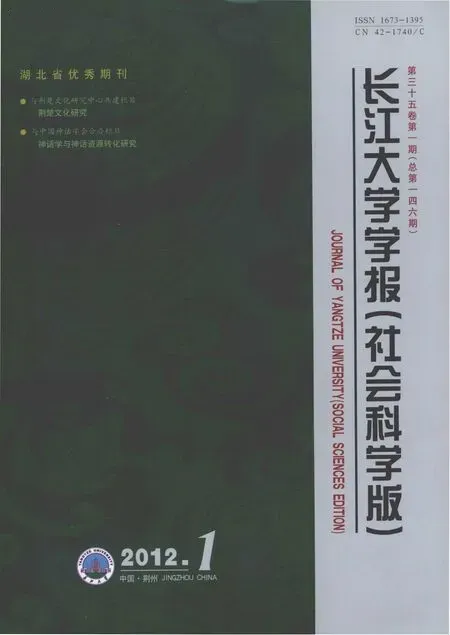《爱无可忍》中的男性身份危机①
娄淑洪
(中北大学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51)
《爱无可忍》中的男性身份危机①
娄淑洪
(中北大学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51)
《爱无可忍》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第六部小说。小说探讨了爱情的本质与人际关系等主题,但深层却隐藏着对男性身份危机的焦虑。通过分析贯穿全文的性别置换、对主人公男性身份的颠覆以及“无能化”等叙事策略,麦克尤恩解构了主人公的男性身份,揭示了当代西方男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爱无可忍;男性身份;危机;性别置换;无能化
二、对主人公男性身份的颠覆
劳拉·穆尔维认为,在电影中,女性以影像形式出现,是“被人看的”,是被展示的对象;而男性则是“看”的承担者,因而占据观看的主动性。观看者具有主动性和控制力,而被看者,即被展示的对象则是被动的、弱势的。[2]她进一步指出:“一种主动/被动的异性分工也同样控制了叙事结构。根据主导的意识形态原则以及支持它的精神结构,男性人物不能承担性的对象化的负荷。男人不容易注视他同类的裸露癖者。因此,奇观与叙事之间的分离,支持男人的角色作为主动推动故事向前发展,造成事件的人。男人控制电影的幻想,同时还进一步作为叙事的代表出现,作为观众的承担者……”[3]
小说中,帕里毫不动摇的凝视使主人公乔焦虑不安,情感生活陷入混乱。帕里守在乔家公寓外,注视着窗口,并且多次尾随乔。帕里的凝视使乔成为被看的对象,成为另一个男人欲望的对象。这种对象化使帕里占据主动性,而乔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即传统架构中的女性位置。帕里的凝视彻底消解了乔长期以来形成的男性优越感。从帕里的同性恋立场看,乔不再是欲望的主体,而成为女性化客体,因而也就丧失了男性特权。[4](P72)麦克尤恩通过帕里的凝视与对乔的执着纠缠打破了传统两性观,颠覆了男性/女性二元对立,进行了性别的置换,将乔置于展示或看的客体(对象化)位置。
正如劳拉·穆尔维所声称的,异性恋者乔不愿意成为对象化的承担者,即另一个男人凝视的对象。因此,出现了凝视与抵制凝视,消解与维持或巩固男性身份的矛盾。小说中,乔一直执着于证明帕里是患有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的疯子,他的爱是不正常的,这一执着行为正体现了这一矛盾。实际上,其深层原因是乔对自身男性身份的消解即女性化的忧虑和不安。
三、“无能化”
根据父权制社会的传统两性观,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非理性的;男人心胸开阔,女人猜忌多疑;男人冷静自持,女人情绪多变。小说中,主人公乔竭力表现出传统两性观中男人的基本特征:以事实为导向,怀疑情绪的和其他非逻辑的事物,对自己的看法极端自信。[5](P166)但是,乔的思想行为却多次与这些男性特征相反,出现了传统框架中的性别置换。
例如,在图书馆,乔感到有人在其背后活动,心中涌上“不祥之兆”。追出去后,他在街道拐角处,把纪念一个已故女警察的瓷花瓶扶起来,推得离扶栏近些,以防再被踢翻。
“我不由自主地觉得,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好运,确切地说,是保护。我还觉得,在这样充满希望的抚慰行动中,在抵挡那些疯狂猛烈而不可预测的力量过程中,所有的宗教都得到了创建,所有的思想系统都得到了展现。”[1](P55)
这种迷信的非理性的女性化思想行为与乔所坚持的男性身份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克拉莉莎对乔所说的有关帕里的事情有所怀疑,乔感到克拉莉莎对他不关心,甚至怀疑她有了新欢,企图以帕里事件摆脱他。于是,乔搜寻克拉莉莎的书桌,以期找到线索,“甚至把抽屉就这样开着,让[克拉莉莎]一进房间就看见了。”[1](P161)乔的这种猜忌多疑的行为,对克拉莉莎来说是一种背叛,同时也进一步破坏了二人曾经牢不可破的爱情关系。麦克尤恩在这部小说中不断彰显乔的主动、理性和自信特征,但却利用传统框架中的女性化特征悄悄进行性别置换,削弱甚至破坏了乔的男性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克拉莉莎说乔“太理智了,有时就像个孩子……”,而帕里也把乔的文章和著作贬为“就像一个疲倦的婴儿耍赖跺脚时留下的小小脚印”。克拉莉莎和帕里用孩子(婴儿)形象来形容乔,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对乔的传统两性观中男性特征(男子气概)和成熟理智的一种挑战。[4](P66)与前面的女性化手法相互呼应,进一步消解传统框架中主人公的男性身份特征。《爱无可忍》中,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乔都经历着对自身男性身份的威胁。无能或无力感使乔陷入弱势甚至“去势”(emasculation)的境地。
孩子是麦克尤恩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在《爱无可忍》中,克拉莉莎因年轻时的一次医疗事故失去了生育能力,二人在一起生活七年,一直没有孩子。尽管乔在生理上并无缺陷,但对他来说,“从未经历过为人父母者自我牺牲的真火淬炼”,势必造成男性身份的不完整。和孩子在一起,乔得“掩饰内心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的深层原因则是父性的缺失。而加速乔的男性危机的正是小说开始的那场气球事故。约翰·洛根为救一个男孩丧生了,而乔则出于求生本能和其他人一样放手了。这场事故加剧了乔内心的挫折感和对自身身份危机的忧虑,突出了乔的“无能”:面对事故,他不够男人,颠覆了乔对自身男性气概的一贯认知。
乔把气球事故与他二三十岁时偶尔做的噩梦联系在一起:“我梦见自己站在一处突出的位置上,目睹着远方正在发生的一场灾难——地震,摩天大楼大火,沉船,火山爆发。我可以看见许多无助的人们正惊恐地四下奔逃,……成千上万的只有蚂蚁般大小的人尖叫着,即将陷入毁灭的境地,而我却无能为力。”[1](P22~23)这个噩梦揭示了乔的心理上的无能感由来已久,而气球事故则起到了印证并强化他的无能感的作用。
这个噩梦是乔对现状不满却又无能为力的心理映射。他已过不惑之年,是个事业有成的科普作家和科学文章撰稿人。这份“在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牵线搭桥”的工作却使他产生了“我是寄生虫”的想法:“所有的观点都来自别人……我只是在简单地核对和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再把它们传播给广大普通读者。”[1](P93)他曾经是物理学学位和量子动力学博士学位的拥有者,学术会议的积极参与者,现在却成了一个学术的局外人,“就连实验室里的技术员或者学院的门卫都不会把我当回事儿。”[1](P97)乔的工作被边缘化,无法给他带来创造性的自我实现。帕里的骚扰加剧了乔对自己的不满,同时,在帕里的凝视下,乔长期以来标榜的“权威”受到了质疑:他“是被雇来吹捧别人产品的广告推销员”。科学的发展使他重返学术界的努力成为泡影。工作被边缘化,却又无法改变现状,这使乔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
四、结语
通过分析贯穿全文的性别置换、对主人公男性身份的颠覆以及“无能化”等叙事策略,伊恩·麦克尤恩解构了主人公的男性身份。《爱无可忍》利用上述策略对主人公进行艺术阉割,在文本深层揭示了当代西方男性面临的身份危机。
[1](英)伊恩·麦克尤恩.爱无可忍[M].郭国良,郭贤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Mulvey,Laura.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M].London:Macmillan,1989.
[3]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修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Childs,Peter.Ian McEwan’s Enduring Love[M].London:Routledge,2007.
[5]Malcolm,David.Understanding Ian McEwan[M].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2.
I106.4
A
1673-1395(2012)01-0039-03
一、性别置换
2011 -10 -22
娄淑洪(1977—),女,吉林白山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本文属中北大学校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课题(2011Y013)产出论文。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自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获得毛姆文学奖以来,他的创作生涯便与各类奖项入围名单相互交织。《爱无可忍》是麦克尤恩的第六部小说,也是他最成熟、最吸引人的长篇小说之一,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于2004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在《爱无可忍》中,主人公乔与爱人克拉莉莎的野餐被一场气球事故打断。这场事故将乔、帕里、洛根等人联系在一起:洛根为救气球里的小孩从高空坠地身亡,其他人则出于求生本能放手。乔为此深感内疚,而帕里却因此对乔产生了疯狂而执着的爱。从此,帕里对乔开始了追踪和骚扰,乔和克拉莉莎的平静生活被打破。经过努力,乔最后证实帕里是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带有宗教暗示色彩的同性色情妄想者。但乔与克拉莉莎的世界则完全混乱失序,爱情不复当初。该小说的显性主题是爱情本质与人际关系等,但文本深层却隐藏着对男性身份危机的焦虑。笔者通过分析贯穿全文的“性别置换”、“无能化”等艺术阉割手法来解构传统男性身份,揭示文本深层的男性身份危机。
“创世记”中,上帝用泥土造亚当,又取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确立了原始的亚当/夏娃,即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上帝将二人放置于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幸福地生活在乐园中,直到撒旦化作毒蛇,引诱夏娃吃禁果,连累了亚当,致使二人被上帝逐出伊甸乐园,从此陷入生死轮回的充满艰辛的世俗世界。在失乐园的故事中,夏娃是被引诱者或灾难引入者,而亚当则是被连累者。亚当/夏娃(男/女)的二元对立结构演变为被连累者/被引诱者或灾难引入者的关系。小说《爱无可忍》开始,麦克尤恩也营造出伊甸乐园的情景:乔和克拉莉莎在公园野餐,“沐浴在明媚的阳光里”,享受着“苦栎树旁那片鲜嫩的春日草坪上的幸福时光”,他们“自由奔放,亲密无间地生活着,存在着,没有什么能威胁到”[1](P11)他们。一场气球事故使乔和帕里相遇,打破了乔和克拉莉莎的“伊甸乐园”。“邪恶的”“毒蛇般的”帕里闯入二人的野餐(生活),将乔“引诱走”:“我们正像恋人一样奔向对方,对这份羁绊即将带来的哀伤一无所知”。[1](P2)帕里作为乔的爱慕者开始了对乔的跟踪、纠缠,从此,乔和克拉莉莎的生活陷入混乱和痛苦之中,“幸福、安闲、舒适”的生活不复存在,二人关系最终破裂。在麦克尤恩版本的“失乐园”故事中,被引诱者或灾难引入者变成了乔,而受牵连者、被连累者变成了克拉莉莎。父权制的传统两性观框架中,亚当/夏娃(男/女)对应被连累者/被引诱者或灾难引入者的模式,在《爱无可忍》中被置换成夏娃(被连累者)/亚当(被引诱者或灾难引入者)模式,即亚当被夏娃化了,乔被女性化了。这种性别置换的女性化叙事策略在文本深层揭示了男性身份危机。麦克尤恩在小说一开始就在文本深层埋下了对男性身份危机的忧虑。在随后的情节发展中,乔和帕里的冲突以及乔执着于证明帕里是德·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男性身份危机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