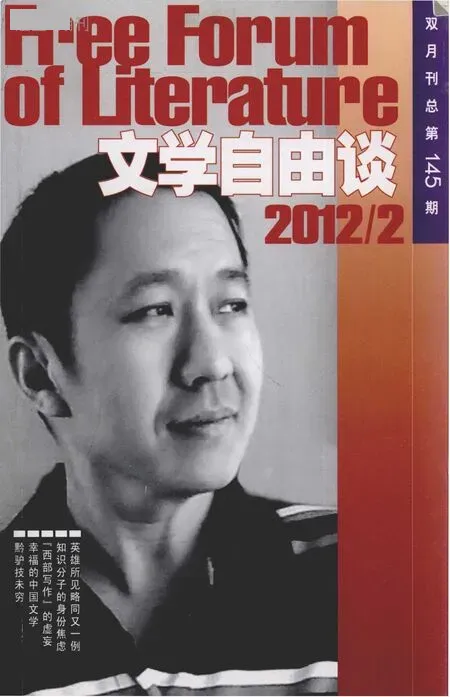我看《十四家》
●文 罗强烈
《十四家》首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其文风。所谓叙述,我认为也可以说就是用语言指陈事实的过程。名与实之间的联系,历来渠道缠绕,有简切者,也有繁复者。用美国作家来打比喻,福克纳的名实之间就很繁复,甚至语义再生语义;而海明威却很简切,语义仅仅指陈事实,然后,让事实本身呈现意义,《老人与海》便是明证。海明威的文风,当然受到其记者生涯影响;巧的是《十四家》作者,据说也是一位记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倡导过“新新闻主义”写作,其中包括文风,也包括文体。二十多年过去了,《十四家》正是我当初倡导“新新闻主义”写作时的心仪之作。
我很欣赏作者的写作追求,包括文风,更包括叙事。用几乎没有修饰的语言,把基本的事实陈述出来,就像觉悟之后的塞尚一样,山和树都是本来面目,连风和光这些容易讨好人的修饰都去掉了。无论是《十四家》作者,还是塞尚,这样做当然有这样做的力量。
我们看看翟益伟家的一个生活小故事:翟益伟到深圳打工,母亲和三个孩子留守贵州老家;一次,翟益伟托人带回三百元钱,给一家老小买粮吃;老大翟莎却想给自己买件像样的新衣裳,老二翟兰知道这是口粮钱,见说服不了姐姐,便把钱一把夺过来跑了,翟莎急得拿起菜刀去追赶妹妹;翟兰跑了一阵回来,弟弟告诉她翟莎上山了,翟兰以为姐姐是到母亲的坟上去哭诉,她上山一看,姐姐吃了农药趴在那里……最后,翟莎是救过来了,三百元钱却交了医药费。
这个故事的力量,就源于生活的面目没有被语言遮盖,而呈现出本身的深沉和多义:十五岁的妹妹知道这三百元钱是口粮钱,十六岁的姐姐能不知道?相濡以沫的姐妹,何以要用菜刀相逼?十六岁的少女想穿件好衣裳,难道没有充分的理由?她喝农药寻死,难道不是这种理由最惊人的陈述?那么,最后那三百元钱既没买上口粮,也没买成衣裳,而是交了医药费,这当然是悲剧,但它却是一个不只一种意义指向的悲剧。
《十四家》是一部纪实文学,写了中国西部的十四个家庭,而且是在与东部的对照中来写这十四个家庭的。从作者的总体追求上看,他写十四个家庭的基本人生,是想通过这种基本人生写出人生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意义。人可以穿得花枝招展,但那是衣裳;人可以吃得脑满肠肥,但那是脂肪;人可以擦得光鲜水灵,但那是皮肤……只有《十四家》这种在柴米油盐的人生基本形式里的基本生活,才是骨头,是生活的骨头,是人生的骨头!能够如此对生活和人生入骨三分,是《十四家》最打动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