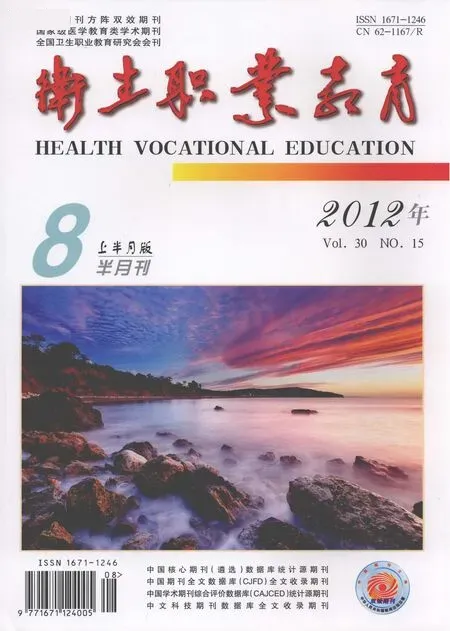在汉英语言对比中探寻汉语真句
杨千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汉英语言对比中探寻汉语真句
杨千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印欧语研究模型下,描写的汉语句子并不能在整个汉语语法体系中发挥其实际作用[1]。这种模型下句子并不是真正的汉语句子,也不等价于英语的sentence。本文对英语句子概念形成过程进行对比、分析,以英语、汉语自身特征为切入点,探寻汉语真句——音义互文句。
马氏文通;sentence;汉语句子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语法的研究常常陷入一种“困圈”。如翻译“村东头种了百来棵枣树”、“山那边跑来两匹马”,因为找不到对应英文sentence的主语(subject),勉强将“村东头”、“山那边”冠之“主位”[2]。这种替代“主语”的做法,未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对英汉句子概念形成过程进行对比、探究。
1 英语sentence概念形成过程
首先,追溯到Plato时代。Plato在他的《克拉底鲁篇》和《智者篇》里,认为sentence有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onoma(noun)和rhema(verb)。前者表示发出动作者或所谈论的事物,后者表示动作,两者缺一不可。不过在当时,这种表述还只是停留在词类名称层次上,并未作为sentence成分对待。
继承和发展Plato说法的是Aristotle[3]。他是第一个正式使用subject的人。最早可见《范畴篇》(Categories)。当时Aristotle用它表示两层意思:第一层表示陈述的对象。所谓陈述对象就是回答范畴方面的问题。第二层表示实体。即实体跟其他的范畴是对立的。实体可以独立存在,不依赖于其他范畴,而其他范畴则依赖于实体,离开了实体,就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两层意思是互为联系的。Aristotle将subject纳入逻辑研究中,使sentence有了抽象的规定性,这是因为思维跟语言密切联系。Aristotle逻辑研究对后世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David Grystal在《语言学与语音学词典》中指出,sentence是最大的结构单位,一种语言的语法借此组织成形,即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构建更大的语法单位,如discouse或text[4]。
Jesperson则进一步在《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中得出结论:sentence是一个完整的和独立的人类“话段”——其完整性和独立性是由其独立成句的形式或其独立成句的能力体现出来的。这里的“能力体现出来”就是由形式加内容构显出的一个动态的抽象的想法,尤其应关注的是人类的“话段”概念表现出的自主性或完整独立性[5]。
20世纪50年代,sentence深受Chomsky语言学影响。Chomsky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中提出,A sentence is not just a string of words in a linear sequence but is structure into phrases,all ofwhich connect together tomake up the whole[6].可见sentence在Chomsky语法体系中是一个动态的、抽象的,可以自我发展,可以转化生成的独立单位概念。
怎么认识subject在句中所处的空间位置?Chomsky的普遍生成理论认为,英语是形态语言,巧合的是当subject在句中生成,位移时,大多数情况正好位移到首词位上,占据specifier位置。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在由深层向表层转化时,没有移到这个位置。
如Happy is theman who is our teacher of English.subject应视为theman。
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证明句子的“动态性”。总之,英语sentence是动态的、抽象的,能独立构成一个语言单位。
2 汉语句子概念形成过程
“句子”是现代汉语的叫法,古汉语大致称“句读”。据《说文解字》(许慎)和《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句”的本义是“弯曲”,“句”是“勾”“钩”的本字。“章句”的“句”是派生义,表示此处可停留,可打勾。“读”,读作“逗”,一般认为,是点在句子中间,表示此处需要语气停顿,即使语意未完。《文心雕龙》指出:“置言有位,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马建忠深受西语影响,但对古语“句读”的理解有偏颇,他在《马氏文通》中指出:“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因此,他将“句”理解为:“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句者,所以达心中之意。而意有两端焉:一则所意之事物也,夫事物不能虚意也;一则事物之情或动或静也。”而“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所以他最后把定义修改成了:“起词、语词”两者备而辞意已全者曰句。”[1]
马建忠谈到的“不能虚意”就是把汉语句子主语理解成为具体的、静止的。所以“起词”、”语词”就是要对应于英语sentence的subject和predicate。显然,这个“起词”被机械定位于“凡字相配”的词序层面,没有真正理解或意识到英语sentence中各成分语义生成的动态性,也就无法理解sentence的抽象性本质,以致生硬地套用了英语sentence表层结构的词序,因此,造成后来在此框架下汉语研究陷入“困圈”的情况。
3 《马氏文通》后阶段
汉语研究与其说接受了西方语言研究模式,不如说是接受了马氏框架模式。在马氏模式下,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开始谈论词类、句子成分等。他们对句子定义也都跟马建忠观点差不多。
王力对句子定义:“句子”是“包含一个大首品(主语)和一个大次品(谓语)”。吕叔湘认为:“我们说的话,书报上印的文章,句子的数目是无限的,可是句子的格式是有限的。语法就是讨论句子的各种格式。句子的格式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7]
1948 年,《马氏文通》发行5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赵元任在美国出版了《Mandarin Primer》,指出大部分汉语句子是整句(full sentence),是subject+predicate[8]。
但是,当他们进一步研究汉语语法时,陷入如:“我是两毛钱”、“这个地方可以浮水”语法分析的“困圈”,因为“主语”不表示所指示的实体行动或性质。为解释汉语这一现象,中国语言研究者进行了一番探索努力。王力认为:“主语并非中国语法所需求,故凡主语显然可知的时候,以不用为常。”[9]赵元任主张:“动词可以做主语。”[8]吕叔湘提出了区分“静态单位”跟“动态单位”的主张,他把语素、词、短语等归作“静态单位”,句子加上语调归入“动态单位”,“不同的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7]。虽然从结构上说,句子大多具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可是这不是绝对的标准。即使只有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在书面语中,句子终了的语调用句号、问号、感叹号来代表,有时也用分号。Chomsky在《Universal Grammar》中,将汉语句子归入“pro-drop”一类,即大多数情况下汉语subject“丢掉”了。
以上有关汉语句子的分析主张和理论,表面上虽能自圆其说,但没有对其进行深层次分析,难以令人信服,面对西化的或白话文的汉语句子,这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中国语言研究者的出发点还停留在实际意义运用的层面上,没有对“马氏框架”句子本身进行理论的反思。如果我们反问:长达数千年的古代汉语怎么理解分析?倘若现行汉语语法不能解决古代和现代汉语结构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个语法的普遍性令人质疑。
4 探寻带有普遍意义的汉语句子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汉语句子似乎很像utterance(话段),《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对句子是这样定义的:What is said by any one person before or after another person begins to speak[10].赵元任在《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提到:A segmentof speech bounded at both ends by pauses.他提出:“在汉语里,主语和谓语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施事与动作关系,不如说是话题—说明的关系……因此在汉语里用含义更为广泛的话题说明也许要合适得多。”[8]
值得肯定的是,赵元任是第一个用“抬升”句子法研究汉语语法的[11],其本质上是将汉语句子理解成为抽象性的语言单位,改变以往汉语研究只注重表层结构,忽视逻辑形式,注重实用,忽视抽象的做法。但当分析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悠悠岁月,沧海桑田”这样的句子时[12],这种unterance(话题)分析法似乎力量不够,层次不足,是否再将分析句子的思路“提升”到“篇章”(discourse),有待讨论。
吕叔湘也曾多次讲过汉语的流水句,句子之间的界限不清楚,可断可连[7]。这显然跟修辞研究密切关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加之,中国人历来重视“篇章组织法”,如曹丕《典论》中谈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王充《论衡》、刘勰《文心雕龙》都在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以至于秦汉以来的“散骈”文演化为明清的“八股”文,逐渐形成“文而优则士”。那些“理还乱”的流水句都吸纳在“篇章”骨架中,似乎“篇章”更适合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汉语句子。
冷静思考一下,“篇章”毕竟强调了句子的宏观特征,带有很强的功能主义,偏重的是意义研究;作为语言单位,显然过大。但“抬升”句子研究方法的本质是将句子抽象化,这个思路不应舍弃。
循常例,人们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说法,辩证思考一下,是很矛盾的。形式与内容在一个“完美的”事物里是统一的。没有什么“重”的形式搭配“轻”的内容,也不会有“少”的内容搭配“多”的形式之说。语言是“意”与“形”的有机统一,如果这个“平衡”打破了,这个事物也就不会存在[13]。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汉、英对比的提法,反过来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分析语言的思路:既然两种语言“形”“意”都应是“完备的”,那么就汉语来讲,它的“形”是什么?在哪里?是不是还存在什么语法范畴而我们没有认识到?
5 探讨最典型的汉语句式——骈文偶句
如《文心雕龙》中《丽辞》篇:“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4]这是对流水偶句的说明,其本身也是流水偶句。我们注意到在sound诵出音韵的同时,既可以得“意”,又可以在声韵与句式变化中见“形”;最具特点的是“意”“形”互照,在声韵中“溢出”subject和predicate。钱钟书在《管锥篇》中也提出“语出关联”“文蕴两义”“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
其实,这并不奇怪。英语是所谓的形态语言,是通过词形变化将语义投射出来的。而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投射语义的办法也得借助于他“物”,也就是说需要某一种特殊的“形态”变化担任这个角色。因为投射语义是所有语言的共性。汉语单音而有声调的特点,决定它“向内通过字形字音来表现字义,向外通过相对位置来映衬字义。并列式结构的词可以通过相互对待来确定其整个词的意义,比它更大的单位也可以通过与对应成分的关照来确定其意义”[15]。所以承载这种特殊“变体形态”投射意义的任务就落到“并列竹节语式”与“声韵”相互变化上。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
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
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
句虽长短不一,却有序;在字、词、声韵搭配中,“文义”遥对,溢“意”于“心”,我们不妨将这种以“音”带义,以“并”勾形的句式称为“音韵互文句”。
这种“音韵互文句”符合英文sentence的定义:抽象性、动态性,既可表达一个完整意思,又具有结构自主性或独立性。推演到现代汉语中,所谓无“主语”句子,并非无“主语”,只是互文中“化入”“音”中,曲折反射出subject。只要读者有“声”,“意”立溢而出。所以汉语的“音韵律”就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这是以前我们研究汉语时,没有将其纳入语法体系的原因。
计算机的运用学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语输入计算程序后,它所占的内储比英语要少得多,简单得多,这是由于汉语的“形态”造成的。但如果没有机前的人对汉语“音”的识读,许多“意”也就会“have gone!”或“drop!”。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探寻带有普遍性的汉语句子,从中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必须摆脱《马氏文通》机械套用英语sentence的做法,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特点来研究汉语,这样才能走出汉语研究的“困圈”,真正认识汉语句子。当然这不是否定语言的共性,而是在“共性寓于特殊性”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接近、丰富这一“共性”。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吕叔湘.马氏文通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3]Jowett B.TheDialoguesof Plat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71.
[4]Crystal D A.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M].Osford:Basil Blackwell,1985.
[5]Jespersen O.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London:George Allen& Uniwin,1924.
[6]Chomsky.Syntactic Structure[M].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7]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ChaoYuen Ren.Mandarin Primer[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9]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10]理查兹.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1]Chao Yuen Ren.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68.
[12]曹逢甫.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M].谢天蔚,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13]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4]朱德熙.句子和主语[J].世界汉语教学,1987(1):31.
[15]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G420
A
1671-1246(2012)15-0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