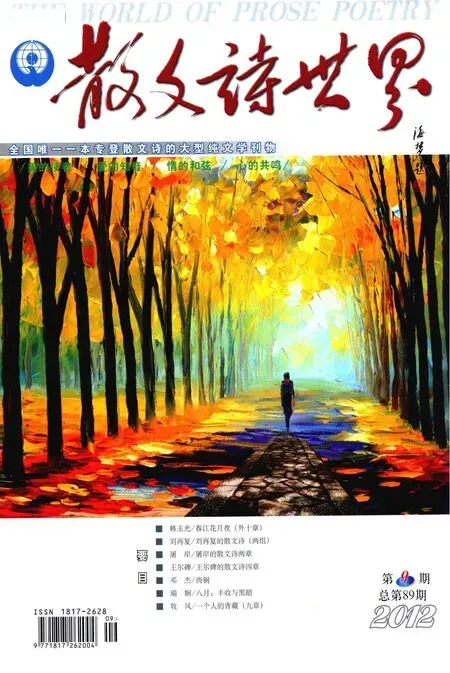月牙泉(外二章)
甘肃 杨玉林

这粼粼的水瘦成的一弯月亮湖,已经是一个被岁月演绎了千百年了的神话。在遥远的西部边塞,它清澈的眼神阅尽了风雨沧桑,你看,千百年来,它就被沙漠紧紧地搂在胸前,那么柔情蜜意,那么持之以恒。
山泉共处,沙水共生,山因庇护水而雄伟,水因守护山而奇丽。是谁还在坚守最后的纯净?在风雪肆虐的千里之外,还要再坚守一千年吗?月牙泉,如果,这世上没有了光亮,你就是最后一丝。如果人间没有了诗歌,你就是最后绝妙的一首。你是历经千年苍茫却保持青春容颜的女子,也只有你才能把这圣洁的王冠一戴千年。就是这样的,风沙可以在经过你时绕过,让你的眼睛永远清澈而不浑浊;是这样的,你用坚守的信念将内心镀亮成蓝天的颜色,古老的沙漠才能在沉重中透露出轻盈和大美。
有歌声传来:那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是天的镜子!是苍天不小心遗失了一面铜镜,被风深藏在了沙漠,或者是天把镜子安放在了边塞,用整个敦煌作为支架。矗立在月牙泉旁,我们的眼睛突然显得多么渺小,渺小的可以被温暖的阳光忽略。
骄阳如火,阳光细密地渗入沙漠,掩埋了我们赤裸的脚。沙山环绕,钟声悠悠。在月牙泉边,我们手拉手跳舞,我们的手围绕成了圆圆的月亮,我们的身子站成了月牙泉的模样时,蒙古族少女的舞姿开始翩然而起,骆驼从身边走过,远处的驼铃声就要在风中消逝成一首晚风中的歌谣。
而不远处的月牙泉静若处子,它的一汪碧绿的身子如被微风吹着的绸缎,在阳光下燃烧,如一条早已被打开的金色诗卷。
鸣沙山
大漠。孤烟。玉门关。偏有沙岭晴鸣,响一处江南。
当风吼起,比一首边塞诗里面的风声还要大,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它先是在长城中溜达了一会儿,沿着祁连山的雪花,现在它终于停留在了绵延四十千里的热情的沙漠。
“沙——沙”,是风把嘴唇贴在沙漠耳朵上的一阵诉说吗?抑或是沙漠愤怒的时候发泄给风的一通气话?当朔风而起,那些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抑或黑色的沙子便奏起天籁之音,整个沙漠就突然组成了一场音乐的盛宴。
见惯了城市高楼大厦或者听腻了车水马龙的噪音,当伫立沙漠,就这样听风的声音,或湍急,或潺缓,或温柔、或凌厉,细微又宽阔,因风,这座山才有名,当风吼起的时候,才是山的灵魂被紧紧依附在了身上。就这样,绵延四万里的孤独和寂寞,就被岁月的风一吹千年,吹出了一座真正的鸣沙山。
看,被风吹了千年的鸣沙山正在将头枕在莫高窟的怀里,将腿伸到了党河口。我是那么地喜欢它那形如金字塔,棱角分明得模样,喜欢它形如巨蟒,长长而卧的模样,喜欢它形如月牙儿,肩与肩靠在了一起的幸福模样。当沧桑的风骑在了鸣沙山上,当骆驼的足迹铭刻在鸣沙山上,无论来自周围多少的重压,山吼出一声声沙石般的声音,或赞美、或叹息都是一声千古绝唱。
仰望鸣沙山,像天下垂了一面梯子,也像大地陡然竖起后细软的模样。我们光着的脚伸了进去,在脚底的黑暗中迂回前进,当我们拔出了一脚一脚的黑暗,又用脚丫掩埋了一脚一脚的光明,我们就到了鸣沙山顶。这时,静坐下来,吹一只陶埙,陶醉其中,如陶醉在唐朝的风中忘记了清代的雨……
莫高窟
面对莫高窟时,时光似乎是先回到了一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夜晚:奇异的三危山为一位手执赐杖的乐僔和尚打开了一道智慧的灵光。乐僔的第一斧头凿进了岩石:一个道人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完成了涅槃,诞生了一方佛光四照的圣地。
“舜逐三苗于三危”。千佛跃动,金光闪闪。四百三十五个洞窟经过的不是时光,是佛光。佛光牵引着梦中的敦煌照亮了十六国,四万五千米的壁画、两千四百一十五尊佛像在祖国的天空升起万朵祥云。
我佛善哉!凿岩壁,叮当有声,敦煌好似被“一画天开”,不绝悦耳于河西走廊:这个沙的世界。千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背靠世界,面对莫高窟里的一尊尊佛像之时,面对飞天、伎乐、舞蹈、饮馔之时,一个人的身体里会没有了虚伪、杂念、险恶,没有了痛苦、诅咒、怨恨,因为佛早已把人的心分为两半,一半是慈,一半是善。
是的,莫高窟的时光却是温暖的,仿佛是佛的目光,一点一滴融进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已经穿越时空在时光的流里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就这样在静默时,遇到灵魂。望着那些沐浴了千百年佛光的建筑、彩塑、壁画仍然在今天的时光中云蒸霞蔚、浓郁如新,透露着神秘、荒凉、静谧、宏大。万物皆会朽,唯有这里的一颗颗博大的爱心,与宇宙是永恒的。
“所谓成佛,就是一个人把一颗心献给了天下的众生”。站在莫高窟面前,我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如一颗新生的露珠,我深感自己终于把自己还给了这个世界,把梦还给了岁月,把岁月还给了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