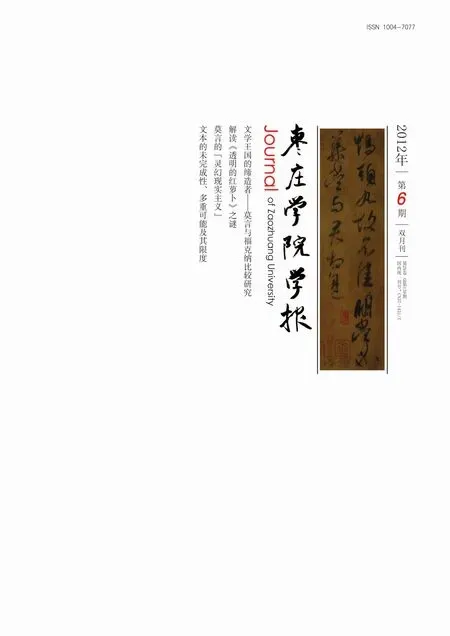中国古典医学中的视觉知识
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著,张春田译
(1.美国哈佛大学 东亚系;2.香港教育学院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那么,关于花的主要事实是:它是植物在其生命最热烈的阶段所发展出的那部分形式,这种内在的狂喜,通常在外观上向我们显现为一种或更多基本颜色的绽放。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空气女王》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希腊古典医学关于人体的描述和中国古代医师关于身体的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奇怪差异?两种悠久的文明是如何以极为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基本并且最隐秘的人类真实的?
我们从晚期中国和欧洲医学的两本著作——元代医生滑寿所撰《十四经发挥》(图一)和安德鲁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所著《人体的构造》(Fabrica)(图二),来看一下这种分歧的遗产在插图上的体现。如果并排看,这两幅插图都不忠实于“腔隙”(lacunae)。在滑寿的图中,我们正好失去了维萨里图中人的精确连接的肌肉。事实上,传统中国医学中,没有与肌肉概念真正相等的东西。迷恋肌肉组织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反过来,在受针灸者身上标记出的那些点,也必然排除了维萨里关于身体的幻想。因为它们,即使对于中国人的眼睛,也是不可见的。这样,当17至18世纪欧洲人开始浏览中国医学文献,他们所见的身体描述,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来自想像之地的叙述。一个英国医师会认为它们是“奇妙的”,而另一个会认为它们是“荒谬的”。中国“解剖学”一点也不像伽林(Galen)或者维萨里所曾看到的。
这些区别不是永恒的。对针灸网络的经典理解只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而系统的解剖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发明。并且,在中国汉代末期,——在希腊世界那时正是伽林(129~200年)活跃的时期,——传统欧洲和传统中国在身体观念上的显著对比,已经形成了。滑寿和维萨里描述上的不一致,返回了希腊和中国的古代遗产。
在这篇文章中,我计划探讨一个特别的对比:观看方式的区别。我尤其想对于中国医学中视觉知识的本质,及其与中国人身体理解之间的关系作一些阐释。
它们之间表面上看不出有关系。人们会认为,图二和图一的差异反映了看和不看的对比。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特殊性,正在于中国医师忽视了眼睛的证据这一事实。尽管不把中国观念当作白日梦而拒绝,人们会这样想:不同于依靠视觉,中医采用的是另一种、非视觉的方式去接近身体。这很大程度上是确实的,中医从来不承认由希腊解剖学家们发现的细节,而对于那些为解剖学难以证实的不可见结构则加以整合。中国人身体观念使人困惑的他性(otherness),大部分存在于它对于解剖学主张的抵制上。
然而,如果我们将全部或绝大部分中国身体观的奇特之处归结为某种异域的视觉冷淡,那就错了。看与不看之间的对比,使得不“解剖学式地”(anatomically)观看被误解为根本不看;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古代中国对解剖的忽视,却伴随着一个对视觉能够揭示什么的特别信仰。实际上,像希腊解剖学家一样,中医不仅观看并且专心地看,只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观视。
扁鹊的传奇证明了医学和观看之间特殊的联系。这位古代最有名的医师最初和医学没有什么联系。他在管理一家客栈时,遇到一位叫长桑君的客人。一次,长桑君把扁鹊叫到一边,偷偷告诉他:“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长桑君拿出怀中之药,解释道:“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配用新鲜露水喝下这个,三十天后你会知道了)。”扁鹊按照他的指示做了,很快能够看透石墙,还能看穿人体。[1]
因此,扁鹊向“中国的希波克拉底”(the Hippocrates of China)的转变,开始于敏锐的透视力的获得。如果他的名字和医学天赋是同义的,那部分是因为他能够观视,而其他人却不能。他对蔡桓公的著名诊断正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扁鹊检查蔡桓公的病情,不是通过询问他,——因为蔡桓公自己没有意识到生病;也不是通过闻嗅气味或触摸患部;而只是从很远的地方观察他,就发现了病况。[2]
透视力的奥秘不仅局限于圣徒传式的传说中,在基本的经典医学文献中也可发现其回响。在《黄帝八十一难经》(以下简称“难经”)中,“望”而获知疾病,被称为“神”;“闻”[3]而获知,被称为“圣”;“问”而获知,被称为“工”;切脉而获知,被称为“巧”。具神性的透视力,是理解方式中等级最高的。《灵枢》对于感知能力的分等和界定与之有些不同,但是它也把“明”的观照放在优先位置。[4]《伤寒论》明白地说:能够通过观看而知道病况的医师属于“上工”,通过询问而了解的医师属于“中工”,通过触诊而了解的医师属于“下工”。[5]精通医学需要一双非凡的眼睛。
当然,视觉一直居于西方认识论的中心。一方面,被用来建构知识的主要是视觉经验,以致科学话语会把视觉和知觉,观察和经验,解剖性(autopsia)和经验性(empeiria)有规则地合成到一起。另一方面,对这种特别的思考和了解的经验的理论反思,也被作为观看的形式。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6]
这使得一些学者认为视觉霸权是一个西方独有特征,或许根植于印欧语系的本质。[7]但是,中国哲人们也谈到“玄”、“微”之道,智力上的“明”,以及宇宙原则上的“观”。在中国医学中,知道什么和意欲了解什么,都和看的行为密不可分。
因此,对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追求另类的视觉知识,我们也必须考察一种另类的视觉风格。[8]尽管中国医师像希腊解剖学家一样,赋予了视觉以极大的重要性,但如果从解剖学的视角看来,他们观看的方式像是一种失败的观看。我的论文考察这种不同的观看方式的本质和神秘性,及其对于中国医师如何了解、为何如此了解的含义。
观看的对象
眼睛到底能够知道什么?什么看到的东西证实视觉的威权?中国医学经典给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答案:观看是观“色”,观“五色”。如果说希腊解剖学家的眼睛专注于结构,那么汉代的医师们则专注于颜色。
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手指触摸皮肤的纹理、肉体的温度和质感、脉搏的跳动,鼻子嗅闻病人的身体和排泄物,耳朵倾听嗓音音调、呻吟声,还有病人经历的报告。眼睛观察很多东西——体形、步态、睡觉姿势、水肿、皮疹。但首先,医生们“望色”。医学实践中,颜色吸引着最为持久、一贯的视觉注意力。理论上,颜色规定了视觉的功能和基本原理。在传统中国医学中,把“看”等同于“望色”,是一个最为基本、不容怀疑的假设。
这让人迷惑。如果我们问自己一个医生应该看什么,“颜色”这个词很可能不会马上浮出脑海。我们也许会在观察的东西中包含病人的脸色,但是,正如回答“鼻子能辨明什么”的询问时,只答“气味”看上去就足够了;从颜色中提取视觉证据,看上去太奇怪了。这种关注的动机是什么?对色的关心是如何与透视力的神秘性联系起来的?更基本的,“望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是关键的问题。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上说,脸色发黄或发红,是发烧的症状;脸色发白,意味着伤风;脸色发绿或发黑,表明痛苦。[9]肝脏发热,红色首先显现在左脸颊;肺部发热,显现在右脸颊;心脏发热,显现在前额。[10]这是“望色”的一种形式:注意脸色的变化,把它们和身体的变化联系起来。虽然我们可能会怀疑这样的诊断,但对这种观察的精神是十分熟悉的。我们也会从脸上面色苍白、或发烧般的潮红、或黄疸中,推断出那些人的健康状况。中国医师留意面色这行为本身,没有什么令人困惑的。
使人困惑的是,颜色被视作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医师把“看”等同于“望色”,而且相对于其他认知方法“望色”占据了最高位置。颜色作为疼痛、发烧和伤风的暗示的价值,并不就足以证明判断。这不仅因为疼痛、发烧和伤风只是医生需要认知的一些状况,而且因为它们只是宽泛的症状,其间存在无数细微差别和各种可能病因。如果“色”揭示的是如此含糊的状态,那么坚决主张“色”的标准,是很难理解的。
事实上,存在另一种更有影响力的阐释,即赋予颜色以宇宙的和肉体的意义。绿红黄白黑五种基本颜色,每种对应于宇宙变化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的一个。通过观察病人脸上显露的颜色,医生能够确定主导病人状况的一“行”。比如,红润的面容,显示了“火”占主导;发黄的脸色,显示了“土”处于旺盛。[11]颜色深浅的细微差别,各种颜色出现的时间和位置的不同,以及其他感官的迹象,都会增加实际的复杂性;但是主要原则很简单:看就是“望色”,因为五种颜色使眼睛与伴随宇宙的五种形式变化联系起来。
这种接近颜色的方法在汉代权威的经典中已经显露头角,并且为所有关于诊断的视觉的后经典注解奠定了理论框架。今天,它仍然是传统医学的现代教科书中普遍给出的研究色的基本原理。
这种诉求不难理解。通过将辨析颜色与细察生物宇宙变化的五行节律相等同,这种阐释把视觉知识紧紧嵌入了传统医学理论的阴阳/五行框架中。此外,不单只有医师把颜色和更大的意义对应起来。对于政治理论家来说,五种颜色激荡起朝代的兴衰。白色是商朝的颜色;红色,是接下来的周朝的颜色。有传说,后者征服前者是有预兆的,那就是一条白鱼被捕获,并且出现了一条闪电,随即又变成一只发亮的红色乌鸦。[12]秦始皇把他的朝代的命运和“水”相联系,因为“水”征服了红色(周朝)的“火”。他还下令官方旗帜和庆典礼服采用黑色(“水”的相关色彩)。[13]
颜色的含义也不局限于时间上的交替。颜色还融合着空间的区分,与四季的内在动力相联系。司马迁描述了一种仪式。在那里皇帝建造起一个五色土的土堆,作为对土地众神的祭坛。这个土堆东边是绿土,南边是红土,西边是白土,北边是黑土,顶上由黄土覆盖。当一个诸侯被授予了东方的封地,他得到一些绿色的土壤;封地在南边的诸侯,得到红土;封地在西边的诸侯,得到白土;封地在北边的诸侯,得到黑土;然后每个人把这些土壤带到他的封地去,环绕这些土壤建造一个祭坛,在上面盖上他同时得到的黄土。[14]
于是想像颜色就是想像权力。在汉文化中,从宫廷旗帜到仪式器具,从服装到建筑设计中,充满了色彩意识。所有这些,使得汉代医学中对颜色的细察显得极其自然。五种颜色的宇宙回响看起来为观“色”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接下来,我将提出事情不那么简单。聚焦于“色”也伴随某些关注超越那些由五行对应的框架。尽管传统这样认为,但是颜色与宇宙节律的联系,只解释了中国注视的一个方面。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模糊不清。
一些未解之谜
一个不解之处是注视的奥秘。五行分析中没有什么表明眼睛比耳朵或鼻子更具备辨识能力;也没有什么表明五色比五声或五味更接近于体察宇宙变化。五行对应的理论并未将视觉知识特殊化。然而,它却是特殊的。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认为视觉优先的等级只是一个理念,并没有反映真实的实践情况。这有很多证据:《内经》和《难经》中最细致的诊断教案,详述了脉搏的症状,而非视觉的检验。汉代著名医师——淳于意、郭玉和华佗——的传记中,都突出了脉搏学的本领,不同于周朝传说中对于扁鹊透视力的强调。比如,郭玉最著名的医道就是,他在根本不被允许观察他的病人的条件下,仅仅通过触摸伸出帐外的两只手腕,就进行了诊断。[15]这后来成为医学专家的标准形象。医学诊断的概念与脉搏检查密切地结合起来。
然而,透视力的奥秘不能如此轻易地错过。即使注视的优先性只是一个理念,对这个理念仍然需要给予解释。而且,实际情形会更多取决历史的变动,而非实际与理念的截然二分。在古代中国医学的发展中,脉搏检查出现得相对较晚;或许在战国晚期和汉代早期才作为一种主要技艺出现。[16]这意味着扁鹊与郭玉传记中的对比,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周代与汉代医学之间的不同。
即使在搭脉搏变成诊断的首要方法之后,望色仍然是其必要的补充。特殊的双重逻辑使得它们不可分割。对脉搏的可信判断需要参照视觉的证据,反过来也如此。如果颜色与脉搏的迹象彼此相配,例如两者都指向“木”的失调,那么病人还可存活;如果一个显示“木”,另一个显示“金”,那么病人就会亡故。[17]耳朵、鼻子和舌头的颜色能增添一些辅助性的信息,但是判断的关键还是手和眼睛的辩证法。了解“色”对于了解身体仍然非常重要。为什么?五色与五行之间的对应并没有给出答案。
第二个不解之处是对于“色”的关注颇为笼统。可以看到,这种关注不仅局限在医生中。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8]即重复了古代中国标准的感官区分:色之于目,就像味之于口,声之于耳。[19]颜色不是视力的某个对象,就像味道作为鉴别力的某个对象——它就是观视之物(the object of sight),其感知经验规定了眼睛的固有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师细察颜色是不奇怪的。就像希腊解剖结构的研究,植根于有关形式的更为广阔的哲学话语之上,因此对“色”的关注所带来的实践远远超过了医学。那是怎样的实践呢?是什么让人的眼睛不仅仅作诊断性的观视而与“色”密切关联?
孟子的论说除了拓宽了这一难题的范围,也再次暗示仅仅根据五种颜色来解释“色”的论述是不完善的。是《吕氏春秋》最先系统地应用五行分析,发展了一套宇宙对应理论,孟子(公元前371~289年?)的出生比《吕氏春秋》的编写早一个多世纪。尽管《孟子》中有二十多处涉及了“色”,但“五色”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孟子对于颜色的评论,还是早期对五种颜色的提及,都没有暗示因为有五种颜色,或者因为颜色联系着宇宙变动,所以眼睛需要固着于颜色。几乎可以肯定,视觉与“色”的结合不能仅仅用五行分析来解释。
色的含义
也许对于颜色的实践,实际上并不奇特。亚里士多德在他关于心理学的论述中断言,观视之物是“可见物”(to horaton),然后解释道,“可见物是颜色。”[20]如果就像中国人所理解的,把白和黑当作颜色,我们也必须承认颜色对于视觉是最基本的。没有光亮和黑暗的区别,我们甚至不能辨别出阴影。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而且,通常颜色反射出神秘的联系物。《礼记》上记载,商代的人们在葬礼上“尚白”。[21]商代最重要的仪式——“寮”祭上,需要燃烧一只白色的狗。在其他语境,铭文中时常提及的白牛、白马、白猪和白鹿,似乎都证明了商代文化中白色的象征性共鸣。[22]这比用五行理论将颜色的解释系统化和合理化,要早很多。换言之,中国人赋予颜色以深刻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其他的文化是一样的。
然而这些考虑也仅仅如此而已。因为一方面,它们从来没有被明确地确认。当孟子和其他人把眼睛和“色”联系到一起,他们既没有指出强调颜色象征性的重要性,也没有强调阴影在感知形式中的优先性。但还有一个更决定性的限制:这些以及其他注重于色的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看与“望色”之间的等同。因为“望色”并不只是看颜色之谓。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色”是一个普通的术语,但是在大部分例子中,并不是指颜色,至少不是那么简单和直接。色意味着其它东西。
相关的复合词“颜色”提供了有益的暗示。在现代中文里,“颜色”是表示色彩的标准词汇。要知道朋友新的丰田汽车的颜色,我们直接询问其“颜色”。这个词很古老,孔子就用过这个词,其词义跟现代不同。“子曰:侍于君子有三: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23]对于孔子(公元前 551 ~479年),“颜色”不是指物体的色彩,而是指脸上的表情。这是典型的古代用法:在早期中国文献中,“颜色”一词没有一处是表示色的抽象概念的。“颜色”的本义专指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现在“颜”这个字指脸,更确切地说,指前额。从这里可以推断,“色”本身意思是面容或外表之类。后来,在后古典佛教(post-classical Buddhist)的用法中,“色”指表象的领域,与本体虚空的“空”相对。如果这就是它在古代的意思,那么把观看等同于“望色”是正常的,因为色包括了所有感官知觉。但是,在前佛教(pre-Buddhist)文献中,这个词并没有形而上学的意思。它通常并不泛指表象,而特指脸上的表情。当孔子经过雉门外所设的君王之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24]《论语》这一段中,首先用“色”指脸色,然后又用“颜色”指脸色。这两个词显然是同义的。在周代晚期和战国时候,色最普遍的意思是外表、容貌,而不是颜色。
孟子观察到暴君统治下的人们脸上有“饥色”,而在仁慈的君主治理下,人们脸上都有“喜色”。庄子发现那些必须要觉悟“道”的人面露“忧色”。[25]当五色/五行分析兴起后,“色”与颜色的联系变得很普通了。即便如此,中国最早的字典——汉代的《说文解字》把“色”定义为“颜气也”。很久以后,清代注释者段玉裁仍然解释道:“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是之谓色。”现代的《辞海》也坚持以“颜气”为“色”的第一个义项,引用段注作为支持。颜色列为第二个义项。
这为中国人为什么把“望”加诸“色”提供了一个理由(我接下来还会谈到另一个理由)。现代对于传统诊断检查的概括,往往传递给人一种简单工作的印象:医生观看病人脸上的颜色,然后判断五行中的哪一个占优势。然而检查“色”时用的标准动词“望”,表露出一个微妙的质疑。最早代表“望”的金文,是眼睛连带一个向前倾的人形的图案。“望”字成形后的字体,显示了一个人尽力对遥远的月亮投去一瞥。两个字体都反映了“望”这个字的字源:“望”(凝视)与“亡”(消失的)和“茫”(晦暗的)同源。[26]换言之,望(凝视)表达了一种尽力观看在远处的或者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感觉的事物。望色以某种方式包含了紧张地运用眼睛,接近那消失或者晦暗的东西。
把色解释为表情,为这种用力感提供了一个来源。当我们注视面容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上扬的眉毛,眼睛中闪出的光,颤抖的嘴唇,颜色的缺失或充盈——所有这些无疑都是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但我们通常并不单独地、自觉地注意它们,不会像逐字逐句地读书那样。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或者认为我们看到的,因为常常难以肯定——是犹豫或急躁,失望或渴望,狡猾或坦率。我们注视的是态度与倾向,它们明显是可见的,尽管又很难看清楚。这就是望色最开始所承担的。我认为面部颜色的医学研究,是从对面部表情入迷的悠久传统中引发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凝望之谜只是部分地与色彩有关。它也和观望脸庞联系在一起
作为表达的色
研究面部表情最明显的原因是它们在表达。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多了解我们周围的人。正如孔子所说的,“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观察对方的脸色,上来就说话,这就叫睁眼瞎)。
当然,阅读脸需要技巧。表情是最生动也是半透明的,而人们又会掩饰。《书经》告诫说选拔官员不能根据“巧言令色”。[27]至于孔子,他对一个人表面的仁慈、友善、勇敢与实际的性情之间可能存在分裂,表示出一种一贯的警惕。[28]但这样的警告也并没有怎么否认脸作为需要敏锐洞察的信号的事实。
技术好的观察者可以看穿伪装。他们甚至能洞悉沉默的想法和隐藏的计划。王充记述了齐桓公有一次与他的大臣管仲密谋去攻打莒国,奇怪的是,在他们宣布他们的计划之前,即将征伐的消息就在国内传开了。管仲说:“国必有圣人也。”计划未曾泄露,却暴露于世,除此还会有什么解释呢?他怀疑一个叫东郭牙的人。于是把他召来,问道:
“你就是传出我们要攻打莒国消息的人吗?”
“是的。”
“我没有说过要攻打莒国,你是怎么知道的?”
东郭牙解释说,不过是因为善于领悟潜在意图。他只是从管仲的脸上(色)读出来的。他过去已会观察管仲喜悦、沉思和为战争而烦躁时的表情。通过观察管仲的表情,结合当前的政治情势,他就能预言即将来临的事。[29]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敏感的淳于髡由于看穿梁惠王的心猿意马,使梁惠王倍感惊讶。王充评论道:“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为什么?因为他“观色以窥心”。[30]
从这些因为洞穿秘密而引发的惊愕,我们可发现视觉神秘性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王充理性化的解释中,观察的敏锐性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众所周知,王充是一个异常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的解释明确地试图反驳广为传播的超自然的预言。当时流行的传统将东郭牙和淳于髡不只是当作敏锐的观察者,而是当作圣人——像扁鹊那样的预言家,——他们能看到什么隐藏在身体、思想和时间中。王充是反对这个传统的。
这是把“望”加诸“色”的另一个、也许是直接的理由:看和预言的联系。医生看病人的脸色(“望色”),预测病情的过程,很像另一批占卜者观察空气(“望气”)来预言军队和国家的命运。望气是一种预言的技术,在秦代和西汉的时候特别流行。就在同时,医学正开始形成其古典形式。[31]它的前提是气候、政治命运,还有最重要的战争进程的转变,都首先出现在微妙的大气变化中。[32]望气家宣称,当飘浮在一支军队上空的云朵呈现某种野兽状,那么这支军队会获胜。小束洁白的云,是一个凶狠的将领率领胆怯的士兵的信号。前面降到很低的青白色的云,是战胜的预兆。前面显出红色、又在上升的云,预告着战争不会获胜。在一些地区的大气是白色的,另一些地区是红色的,还有一些地区的大气下面是黑色,上面是蓝色的。“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33]望气随即就成了细察远处云朵和大气的特质,窥测将要到来的未知之事。
医学的检查“色”,与这种气的预测有很多共同之处。不管望色还是望气,预测者努力察觉变化最初和最无形的表现。《灵枢》说,“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当一种特别凶狠的病菌袭击身体时,病人会颤抖、摆动身体。疾病表现为剧烈的颤抖,没有人会忽视。但如果病菌不是那种剧毒的,开始的症状是不明显的。“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34]观看而知,意味着在事物成形之前就了解,把握那种“在而不在”。这是医学洞察力的顶峰。当病情变得更严重,它对应的颜色也加强了;如果颜色减退(如“云撤散”),说明病很快就会过去。通过观察颜色的隐显浮沉,我们可以知道病情的深浅程度;通过观察颜色是散开还是集中,可以知道危险是否临近。所谓“积神于心,以知往今”。[35]病在体内成形之前,它会通过脸色或变化的“气”发出预告。
西方对于中国医学和哲学的评论一般会强调中国人身体/自我的整体性统一,认为其违背了极为深刻地形塑了西方对人类状况理解的二元论。整体统一的观念与二元论——神圣的灵魂与污浊的肉体,无形的精神与有形的身体——是彻底相反的。它没有这样的极端对立,这是最引人注意的关键差别。但是中国思想中排斥两分法的认定,也经常会导致忽视中国人确实做出的区分。形—脸(form-face)区分就是其中之一。
准确地说,这个区分存在于“形”和“色”。孟子认为,“形色,天性也”,是我们天生的。[36]还有另一些词与“形色”一词相呼应:“形神”、“形生”、“形气”。我们可知其大意:人是由外形和更多一些东西构成。在某种意义上,这好像离身体和精神的区分并不太远。但事实上是有差别的。因为使更多一些东西区别于仅仅外形的,即“色”区别于“形”,不是一种本体上的分裂,而是表达上明晰程度的差别。正如《灵枢》所指出,有现象的方面,如总体形态,四肢和躯干发抖等,这些是一清二楚的。但也有一些方面,虽然可以看到,但很短暂和模糊,“若有若无,若亡若存”。“色”对应的正是后者。
明晰程度的区别同时对应着一个区分,即人身上变化很慢的、或只在强力的作用下才变化的那些方面(如“形”),与以敏锐的感受力而做出发应的方面之间的区分。医生重视“色”,因为它能反映最细微的变化。体形和相貌是长年累月逐渐形成的;到疾病改变了体形和相貌的时候,疾病已经运转了很久了。然而,早在疾病使人消瘦、憔悴之前,它已经在容貌上显出转瞬即逝、难以言喻的变化。真正“望色”、凭观看而获知的医生,能够看出对于其他人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的真相。
还有一个更一般、更道德化的层面。根据孔子的说法,那些可以谓之“达”、把握了大道的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重点为笔者所加),虑以下人。”[37]“色”这个字就是指他们脸上的表情。通过把它和公正、正直、谦虚这些主要德行并列在一起,孔子赋予“观色”以很高的地位,我们自己通常不会这样对待。然而,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孔子这样想。原因肯定在于他所设想的道德发展,是把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为了适当地回应别人,我们必须理解他们;为了理解他们,我们必须仔细注意他们的言词和脸色。
那么,我们必须在他人那里理解的是什么呢?言词和脸色表达出了什么?我们先考虑言词。一个理解它们的常见方式,是把它们作为意图和想法的象征性替代物来考虑。从这个角度,理解一句话,就是把握这句话代表的想法。要求给出定义,以及“你用那个术语是什么意思”之类的问题,一直是以这个观念为基础的。但是激发儒家坚持文字上的敏感性的,不是语言的标准模型。孟子相信“知言”是使他高出常人一筹的两个特殊本领之一。他说:“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38]“知言”与清楚的定义或者掌握特别的术语,并没有多少关系。“知言”更多是意味着听出语言背后隐藏的内心看法和状态。敏感的听就是从有意的讲话中听出无意的暗示。
这同样适用于脸色。对于敏锐的眼睛,“色”表达了甚至一个人想掩饰的那些倾向,甚至那些和他自己的意识不相符的愿望。当人“变色”或“作色”时,他们经常是突然本能地这样做:“勃然变色”、“勃然作色”、“忿然作色”、“怫然作色”[39]——没有预谋,突然被惊讶或愤怒所抓住。这些成语提醒我们从表情到颜色的转变是容易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突然改变了颜色”、“突然变色”,或者更宽泛地,“因震惊而畏缩”、“因愤怒而脸红”、“因羞愧而脸红”。在“色”上,人们可以说显示出了他们真实的颜色。当孔子从朝会中走出来,他“逞颜色”。——翻译出来就是,“放松了表情”,让他的情绪显露出来。——通过望色,我们看到了自我。
《庄子》中记载了,在一个神秘的“为圃者”的尖锐批评下,子贡感到吃惊和惭愧,他“失色”了:
子贡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为者邪?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终日不自反邪?”[40]
“失色”等于是立刻失去了颜色,而且失去了自己。
在前面,我对比了“形”变化的长期性与“色”无形的可变性。当然,脸上的表情不是随便地变化的,也不是只反映了瞬间的激怒。它们也表现了长年无意识的习惯和有素的训练。中国的思想者很清楚这一点。在他们的心中,“色”宣扬的不仅是作为看到的东西,作为物;而且是作为主观修养的东西。当孔子谴责浮华的举止时,他自己把精通表达作为自我修养的核心。“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41]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中,有两件都要求控制脸色,第三件是涉及到言。再次注意“色”和语言的关联,还要注意在说话中最要紧的,与其说是想明确表达的想法,不如说是“辞气”。脸上的表现就像说话语气中的表现一样。“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42]
承担繁重的家务,供养年迈的父母,这些事情是孝顺的子女必须做的,但一个人仅仅做到这些,还不足以称为孝顺。孝顺义务的履行必须伴随着脸上适当的表情。这是最难的。就像在礼仪表现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43]任何人都能讲话、走路、鼓掌、鞠躬。要做到这些是容易的:只要他决定要做并且去做就行。但是,语调、态度、脸上的表情、仪式中准确的精神,这些属于不同的东西。正像走路、鞠躬,它们受制于意愿,而人对它们的控制更为有限、间接,也更不稳定。它们需要长时间耐心的培养和不断的实践。
因此,“色”透露了生活过的岁月,有时候是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比如,《庄子》中说过,一个七十岁老者显现出的“色”好像一个年幼的孩子一样。[44]华佗的传记中作者也惊叹,在华佗老年时,返老还童的本领使他显出年轻人的“色”。[45]在这两个例子中,“色”可译为肤色或脸,很可能包含两者。为判断年龄,我们部分地依靠观察脸的表情,看看某人看上去是饱经沧桑还是未经历练,是厌倦生活或稚气未脱。我们也斟酌皮肤的颜色、韧性和光泽。作为年龄或健康的显示,“色”于是与“色理”(“理”指皮肤的毛孔)、“色泽”(“泽”指皮肤的光泽)是同义的。“色理”和“色泽”指皮肤的纹路和颜色,它们是生命在身体表面的显现。那位老者和华佗都是年纪很大、但看上去很年轻的人。这是人的面貌的另一个方面,不管他们看起来是年轻还是衰老。
我们在希腊“chrōs”的概念中,发现了与中国“色”的观念的有趣相似。chrōs也指向微带表情的脸。在克里特的(the Cretan)将领眼中,胆怯者和勇敢者的区分是很清楚的:“胆小者的颜色始终在变”(trepetai chrōs alludis allē),而“勇敢者的颜色从不改变”。[46]但 chrōs 还指维持着生命的身体。比如,由花蜜和鲜果保护着的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es)的身体;[47]或者阿基里斯(Achilles)的身体,——如阿革诺(Agenor)所想,——一定是像所有凡人的身体一样易受铜矛攻击的。[48]赫克托尔(Hector)的身体/肉体(chrōs),虽然是可被亵渎的,但仍然奇怪地受到保护了。[49]后来,希腊医学中的体液分析的兴起,无疑部分地应归功于这种将之当作有生命力的肉体的身体想像。
明显是黄色或黑色的胆汁、粘液和血液的人,很容易在脸色上显现为黄色、黑色,或白色、红色。所以希腊医生在诊断中也考虑颜色。伽林甚至把视觉等同于理解色彩的变化。[50]但是,两个不同之处值得注意:(1)中国医学中的“色”包含了强烈的兴趣,其意义范围是希腊医学中的颜色所不能匹配的。(2)中国的“色”不是体液的颜色。《灵枢》解释道,不良的血液循环会导致脸和头发失去光泽。[51]这是中国医学经典中最接近于体液分析的了。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作为有色流体的混合物,中国医师们是怎么想像脸上呈现出的颜色的?为什么脸上会有颜色?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必须更仔细地着眼于和“色”的观察形成对比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分析解剖学的观看。
解剖学的视角
如果解剖就是指切开身体并且加以观察,那么说古代中国对解剖没有兴趣是不准确的。《灵枢》明确谈到了“解剖而视之”的可能性。[52]《汉书·王莽传》记载,公元16年真实地发生了一次解剖的事。[53]然而,这两段都很简短,都没有留下详细的观察记录。而且,整个汉代仅见这两条明确言及解剖的材料。[54]它们是单独的例外。
而且,这两段同样具备一个奇怪的特征。它们都表现出对测量的关切。《王莽传》记载,解剖王孙庆身体时,五脏的测量结果被记录了下来。《灵枢》则更明白地写道:“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此天之高、地之广也,非人力之所能度量而至也。”但是人体可以直接接近,并且大小合适。可以测量人的身体表面,还可以在人死后进行解剖。通过解剖,可以测定内脏器官的坚固性,腹腔的大小,消化系统食物的多少,脉管的长短,血液是清浊以及血液量,哪一些脉管血比气多,哪一些脉管气比血多。所有这些都有它们的标准——“大数”。
事实上,《内经》和《难经》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具体数字。《灵枢》中认为,嘴有2.5寸宽;从牙齿到喉咙的后部是3.5寸;口腔的容积是5合;舌头重10两,长5寸,宽2.5寸。胃重2斤2两,长2尺6寸,周长1尺5寸;容积是3斗5升。膀胱重9两2铢,宽9寸,容积是9两9合。清单上列出了每个器官的情况。[55]当然,大量精确的间距,描绘出了身体表面许多针灸的点。
我想指出的是,打开身体并且观看,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当中国人很偶然地解剖时,他们更多注意的是特征,而不是其它那些吸引希腊解剖学家的东西。这是另一个解剖模式,这个例子提示我们不能满足于希腊解剖学的解释,即只把解剖看作是某种笼统的“经验的精神”的表达。希腊解剖学代表了观视身体的一种方法。它反映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观察的意愿。
对这种方式的完整说明显然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了。这里我只能简单而武断地提出两个主题,它们特别关系到与中国观视的对比。
第一个主题是有意的设计。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部分》(Parts of Animals)中承认,“当观看血液、肌肉、骨头、血管以及构成人体的类似部分时,不可能没有相当的反感。”但他强调,这些并不就能说明解剖学是什么。解剖的目的,不是要看那些引人厌恶的、直观的器官本身,而是专注于(theorein)大自然有意的设计。只要一个人训练自己的眼睛在观看时能透过构成动物的物质,并且理解整个构造(he hole morphe)——这种形式(the Form)反映了自然的目的;那么,解剖学这个令人厌恶的事业甚至能被描述为美丽的。[56]
一种意图明确的心理,使得解剖学的观视成为可能,并界定其目标。在柏拉图的目的论中,宇宙的创造者是一种工匠。正如苏格拉底提醒我们的,工匠“不是随便地选择和使用材料来工作的,而是抱持这样的观点,即所有他们的产品都要有一定的形式(eidos)”。[57]制造一个桌子或者躺椅,工匠会“眼睛盯着理念或形式”。[58]创造就是一种复制的行动,是一种将视觉图像变为物质形式的翻译。这也适用于造物主(Demiurge)。当他创造世界时,他脑中必须要有“不可改变的模型”。[59]
伽林这样的解剖家试图去领会的,正是这原初的意图。他规劝道:“让你的脑海摆脱物质上的区别,只看纯粹的艺术本身。”[60]普通人从不能超越构成东西的物质去观视,但是,科学家(technites)却惊讶于大自然——这个伟大的工匠——是如何“从不做无用功”的。观看并了解身体,就是观看并了解它背后的激发的意图。从解剖学来看,身体表达了预见。
我想提醒注意的第二个主题是意志,文章开始时那幅维萨里的图,为肌肉在解剖学的身体观念中的优势位置,提供了完美例证。伽林在他的《解剖的程序》(Anatomical Procedures)中,把前九卷中不少于四卷贡献给了他们的解剖学。然而有趣的是,“肌肉”这个词直到荷马史诗中才出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里频繁地提到身体的肉和腱(flesh and sinews),但也没有提及肌肉。肌肉确实在希波克拉底时期的论述(the Hippocratic treatises)里出现过,但非常少。即使在人们看来算是对肌肉系统最为关注的、那些希波克拉底时期的著作中,比如《外科》(Surgery)和《骨折》(Fractures)等论著,更倾向用的词不是“肌肉”(mascles),而是“肉”(flesh,sarx)。《骨折》(Fractures)的希腊作者写道“骨、腱、肉”,而不是“骨、腱、肌肉”。[61]这个模式,跟在中国发现的情况相似。只有希波克拉底之后,肌肉才成为希腊身体观的主要特征。
现在人们会认为,后希波克拉底(post-Hippocratic)时期对于肌肉的入迷,来源于古希腊式解剖学的兴起。人们认为,希腊的医生们更明确地提“肌肉”而不是泛泛地说“肉”。因为他们探测皮肤表面之下的东西,而且区分出一块块单独的肌肉。这与他们的希波克拉底时期的前辈,形成了对比。
然而,他们接近肌肉,只是以之为视觉理解的对象,而对于解剖经验的单独诉求,忽视了有关肌肉的新话语的主要特征。肉起初是指对人的肉体的视觉和触觉的感受,但是古代晚期的希腊医生们,已经借助肌肉来分析人的运动。肌肉不只是感觉更为精微的肉,它们是具有专门和独特功能的器官。
这让我们最直接地想起胃、子宫、膀胱,还有最重要的心脏。对于现代解剖学家来说,这些都是肌肉组织。但对伽林来说,它们却不是。伽林举出了这些器官与真正的肌肉之间的多种区别——纤维的排列、颜色、味道。但是决定性的区别是:后者遵守意志的命令,而前者不是。尽管心脏的肉压缩得很紧,看上去像肌肉,但它不是一块真的肌肉,因为它出于它自己的意愿而运转。[62]我们不能像命令我们胳膊和腿的肌肉那样控制它,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意愿让它开始或停止。
伽林在《论肌肉的运动》中的讨论,集中在探索行动和意图之谜,以及详述肌肉的功能上。[63]它证实在晚期希腊医学中,对肌肉的兴趣与对力量的分析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伽林注意到,一些身体活动的进行,发生在我们并未留意之时;并且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直接影响它们。消化和脉搏跳动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也有一类重要的活动,如走路和说话,直接依赖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能选择走得快一点,或者放慢一点,或者站着不动。我们能变换说话的调子。我们能做到这些,因为我们除了胃、肠、动脉之外,有叫作肌肉的特殊器官。[64]伽林把肌肉定义为“按照意愿运动的器官”。[65]它们的活动表达了心中的冲动。它们允许我们选择行动的幅度和特征。以自愿的行动区别于非自愿的活动的选择,确证了我们是真的能动者。
把身体结构当作有意的设计来研究,和把肌肉当作意志的器官来关注,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希腊解剖学的想像,都是由希腊人心理的假设和关切所塑造的。众所周知,我们如何看东西受到我们把东西想像成什么的影响。但在身体这个问题上,那被想像之物正是我们自己。这就将引出我的主要论点了:希腊和中国医生在观看身体——将之作为一个外在的东西——方式上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们从内部设想和体验作为人的他们自己的方式上的区别。
一些人也许会反对说,在希腊人看来,无论意志还是意图(尽管对后者的争论还不明显),都不是独属于人类的,动物也有。但我们知道,正是人与动物的这种相近,对希腊解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实际的意义。较之中国式对于人的理解,它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花之精神
我已如此宽泛地讨论了“色”的表现性:反映感觉和倾向的脸部,指示人的五行状况的颜色。总结一下,我想更确切地强调的是:色到底是如何与它表达的内容相联系的?
人和人的脸色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同于开始走路的决定和相关肌肉的收缩之间的关系。露出表情不只包括一个决定。一个人能试图看上去孝顺,但是努力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同样不能保证实现的,还有色和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关系,正如柏拉图笔下匠人的制造物与这些制造物是物质的实现的期待之间的关系。色不是一个预先计划的设计。
当然,意志和意图有它们的角色:人们通常会努力表现出某种表情,这种努力会影响到他们怎么做,准确地说是他们表情如何。比如,在《论语》中不断看到对孔子表情的记载。但是,相对于仅仅是权威、敬畏或者仁慈的外表,居高临下的、敬畏的或者仁慈的真实表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装出来,也不是任何人想装就能够装的。需要更多的东西。而且,我们已经提到,不管一个人愿不愿意,正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刻,色表达得最深刻。当“色”表现年龄和健康时,意志和有意的设计的功能,更加表现出其有限性:一个人的颜色、皮肤的光泽和弹性、年轻而有活力的表情——或者它的缺失,如果说从根本上说表达了意志,那也是间接的,因为它们是经年累月的、无数的决定和非决定的总和。
那么,应当如何想像“色”的表现性呢?更直接的说,古代中国人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认为他们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考虑“色”的。《素问》记载:“色者,气之华也。”[66]“夫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67]“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68]色之于人,就像花表现了植物一样。
这些论述很容易被忽视。中国医学中植物性的类比是如此的普遍。比如,关于各种器官和其所控制的身体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脾脏不再更新,肉会变软,而且舌头会“萎”;如果肾脏不再更新,骨头会变“枯”。[69]同样,一方面是气,另一方面是色和脉搏,它们之间的相互呼应也类似于“本末根叶”。[70]《难经》上说,“生气”相当于身体的茎和根,当根被切断了,枝叶就枯萎了。[71]这样的例子可以很容易举出来许多。中国古典医学的文献使用了很多隐喻来解释身体,最普遍深入的,还要属植物的生长这个隐喻。
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华色”的形象只当作这个普通隐喻的又一个例证。相反,我们需要把这个形象当作体会植物类比的更深入含义的一条线索。它表明对身体的植物性想像,既是字面上的,也是在象征性的想像。中国医师不只是把“色”当作花,他们视之为更多东西。
我这样说有两层意思。最直接的,我是指医生观察脸的方式和园丁检查植物状态的方式差不多。植物健康状态不佳的明显信号包括柔弱、起皱、干枯等。中国医师会用同样的词描述病人的身体。也许正是花和叶子的颜色和光泽,呈现出最精微和隐秘的生命力的指标。
我的邻居正好是一个殷勤的园丁,而我自己却往往不管我的院子。每个春天,明显的区别令人难堪。我邻居的杜鹃花开放得格外绚烂,这说明它们在精心照料的、肥沃的土壤中,受到了辛勤的培育。而我自己的杜鹃花(前一个房东种的)则相反,呈现出苍白的颜色,因为它们长时间地在乔治亚州的泥土中艰难生长。我邻居的植物的叶子,确实放出富有生命力的光泽。而我自己的看上去明显是黯淡和褪色的。中国医学中对脸色的注视,也会考虑到光泽。比五种颜色之间的区别更为根本的,是同样颜色,有没有光泽之间的区别。比如,猪肉的亮白、鸡冠的火红,乌鸦羽毛的乌黑;与干枯骨头的惨白,凝固的血的暗红,烟灰的淡黑之间的区别。前者预示着复原,而后者是死亡的信号。[72]
希腊医生也承认动物(包括人)和植物之间的相似性。虽然能否自主运动把动物界与植物界区别开了,但动物和植物都自己吸收养料而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发育和营养被认为是所谓“生魂”(vegetative soul)的功能。然而在中国,植物性的类比不是仅仅用于人的系统里被挑选出的、低级的方面。它描述了人的本质本身。
为了捍卫后来成为儒家正统的基石的性善论,孟子利用植物来解释人性中固有的善良。他说,所有人天生都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由四种品质构成——仁、义、礼、智。它们就像四株嫩芽,其发展需要精心的培养。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关注它们,但又不能强迫它们发展。他举出了一个宋国人的愚蠢行动: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73]
自我修养和培育植物所需要的努力,不同于搬动石头所要的那种努力。这不是只要决定后,直接推或拉,——我们称之肌肉力量,——就能做好的事。这就到了我要说的第二层、更深入的意思:细察“色”与注视植物的花是十分相似的。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提出了希腊解剖学研究与关于人类表情的两个有影响的模式之间的关联。其中一个模式强调意图的表达;另一个模式强调意志的显现。这两个模式在中国的自我定义中都没有位置。在中国决定性的模式是关于植物的生长和健康的模式。人像植物,不仅在生理的功能(如发育和营养)上,而且在他们的道德发展和个人表现上。在这方面,他们成长,并显示他们自己是人。
据此,中国人观视的重点在“色”上。孟子发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74]同样,《国语》中也有一处,把“貌”(脸色)等同于“情之华”。[75]如果色是“气之华(花)”,反过来用一个普通的注解,“花者,色也。”[76]
从富有表现力的花的形象中,我们能朝向各种方向。比如,我们可以追踪中国人偏爱植物式的类比的社会经济起源。或者,我们可以思考这种类比的结果:它是促使中国医师对结构和功能问题相对冷淡。但这些是未来研究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想说明的,是中国医学中视觉知识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想像和成为人”这个问题的密切关系。[77]
(译自堂·贝茨(Don Bates)编:《知识和学术性的医学传统》(Knowledge and ScholarlyMedicalTradi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译文由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教授校。)
注释
[1]《史记》,册6,第105篇“扁鹊仓公列传”,第2785页,香港:中华书局,1969年。关于扁鹊的可获得的材料,一个完整和准确的分析,参见 Yamada Keiji,‘Henjaku densetsu’,Tōhō gakuhō,60(1988),73 -158.
[2]《史记》,第2793页。此事亦见《韩非子》,第21篇“喻老”,卷7,页2b-3a,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
[3]“闻”事实上包括听声音的音色和闻身上的味道.
[4]《灵枢》,第4篇“邪气藏府病形”,收入《黄帝内经章句索引》,第275页,台北:启业书局,1987年.
[5]《伤寒论》,卷1,页19a,台北:中华书局,1987 年.
[6]Bruno Snell对荷马的(Homeric)概念“心智”(noos)的反思,提醒我们,noos的动词形式noein意思是“获得关于某个东西的清晰的心灵图像。noos很重要。心智是作为清晰图像的接受者,更简单说,清晰图像的器官……Noos好像是精神性的眼睛,展现一幅晴朗的图景”。参见《希腊哲学与文学中心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T.G.Rosenmeyer译,New York:Dover,1982,p.13。这几句外,还可以补充柏拉图对真实知识对象所用的术语——“观念”(idea)。Idea是动词horaō(意思是“我看”)的分词。柏拉图显然是第一个说“心灵之眼”(to tēs psychēs omma)的人。参见《理想国》,533d;以及Paul Friedlander,《柏拉图之一:导论》(Plato I:An Introduction),Hans Meyerhoff译,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13.
[7]参见Stephen A.Tyler,《西方的视觉追求,或心灵的眼睛看到了什么》(The Vision Quest in the West,or What the Mind’s Eye Sees),《人类学研究月刊》(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40(1984),23 -40.
[8]关于视觉和科学的关系,Svetlana Alpers《描述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提供了很多启发。我还要指出另一篇以视觉风格为主题的研究,《眼心之间:十八世纪日本解剖学》(Between Eye and Mind:Japanese Anat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入Charles Leslie和Allan Young合编的《亚洲医学知识之路径》(Paths of Asian Medical Knowled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21-43。我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和我在这篇论文中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9]《素问》,第39篇“举痛论篇”,收入《黄帝内经章句索引》,第113页,台北,启业书局,1987年。也参见《灵枢》,第49篇,第401页。有时,黑色与绿色被认为有不同含义,见《素问》,第56篇,第151页;《灵枢》,第74篇,第455页.
[10]《素问》,第32篇“异法方宜论篇”,第94页.
[11]五种颜色和五行是这样对应的:颜色 绿 红 黄 白 黑行 木火土 金水
[12]《史记》,册1,第4篇“周本纪”,第120页.
[13]《史记》,册1,第6篇“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
[14]《史记》,册4,第60篇“三王世家”,第2115页。另参《尚书·虞夏书·禹贡》注释,见《尚书正义》,卷6,页6b,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
[15]对《后汉书》中这段记述的翻译,见 Kenneth J.DeWoskin所译Doctors,Diviners,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Bi-ographies of Fang-shi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75.
[16]参见 Yamada(note 1),p.120.
[17]《黄帝八十一难经》,13.
[18]见《孟子》,7B.24.
[19]如参见《庄子·天地第十二》,卷5,页11a,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
[20]《论灵魂》(De anima),2.7.
[21]《礼记·檀弓》,见《礼记正义》,卷6,第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2]Nakajima Yosuke,Goshiki to gogyō.Kodai chūgoku tenbyō(Tokyo:Bon Books,1986),p.89.
[23]《论语》,16.6.
[24]《论语》,10.3.
[25]《孟子》,1A.4,1B.1,3B.9,即“梁惠王上”、“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篇;《庄子》,“至乐第十八”,卷6,页18b;“山木第二十”,卷7,页9a.
[26]参见 Tōdō Akiyasu 编,Kanwa daijiten(Tokyo:Gakushō kenkyusha,1978),p.619。Tōdō还指出其它字的字源联系,如“慕”(渴望)与“募”(征招).
[27]《尚书·周书·冏命》,见《尚书正义》,卷19,页8b.
[28]《论语》12.20;17.10.
[29]《论衡·知实篇》,卷2,第1089-1091页,见黄晖编《论衡校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30]《论衡·知实篇》,第1091-1092页.
[31]Onozawa Seiji,Fukunaga Mitsuji and Yamanoi Yū(eds.),Ki no shisō(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8),pp.154-6;183-4;230.
[32]望气与军事的隐秘联系,参见 Sakada Yoshinobu,Chūgoku kodai no sempō(Tokyo:Kembun Shuppan,1991)之第4、第5章,pp.128-83.
[33]《史记》,册3,第27篇“天官书第五”,第1336-1337页。司马迁在给项羽作的传中写道,在项羽和刘邦会战之前,他向一个望气家请教,望气家告诉他不要攻击刘邦的军队,因为他们军队上的云朵呈现出染上五色的龙和虎状。这明显是上天庇佑的标志(《史记》,第7篇“项羽本纪”).
[34]《灵枢》,第4篇“邪气藏府病形”,第275页.
[35]《灵枢》,第49篇“五色”,第401页.
[36]《孟子》,7A.38.
[37]《论语》,12.20.
[38]《孟子》,2A.2.
[39]参见《孟子》5B.9,1B.1;《庄子·天地》,卷5,页7a,10a;《论语》,10.3.
[40]《庄子·天地》,卷5,页7b.
[41]《论语》,8.4.
[42]《论语》,2.8.
[43]《论语》,8.2.
[44]《庄子》,“达生第十九”,卷7,页3b;另见“大宗师第六”,卷3,页7a.
[45]《三国志·华佗传》。参见Kenneth J.DeWoskin所译Doctors,Diviners,and Magicians of Ancient China.Biographies of Fang-shih,note15,pp.140,150.
[46]《伊利亚特》(Iliad),13.278-84.
[47]《伊利亚特》,19.38-9.
[48]《伊利亚特》,21.567-8.
[49]《伊利亚特》,24.413-14.
[50]Galen,De symptomatum differentiis,1.1,.K7,p.44.
[51]《灵枢》,第10篇“经脉”,第305页.
[52]《灵枢》,第12篇“经水”,第311页.
[53]《汉书》,册5,69B,第4145 -4146 页,台北:鼎文书局,1981 年.
[54]在如此庞大的中国正史里,《王莽传》是可以找到的、唯一提到解剖的地方。然而,根据医学材料,很清楚在后来时期,没有出现解剖。关于传统中国的解剖的考察,参见Watanabe Kōzō,‘Genzon suru Chūgoku kinsei made no gozō roppu zu no gaisetsu’,in his Honzō no kenkyū (Osaka:Takeda Kagaku Shinkōkai,1987),pp.341 -452.
[55]《灵枢》,第31篇“肠胃”,32篇“平人绝谷”,第359-362页。《难经》,42和43。对古代中国“解剖”更详细的评论,及相关篇章的翻译,参见 Yamada Keiji,‘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Chinese Science,10(1991),39 -52.
[56]《论动物部分》,645a.
[57]《高尔吉亚》(Gorgias),503e.
[58]《理想国》(Repubic)10.596b.
[59]Timaeus,29a.
[60]De usu partium,book3,3.
[61]《骨折》,2.另见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部分》,2.8.
[62]Galen,On the Motion of Muscles,1.3,K4,p.377;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6.8,K1,pp.319 -20;On Anatomical Procedures,7,K4,pp.367-464.
[63]On the Motion of Muscles,K4,pp.367 -464.
[64]Galen,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16.2,K2,p.380.“自然在动物身上创造了一种叫作肌肉的工具,以便它们能按照意愿地运动。”
[65]Galen,On the Motion of Muscles,1.1,K4,p.367.
[66]《素问》,第17篇“脉要精微论篇”,第50页.(华,通“花”——译者注)
[67]《素问》,第81篇“解精微论篇”,第254页.
[68]《素问》,第10篇“五藏生成篇”,第34页.
[69]《灵枢》,第10篇“经脉”,第305页.
[70]《灵枢》,第4篇,第275页.
[71]《难经》,8.这解释了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怎么会发生脉搏突然停止。这和植物的情况一样。当根突然断了,这时仅看花和叶子,植物一开始似乎还很正常.
[72]《素问》,第10篇“五藏生成篇”,第34页;第17篇“脉要精微论篇”,第50页.
[73]《孟子》,2A.2.
[74]《孟子》,7A.21.
[75]《国语·晋语五》,见《国语 战国策》,卷11,第1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76]参见《汉书》,册3,27C“五行志”,第1442 页.
[77]Derek Bodde在最近发表的研究中指出,“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对庄稼和植物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动物的兴趣”。他接着引用何炳棣(Ho Ping-ti)关于中国畜牧业的落后情况的论述:“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时期,农业系统始终偏向于粮食生产,畜牧业只扮演一个辅助角色。……最显著的特征是缺少足够的知识来制造和使用乳制品。……中国人还有另一个罕见的特征,很晚才在耕作中开始利用牵引动物,而且始终不曾充分利用。”See Ho Ping-ti,The Cradle of the East,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 -1000B.C.(Hong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and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5),pp.113 -14.Bodde的讨论,见 Chinese Thought,Society and Science.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 - Moder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p.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