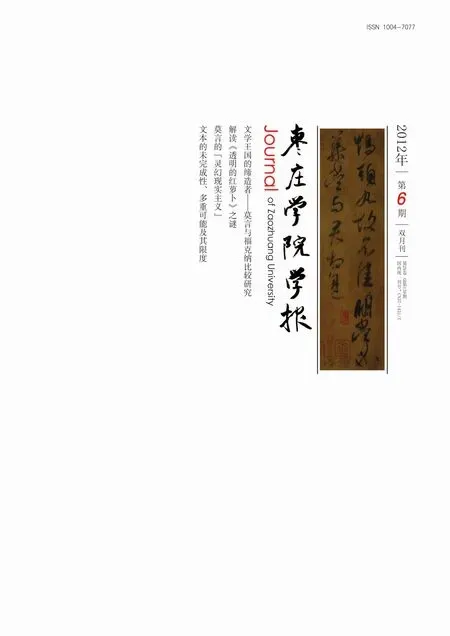文学王国的缔造者
——莫言与福克纳比较研究
胡小林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莫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在一九八五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P298)一九九九年,莫言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坦率地承认自己是福克纳的学生。[2]而二OOO年三月,莫言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演讲的题目是《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莫言讲到了他读福克纳的小说时给他带来的阅读震撼和强大的心理冲击力,他的文学创作天地由此豁然开朗,而福克纳的小说对于他是常读常新。[3]
莫言认为,福克纳对邮票大的故乡小镇,他的杰弗生镇,是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这是一种地区主义,它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则是无限的。福克纳的创作生动地体现了人类灵魂家园的草创和毁灭的历史,显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螺旋状轨道,呈现出大家气象,是具有恢弘的哲学风度的作家。[1](P299)而福克纳经过一段早期的创作实践后,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创作意识:
打从写《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我一辈子也写它不完,我只要化实为虚,就可以放手充分发挥我那点小小的才华。这块地虽然打开的是别人的财源,我自己至少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天地吧。我可以象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遣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4](P274)
福克纳此处所说的“天地”就是他许多部作品的地理背景,他所虚构的一个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人们称福克纳的这一部分作品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饶有趣味的是,福克纳在他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出版时,还亲自绘制了一幅“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生镇”地图,并且说明这个县面积为2400平方英里,人口中白人为6298人,黑人为9313人。最后注明:唯一的业主和所有者是威廉·福克纳。福克纳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近百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福克纳这个小说王国的主要脉络是这个县杰弗生镇及其郊区的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族的几代人的故事,时间从一八OO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600个。这些人物在各个长篇、短篇小说中穿插交替出现,而且这部(篇)小说中的故事与另一部(篇)小说里的故事多少有关,每一部(篇)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约克纳帕塔法县与杰弗生镇是以福克纳的家乡拉法埃特县与奥克斯福镇为原型的,但是,这个“世系”,这个小说王国并不仅仅是当地历史文化、现实的忠实写照,并不仅仅是一般的乡土文学、美国南方文学,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和人类命运的表现。福克纳曾说:“我总感到,我所创造的那个天地在整个宇宙中等于是一块拱顶石,拱顶石虽小,万一抽掉,整个宇宙就要垮下。”[4](P274)
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的末尾写道:
福克纳是我们的——起码是我的——光辉的榜样,他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但也为我们设置了陷阱。你不可能超越福克纳达到的高度,你只能在他的山峰旁另外建造一座山峰。[5](P253)
一九八四年秋天,莫言在《白狗秋千架》这个短篇小说中第一次打起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成了文学的‘高密东北乡’的开天辟地的皇帝,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要谁死谁就死,要谁活谁就活,饱尝了君临天下的乐趣。”[5](P232)莫言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以他化实为虚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这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莫言创建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是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致敬。“如果把莫言小说发表时间的顺序打破重新组合的话,就会发现他也描写了故乡从开创到今天的历史变迁。《马驹横穿沼泽》中,那美妙神奇的传说,描绘了高密东北乡食草家族创世纪的经历。《秋水》中,‘我’的爷爷奶奶因杀人放火逃到高密东北乡大涝洼子的蛮荒之地,男耕女织,休养生息,那漫野的秋水,传奇般的爱情故事,横生的鬼雨神风,为这块涝洼地蒙上种种魔幻的色彩。而后陆续便有匪种寇族迁来,设庄立屯,自成一方世界。这颇似《百年孤独》中马孔多镇的草创史。以后便在这块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惨烈、生死恩仇、男欢女爱的悲剧、喜剧和正剧。从《生蹼的祖先们》、《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红蝗》、《红高粱家族》,经《大风》、《老枪》、《透明的红萝卜》、《复仇记》、《筑路》等,到《欢乐》、《球状闪电》,高密东北乡人民多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都得到了艺术的表现。”[6](P80~90)这只是表面上的效仿或相同,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认识、理解甚至崇拜,更关注的是核心的、深处的东西,如作家的思想、灵魂世界,他的历史时间观、道德观等。莫言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最初注意到的只是艺术上的特色,后来他意识到这些其实是雕虫小技,“应该通过作品去理解福克纳这颗病态的心灵,在这颗落寞而又骚动的灵魂里,始终回响着一个忧愁的无可奈何而又充满希望的主调: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时间像汽车尾灯柔和的灯光,不断消逝着,又不断新生着。”[1](P299)莫言的感受和把握无疑是敏锐和准确的。
福克纳的历史时间观是向过去看,向历史深处看,人是久远无穷的生命的延续,生命无始无终;但是,所有过去存在于其中的东西,现在仍继续存在并产生巨大影响。在现代主义作家中,福克纳向后看的历史心态恐怕是最突出的,在他看来,所谓过去都是活生生的现在,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甚至控制着人们。他的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受到柏格森关于时间流动性观点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美国南方文化传统和自己生活经历的深刻影响。美国南方历史意识的核心就是向后看,而他从小总是在听人们讲述自己家族和这个地区的过去的故事,强烈感受到人们对过去的怀念和过去对人们的影响,从而使这种向后看的历史意识自小就深入到他意识深处。而他长大后看到的现代南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惟利是图和冷酷无情的工商势力对南方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侵蚀和瓦解更加强了他向后看的历史意识。由于这些原因,他的作品中,“往昔”经常是压倒一切的因素,他小说中的许多主要人物,比如艾克、洛沙、沙多里斯家族、康普生家族成员都被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之中,或者简直就是生活在过去。
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九三九年,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萨特就以如炬慧眼指出:“福克纳看到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来比拟。……在这里,过去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性质;它的轮廓是明确、清晰和不变易的。不定而闪避的现在在它面前是毫无办法的;现在全是些窟窿,过去的事物,固定,不动,沉默,都溜过了它。……现在在影子里进行,好比一条地下河流,在它已经变成过去的时候,才重新出现。……过去是不幸地永远也不失去;它永远在那里,几乎象是鬼迷。”[7](P161)
莫言同样有着向后看的历史时间意识。他的历史时间意识与其创作的原始生命力主题是相辅相成的,“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北方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在《红高梁家族》中,那场可歌可泣的抗日伏击战的主角是一群由土匪、轿夫、流浪汉、残疾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草民身上,莫言发现了他们强劲的生命力。这些人是未被文明驯化的野蛮族群,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从正统文化立场上看是大逆不道的,莫言却赋予他们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一种民族的血性和伟力,一种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蛮的生命意志。而莫言小说的生命力主题又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文明批判主题,他将文明置于生命力的对立面,把它看作是一个压抑性的机制,并由此发现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红高梁家族》中,存在着一个族系级差,在“我爷爷”——“我父亲”——“我”的这一“族系链”中,就生命力角度而言,明显地表现为力的递减。“我’’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分子,满身臭气,思维僵化,精神上遭“阉割”,是一个孱弱的不肖子孙。莫言的小说表现了感官和肉体的充分解放状态,一种生命的自由形态,以此在精神上、心理上抵御现代文明对“人”的抑制。
作家笔下的“过去”是一种心灵中的时间感受,我们经历的一切人和事并非自动储存到记忆中并浮现出来,惟有它们本身内在的价值和它们与我们生活的联系程度才能确定它们浮现的程度。无论是汽车柔和的尾灯还是敞篷车后面的风景,都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福克纳向后看到了什么?他的往昔世界表达了什么样的理想寄托?
福克纳相信只有过去时代的人们身上那些古老的美德和荣耀,那些人类的永恒价值和人性的本质,才能帮助现代人克服自身和社会的弊端,阻止道德价值的沦丧,帮助人们在病态的现代社会里保持人的尊严,活出人的样子。这样看来,福克纳是一位浪漫的、成熟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对故乡邮票大的地方的不懈耕耘,缓慢地、艰苦地向异化的世界显示了他与这个生存的世界的密切联系,显示了人性基础的重要性,显示了一位作家的最高天职和荣耀,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作家和人类的代言人。
而莫言的创作也表明他最大限度地超越了阶级、时代、民族、现实,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他曾有言:
看起来我写的好像是高密东北乡这块弹丸之地上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把天南地北发生的凡是对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东北乡来。时至二十一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作家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5](P290)
从福克纳返观过去的历史时间意识中走出来的人物往往被英雄化或恶魔化,他们怀着单一的信念生活着,遵循着古老的道德观念:勇敢、荣誉、骄傲、爱正义、爱自由,他们成为古老的南方的象征,战争与重建的象征。按照《喧哗与骚动》中昆丁父亲的说法,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是人,也像我们一样是受害者,不过,是不同环境下的受害者,更单纯些,因而,作为一个整体,更大些,更英勇些,人物也因此更为英雄气概,不是侏儒似的思虑重重的,而是清晰的、不复杂的,他们有在世界上生一次或死一次的才能,而不是闭着眼睛从摸彩袋里一只胳膊一只大腿摸出来、拼凑成的烟云一样不可捉摸的散了架的家伙,他们是一千次凶杀、性交与离异的作者与对象”。换言之,这些人物单纯、勇猛、剽悍、敢爱敢恨,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南方家族的缔造者、祖先,他们的形象在人们的传说中或子孙后代的记忆里变得愈来愈高大起来。这类形象在福克纳作品中占据突出地位,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正是对这一类人的形象塑造及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的描绘,作者深刻地探索了美国南方的历史和传统,寄寓了自己丰富、复杂的情感。
在《八月之光》中,希陶尔德爷爷在南北战争中抢劫鸡场时被打死,但他却被神化为一个跃马横刀、叱咤沙场的勇士,成了旧南方骑士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象征。《押沙龙,押沙龙!》里的塞德潘是南方早期怀有庄园梦的拓荒者形象,是典型的家族统治者,是个具有超人意志、冷酷无情、令人畏惧的人物,是一个恶棍英雄,为了创建一个纯白人血统的贵族式家族并使之永恒这一梦想,他做出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恶行。在《沙多里斯》中,约翰·沙多里斯是约克纳帕塔法县沙多里斯家族的始祖,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用自己的钱招募了一支队伍同北方军作战,战后他又创建了当地第一所银行和第一条铁路,并成为州议员。他勇猛刚烈,崇尚骑士精神,充满英雄气概,但又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是南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他死后关于他的传说越来越神奇,他成了一个精灵或神祗。他其实是美国旧南方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象征。《去吧,摩西》里的卡罗萨斯·麦卡士林同样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但在后人心目中他却是具有超人力量和意志的祖先。这些祖先形象是美国南方清教主义父权制传统、庄园社会和种族主义同“美国梦”相混合的奇怪产物。
这些家族的祖先们的高大身影笼罩在他们后代身上,左右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思维,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八月之光》中的陶希尔无论在清醒还是在睡梦中,他爷爷威风凛凛、搏杀疆场的场面都充斥着他的心灵,以致他无法正常布道而失去神职。沙多里斯的巨大阴影使他的后辈生活在对他的景仰与对自身的绝望之中,结果小白亚德为了证明自己不具备的勇气而丧失性命。《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那些白手起家的祖宗和当过州长、将军的先辈,他们的荣誉及辉煌的过去同样给他们后代的心灵上留下重负,使他们一个个以不同的方式成了这个家族的辉煌过去的牺牲品、殉葬品。这些子孙们是软弱无能的,他们无法面对现实生活,而逃避到一个充斥着酒精、温驯、疯狂的梦想世界中去,迷恋过往的、消逝的一切,是生活中的懦夫。
福克纳对南方充满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他珍视南方的价值观念,对它的过去充满怀恋之情,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看到南方社会和历史中的各种问题和罪恶,这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相冲突。这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而福克纳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和生活的现代化进程则持怀疑、反对和批判的态度,这一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北方佬形象的塑造上。
莫言作品中同样存在着恋乡与怨乡的双重心理情结。在《红高梁》中,作者这样评价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以此直接表达他“极端仇恨与极端热爱”的感情。
在莫言小说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形象,和福克纳小说中一样,大多是爷爷奶奶一辈人,他们无论男女,形象魁伟俊美,情感奔放,血气方刚,勇武过人,技艺超群。《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余占鳌,杀死致使自己受辱的和他母亲姘居的和尚,又因对“我奶奶”戴凤莲的钟情而杀死她公公和丈夫,进而杀死侮辱她的土匪白脖子,后来成为乡民领袖,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与他同类的形象还有《秋水》中的爷爷、奶奶、紫衣人、黑衣人;《老枪》中的奶奶、“父亲”;《姑妈的宝刀》中的姑妈等。《大风》中的爷爷则是另一类好汉,他精通各种农活,是个好把式,饱经忧患而乐观、达观,是坚韧的英雄。这两种类型的“爷爷们”体现了中华民族民间精神的两个方面,一是勇敢抗争,一是勤劳耐苦,这两个方面构成中华民族的内聚力。
相形之下,父母一辈的大多数形象则显得毫无生气,他们几乎是为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而耗尽了生命的全部光彩,贫困、潦倒、卑屈、懦弱、愚昧、保守、自轻自贱、自私残忍。莫言的一系列作品,诸如《枯河》、《球状闪电》、《爆炸》、《欢乐》、《透明的红萝卜》等等,其中的父母一代人的形象均是这样,他们既集中了民族性格中最落后阴暗的方面,又代表了人性中最丑陋衰朽的内容,是种族退化的象征。而与叙述者同辈的子孙一辈,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枯河》中的小虎、《球状闪电》中的蝈蝈以及《红高粱家族》、《大风》、《红蝗》等一系列小说中的“我”,《老枪》、《欢乐》中的“他”、齐文栋,背负着父辈沉重的人生,带着与生俱来的早熟的忧郁症,宿命地纠缠于上述两种生存状态的内在冲突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和痛苦。其中,《老枪》中的“他”,抵挡不住使爷爷成为当地历史上英雄传奇人物的那把挂在墙上的老枪的巨大诱惑,拿着它去打野鸭,承受着强大的紧张、焦虑的心理压力,最终因枪走火身亡,这一点与福克纳《沙多里斯》中的小白亚德的命运相似。
莫言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一种隐形的民间集体无意识心理原型和民族民间神话世界。《红高梁家族》中,大奶奶、二奶奶的死亡仪式,都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和死亡崇拜。《秋水》极近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只是主人公不是神性的英雄,而是人性的民间本色英雄,洪水的故事相同于世界各民族洪水故事的救世神话,而血亲仇杀的主要情节原型可追溯到上古史传故事和《圣经》及古希腊神话。莫言小说整体的潜在的神话结构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民间好汉的人格神话,英雄崇拜的史诗灵魂,鳖精狐怪之类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观,人生神秘感、宿命论、因果报应的潜在思维模式等。[8]
而这种神话模式、神话原型在福克纳小说中无疑表现得更加突出。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我们祖先反复经验所形成的原始意象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积累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人格、行为、意象,而伟大的艺术家具有超人的原始想象力和利用原始的意象表达其经验和感受的能力。福克纳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对《圣经》了如指掌,他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结构都是基督受难的原型。书中的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七日、八日,恰好都在复活节的一周里:基督受难日,复活节前夕和复活节。第二章的标题是一九一O年六月二日,为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因此,康普生家历史中的这四天都与基督受难的四个主要日子有关联。不仅如此,从第一章的内容里,也都隐约可以找到与《圣经》中所记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处。福克纳以基督的庄严、神圣反衬康普生家的子孙更加猥琐,而他们的自私、没有爱、失败、相互仇视,也说明了现代人违反了基督死前对门徒所做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教导。福克纳以这种神话模式手法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一层反讽色彩,更是使故事从描写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的寓言。
《押沙龙,押沙龙!》这部小说直接借用《旧约》中大卫王的故事和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福克纳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去吧,摩西》(取自圣经中的人物)中的《熊》可以相对独立成篇,它表现了英雄原型中的启蒙、成长、追寻的精神主题。英雄从无知幼稚到涉世成人要经历一系列痛苦的艰难磨砺,这是他的成年仪式,《熊》中的主人公莫克的成长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体现了这一原型。《我弥留之际》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寓言,一次历险,是《奥德修纪》的变形。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艺术试验主要表现在多角度叙述手法、内心独白、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等表现技巧的运用上。
多角度叙述就是让叙述在几个不同的视点和层面上展开,让读者倾听不同的、多个叙述者的讲述,从而获得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艺术效果。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把同一个故事讲了五遍,第一遍(即小说第一章)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白痴班吉叙述,第二遍(第二章)由昆丁叙述,第四遍(第四章)由女佣迪尔西叙述,小说发表十五年后,作者又以附录的形式讲了第五遍,即以评论家的身份重述了一遍故事,把康普生家族兴衰的来龙去脉和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结局作了交代。《我弥留之际》被分成五十九个部分,分别由十五个叙述者讲述,包括七个家庭成员和八个外人。这些叙述者在进行着某种对话和话语碰撞,他们对某一个人物或事件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使读者无法轻易相信哪一个,无法轻易下结论。这种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述构成了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押沙龙,押沙龙!》有一个侦探小说的外衣(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同样如此),分别由老处女洛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他的哈佛同学史立夫讲述塞德潘的故事。由于他们立场不同,对旧南方、对塞德潘家族的态度和感情不同,他们叙述的中心、对时间的看法、对各种谜团的解释都相去甚远,每个人的讲述都在颠覆、解构着其他人的讲述。他们的叙述语调有着鲜明的个性:洛莎发出的是刺耳的、尖利的、歇斯底里的复仇呼声;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具有貌似安详、开朗的气氛;昆丁企图使故事传奇化,他叙述的特点是一种病态的激情的高亢;年轻好奇、富有浪漫主义的史立夫叙述他与同宿舍好友之间反常的友情,是他唆使了昆丁的叙述。福克纳在对时间的感知上深受柏格森的影响,他的小说注重表现心理时间、人物的潜意识、非理性,大量运用意识流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喧哗与骚动》前两章和《我弥留之际》的一些章节,前者的第二章昆丁的部分,标题是《一九一O年九月二日》,他将在这一天自杀,他的精神状态已接近崩溃,小说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写出了他的狂躁、焦灼,他的乱伦倾向,数十年的生活现实回忆及颓败的家族命运使他产生的幻灭感、绝望感。
福克纳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象征、隐喻。如《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部分,金银花这个意象出现了三十多次,它象征着凯蒂的失贞、昆丁的软弱、对童年时代的眷恋等。这一部分中,作者还使用了一系列象征时间的意象:手表、钟声、太阳及影子,它们象征着无所不在,无法停止、逃避的时间和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变革。昆丁竭力想打碎祖父遗留下来的手表,倒退着走路并践踏自己的影子,这些都象征着他想从时间与变化中逃出来的绝望心情以及他注定毁灭的命运。凯蒂弄脏的内裤、水同样具有象征喻义。此外,《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紫藤,《我弥留之际》中的送葬之旅、洪水、火灾、棺材、马,《去吧,摩西》中的森林、大熊等,都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独到的象征手法、意象。
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奇认为,莫言一九八五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枯河》在文体与结构上显示了福克纳影响的痕迹。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不招人喜爱的男孩受到村支书女儿的挑战,上树折树杈,好用它削一杆枪,不料他从树上摔了下来,正砸在那女孩身上,她当场丧命,村支书及他的家人对他进行了野蛮的毒打,后来,他从家里逃了出来,投河而死。
托马斯·英奇认为,莫言以男孩小虎的视角展开叙述,而小虎“总是迷迷瞪瞪,村里人都说他少个心眼”,因此,他被一团令他困惑的景象、声音、气味所包围,这些困惑是他的智力所理解不了的,这一点类似《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枯河》中写到小虎从大树上摔下来之前,往下看全村及整个成人世界,象征着下面被暴力、不忠所笼罩的腐朽的世界;而《喧哗与骚动》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小姑娘凯蒂爬上梨树观看奶奶的葬礼,她短裤上的斑斑泥迹被树下的孩子们看到了,象征着日后凯蒂丧失贞节、堕落。当小虎投身“难以忍受的寒冷”的河水时,我们再次想到昆丁也绝望地跳进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查尔斯河里。而《枯河》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某种超现实主义的意象,运用外部世界的具体细节将我们带入内心情感的困惑和焦虑的现实中来,这是莫言的独创之处。[6](P340)
莫言的小说同样大量运用了多角度叙述。如《球状闪电》、《十三步》、《檀香刑》等,这三部小说也运用了内心独白、意识流手法。而意识流手法运用得最突出最成功的小说是给莫言带来很大麻烦的《欢乐》,这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一个成功范例。与《喧哗与骚动》中第二章昆丁自杀那天的潜意识活动—样,《欢乐》写了一个农家子弟的高考落榜生自杀前的迷乱的精神状态。
莫言小说中的象征是新颖、独特的:透明的红萝卜既象征着人生美好的憧憬又象征着性;红高粱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象征着超拔脱俗、血性铁骨的旺盛生命力和民族精魂;所有姣好的女性都穿着红色衣着,红色象征着情爱、欲望、激情、生命力;相反,《欢乐》中的齐文栋一再诅咒绿色的玉米地,此处绿色象征着蒙昧的生存状态,摆脱不掉的残酷无望的农村生活。此外,像鲜花(《怀抱鲜花的女人》)、大水(《秋水》)、球状闪电(《球状闪电》)、水中睡莲(《罪过》、《钓鱼》)等均有象征意义。
福克纳的文体曾遭到众多批评家的指责,,认为是哕嗦、臃肿、冗长、堆砌词藻等等。后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独具匠心的多才多艺的文体家。福克纳在叙述中喜欢用连续性和包容性很强的长句,他的句子像一个雪球,急速向前滚动,一路上把各种信息、修辞、限定、解释一并吸收进来,插入语、同位语、从句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上面,越滚越大,读起来让人透不过气来。与之同时并存的,几乎在福克纳所有所品中,又有一种切实、生动活泼的口语文体,特别是在人物对话中,在运用口语方面,美国当代小说家无人能与之匹敌。
莫言的叙述语言同样是丰富、繁复、芜杂的,是披头散发的,有时又是泥沙俱下的,充满着大量的修饰语和附加成分。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莫言的语言感觉是出类拔萃的。他的长句式舒缓、厚重,密集调动各种感觉,对读者进行语言轰炸;而他小说中的口语化短句多出现在人物对话和人物独白中,简练、生动、形象、质朴,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气息,是生活化的乡村习语,野腔野调,完全符合环境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我们从那活灵活现的语言中能够感受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另外,莫言和福克纳都同样具有一种乡村幽默。
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坦率承认自己受到外国文学影响,承认自己的师承的作家,他把福克纳看作自己的导师,由必然的学习、模仿阶段逐渐走上一条超越之路。作为一个在农村长期生活过的中国作家,莫言的人生经验、观察和感知生活的方式、精神世界、想象力、语言表达既是中国化的又是个人化的,莫言以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来,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和立场表达人类共通的精神和命运,获得世界性的广泛认可。
莫言和福克纳在“文学王国”的缔造、文学版图的描绘,历史时间意识,神话原型,小说主人公对祖先、故乡、家园的复杂情感,多角度多声部的叙述艺术和叙述语言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J].世界文学,1986,(3).
[2] 莫言.锁孔里的房间——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M].广州:新世界出版社,1999.
[3] 莫言.老枪·宝刀[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4]福克纳:福克纳谈创作[A].福克纳评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 莫言.莫言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6]贺立华,杨守森.莫言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7] 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A].福克纳评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8] 季红真.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J].北京文学.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