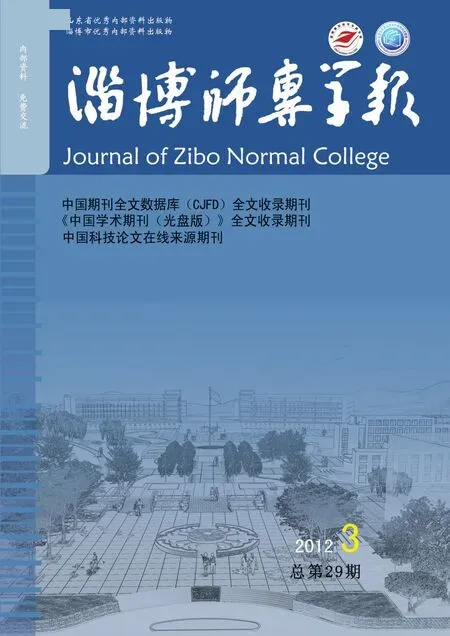中华族蒲氏源于中原汉族
——蒲松龄原族源于中原汉蒲
蒲先慧(淄博市淄川区洪五生活区委员会,山东 淄博 255138)
在蒲学研究中,多年来尚未见有关中华汉蒲渊源的探讨。然而,却出现了般阳路蒲氏多民族归属的论述。近年来,笔者发现《蒲氏起源》中将中原汉族的般阳蒲氏后裔蒲松龄纳入蒙古族蒲甘一支,同时又将蒲松龄归入到回族蒲寿庚脉下一支;而且再次将名人一节中的蒲松龄列入蒙古族论述。经过考证,笔者认为以上两族所论确未列出重要且有用的依据。
一、中华族蒲氏渊源中原汉族
要知道蒲松龄的民族归属,只有将中华族蒲氏,即汉族蒲氏考明渊源之地。故需以史料逐一稽察,以求径入渊源之脉。
《蒲氏族谱》序中云:“稽古帝舜拜蒲衣为友。是黄帝后已有蒲姓;汉蒲茂之女,以考显改邑名曰“蒲台俊”[1](P1-7)汉蒲元性为武侯铸刀,分汉涪水。以此论之,蒲为中华族无疑。此指出了蒲姓源于古舜帝时,且以汉族的蒲茂之女考显之绩及三国时四川的铸造兵器家为诸葛亮。铸刀三千于分汉涪水,以证淄邑蒲氏为中华族无疑。
稽《辞海》蒲条载:“蒲衣名人,释文:‘尸飞云:蒲衣八岁舜让以天下’”。
以此两说,均明古舜帝时已有蒲姓。但亦未明舜、蒲所出之源何处。
稽《蒲氏起源》(下简称《起源》)认为:一、二、三源均出之蒲氏虽出于多头人源,确均属源于中原汉族。主要源出于两组:第一组 蒲姓概况共七源,第五源出蒙古族;第二组源出“蒲氏渊源”共八源,第六源出蒙古族。第二组与第一组不同,且两组所出蒲姓顺序不一致。原文不一致,一、二、三源全同。
第一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远古舜帝老师蒲衣,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舜帝的时候,十八岁的蒲衣成为舜帝的老师。”
第二个渊源“源于已姓,出自夏王朝时期,舜帝裔孙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相传在夏王朝时期,舜帝裔孙被封在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此说明夏王朝时蒲姓源出舜帝的裔孙封地蒲坂,以蒲为姓。
第三个渊源:源于高阳氏,出自帝少昊后代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在春秋时期,帝少昊后代的封地在蒲地(今山西隰县)后建立蒲国。蒲国王族的后代以国名为姓,称“蒲氏”。
以上三个源出蒲姓,虽然源出之人较多,但均属于中原之地(山西省境内)。
据笔者分析,中华原指古代称黄河一带,中华是汉族最初兴起之地,后来统称“中国”。中原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大部地区,山东西部和河北、山西南部(或说全省范围)。所以,可以说中华族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汉族蒲氏源于中原之地(称汉族为中华族)。可见,《起源》的一、二、三源源出皆为中原所出汉族之蒲。
另外,四源出于嬴氏、东晋氏羌西戎酋长苻洪属于植物名称为氏;五源出于女真族,是东真国主蒲鲜万奴的后裔子孙;六源出于蒙古族,属汉化改姓为氏;七源出于回族,属汉化改姓为氏;八源出于满族,属汉化改姓为氏,源出蒲氏之地,均不在中华的中原之地,不属于汉族蒲氏。
稽《史记》可证中原汉蒲之源。[2]《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
舜帝的家乡在今河北省南部的冀州,属中原地域。舜帝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登临帝位后,勤于政事,常巡行天下。据说,虞舜巡行北方时于途中得闻:蒲坂地域的虞氏部落有位德才兼备的大贤蒲衣时年只有八岁。舜帝认为蒲衣是位难得的才智之才,便直奔蒲坂而去。当时蒲衣正与大禹及其他人在河岸上制作渡河排筏。蒲衣与大禹下岸见舜帝时,舜帝先迎上施礼:
“舜特来拜见大贤蒲衣,还望不辞赐教。”
酋长大鲧抢先开口:“帝君,蒲衣乃本部落蒲公英的后裔小儿,而且是个只有八岁的无知无才的顽童,勿需致此大礼……”
帝见治水大臣兼部落酋长的大鲧如此轻视蒲衣,本想表达几句看法,但还是禁不住好奇:
“部落中如何出了位蒲公英?且是蒲衣的先祖?”
“蒲公英乃部落的普通一户蒲姓人家”,大鲧随即将蒲公英的源出细述出来。原来,若干年前的一场大雨,造成洪灾,有个汉子被水冲到沚地上搁浅了,挨过日夜,发起烧来。为了活命,他再沚地上寻得野棵蒲公英充饥,不仅不再饥饿,也退烧了。被大家救出后,他就开始用蒲公英为发烧的人医治,很有效验。于是这人为不忘救命之恩便以蒲为姓,名叫蒲公英了。蒲衣便是蒲公英的子孙。
舜帝很有感触:蒲公英的由来实乃天意,这事乃蒲地的一大神奇。蒲衣是钟灵毓秀的蒲坂之地所育奇才,于是向蒲衣请教谁能治水?蒲衣建议:事有大小轻重之分,人有才智高下之别,量才任用能者重任。大禹常随鲧老治水,见多识广,有实践经验,人也聪明,可任治水一职。”
于是,舜帝当众拜大禹上任治水大臣,并希望将来把天下让贤于蒲衣。蒲衣提出:“圣帝百年之后,当有大禹继统天下。”
舜帝领略了蒲衣之才,实乃难得的博大胸怀与高超的处世方略之智,又希望蒲衣做相,辅佐其治理天下,并去留自由,蒲衣依然力辞。最后,舜帝诚意拜蒲衣为友。
此段传说表明,蒲衣源出之祖蒲公英大约在舜帝的家乡,而舜帝家乡均在中原。可见,中原不仅是蒲姓源于汉族之地,也是中华汉族最初兴起的最集中之地。
依《起源》所云:蒲氏“郡望”之地分析,蒲氏所居“郡望”之地,亦属中原。以《郡望百家姓》和《姓氏考略》所载:“郡望为河东郡,表明蒲氏曾长期繁衍生息于该地区。”河东郡古代有四处:一处指整个山西省。一处指秦朝时治所在安(今山西夏县)东晋时移到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隋朝又分蒲坂,以河东县为治所。一处指唐朝由河东设节度使,治所在蒲州,节度使治所在太原。一处指宋朝有河东路,治所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兼有陕西东北角。
以上可见,“郡望”之地仍未出中原汉族源生之地,即中华族蒲氏源出兴旺发达之地。
二、蒲松龄远祖源于中原汉族蒲氏
各民族的演变大概有两个因素:一个乃战乱、兵火;其二天灾、旱涝。“汉末魏晋时期,中原扳荡,狼烟四起(文见《起源》)。北地(即中原一带)蒲氏族人为避兵火而迁徙于今四川之地者。”与“唐末五代动荡不安,导致北方蒲氏族人迁徙南方者甚众……”
(一)稽宋史
五代后期周显德六年(959年)[3](P460)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起,连年征战,随处均有不堪战乱之苦的人家纷纷外出逃避,世传中原的蒲氏人家亦有一伙东迁山东。他们在淄邑孝妇河畔开荒耕种搭棚定居下来,经过多年艰苦创建,建成淄之城乡蒲家庄(即今高家店子)。其他姓氏人家也先后建成招村、黄家铺、望娘沟等村。
同时《淄川区志》云:“店子约建于宋代,蒲氏先居名蒲家庄元末以姓改称高家店子。”可见,《宋史》所载与世传无误。至于区志中提及蒲家庄后来改成店子村。关于其中原委,笔者在自己的其他文章中早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二)南宋时期因灾荒淄邑蒲氏外迁流变者亦未加入蒙古族
稽《淄川区志》:“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这年四月大旱,六月霪雨,是年大饥。斗米值余钱。”世传这年原蒲家庄与其他村庄一样,许多人家结合外逃。蒲家庄的蒲云超、蒲鲁琪与族人合伙携眷北去,未几即进入蒙古南方定居下来。蒲云超之子蒲鲁浑,蒲鲁琪之子蒲居仁长大成人后参加了成吉思汗的大军征战中原。蒲鲁浑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封为大将军。之后调进京城封做中书省二品官,后来又封为元宫廷“伴朝”之职,世人为之称“蒲伴朝”。然后又调回山东,两人被并任山东东西道、般阳路总管。二者先后殁逝于任,被御葬于故乡原蒲家庄西北旁。因墓园中石人较多,故称“石人坡”。由原蒲家庄中原汉蒲人家迁徙蒙古,虽生活多年,然后再回到山东淄邑,蒲氏仍然没归入蒙古族。而且蒲鲁浑等大户及其子孙不忘中原汉蒲的故乡蒲家庄之先祖,在城中建了蒲家祠堂,按时节祭祀。另外,还于祠堂门两侧贴上楹联:
上联曰:银鱼赐佩名臣度
下联云:蒲坂风高虞帝师
上联的意思特指宋皇佑进士蒲宗孟,官尚书佑丞,被赐佩银鱼之荣;下联特指汉族蒲氏源出之地蒲坂的风脉尤佳,出了位虞舜之师蒲衣。可见中原山东淄邑东乡蒲家庄的蒲氏族人,没有失去中原汉族气节。于此可证:淄邑汉蒲不忘原族,没有加入蒙古族。
蒲松龄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始修族谱于序中云:“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蒲家庄西北旁)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授职不引桑梓嫌也”“吾族田赋世居在城”故蒲家庄的蒲氏没有易为蒙古族。蒙古族人也没以功臣将蒲鲁浑、蒲居仁纳入蒙古族。
(三)元朝廷以梦夷蒲族,遗孤嗣宗:亦以中华族自誉
《蒲氏族谱》蒲松龄为始祖蒲璋小传云:“相传蒲为元世勋,元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家,外族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此亦传疑之说,无所考信矣。”原中原汉族蒲氏能否复姓嗣宗落得全靠蒲璋一人之身。
据族传:蒲氏被夷族之时曾有强力者冲出重围奔逃于南方,但始终不知脱逃者下落,有无易族者。淄邑惟有匿于外祖杨家的蒲璋,在杨家生息,十六岁左右杨家为他聘了杨氏女订了未婚妻。蒲璋怎样成亲立家复姓嗣宗的未见文字记载,有段族传故事可解。传说,元朝时,淄川来了头西怪铁牛,到处毁坏农田和家畜。朝廷下旨,淄邑限期以火化除牛害,化了的有赏,否则就地杀头。原蒲家庄蒲家的管家卢江被误认为炉匠抓去化牛。前头的化铁匠已被杀,卢江深知有去无回。于是在化牛前为自己唯一的闺女定了终身,其未来的夫婿便是同龄的蒲璋。炉匠化牛期限到之日,卢女为父送来最后一次早饭。听说铁牛没死,她绕上靠大崖的炉顶,只见铁牛安卧炉中,她很着急。忽然间,她的一只耳环掉进炉内牛耳上,眨眼牛耳化了。她认为,一只耳环能化去一只牛耳,如果自己跳下,应该能将铁牛全部融化。扎进熔炉,铁牛瞬时化为了铁水。
自幼相处一院,一直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就这样死去,蒲璋悲痛欲绝,遂大病。医者诊言:要公子病愈,一要尽快为他完婚,二要向南搬迁,换个村庄定居。杨家依医所言赶紧照办,为蒲璋速娶杨氏为妻,并搬去三槐庄籍居,这就是后来蒲家庄的初名。
朱元璋打垮元帝开科走向正规取仕之时,蒲璋进京赶考得中进士,朱元璋为蒲璋一族翻案复姓中原汉蒲并成了淄邑富户。三槐庄随柳泉井的水满外溢易名“满井庄”,后当蒲璋的子孙繁衍生息成为丞民大族之时,在乡亲的支持下又将满井庄易为“蒲家庄”了。蒲松龄于修族谱序中云:“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至此,元朝夷蒲族后,蒲璋匿于外祖家随母姓为杨到元鼎既革之后,又复姓中原汉蒲。以中华族的气节,复中原汉族蒲氏。蒲璋堪称具有中华族坚毅气节之志,未被艰于生存的威胁撼动其中原汉族的归属,蒲璋复起东乡蒲氏一支,深感自豪。
(四)蒲璋的第五子,蒲子忠的子孙分散嗣宗于四川
《族谱》自蒲璋被朱元璋为之翻案复姓之后,其子孙非常珍惜复祖姓之艰。在二、三代中,即开始分散嗣宗。始祖的第五子蒲子忠与子孙迁吴桥后不久即与他的第五子蒲成及蒲成的两个儿子——蒲和、蒲籍全家去四川籍居,时年约明洪武十年左右。子孙众多的时候,仍为四川的中原汉族,大约于晚清之时。其后裔蒲殿俊的祖父蒲瑞溪一支于四川广安城北沟生息定居,其父蒲玉林(县生员)到蒲殿俊之时已是众多一支,他们仍是中原汉蒲后裔——山东淄邑蒲氏于元末夷族之后蒲璋的裔孙之后,也未闻有人改族之事。
蒲殿俊字伯英,著名民主革命先驱。十八岁考中秀才第一,第二年又以优异成绩成为州里稟生第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乡试得中头名解元。一年后北京考中二甲进士,被授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派他到日本留学(法政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回国,担任法部主事兼宪政调查馆行走,回四川后被选为姿议局议长……后来他谢绝了北洋政府之聘当政府教育部长的“美差”而应了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在此期间(1923年)蒲殿俊以淄川中原汉族蒲氏的后裔身份到山东淄川与东乡蒲家庄阖族为蒲鲁浑立了大石碑。碑的正面正中大字“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之墓”,左下角小字两行,“后生殿俊敬书”与“后裔合族公建”,右为年代是“中华十二年葵亥谷旦立”。两边刻有联语:上联为“德行科从孝悌演起”,下联为“文明世自礼让油生”。大碑原立于原蒲家庄西北旁墓园中,即世人所称的“石人坡”。
蒲殿俊淄邑之行,不仅表明四川蒲璋的后裔子孙,永怀始祖蒲璋,而且永不忘怀念远祖任元代般阳路总管的蒲鲁浑及山东淄邑建蒲家庄的先祖,还说明四川省的蒲氏没有改易别族。
元末夷族蒲氏后遗孤蒲璋五子嗣宗下传,淄邑蒲氏如今已成众大之族。就《蒲氏家谱》记载:谨祖后,移居坡地;彦祖后,迁居临朐;木祖后,迁居莒州。三个支族已成丞民之众。蒲家吴桥族人,已成为蒲家族庄,成为淄邑东乡的蒲家庄为中心的第二支族众。淄邑蒲家全族已成为以蒲家庄为中心的五大蒲氏支族(莪庆蒲氏于蒲家庄合为中心之族)。几经更代战乱,荒时岁月,尚未闻有更族之事,包括四川同族。
三、蒲松龄不是回族,亦非蒙古族
依南宋嘉定三年蒲家庄的蒲运超携家与族人外出逃灾荒起,作为淄邑蒲氏一世排序。[4]
一世:蒲运超(1180~1262年);二世:蒲鲁浑(1202~1279);三世:蒲震恒:兄弟九人,生卒年不详;四世:蒲迎祥(同上);五世:蒲维利(同上);六世:蒲永阜(1325~1354年)七世:蒲璋(1326~1416年左右);八世:蒲子忠;九世:蒲整;十世:蒲海;十一世:蒲榛;十二世:蒲永祥;十三世:蒲世广(高祖);十四世:蒲继芳(曾祖);十五世:蒲生衲(祖);十六世:蒲槃(父);十七世:蒲松龄(1640~1715年):于康熙二十七年戌辰(1688年)始修族谱时为今族又撰了三十二字辈诗:
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起源》却将“先”字误为“显”字)
依此序之:蒲松龄当为十七世孙;依蒲璋为始祖,当为十一世孙。般阳蒲氏为原蒲家庄蒲氏的子孙,未闻族中有人于各种灾荒外逃与战乱中外迁徙他乡异地者,改汉族入蒙古族或是入回族的传说。
依蒲松龄的上几辈入仕中的名人记之:(《蒲氏族谱》中所载)汉蒲茂之女孝显改邑名曰:“蒲台俊”;蒲茂三丈因为氏。为氏为河东人(即中原地域中原汉蒲),又云:蒲显道、蒲之道、蒲竑、蒲泽之。俱阆中人,皇祐举进士;蒲卤为南部人,其母任知书里,号任五经。卤受业于母,元丰举进士。又蒲宗孟及第,宋神宗赐佩银鱼,官集贤校理,翰林学士,尚书右丞。以上均四川同汉族蒲氏。无人弃汉族易蒙古族或易回族的事。到元代,蒲鲁浑等仕官之时也无人弃汉族,被纳为蒙古族。淄邑的中原汉族蒲氏,从始祖蒲璋起,到蒲松龄的高祖蒲世广(邑禀生,少聪慧,才冠当时)以下有四子:蒲续芳、蒲继芳、蒲绍芳、蒲联芳,均邑庠生说起。蒲联芳明训导:蒲继芳的长子,蒲萌襄阳府典史;次子蒲生池明贡员,直隶无极知县,有政绩,志载《通志·训良传》;第三子蒲越明祭官。(叔祖)蒲生汶明嘉靖四十三年乙酉举人万历十年壬辰科进士,官直隶县的父母官,性好学,手不释卷,闻母病,哭几绝。素赢吐血数斗而卒。蒲世芳明末镇守东北抚顺,于抗敌侵入中阵亡。蒲越的次子蒲兆昌,明天启举人(卒于1621年)。蒲生池的长子蒲小川以孙瑞贵膺赠文林郎。蒲瑞字信候,号松执,顺治辛卯(1651年)举人,顺治十年(1658年)进士及第,官浙江金华府汤溪县知县。
蒲松龄的族侄蒲振缨,顺治十六年中举,拣选知县;祖孙蒲念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任曹县教谕。淄邑蒲氏虽无状元,宫廷名臣,亦可属。科甲相继于世家族。就明万历间,合邑食饩者八人,族中占六人焉。到蒲松龄本人虽未实志入仕,然其与世业绩:以《聊斋志异》饮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争得世界文苑一席之地。大概与状元宫中名臣相比或各具千秋。以上仕官名人皆无人被改汉族为蒙古族之事,亦无人被易为回族。今人不解的是:蒲松龄上下族人仕官名人中,无人将其仕官某人纳为蒙古族,也无人将蒲氏为朝中名臣者蒲鲁浑等人收为蒙古族,或是阿拉伯回族。到蒲璋的后裔孙,四川的蒲殿俊,也算高阶人物,亦无人将其录于蒙古族或是回族。单单的蒲松龄,未沾上一点官名,竟被《蒲氏起源》分给了蒙古族的蒲甘氏一支和阿拉伯回族的蒲寿庚脉下的一支蒲氏。他们将淄邑蒲氏的祖宗中原汉族的蒲氏,不顾其汉族的族祖之籍,独将先祖之裔孙蒲松龄分给了两个族脉不相干的祖籍。如此之论,不合史实,当该商榷。
四、与《蒲氏起源》所述蒲松龄蒙古族、回族族属商榷
中华族乃正宗源出中原汉族蒲氏之族。从中原源出汉族蒲氏到山东淄邑蒲氏,元末夷族后遗孤蒲璋复姓嗣宗在外祖家几经沧桑之苦,分散嗣宗求生,皆未闻有弃汉族更别族之事,更无改称蒙古族,也没改称阿拉伯回族的事。为何到蒲松龄著有《聊斋志异》后,被《蒲氏起源》述为蒙古族与阿拉伯回族。既未考辨,又未推理。理据何在?
(一)蒲松龄家谱,并非蒙古族蒲甘氏一支蒲氏
《起源》于第六个源出(蒲氏)“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蒲甘氏宋朝时期原为今缅甸地区的一个泰族氏族部落,与今傣族的民族属性相近。宋末元初因助南宋抵抗元朝军队被元军歼灭,后族人被裹胁分散为蒙古奴役,逐渐融入蒙古族。”“明朝时期,蒲甘氏即随改土归流运动。以原部落名称首音改汉姓为蒲氏,世代相传至今。著名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就属于这一支蒲氏。”
《起源》如此,既不言依据,也不说明原因,竟将中原汉族的文学家蒲松龄说成了蒙古族蒲甘氏一支。
《起源》所述,蒙古族的蒲甘氏远祖之出,与中原汉族的蒲松龄远祖之出相距甚远。蒲松龄远祖乃中原汉族,是于宋初东迁山东淄邑在孝妇河畔建族的蒲氏。若论蒲松龄淄邑的远祖,即淄之城乡蒲家庄的原蒲氏;较近的先祖,即为原蒲家庄蒲氏的后裔蒲鲁浑、蒲居仁;而最近的祖先,即是元末朝廷以梦夷蒲族后,遗孤(始祖)蒲璋。若依蒲鲁浑之父蒲运超向下排序,蒲松龄当为十七世孙;若以始祖蒲璋序起,蒲松龄应为十一世孙。《起源》的作者将中原汉族后裔的淄邑蒲松龄与蒙古族的蒲甘氏合为蒙古族的一支,便无法解释两人的上辈族属。
明朝时期蒙古族蒲甘氏随改土归流时,蒲松龄的始祖蒲璋已近五十岁,这时是明洪武帝朱元璋时代。当蒲璋一族复姓中华族蒲氏之时,蒲甘氏一族才开始以原部落名称首音改汉姓为蒲氏。可见,从时间上来看,蒲璋也无法被还未改姓蒲氏的蒲甘氏收为蒙古族。当然,将清代康熙年间的蒲璋的后裔十一世孙蒲松龄收为蒲甘氏一支蒲氏更荒谬之极。若向前推:“宋末元初,因蒲甘氏一族助南宋抵抗元朝军队,被元军歼灭。后族人被裹胁,分散为蒙古奴役”之时,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时为元朝的大将军。所以,就这样相差甚远的蒲甘氏与蒲鲁浑根本无任何瓜葛。而《起源》的作者将蒲松龄归属于蒲甘氏这一支蒲氏,无异于承认宋末元初蒲甘氏与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有同族之脉。这样的推断显然是错误荒谬的。
《起源》在名人中云:“蒲松龄,蒙古族,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临淄人(今山东省淄博市)著名清代文学家。”
察蒲松龄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始修族谱序中云:“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授职不引桑梓嫌也……而吾族子姓日蕃,所居满井庄由此而易其名(改曰“蒲家庄”)。”清代蒲家庄乃淄川县东乡八里的一座小村,淄邑北邻张店,南邻博山县,西邻章丘县,东邻益都县。建国后划归淄博市管辖。《起源》的作者不仅将淄川县的蒲家庄——蒲松龄的族庄不提,还将蒲松龄归了淄博市临淄人?更属荒唐!
(二)蒲松龄亦非阿拉伯蒲寿庚的回族一脉支谱
《起源》云:“山东淄博蒲氏族谱(蒲松龄的家谱)(清)蒲人鸿、蒲国俊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手抄本四册,属蒲寿庚脉下的支谱,蒲寿庚为总谱第七世。”
此云有误:公元1911年蒲家第六次续修族谱乃蒲治善、蒲人鸿两人主修,并非蒲国俊参于此次修谱。另外,蒲治善、蒲人鸿所修族谱于蒲寿庚脉下之谱毫无瓜葛关系,此说乃蒲寿庚节外生枝。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无节生枝。
《起源》云:“多数学者认为,蒲寿庚祖籍阿拉伯回族公元十世纪前(即宋初)定居战城,公元十一世纪移居广州(约宋徽宗元年),公元十三世纪(约元成宗大德三年,1300年)再迁泉州。”
此时,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早已是元军大将军;调回京城被封为中书省二品官员。那时,无人承认蒲鲁浑是蒲寿庚脉下支谱中的人物。依《起源》所述:“宋末时期阿拉伯人蒲寿庚由广东广州徙福建泉州。降元后(时约元成宗五年)贵显非常。”也就是说,这时期,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两家正显赫于元京城,蒲鲁浑并有元宫廷“伴朝”之名。这时,也无人将山东淄邑原蒲家庄(即蒲鲁浑的故乡)的蒲氏中任何人收为泉州降元显贵非常的蒲寿庚脉下一支蒲氏。可见,降元的蒲寿庚是元军征战中原的大将军,蒲鲁浑不会拉同“回族”支脉的关系。所以,六百余年后的清宣统三年(1911年),将蒲鲁浑的十六世孙蒲松龄划给阿拉伯回族的蒲寿庚脉下亦属无稽之谈。
总之,《起源》作者在同一文中将蒲松龄归给了蒙古族的蒲甘氏脉下一支,又将蒲松龄分给了阿拉伯回族的蒲寿庚脉下一支,实属荒唐之举!
(三)从《聊斋志异》中的民族思想寓意,亦可见蒲松龄确系中原汉族
从《聊斋志异》的内容来看,似乎包罗万象。一般说来,作者若有“暗寓之意”在文字狱盛行的大清一定会设法掩护,但却难掩方家之目。《聊斋》里的确有民族思想。笔者意外地发现晋陀先生三十年前的一篇《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一文。[5]该文已对蒲松龄的民族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条分缕析的论述。该文以《聊斋》故事《林氏》被“北兵”掳去,不辱自刎;《张氏妇》杀死三个要强奸她的大兵(即清兵);以《张诚》、《乱离二则》揭示出民族压迫的残酷事实等回答了《聊斋》确有民族思想的事实。晋先生又以蒲松龄的一首诗旁证:
城中鬼哭如荒村,惨绝国殇贞烈魂。庭广无人月凄冷,天阴雨血昼黄昏。泣拋儿女死心决,笑入黄泉生气存。冤愤千年作云雾,而今井水有余浑。——《王烈妇》
晋先生以诗论道:
清兵的屠城政策,前四十五年就下令停止(顺治十六年,1654年,曾下令停止屠城)。这时怎么会出现“城中鬼哭如荒村”的景象?实际这一年是甲申年。古代干支纪年,对于支六十年周期看得很重,分明是作者表扬节烈和封建伦理挂钩抒写自己的亡国痛!
可见,蒲松龄是具有中华族气节的著名文学家……
参考文献:
[1]蒲治善.蒲氏族谱(序)[M].蒲氏家族第六次续修族谱.
[2]李史峰(主编).史记.五帝本纪[A].中国通史[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李史峰(主编).宋史[A].中国通史[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蒲章泰.元宫疑案[M].(拣记)。
[5]晋陀.《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A].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专刊[C].济南:齐鲁书社,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