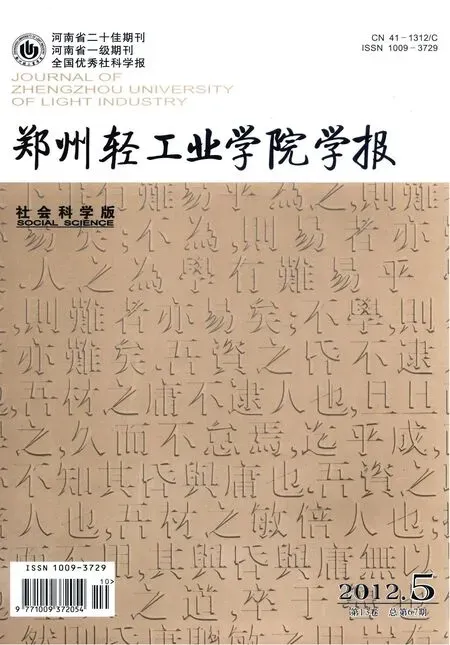论中央银行立宪
吴礼宁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是惊心动魄的,究其根源,金融危机是由于货币当局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发行权不受限制造成的,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同一个机构联系在一起,即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作为政府部门,是宪法学当然的研究对象。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等,都将货币当局(主要是中央银行)比作一种立宪政体,主张把货币当局视为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一样的国家机关,以便将其纳入宪法的规制之下。[1-2]哈贝马斯、史提芬·霍维茨、芬恩·基德兰德、马可·怀恩和彼得·波恩霍尔兹等宪法学者和经济学家,也都提出了通过限制中央银行权力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设想。
在国内,经济学家对中央银行制度以及货币发行等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刘丽巍[3]对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权限、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认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中央银行理论与实践的首要任务;范方志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则是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4]。此外,张维迎的《危机中的选择》、吴志攀的《中央银行法制》、陈晓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宋鸿兵的《货币战争》等,都对中央银行制度及货币问题进行了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是从经济学或经济法的角度展开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从宪法学角度对中央银行制度的专门研究尚未见报道。虽然一些关于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和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讨论,在一定层面上涉及到中央银行的宪法定位及其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同样很少从宪法学角度展开,并且通常的观点认为应当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对中央银行权力进行宪法规制的现实意义。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宪法学者也没有对中央银行给予必要的关注,这与中央银行的宪法地位及其经济功能是极不相称的。
在实践中,以美国为例,由于其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游离于宪法的控制之外,导致了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并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波及全球的恶性通胀。具体到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我国中央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受限。鉴于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加强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规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抑制通货膨胀以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突出而紧迫的宪政命题和时代任务,也是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本文拟从宪法学视角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界定中央银行及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地位,探寻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梳理出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脉络,丰富宪法学的研究内容。
一、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脉络
如果说货币宪法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则是货币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通常来讲,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包含理论基础、独特的研究对象、基本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等。对于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而言,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只不过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而已。至于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对象,则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中央银行的宪法属性及其宪政定位。中央银行是由中央政府组建的金融机构,负责控制国家货币供给、信贷条件,监管金融体系,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由此可见,中央银行是一国重要的政府部门,行使着重要的公权力,因此应受宪法规则的约束。(2)中央银行立宪的宪政意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滥用构成了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侵害,而宪法的基本价值在于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通过宪法性规则规范中央银行权力,乃是当代宪政的历史使命。(3)中央银行立宪的基本模式。通过宪法性规则,明确中央银行的职责权限,建立具体的宪法性货币规则,规范货币发行行为,规范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确立中央银行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基本宪政模式。(4)中央银行立宪与中国国情。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法律责任,中国的财税制度、中央银行体制,均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政体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在中央银行立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方法,自然离不开价值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和规范分析等方法。尤其是,中央银行及其行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财产行为,发挥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实证性的研究和规范性的分析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不仅要注重规范分析和学理阐释,更要通过诸多的政治、经济、历史现象,深究迷雾掩盖下的事实,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规则背后的真相之后,才能进一步探悉规则的真实意涵,学理阐释也才更有效、更准确。然而正是在这一取向上,中央银行的立宪主义研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是由于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理论上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实证资料真伪难辨,使得相关研究举步维艰。尤其是西方的中央银行,其历史和现实均裹着一层面纱,只有朦胧轮廓,研究者无法获取其真实的全貌。无论是伍德的《英美中央银行史》、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还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都没有给出中央银行一个整体的形象。故而,对于中央银行背后的宪法命题,也难以进行有效的梳理。不仅如此,对于日常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解释总是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专业人士,也不明就里,难以解读。由于正史的支离破碎,官方解读的糊里糊涂,一些可以用来相互佐证的“野史”和“传闻”便是至关重要的。《看不见的手》、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以及各种版本的《货币战争》等,这些被认为不够严肃的作品,却为我们提供了深挖中央银行背后宪政危机的重要线索。结合信史的记载,尤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国家立法,我们发现,这些所谓“野史”、“秘史”和“传闻”,所展示出的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当然,野史毕竟是野史,不免会加入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大胆猜测,所以在借鉴野史时自然要加以甄别,应与信史和官方说明互相对照,以求得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二、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证成
中央银行立宪的一个基本思路便是将中央银行纳入宪法体系之中,使之接受宪法规则的外在约束。而这一设想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前提,乃是确认中央银行是作为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从字面上看,中央银行是与地方银行相对应的金融机构,而事实上,中央银行对应的是一般银行或商业银行,二者的根本区分在于是否享有特权[5]。这里的特权首指货币发行权。基于其特权,中央银行又被称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这是针对早期中央银行所具有的职能进行的概括。
“发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家立法集中和垄断货币发行权,并作为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存在(在有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硬辅币的铸造与发行由财政部门负责)。[4](P33)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是中央银行最基本、最核心的标志。但货币发行的垄断不像其他行业,它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政府选择或国家立法的结果。货币发行权是政府权力之一,将其从财政部门手中剥离转而赋予中央银行,同样没有改变其公共属性。
“银行的银行”,指的是中央银行并不与市场主体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为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并在业务和政策上发挥管理与制约作用。银行的银行体现了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这一地位的获得,是以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为前提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该角色由政府直接扮演,如1850—1907年间美国的财政部以及1907—1934年间的加拿大政府(在1850—1907年间,美国财政部的做法是将自己拥有的黄金存进银行体系,并且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证券,及时地扩张银行储备量;加拿大政府在1907—1914年间补充银行储备,而在1914—1934年间则提供了最后贷款人贴现便利)[4](P38);作为全国票据清算中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清算体系,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并控制和监督金融机构的运转。总的来看,这几项功能都显示出,中央银行是作为金融领域之监管主体而存在的,并且行使着特定的公权力。
“政府的银行”,是指中央银行代理政府,经办国库收付,为政府开立账户,代理政府发债,经理还本付息事宜[6],并提供其他金融服务。中央银行有时还担当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职责,并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对话,黄金和外汇通常也由中央银行保管。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乃是管理、调控货币金融活动的国家机关。就货币政策来说,本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宏观政策,而各国法律一般均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交由中央银行行使,从而确立了中央银行的国家机关的地位。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央银行的一些财政职能可能与控制通胀的任务相矛盾,因此要强化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就应当弱化其他职能。总的来说,上述这些职能都反映出,中央银行是重要的政府机构[7],而不是私人部门。
根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的规定,作为我国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享有与货币、金融相关的执行权、立法权以及对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都在行使着特定的国家权力,只不过其所行使的权力本身具有特殊性,即事关货币、金融的行政和立法等权力,特别是体现在立法权上。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其他的法律、法规,制定规章和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令”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立法权是最重要的国家公权力。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中央银行一直行使着制定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第90条):“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虽然该条文并未从字面上赋予中央银行立法权,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一样,中央银行的立法权来自宪法,是由其行政职能派生出来的,是实现其行政职能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央银行乃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而绝不是一个私人的公司或机构,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也不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
三、中央银行立宪的理论难题
虽然我们认为中央银行属于政府部门,然而就各国的立法来看却并不尽然。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其依据是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美联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部股份私人所有,其最初成立时由私人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并且一些股东直到现在仍在分红。[8]由此可以看出,美联储实际上是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而其看似民主的管理决策机构,实际暗藏着货币利益集团控制货币发行的玄机。[9]法国、德国、英国等先发民主国家也曾经历过中央银行私有化的过程,即便在二战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但其真实性仍是值得怀疑的。如在英国,1946年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实现银行资本国有化,资本总额仍为120万英镑,然而早在1816年,英格兰银行的资本总额已经增至1455.3万英镑,很显然,这次国有化实践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是独立于政府的,政府通过国有化运动监管中央银行的目的亦无从实现。国有化之后的英格兰银行隶属财政部,1946年国有化法案规定:财政部在与银行总裁协商之后,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对银行发布指令(第4条第1款)。这一规定实际上限制了财政部的权力,而财政部也从来没有行使过这项权力。政府从不过问货币政策的制定,也不参与董事会的评议。现行《英格兰银行法》更在前一条款之后加入一个但书:但货币政策除外(第10条)。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全体的财产利益,若不加干涉而任其自为,难免不被滥用甚至用以谋取私利,使得现代人对民主、法治的追求落空。反过来,历次特许令的发布或银行法的修改,不仅没有使中央银行的权力受到任何实质性约束,反而使其不断膨胀。在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其中央银行至今仍是私人部门。这与我们所界定的中央银行乃是行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的观点明显相抵牾。当然,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出现,使我们不能断然认定私有的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将货币发行权之一部分交给私人部门亦有其合理性,但是货币政策制定权,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权,货币本位制的选择等,这些事关全民利益且具有立法性质的权力,仍应当为立法机关所保留。
恰如卢梭所认为的,立法乃是主权行为,也只有立法才是主权行为,至于行政权、宣战媾和等,只是立法权派生的,不构成主权权威的组成部分。[10]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立法权又是一种最高的普遍性的国家权力,那么,在民主政体之下,立法权毫无疑问应当属于人民。在立法权的归属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基本的论说有三种:(1)君主或贵族主权论,如西塞罗认为国家的立法权应当由贵族和前任执政官组成的元老院行使;(2)人民主权论,即立法权由人民行使;(3)立法权的归属与一定政体或政制相联。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的归属直接受政体的影响,在共和政体下,只有人民有权立法,在贵族政治的君主政体下,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和少数贵族手里,在专制体制下则无所谓立法权。洛克认为,政体、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权力即立法权的隶属关系而定,如果立法权属于国人共有的是民主政制,把立法权交给少数精选的人和他们的嗣子或继承人的是寡头政制,把立法权交给一个人的就是君主政制。[11]虽然将行政权乃至司法权委托私人部门行使,并不必然改变主权的性质,但是出让立法权显然是不当的举措。当然,我们可能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假设:随着法治的发展,立法民营化也未必不会在将来出现。但就目前而言,即便是在所谓先发民主国家,其民主的成熟程度也远远无法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公意意志,在金融寡头和利益集团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立法民营化自然无从谈起。显然,在短期内,我们仍应秉持立法权的公共性,因而将立法权交给私人部门是不合适的、有违国家体制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所以在“国会保留(立法否决)”一案的判决中确立了立法保留原则,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民主宪政时代政府的可信度也是有限的,即便是民主产生的政府,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部门,不可避免具有为自己谋利的倾向。并且实行科层制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缺乏民主性,权力很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团加以利用。与议会立法相比,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也是有问题的。因此,某些特别重要事项的行政行为,应当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依据经授权的行政立法。[12]连民选的政府都不可靠,将事关全体财产权利和整体经济安全的货币立法权以及执行权打包交给私有的中央银行,其危险性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联邦储备法》第13条却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交给了美联储,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设计,名义上是为了让它享有充分的独立性,以便在国会授予的既定目标下自由行动,结果却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私人部门。不仅美联储如此,诸多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诸多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也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也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为所欲为、翻云覆雨的制度根源,同时也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不过是国家(中央银行)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在正常情况下,即便中央银行是私人部门,也不能改变其所行使的权力的公共属性。公共权力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下,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是对所有国家权力提出的要求。而将相关的权力交由私人部门行使,恰恰使其可以规避法律的约束,事实上就是私人窃取了国家权力,进而依凭国家权力“名正言顺”地谋取私利。这不仅同公共权力的性质不符,也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政治伦理。
四、结语
货币权力已被论证为最具统治力的社会权力,中央银行则是货币权力的首要载体。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金融调控、外汇管理等途径,使货币权力的统治力得以实现。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私有的中央银行俨然成了社会的真正主宰。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现象,无不同货币、公共财政发生联系,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就业、选举等,即是说,中央银行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中央银行本身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存在的,弗里德曼甚至试图将它界定为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并不能停留于财政、金融层面,更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对其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作为重要国家机构的中央银行及其所行使的货币权力进行宪法层面的检讨与论证,并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充分的宪法依据,确保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
[1]Buchanan J M.Predictability: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55.
[2][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7 -61.
[3]刘丽巍.当代中央银行体制——世界趋势与中国的选择[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4]范方志.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5]梁钜文.中央银行制度概论[M].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1.
[6]孙树茜,张贵乐.比较银行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118-119.
[7][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2.
[8]张功平.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的制订及调控手段的运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业务考察报告之一[J].内蒙古金融研究,1994(7):3.
[9]王卓.关于改革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探讨[J].经营管理者,2009(10):71.
[10]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51.
[11]周旺生.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62-263.
[12]孙展望.法律保留与立法保留关系辨析——兼论立法法第8条可纳入法律保留范畴[J].政法论坛,201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