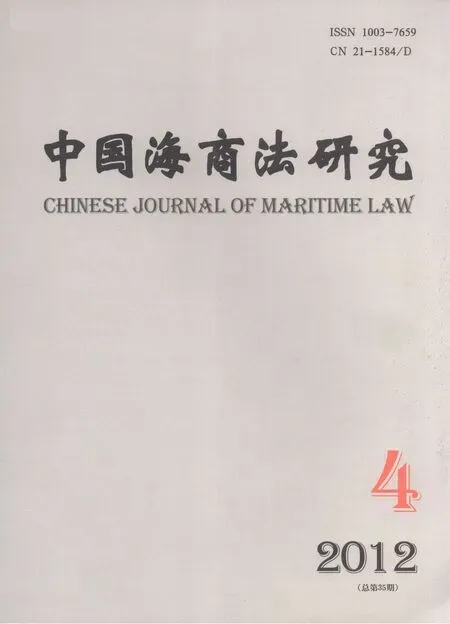提单提货凭证信用维护之法律机制研究——兼评《鹿特丹规则》下的无单放货机制
陈 芳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1306)
一、问题的提出
提单(指指示性提单和无记名提单)签发创设了提单上所表彰的权利——提货权,提单上提货权的确立,使提单法律性质从单纯的货物收据擢升为提货凭证(Document of Title)①“Document of Title”这一外来词由于被误译为物权凭证,一直成为被广泛沿用的表达方式,实质上提单所表征的提货权是债权,物权凭证表述与提单表征权利性质不符,一度在学界引发提单法律性质大讨论,在对“提单是物权凭证”表述的纠偏中,出现了提单是有价证券、权利凭证、债权凭证等表述。笔者持提单法律性质是有价证券的观点,但笔者讨论的是提单表征提货权的商业信用,而非提单法律性质归属,鉴于“提货凭证”这一指称的直观性,笔者舍弃“有价证券”这一较抽象表达而采“提货凭证”表述。,奠定了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即提单代表了提货权,持有提单即能享有提取提单项下货物的权利。
提单提货凭证性质决定了提单上提货权的行使与履行都有特定的要求,即提单持有人行使提货权时,须向承担货物交付义务的承运人出示提单,承运人在履行货物交付义务时须“认单不认人”,仅向持有全套正本提单的提单持有人履行交货义务。因此,提单上提货权实现的保障,或提单作为提货凭证的信用完全依赖于作为提单债务人的承运人“凭单交货”。正是如此,“凭单交货”才由商事习惯而逐渐被各国海商法确认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定,[1]成为承运人履行交货义务的法定条件与方式。
“无单放货”无疑是对“凭单交货”法定义务的违反。由于船舶速遣及集装箱技术的广泛运用,货物到港速度远远超过提单流转速度,货到单未到的情况比比皆是,导致航运实务中,承运人凭收货人的保函及副本提单完成货物交付义务,此谓“无单放货”。很长一段时期内,“无单放货”现象盛行乃至泛化,有学者统计,在中、日、韩等近海的亚洲国家,进口货物中有80%~90%是无单放货,而某些重要商品如矿物、油的交付中,无单放货高达100%。[2]
“凭单交货”法定义务与航运实践中“无单放货”现象蔓延的现状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引发了对提单提货凭证信用消解的疑虑,进而质疑提单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功能,产生了所谓的“提单危机论”。因此,剖析提单制度法律规定与提单实践活动的二律背反现象,明确法律逻辑与其调整对象之间的冲突,研究提单制度如何应对提单实践中新问题,实现对提单活动的有效调整,是提单制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二、“凭单交货”原理
提单虽然始于运输环节,亦终于运输环节,但提单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推动作用、提单经济功效发挥的场所却在运输领域之外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及国际结算领域。而保障提单权利凭证信用的“凭单交货”则是基于国际货物贸易活动的需要而课以承运人运输合同之外的特别利他义务,是商事活动中商主体间基于经济效率需求而进行互助的理性选择。归根结底,承运人作为运输合同的义务人,在运输途中谨慎管理货物,货到目的港,完成货物交付即尽到了运输合同下的义务,至于向特定提单持有人凭单交货则完全不是运输合同下的义务,而是提单项下的义务。承运人之所以承担提单义务而“凭单交货”,是商人们依据国际货物贸易活动与运输活动的相互牵连,为满足在漫长的海上货物运输途中货主转运货物的需要所作的精巧的设计。因为提单法律性质从仅是货物收据演变为权利凭证,提单成为能表彰提货权的权利凭证,是由国际货物贸易活动推动的,如对海运途中的货物再次转让的需要,以及在信用证结算下,因银行介入贸易活动而为银行对卖方预先付款提供提单权利质押保障等需求,才赋予提单这张货物收据以提货权,使运输合同下的提货权以独立权利的形式附体在提单上。凭借提单上表征的提货权,提单才能通过背书或直接交付代替货物实际交付,用以转卖提单项下的货物;提单才能作为权利凭证被质押给信用证下的银行,发挥信用证平衡国际货物贸易中买卖双方利益风险的功能。正因提单表征了提货权的商业信用,提单活动轨迹才从运输领域拓展至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以及信用证结算领域,成为国际商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商事单证。
由于提单在国际货物贸易活动中的巨大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签发提单是其法定义务。承运人签发提单使得独立的提货权得以产生,该提货权与运输合同下的提货权从法律视角观之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运输合同下提货权权利之实现,无须依赖提单,仅依运输合同约定即可。但提单项下的提货权,其权利行使与义务的履行却与提单密不可分,因此,承运人一旦签发提单,即对提单上所表彰的提货权承担给付义务,须凭单识别特定的提货权人而履行交货义务。实质上整个提单活动,承运人都是为他人作嫁衣,承运人作为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其获取运费的对价是为货物提供位移服务,即依约将货物从装货地运到目的地并交付,从整个运输活动双方主体权利、义务实现的目的来看,根本不需要提单。之所以要求承运人签发具有能够表征提货权的提单,如前所言,意在便利及促进国际贸易活动,是法律对基于经济效率理性而自发形成的商事实践予以认可,而课以承运人的特别利他义务,这就是承运人签发提单义务法定及“凭单交货”法律规定的法理依据。
三、“无单放货”行为合理性探析
承运人作为商主体之一,追求经济利益是其根本价值目标所在,其之所以自觉承担运输合同外的“凭单交货”利他义务,以便利贸易活动,须是在保全自身正常营业利益前提下,换言之,承运人承担“凭单交货”特别义务是有底线的,即不得影响其正常的航运营业利益,其所承担的利他义务所带来的不便与影响不得超过其在航运活动中正常的商业风险,这是由商人自利的本性所决定的。具体言之,“凭单交货”能够平衡各方利益,不致产生利益冲突,是有一定条件的,即提单流转的速度应早于或等于货物的运输速度,如果反之,货物的运输速度早于提单的流转速度,货物到港时,因各种原因,收货人还未取得提单,此时,对承运人而言,其虽然完成了货物运输义务但仍不能交付货物而摆脱运输合同的羁束,已到港的货物须等待提单到港而“凭单交货”,如此一来,压货、压船不可避免,承运人因此会蒙受程度不等的甚至巨额的经济损失。
虽然目前对持单人在因无单放货所遭受的损失及承运人在严守凭单放货所引起的滞期费损失及下一个运输合同违约的损失之间尚缺乏实证分析,但让承运人为了维护提单信用以便利贸易活动,而承受超出其航运经营正常商业风险之外的经济损失,此种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也与航运商业营利规则相悖。而另一方面,未持有提单但能以其他方法证明自己享有提货权的贸易关系中的买方亦受制于“凭单提货”,不能及时提取货物,无法通过及时受领货物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而且还要承担货物价值波动下跌的风险及额外高昂的仓储保管费用。再者,对于到货港而言,由于等待凭单交付的货物在港口大量积压,使港口的吞吐量大受影响。因此,很多情况下,严守“凭单交(收)货”无法实现货畅其流,造成了承运人、收货人、港口三输的局面。在某些航程短,船舶到港速度较快的近海货物运输中,避免经济损失的需要使得提单关系中的双方不约而同产生突破“凭单放货”法律约束的动力,因此,提货权人(买方)以副本提单加保函的形式取代提单要求提取货物,承运人亦愿意以此种形式“无单放货”,提单关系双方主体因“无单放货”而实现了双赢。
由此可见,“无单放货”一定程度上因能满足商事效率的需求,符合商人自利本性,亦具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航运领域,将每个商个体追求利益的共性行为联系起来,“无单放货”现象的泛化并不是偶然的,无单放货泛化现象可以说是现有法律格局下航运技术的发展导致运输、贸易主体利益失衡而自动修正的结果。如果仅仅依据现行法律规定,简单地将“无单放货”定性为违法行为,无助于解决提单及提单制度的危机,无助于解决法律逻辑与其调整对象之间的冲突。看待“无单放货”问题必须秉承经济利益分析方法,通过对承运人“凭单交货”法定义务及无单放货行为经济利益分析,审视无单放货经济动因及相关贸易、运输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牵连性,即会发现无单放货现象泛化是商事活动中商事主体利益失衡后自行协调的结果,是商事主体逐利的理性体现。鉴于此,在看到无单放货其弊之时,亦应看到其利,在维护提单“凭单放货”的法定规则与提单权利凭证信用之余,也应正视“凭单放货”与航运技术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无单放货”视为是缓和二者紧张冲突的价值中性的行为,更能接近对“无单放货”问题认识的本质,那种对“无单放货”持全盘否定观点,认为“无单放货”是对提单制度的侵蚀,甚至认为“无单放货”的泛化造成了所谓的“提单危机”,会导致提单消亡,认识未免太过片面与消极。因此,正视“无单放货”行为事实的存在,对“无单放货”在货物交付中的普遍现状,在认定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之余寻求解决之道,这是法律制度应对调整对象的变革而应该持有的积极态度。
如上所述,在多方主体激烈角逐利益的提单世界里,诸多行为的判断绝对不是非黑即白的,承认“无单放货”行为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瓦解、消除“凭单交货”法定义务。“凭单交货”是提单权利凭证性质的体现与保障,关涉提单在贸易活动中及银行结算活动中的信用,是提单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基础。如何处理保障提单作为权利凭证信用与无单放货行为合理性的悖论,是提单制度能否适应航运业发展的现实而完成自我变革的关键,也是每一个对提单及提单制度进行关注与研究的学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笔者认为,提单提货凭证信用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及国际结算领域的巨大功效,使其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顺利进行的基石。因此,保障提单提货凭证信用是提单制度的基本宗旨,“凭单放货”仍然是提单制度应坚守的基本规则,是承运人履行交货义务的法定条件,此点不能改变与动摇,否则,提单制度的根基即被撼动,提单信用荡然无存,使提单各项经济功能得以发挥的流通性亦灰飞烟灭矣。
提单的消亡或繁荣,并不取决于提单制度,而是取决于提单所作用的国际贸易、国际结算领域对提单的需求程度,如果运输途中的货物有再次转让的需要,如果贸易活动中存在信用证支付方式,这些提单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会支撑提单在过去、现在、将来仍然盘踞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舞台中,并且光彩如初。反之,作为上层建筑的提单制度能否适应其调整对象的变革,在航运业无单放货泛化背景下,能以有效的法律机制维系提单提货凭证信用,才是事关提单制度价值的根本问题。所幸,国际国内提单制度以不同的立法进路所形成的事后救济及事先授权两种法律机制模式,殊途同归,为此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
四、无单放货损害赔偿替代责任机制模式
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的出台,平息了中国司法实践中关于无单放货纠纷诸多法律问题的争议,为“无单放货”纠纷的裁决确定了统一的依据。该司法解释同时确立了中国应对“无单放货”泛化所采用的机制模式,即无单放货损害赔偿替代责任机制模式。申言之,在坚持“凭单交货”一般性规定之下,用无单放货的损害赔偿责任替代“凭单交货”义务来缓和二者之间的冲突,将无单放货法律责任作为维护提单提货凭证信用的堤坝。“无单放货”一旦造成持单人的经济损失,承运人对其损失承担救济责任,以承运人的损害赔偿法律责任替代交货义务的实际履行,借助相应的提单责任来修复“无单放货”给相关当事方造成的损失,以维护提单提货凭证信用。
(一)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机制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机制模式的可行性在于:于持单人而言,只要无单放货的损害赔偿能够填补其损失,其受领的是凭单提取的货物或是无单放货的损害赔偿,都是在其可接受的商业预期范围内。诚然,持单人提货权的实现能保证其获取商业利润,而无单放货的损害赔偿仅是填补损失,二者之间利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但这是商事主体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应当承担的风险。比如商人在签订合同时固然信赖合同的正常履行而获取预期的可得利益,然而商事活动的风险不可能保证每个成立生效的合同都能够得到履行,商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违约的风险,即使《法国民法典》明文规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商业活动中的违约仍每时每刻地发生着,全社会所信奉的合同能够得到履行的一般性信用并不因时常出现的违约而遭致坍塌。提单提货凭证的信用也是如此,“凭单交货”固然是提单权利凭证信用的保障,但“无单放货”并不意味着提单提货凭证信用的消解或摧毁。只要对“无单放货”行为课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提单信用的屏障仍然是坚固的。事实上,与航运实践中屡屡发生的无单放货庞大基数相比,真正酿成纠纷诉诸于法院的无单放货案件则占极低比例,[3]而且这极小比例的“无单放货”纠纷往往还是贸易关系的争议所致,这也是无单放货现象长期存在的实践基础。因此,这些纯因提单运转速度拖延所致的“无单放货”不仅不会有利益受损方,相较于严守“凭单交货”,“无单放货”反而使提单关系的承运人及收货人各自避免损失而实现了双赢。
(二)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机制之法理
总之,基于航运现实的需要,给予无单放货行为一定的空间,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节约立法资源,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规则,将提单提货凭证信用维护的重点放在“无单放货”损害赔偿替代责任上。深刻挖掘商事责任中固有的恢复权利、保障权利职能,对“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融入新的认识,摆脱传统法律责任固有桎梏,基于提单商业活动的实践需要,重新认识和解构“无单放货”法律责任,重视损害赔偿规则的替代性机能,无疑是解决提单无单放货纠纷的新视角。
“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基于从事贸易活动及为之服务的运输活动的商人趋利的需求,已成为相关主体通过法律责任形式的安排与承担,来对自己的利益予以配置的有效手段。“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解构了传统民事责任中否定的不利的后果评价,损害赔偿责任替代债务履行,成为缓解各方利益冲突的减压阀,也使得损害赔偿责任原则在无单放货责任形态中具有根本地位。在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中,已完全剥离了法律责任中的惩罚性,而且传统民事责任中强制性色彩也在削弱,“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逐渐从强制性责任向替代性、相对性责任转变,这使得提单损害赔偿责任与提单债务没有本质差异,[4]提单损害赔偿责任成为基于效率要求平衡多元利益的第二性义务。基于此,“无单放货”损害赔偿责任替代“凭单交货”义务,缓解了“无单放货”泛化与“凭单交货”法定义务之间二者冲突,维护提单提货凭证信用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鹿特丹规则》确立的无单放货机制
《鹿特丹规则》是继三大国际公约之后又一对海上货物运输活动予以调整的全新国际公约。《鹿特丹规则》在吸收、继承三大国际公约的基础上,适应现代航运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立法的后发优势,在诸多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鹿特丹规则》在提单制度上最大的突破是正视航运业无单放货的现状,及时呼应航运业变革的新需求,对“无单放货”行为合法性作了开放性的规定,该规定在公约制订过程中广受瞩目,经参与方多次讨论,汇集各方意见,反复斟酌修订而成。[5]最终条款基于对“凭单交货”法定义务与“无单放货”现状偏离的认识,努力通过制度予以协调,以制度创新方式确立了无单放货新机制,这在国际公约层面上,在维护提单提货凭证信用之余,首次确认了一定条件下无单放货行为的合法性,破解了“无单放货”在既往法律体制下的现实困境,体现了对“无单放货”以疏代堵的立法理念。
(一)《鹿特丹规则》确立的合法无单放货标准
《鹿特丹规则》第47条第2款的规定,确立了货物交付时“无单放货”的条件与标准,即《鹿特丹规则》下的“无单放货”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提单上明确载明:“可以不提交运输单证(提单)”①《鹿特丹规则》在提单的表述上作了全面的变革,以“运输单证”取代了传统的“提单”表述,意味着在《鹿特丹规则》下,提单的表述已成为了历史。但为了前后论述的一致性,在本部分论述中,仍然以“提单”指代《鹿特丹规则》中的“运输单证”。;二是持单人不行使提货权利或持单人未能适当证明其是单证上所载明的提货权人而被承运人拒绝交货或承运人经合理努力无法确定持单人;三是承运人已经通知托运人指示交付货物。只有在以上三个条件成就后,承运人方可解除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义务,承运人无需凭单放货。这三个要件相互联系,制度设计独具匠心,在例外地承认“无单放货”的合法性同时,一并解决了同样困扰承运人及航运实践的“无人提货”问题。
“无单放货”合法性的首要条件,须为承运人签发提单时明确载明“可以不提交运输单证(提单)而交付货物”,该事项的记载与否,有赖于承运人根据航运经验判断估测货物运输速度、到港时间,赋予了承运人履行交货方式的选择权,结合其他条件,承运人可一定程度上决定是履行法定的凭单交货还是有条件的无单放货,而且该记载事项可凭借提单文义性,为任何持单人所知悉,迫使持单人尽相当谨慎的注意义务,密切关注货物到港信息,对承运人所发出的货物到港通知及时回应,积极地行使提货权,在持单人怠于行使提货权或无法确定持单人时,规定托运人应承担货物交付的协作履行义务,托运人有应承运人要求发出交付货物指示的义务,承运人可依托运人的指示交付货物。
(二)《鹿特丹规则》无单放货机制的意义
《鹿特丹规则》所确立的无单放货机制,围绕货物交付,课以持单人、托运人协作履行义务,通过贸易关系、运输关系的三方主体责任联动,将承运人的交货义务从“凭单交货”的绝对羁押中解放出来,承运人通过最终凭托运人的指示交付货物而免除凭单交货义务,将“无单放货”的风险转归于发出交货指示的托运人,体现了承运人履行交付货物义务在运输合同下的回归,恢复承运人交货义务本是运输合同固有义务的特质。使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下的纯粹的交货义务与为便利贸易合同而设定的法定“凭单交货”义务作适度分离与松绑,让承运人不再因便利贸易活动而承担绝对的“凭单交货”利他义务,赋予其一定的选择权,让运输的归运输,贸易的归贸易,贸易中的争议、纠纷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再借助于“无单放货”而转嫁于承运人,使承运人卸下沉重的源于贸易活动的风险负担,保全了承运人的合理利益,破解了“无单放货”现实困境。在航运技术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该“无单放货”机制实现了运输活动、贸易活动、结算活动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再次识别筛选,并在上述国际经济活动中,建立了新的利益平衡格局与秩序。
(三)《鹿特丹规则》下无单放货机制与提单权利凭证信用维护关系辨析
提单作为提货凭证,在债务履行方面具有所有权利凭证的共性,即权利凭证债务人在履行债务时忽略权利人的特定身份,债务人仅通过对凭证的持有确定债权受领主体而履行给付义务,即“认证不认人”。这是因为包括提单在内的所有权利凭证都是其所表彰的财产性请求权的自足证明,无需其他辅助手段,无需在权利凭证之外为相关财产性请求权的存在寻找依据。具体到提单而言,提单自身即为提货权的产生、存在提供了完全的证明,因此,提单提货凭证性质,模糊了提单下提货权权利主体的概念,提单下提货权的行使与提单持有人的身份无关,而仅与对提单的占有有关。因此,承运人履行提单下的交货义务时,可以无视提货人的身份而“凭单交货”(“认单不认人”)。《鹿特丹规则》第47条规定在签发不可转让的提单之下,承运人履行交货义务时,在一定条件下可通过托运人指示而确定受领货物的权利主体,剥离了提货权的行使与提单占有的联系(“认人不认单”)。有学者就此认定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笔者表述为提货凭证性质)②因提单物权凭证功能表述的强大惯性,使得这一表达方式仍然在不少论著被继续坚持使用。实质上,笔者的提货凭证表述与其他论著中提单物权凭证功能表述所指称的内涵基本一致。为了保证论述称谓的一以贯之,在本部分论述中仍以笔者所坚持的“提货凭证”称谓取代其他论著中“物权凭证功能”的表述。有所减损。[6-7]甚至有学者因此对《鹿特丹规则》中的提单制度的未来持非常悲观、消极态度。[8]
实质上,这正是《鹿特丹规则》正视“无单放货”的客观性、合理性,而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给无单放货拓展了空间,体现了《鹿特丹规则》在提单制度上的自我变革和与时俱进。在肯定这一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回答此制度变革是否冲击了提单提货凭证性质,颠覆了提单信用,将对未来的国际贸易和结算活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提单提货凭证信用减损受到冲击了吗?非也。众所周知,在提单的种类中,除了具有提货凭证性质的指示性提单与不记名提单之外,尚有仅具货物收据性质的记名提单。记名提单因不具备提货凭证性质,在诸多涉及到提单问题的论述中,皆被排除在提单范畴之外,虽然因理论探讨的严谨计,提单外延排除了记名提单,但记名提单的客观存在并不因此受影响,记名提单无需凭单交货①当然,《无单放货司法解释》中规定,记名提单须凭单交货,那是对提单提货凭证性质认识混沌的结果。,在任何航运国家的海运体系下,记名提单与指示性提单、无记名提单的商业存在及法律制度都是和谐共存的,记名提单与指示性提单、无记名提单法律性质截然不同,其彰显的商业信用有异,但记名提单的货物收据性质并不削弱、否定指示性提单、无记名提单的提货凭证性质与信用。基于此,对承运人签发时明确载明“可以不提交运输单证而交付货物”的提单,不妨换一个视角观之,将其视为剥离了提货凭证性质的特殊种类提单,在这里姑且将其称之为“可无单放货”提单,以区别于笔者所论述的具有提货凭证性质的一般性提单,即指示性提单和无记名提单。
“可无单放货”提单如同记名提单一样,并不影响一般的指示性提单、无记名提单的提货凭证信用,该新类型提单的创制正是《鹿特丹规则》为解决航运实践中“无单放货”泛化的应对之举,正是提单制度适应航运业的发展而勇于自我变革的体现,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法律制度必须随其调整对象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废、改、立,这是任何法律制度的发展之路,调整提单活动的国际公约也循应了这种立法进路。从《海牙规则》时起,每一个公约中的提单制度都经历了有破有立的变化,《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了提单的最终证据效力(文义性),《汉堡规则》出现了实际托运人制度,现在的《鹿特丹规则》则创制了“可无单放货”提单。虽然《鹿特丹规则》为容纳“可无单放货”新类型提单,以保证提单概念内涵外延逻辑的一致性,有意地放弃了《汉堡规则》中所确定的“提单是保证据以交付货物单证”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否定了提单所具有的提货凭证信用,《鹿特丹规则》第47条第2款对“可无单放货”提单实施条件给予了严格的限制,仅凭承运人单方意愿的记载,尚不足以使法定的“凭单交货”义务变为意定的“无单放货”权利,除了承运人在提单上的明示记载外,尚需提货人怠于行使提货权及托运人发出放货指令等条件配合,说明“可无单放货”提单只是提单范畴中的除外规定。相较于一般性提单,“可无单放货”提单有其严格的限定条件及适用目的,只是为解决无单放货的问题,是新公约在正视、承认无单放货的合理性之余,为解决其合法性问题所设。新公约赋予了无单放货一定条件下的合法地位,给了当事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将“凭单交货”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作了依当事人意志的软化处理,一定条件下变法定的、绝对的“凭单交货”为意定的、相对的“无单放货”。“可无单放货”提单制度立法意图及立法实践效果都不可能否定具有提货凭证性质的一般性提单的存在,正如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创制不会撼动法人独立人格一般性地位一样。
诸多法律制度在变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例外性规定,是法律制度为有效调整一定社会关系而辩证发展,其并不是对制度的全盘否定。提单提货凭证性质是提单经济功能赖以发挥的保障,是提单在国际经济领域价值的核心支点,是提单的信用基点,如果新公约仅为解决一个“无单放货”问题,而全盘摧毁提单提货凭证性质,无异于摧毁了提单的灵魂,提单必然会被未来的商业世界所抛弃。因此,对提单提货凭证性质的维护,既是提单制度精髓所在,也是提单制度的立足点所在,《鹿特丹规则》制订者不可能不明了洞悉其中的利害。事实上,《鹿特丹规则》允许“凭单交货”一般性提单与“可无单放货”特殊性提单并存,目的在于让两种提单各司其职,让承运人交付货物义务在“凭单交货”的一般性与“无单放货”的相对性中实现了新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使提单制度对提单活动的调整更具适应性与灵活性,这是新公约适应航运现代化的需要而必备的开放性、包容性表现。反之,如果《鹿特丹规则》面对“无单放货”泛化现状,悄悄地蒙上双眼,任凭“凭单交货”法律强制性规定与现实中的“无单放货”现象二律背反,而无所作为,那么《鹿特丹规则》的立约价值及法律价值就值得忧虑了。
因此,《鹿特丹规则》通过非常复杂的机制对“可无单放货”提单进行规定,即表明“凭单交货”作为法定的默示义务,仍然是《鹿特丹规则》下所坚守的一般性规定。新公约仍然确定一般情况下,提货权的行使离不开对提单载体的持有,则提单提货凭证总括性质并未因“可无单放货”提单出现而减损抑或沦丧,提单提货凭证信用仍可得到保障,提单仍能给予相关贸易主体、银行其能代表提货权的信用期许,则相关贸易主体、银行因而愿意受让提单而使提单流通特性不变。只要提单流通性不变,提单下的货物就能够顺利转卖、信用证结算下的银行利益也同样能够得到保障,提单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在国际货物贸易、国际结算领域中的功能,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对《鹿特丹规则》下提单权利凭证信用及提单制度的前景悲观呢?
六、结语
综上,正确认识“无单放货”合理性之余,根据国际国内法律实践,应对无单放货泛化问题,维护提单提货凭证信用,有两种机制模式可供选择:一是事后救济,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目前所普遍采用的机制,该机制用尽现有法律资源,发挥损害赔偿规则的替代性机能,以无单放货的损害赔偿责任作为第二性义务,以替代“凭单交货”的第一性义务;二是事先授权,这是《鹿特丹规则》所确立的创新机制,通过立法确立有条件的无单放货授权制度,确认一定条件下无单放货行为的合法性,授予承运人在提单上明示记载的权利,将凭单放货的法定强制性义务依其意志作软化处理,一定条件下变法定的、绝对的“凭单交货”为意定的、相对的“无单放货”。《鹿特丹规则》下独具匠心的制度创新,将对各国国内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1]刘宗荣.新海商法[M].台北:三民书局,2007:285.LIU Zong-rong.The new maritime law[M].Taipei:San Min Book Co.Ltd,2007:285.(in Chinese)
[2]司玉琢,汪杰,祝默泉,沈晓平.关于无单放货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0,11(1):18.SI Yu-zhuo,WANG Jie,ZHU Mo-quan,SHEN Xiao-ping.Theory and practice on delivery of cargo without bills of lading[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0,11(1):18.(in Chinese)
[3]何丽新,付超伟,康南,陈悦,朱明.中国各级法院153个无单放货案件之分析[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2):214.HE Li-xin,FU Chao-wei,KANG Nan,CHEN Yue,ZHU Ming.An analysis on 153 cases of delivery of goods without B/L concerned Chinese courts at all levels[J].Xiame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5(2):214.(in Chinese)
[4]刘道远.商事责任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5):96.LIU Dao-yuan.Introsp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ercial liability legal system[J].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10,25(5):96.(in Chinese)
[5]朱曾杰.初评《鹿特丹规则》[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9,20(1-2):12.ZHU Zeng-jie.Evaluation on the Rotterdam Rules[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9,20(1-2):12.(in Chinese)
[6]傅廷中.《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21(2):20.FU Ting-zhong.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document of title under the B/L at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Rotterdam Rules[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10,21(2):20.(in Chinese)
[7]朱作贤,王晓凌,李东.对提单“提货凭证”功能重大变革反思——评《UNCITRAL运输法草案》的相关规定[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5,16(1):401.ZHU Zuo-xian,WANG Xiao-ling,LI Dong.Reconsideration on the major reform of B/L function of“delivery document”——comments on relevant provisions of UNCITRAL Draft Instrument[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aw,2005,16(1):401.(in Chinese)
[8]赵鹿军.《鹿特丹规则》无单放货规定存隐忧[N].中国交通报,2009-11-10(7).ZHAO Lu-jun.Statute of delivery of goods without B/L is uncertain under the Rotterdam Rules[N].China Communication Newspaper,2009-11-10(7).(in Chinese)